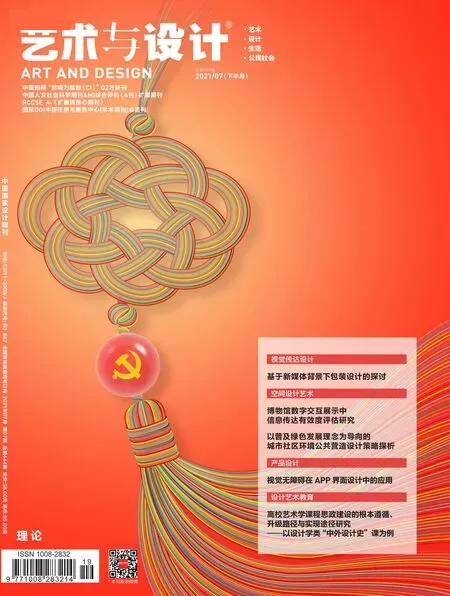基于紅色集體記憶視角下智慧文博的設(shè)計策略
周雅琴,吳波,王佳瑞
(天津理工大學(xué),天津 300384)
一、“紅色”集體記憶綜述
(一)紅色集體記憶遺存分析
“集體記憶”是指群體里對過去的記憶中具有同一性以及特殊文化聚合性的記憶。集體記憶在形成的過程中受教育、信仰、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而形成一種主旋律的集體共識,從精神層面指導(dǎo)行為意識從而為信仰去奮斗去努力,所以對于集體記憶必須在強制性的規(guī)訓(xùn)與軟性的教化共同作用下,引導(dǎo)人們朝著積極向上的方向發(fā)展。“紅色”集體記憶是指具有革命教育意義的集體記憶,這類集體記憶是革命先烈們經(jīng)歷了激烈抗爭后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也是能夠激發(fā)我們的愛國主義、培養(yǎng)我們艱苦樸素作風(fēng)的奮斗精神。而這些“紅色”集體記憶大多是以革命遺址遺跡的形式存在。在《全國紅色旅游景點景區(qū)名錄》中指出了300處具有紅色教育意義的旅游景區(qū),其中大多數(shù)是以博物館、紀念館的形式來加強對“紅色”教育的普及。根據(jù)國家《十四五規(guī)劃綱要》指示精神,為“紅色”集體記憶打造適合當(dāng)代受眾感知與認知的智慧文博,讓智慧文博成為與新時代紅色精神共鳴、共情的共享空間。
(二)文博凝煉紅色記憶的意義
“博物館(記憶+創(chuàng)造力=社會變革)”是2013年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在闡釋集體記憶與博物館之間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時,以歷史的鏡子和對現(xiàn)實的啟發(fā)作為博物館記憶。需要厘清集體記憶的內(nèi)涵以及與博物館之間關(guān)系的機制。而“紅色集體記憶”是過去的革命先烈通過抗爭遺留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能夠使經(jīng)歷過那一時期的群體在共同分享回憶后獲得深厚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這樣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則能進一步塑造一個穩(wěn)定的集體,而沒有經(jīng)歷過那一時期的青年群體通過傾聽、學(xué)習(xí)、了解那段“紅色”的集體記憶,可以幫助他們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培養(yǎng)艱苦樸素的奮斗精神,能凝練出無限的能量與動力。博物館作為這些集體記憶的物質(zhì)載體,能夠幫助受眾在特定的空間中,全方位地感受“紅色”集體記憶所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同時博物館所具備的社教功能可以促進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導(dǎo)向功能,文博凝練的“紅色”集體記憶對個人、集體乃至國家層面都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紅色集體記憶的典型要素分析
(一)集體記憶的產(chǎn)生
人文知識的學(xué)習(xí)過程很大程度上是集體記憶與集體意識的形成過程,最后成為穩(wěn)定的價值觀,指導(dǎo)人群的集體意識導(dǎo)向。“紅色”集體記憶是對應(yīng)著“紅色”文化下的時代產(chǎn)物產(chǎn)生的集體記憶,時代主題呼應(yīng)著紅色文化,集體記憶對應(yīng)當(dāng)時的革命年代,由那段時期的紅色歷史、故事、精神等要素組成的紅色文化聚合體,包含了物質(zhì)、制度、精神、行為多個形態(tài)。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的概念是社會構(gòu)建,是記憶主體在與社會共享過去發(fā)生事情的過程與結(jié)果,是對記憶載體的重新構(gòu)建,必須是群體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共同經(jīng)歷的記憶延續(xù)。集體記憶的存續(xù)不是一個持續(xù)的狀態(tài),而是構(gòu)建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人群的選擇性遺忘以及傳遞空檔。在我國文化建設(shè)中起到傳承作用的集體記憶更應(yīng)該加強對自身的建設(shè),加強整體系統(tǒng)的管理與規(guī)劃,以免出現(xiàn)記憶斷層。在文博環(huán)境中的紅色紀念館、紅色遺址、紅色博物館等機構(gòu)設(shè)施需要將過去時間上的那段紅色的集體記憶,以超越時空的現(xiàn)代方式呈現(xiàn)在受眾面前,使觀者能夠跨越時空去和過去的那段記憶進行對話,將先輩們的精神意志傳承下去。
(二)集體記憶的場域要素復(fù)刻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集體記憶的展示需要通過物質(zhì)化的場所,紅色集體記憶會通過物質(zhì)載體或其他形態(tài)與大眾進行接觸。革命博物館、紅色紀念館都可以是紅色集體記憶的物質(zhì)空間。受眾在參觀博物館、紀念館的過程中體驗文博場域所帶來的精神洗禮,在文博空間中去感知紅色集體記憶想要表達的時代精神。博物館將紅色集體記憶的記憶空間場景進行復(fù)刻,以此來營造記憶場域,讓受眾在參觀過程中對該場域進行認知,對于遺存集體記憶的親歷者來說是一場重啟的過程,為紅色情感提供共情與共鳴的空間要素,營造紅色集體記憶分享氛圍。而對于感受與學(xué)習(xí)紅色集體記憶的“新生”們,則需要通過數(shù)字技術(shù)所打造的沉浸式體驗方式,在智慧文博的體驗空間中深度感知時代精神與紅色文化,將典藏的紅色集體記憶銘刻于心,傳承于世,使紅色精神永存。
(三)集體記憶的文化要素再現(xiàn)
文化要素是紅色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因子,需要通過系統(tǒng)的梳理凝練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要素與視覺符號,才能適應(yīng)于信息快速傳播與精神交流的當(dāng)下社會。博物館、紀念館從空間層面為“紅色”集體記憶提供了優(yōu)質(zhì)的場域空間,而文化要素則是空間里必要的內(nèi)容物,展品的物質(zhì)本體和無形精神共同構(gòu)成了文化要素。因此,多維度的文化要素構(gòu)成需要將展品本體的敘述與展品所承載的記憶進行聯(lián)動,博物館要將記憶與歷史過程視覺化地再現(xiàn)。因此,集體記憶需要深挖、解構(gòu),重塑紅色文化要素,構(gòu)建立體的、可視化的、可參與的文化內(nèi)容,從而充實智慧文博,使其成為紅色精神的重要承載者。
紅色集體記憶的文化要素大都匯聚在展品、遺址、建筑等物質(zhì)形態(tài)上,而由于記憶是具有選擇性的,博物館作為記憶媒介本身就具備記憶“修改者”的特點。將這些不同的展品與歷史故事用可參與、可互動的敘事方式串連起來,讓紅色集體記憶所承載的時代精神在沉浸式文化再現(xiàn)的體驗中,潛移默化地達到深度的文化認同,使觀者在參與的過程中自然融入到文化要素再現(xiàn)的敘事框架中,達到必要的歷史認知與精神價值的高度。
三、智慧文博的集體記憶設(shè)計策略
(一)深挖館藏資源,空間再現(xiàn)對接時間記憶
紅色集體記憶是在特定時間背景下形成的,將特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見證物予以紀念和展示。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革命文物工作會議上強調(diào):“加強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弘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zé)任。”紀念館作為紅色集體記憶的物質(zhì)載體,更需要在保護的基礎(chǔ)上深挖資源,提取有形文物資源背后的無形精神文化資源,再通過將紀念館作為文化展示空間來還原文物背后的那段時空記憶。由于當(dāng)下的生活環(huán)境與特點時間的斷層,“新生”代的受眾很難真實地體會到特定時間、歷史、人物的情景并理解紅色集體記憶的內(nèi)核精神,紀念館以空間再現(xiàn)對接時間記憶能夠幫助“新生”代的受眾在文博空間中深刻地感受特定時間空間中的紅色精神。而空間再現(xiàn)的設(shè)計策略要重點突顯空間的智慧設(shè)計,一方面由于國內(nèi)大部分的博物館的展陳方式還停留在靜態(tài)展陳上,大都以文字的形式對展品進行介紹,枯燥的文字無法激起觀眾的閱讀興趣,更無法滿足觀眾對館藏資源解讀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國內(nèi)的一級大型博物館的建設(shè)過程中采用了智慧化的空間設(shè)計,將文物與科學(xué)信息相結(jié)合,將博物館的文物資料通過數(shù)字化的形式保存下來再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進行展示,最后再通過移動終端智能平臺的影、音、視頻等功能,與展覽空間現(xiàn)場配合,深度激發(fā)觀眾的五感,以模擬情景的方式提供高質(zhì)量的體驗服務(wù),將空間作為再現(xiàn)時間的工具,用智慧化的展陳方式為打造沉浸式的體驗環(huán)境提供了基礎(chǔ)。
(二)打通全年齡層的沉浸式體驗
博物館場域空間是人與周圍場景之間關(guān)系的總和,其場景是核心要素,而對現(xiàn)代的博物館來說,單一的參觀形式與展出形式無法滿足當(dāng)前大眾的觀展需求,大眾需要深層次的體驗來滿足對知識的渴求。所以要提高博物館對大眾的吸引力,就需要展陳的設(shè)計者根據(jù)大眾的體驗需求來豐富博物館的展覽形式。采用沉浸式的體驗,在博物館的場景建造過程中配合投影系統(tǒng)、AR等技術(shù)讓觀眾以第三視角沉浸到博物館營造的虛擬場景當(dāng)中,也可以通過復(fù)刻場景等手段還原歷史場景,結(jié)合故事情節(jié)讓觀眾有深刻的體驗感。這種沉浸式的體驗方式能夠滿足全年齡層的需求,不同年齡階段在相同的記憶場景中充當(dāng)著不同的角色,紅色記憶的經(jīng)歷者與創(chuàng)造者能夠在沉浸式的體驗當(dāng)中找回那段記憶進而引起共鳴,而作為紅色集體記憶的接收者則能在當(dāng)前的時空中體驗過去時空下所發(fā)生的故事,全身心地了解那段歷史,將那段集體記憶升華至民族認同感,締造者為接受者補充紅色集體記憶的細節(jié),還原那段崢嶸歲月。打通全年齡層的沉浸式體驗方式能夠為社會提供智慧化的服務(wù),提高了觀眾的觀展體驗,也為今后的策展工作、研究工作、文化傳播工作建立了服務(wù)路徑。還能使不同年齡層的人跨越年齡、經(jīng)歷的代溝,傳遞給他們相同的中華之魂,從而凝聚中華民族精神,將時代精神傳承下來。
(三)整合文博資源,傳承“紅色”文旅情懷
結(jié)合文旅進行多產(chǎn)業(yè)融合,打造“紅色”文旅情懷的“紅色”文博旅游帶。博物館、紀念館中的文物、史料等能夠反映紅色集體記憶的器物及故事與當(dāng)代社會文化發(fā)展出現(xiàn)了對接缺口,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代人們的生活背景與生活習(xí)慣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紅色集體記憶也容易被新時代的事物所替代,為此紅色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革命遺址等紅色文博資源必須進行整合,開拓出優(yōu)質(zhì)的紅色文化資源并培養(yǎng)紅色文化環(huán)境。打造相關(guān)業(yè)態(tài)產(chǎn)業(yè)與文化路線,將紅色文化形成帶狀產(chǎn)業(yè),人們就能夠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紅色革命文化,同時能夠?qū)⒓t色文化拓展到其他行業(yè)當(dāng)中。讓紅色集體記憶不再是停留于過去的回憶,而是通過智慧文博這個平臺將豐富的紅色文化傳播到社會上,社會公眾的需求與意見也能夠通過這樣的智慧平臺進入到智慧文博體系中,使得社會與智慧文博之間能夠交流互動,加深公眾對紅色集體記憶的了解。在這樣的過程中,紅色文化在大眾的生活中出現(xiàn)的頻率越高,越能形成一種凝聚力,將紅色集體記憶中的時代精神及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聚合在一起,引導(dǎo)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從而對紅色文化起到傳承的作用,也能推進紅色集體記憶的整理、收集和研究工作,弘揚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文化,激發(fā)人們的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
四、集體記憶功能下的文博體系實施路徑
(一)復(fù)刻歷史場景以打造回憶空間
在塑造紅色集體回憶的過程中,博物館需要采用場景復(fù)刻再現(xiàn)的方式,用空間來還原時間,將過去的空間跨時空地展現(xiàn)在當(dāng)下的展示空間中,然后通過一系列儀式化的形式和方法將集體記憶的時空進行重構(gòu)。紀念儀式作為集體記憶的傳承方式,在集體記憶功能下的文博體系當(dāng)中,其必須具有時空特征,能夠通過儀式鏈接過去、未來與現(xiàn)在,重要的是歷史場景的復(fù)刻必須與儀式相結(jié)合,場景能夠幫助觀者在儀式進行的過程中提供刺激記憶喚醒共鳴的作用。如武漢的張之洞博物館就將“思想者的孤獨”(圖1)作為特色場景,還原張之洞在漢陽時曾思考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辦公室,將其進行了復(fù)刻,觀者坐到彼時張之洞先生曾坐過的“位置”上去思考漢陽鐵廠的過去與未來,去回憶那段崢嶸歲月,感受張之洞先生拯救國家民族的大義與情懷。復(fù)刻的歷史場景還原的不僅是空間,更是對人們集體記憶的重構(gòu),將大眾作為主角還原至復(fù)刻的場景空間里,給予真實的回憶空間,激發(fā)情感之間的共鳴。這種沉浸式的歷史場景復(fù)刻設(shè)計也使張之洞博物館吸引了大量的社會關(guān)注,在“云游”張之洞博物館的直播節(jié)目當(dāng)中,這種人文氣息與現(xiàn)代工業(yè)風(fēng)格的歷史場景復(fù)刻場景得到了無數(shù)好評,其節(jié)目當(dāng)日累計觀看人數(shù)就已經(jīng)達到680萬人次。將時間通過智慧化的方式再現(xiàn)成空間,讓過去的記憶穿越到現(xiàn)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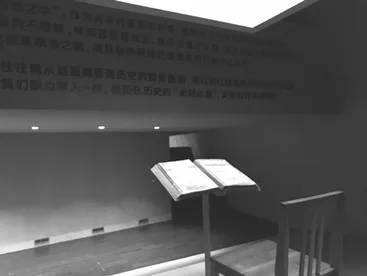
圖1 張之洞博物館“思想者的孤獨”
(二)挖掘傳承要素以促成跨時空的群體對話
在博物館的敘事過程中,處于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交互中的參觀者已經(jīng)將其實時狀態(tài)以及生活習(xí)慣融入到整個參觀過程當(dāng)中,而博物館的單向敘事方式也已不能滿足觀眾的參觀訴求。所以由單向至雙向的沉浸式的體驗方式成為了當(dāng)前博物館最能引導(dǎo)觀眾的重要參觀方式。沉浸式的體驗方式根據(jù)參觀者的實時狀態(tài)與生活習(xí)慣,結(jié)合數(shù)字技術(shù)的虛擬場景再現(xiàn),讓文化場景與虛擬場景相互滲透,讓過去的故事跨越時空在今天與觀眾進行跨時空的交流,觀眾可以通過實體場景與線上虛擬場景的結(jié)合成為紅色記憶的構(gòu)建與發(fā)展的參與者與決策者,在一些主題體驗活動當(dāng)中。依托微信小程序、線上推廣文創(chuàng)以及社教和數(shù)字社教活動的方式將紅色文化資源打造成生態(tài)化的帶狀產(chǎn)業(yè),在社會上營造優(yōu)質(zhì)的紅色文化環(huán)境,將紅色集體記憶轉(zhuǎn)化為優(yōu)質(zhì)的紅色文化資源,通過智慧文博的保護并再利用向公眾進行立體、全面、延展的紅色文化教育熏陶,將革命精神傳承下去并發(fā)揚光大。例如,在鐵人王進喜紀念館的虛擬紀念館中(圖2),將實體的藏品變成數(shù)據(jù)呈現(xiàn)在觀眾的移動端中,在實體展覽中沒有發(fā)現(xiàn)的微小細節(jié)都可以通過手機端的放大、縮小、旋轉(zhuǎn)等進行詳細觀察,還提供了語音實時講解的功能,并且可以模擬出藏品的使用環(huán)境,在手機端體驗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強化觀眾對時間記憶的轉(zhuǎn)化,更能深刻地理解藏品背后所展現(xiàn)的紅色精神。

圖2 王進喜紀念館線上展廳
因此這里的沉浸式服務(wù)體驗不單單是對社會服務(wù),而是博物館在敘述紅色集體記憶的過程中,將觀眾作為集體記憶的設(shè)計者與傳承者,智慧化的服務(wù)能夠根據(jù)觀眾的喜好與訴求,引導(dǎo)他們?nèi)ヅc過去的那段紅色集體記憶跨時空對話,最終將個體需求轉(zhuǎn)譯到整體當(dāng)中,將紅色集體記憶分別烙印在不同的個體當(dāng)中,將紅色集體記憶傳承下去。
(三)提取紅色文化因子產(chǎn)生文博互動體驗
紅色文化的弘揚能夠在當(dāng)代社會喚起人民群眾的歸屬感,提取集體記憶中的紅色文化因子能夠在凝聚社會意識的時候?qū)⒓t色精神作為主旋律。而文博資源作為傳承紅色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必須擁有繼往開來的力量,將過去的歷史、現(xiàn)在的精神以及未來的發(fā)展連接起來,讓過去、現(xiàn)在、未來互動起來,挖掘多元的文化形式,讓紅色文化實現(xiàn)互動化、體驗化、全方面的傳播與傳承。通過線上互動的方式,將最新的展覽、最新的文博信息借助線上宣傳的方式傳達給公眾,使其能有一個最直觀的了解,在智慧文博這個平臺上將提取出來的豐富紅色文化傳遞到社會上,社會公眾的需求與意見也能通過這樣的智慧平臺上進入到智慧文博體系中,使得社會與智慧文博之間能夠交流互動,加深公眾對紅色集體記憶的了解。如廣東惠州的葉挺紀念館的互動展廳(圖3),將數(shù)字化的科技裝置與互動化的理念結(jié)合起來,共同帶領(lǐng)大眾開啟對葉挺生平的互動探索。通過互動觸控查詢點播系統(tǒng),將葉挺的相關(guān)歷史數(shù)據(jù)挖掘并整合成數(shù)字化檔案,為觀眾提供了全面直觀的數(shù)據(jù)。接著通過趣味問答系統(tǒng),引導(dǎo)游客將知識與趣味相結(jié)合,引領(lǐng)游客將枯燥的知識轉(zhuǎn)化成紅色文化因子沉淀在心中。最后感應(yīng)點播系統(tǒng),利用雷達感應(yīng)與定向音響等設(shè)備,將影片資料、專家訪談、親屬回憶等內(nèi)容與游客進行多個視角的互動式講解,將枯燥的人物故事與歷史事件通過場景再現(xiàn)和互動體驗的方式完整又有趣地敘述出來,使其走進大眾的視野中,將紅色文化因子深深植入到人民群眾心中,最終形成更大范圍的紅色文化推廣。

圖3 葉挺紀念館互動展廳
(四)塑造共同話題與拓印紅色精神
在《關(guān)于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shè)的意見》中,要求我們建設(shè)一批紅色法制文化高質(zhì)量的宣傳基地。在推動優(yōu)秀中華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轉(zhuǎn)化過程中需要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弘揚以及對世界上優(yōu)秀的法制建設(shè)成果進行學(xué)習(xí),通過建造紅色基地,深挖我國古代法制的得失與成敗,將民為邦本、禮法并用、以和為貴、明德慎罰、執(zhí)法如山等按照當(dāng)前的時代需要進行轉(zhuǎn)化,并以此在公眾中普及,以普法的方式引起公共話題,通過話題向公眾弘揚代表人物的優(yōu)秀事跡與人物精神,同時在文物方面加強對法律文化典籍的保護與整理,整合古籍當(dāng)中的文字,讓其能夠穿越時空將文化記憶在當(dāng)下再現(xiàn)出來,挖掘其中的優(yōu)良風(fēng)俗與家規(guī)家訓(xùn)內(nèi)容,采用數(shù)字化建設(shè)法治文化的形式,同時智慧化的服務(wù)也能有效地增強觀展的趣味性,線上的數(shù)字平臺也能給受眾推送線上展覽、微講座、互動活動等線上服務(wù),便于開展智慧化的策展、展品研究、文化傳播等工作。在人民日報主辦的“你記得我我就活著”的話題中(圖4),通過對烈士家人的采訪,讓大眾從英雄親人的角度去填補那段紅色集體記憶的細節(jié),通過尋找烈士親人來與社會進行對話,不斷深挖英雄事跡背后的故事,提高社會對紅色文化的關(guān)注度,引起大眾共鳴,弘揚革命傳統(tǒng)、傳承革命文化,提高民族精神凝聚力。

圖4 “你記得我我就活著”活動
五、結(jié)論
本文通過對紅色集體記憶概念的構(gòu)建與原理分析,闡釋紅色集體記憶的目標與價值。結(jié)合博物館的相關(guān)理論,為紅色博物館、紀念館等在打造智慧文博建設(shè)的時候提供了關(guān)于紅色集體記憶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經(jīng)驗。將博物館作為紅色集體記憶的場所,構(gòu)建再現(xiàn)時空記憶的空間,讓現(xiàn)在與過去跨時空進行對話,塑造共同話題來整合民族記憶提高民族精神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