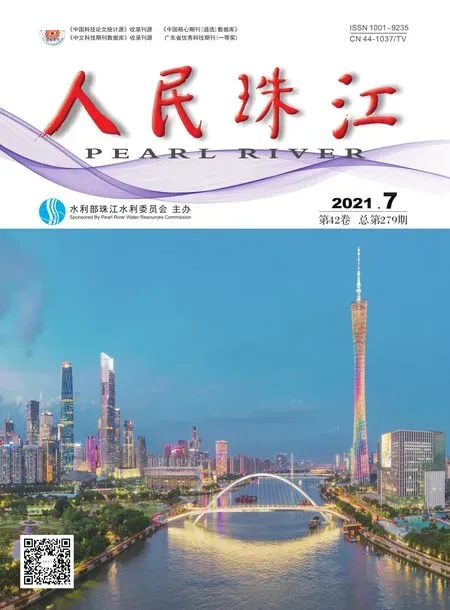基于GLEAM 遙感數據的廣東省近30 年蒸散發及組分時空演變特性研究
王大洋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地表蒸散發(Evapotranspiration,ET)是地球表面和大氣系統進行水分和能量傳輸的主要途徑。 在地表水循環過程中,大氣水分以降水的形式降落到地球表面,地表水分以蒸散發的方式返回到大氣中。在到達地表的太陽輻射中,約48%的輻射量被消耗于蒸散過程,蒸散發過程的汽化潛熱使得陸地上約64%的降水得以重新進入大氣,從而構成了地球最基本的水循環結構[1]。 因此,研究蒸散發及其演變規律對于深刻理解陸氣水分-能量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與地球水循環的其他組分相比,地表蒸散發過程受到的影響因素更為復雜,如太陽輻射、環境溫度、濕度、風速、地表植被覆蓋、土壤含水等。 蒸散發的測量雖不像降水和徑流那樣直觀,但也可通過蒸散皿、蒸滲儀和渦度儀等測量設施進行捕捉。 然而,傳統的觀測方法往往受地表下墊面因素的影響,觀測小范圍、均勻、年月尺度的下墊面蒸散發時較為準確,但對于較大空間范圍、較短時間精度,復雜下墊面和水熱傳輸的非均勻性較強的地區則會顯得力不從心。 20 世紀60 年代,隨著熱通量制圖衛星(Heat Capacity Mapping Mission,HCMM)和極軌氣象衛星(TIROS-N)的發射成功,遙感技術的發展真正意義上帶動了地表蒸散發的測量和估算。 事實上,衛星遙感技術并不是直接測量地表的蒸散發量,而是通過測量與蒸散計算有關的其他環境參數,基于經驗統計或物理過程的估算方法(如Penman-Monteith 公式及Priestley-Taylor公式)來推算地表蒸散發量,這一過程也稱作遙感反演[2-3]。 如通過測量可見光、近紅外和熱紅外等不同波段的數據,反演出地表反照率、植被指數、土壤含水、地表溫度等信息,進而推算出蒸散發量。 與直接觀測相比,遙感在資料稀少、地形復雜的地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隨著遙感技術和反演方法的逐漸發展和成熟,地表蒸散發的測量精度也變得越來越高。
目前,全球范圍的地表蒸散遙感產品有MODIS(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TE(Model Tree Ensemble)、GLEAM(Global Landsurface Evaporation Amsterdam Model)、PML(Penman-Monteith-Leuning)、MET-WB(Model Tree Ensemble-Water Balance)、MERRAa(Modern-Er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等,不同遙感產品在遙感反演方法上存在差異。 本文結合遙感產品的適用性和實時性,選用GLEAM遙感數據對中國廣東省區域的蒸散發及其組分的時空演變特性進行研究。
近些年關于遙感數據的評價研究層出不窮,王艷君等[4]研究了長江流域1961—2000 年蒸發量變化趨勢;邴龍飛等[5]利用NOAH-CLM模擬了中國1986—2009 的陸地蒸散發。 研究結果表明,植被覆蓋度和土壤水分是影響蒸散發的最重要的因子;Li等[6]通過對中國1982—2009 年蒸散發進行估算,結果顯示ET整體呈增加趨勢;楊秀芹等[7]基于GLEAM遙感數據對中國淮河流域多年的地表蒸散發時空變化進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蒸散發的季節性變化規律。 牛忠恩等[8]基于PT-JPL遙感數據分析了2000—2015 年的蒸散發時空變化特征及影響因子。 上述研究中多為從全國大范圍空間尺度進行分析,針對廣東省區域的研究相對較少,且上述研究多為對總蒸散發量進行分析,而針對各個組分的時空變化研究較少。 鑒于此,本文基于最近更新的GLEAM遙感數據,對廣東省1989—2018 年近30 年陸面蒸散發及其組分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研究,以期為更加深刻地理解氣候變化下蒸散發對水循環的影響提供科學參考。
1 研究數據及區域
1.1 研究數據
GLEAM數據[9-11]是由英國University of Bristol地理科學學院Diego G.Miralles博士研發的遙感蒸散發產品,數據可以公開免費獲取。 GLEAM模型算法是基于物理過程的Priestley-Taylor公式,通過多顆衛星的遙感觀測數據反演得到,其空間分辨率為0.25°×0.25°,時間分辨率分為日尺度和月尺度,GLEAM模型包括4 個模塊:①Gash 截留模塊;②Priestley-Taylor潛在蒸發模塊;③考慮根區含水和植被光學厚度的蒸發脅迫壓力模塊;④土壤濕度模塊。本研究所選數據為1989—2018 共30 年的蒸散發數據,主要包括截留蒸發(Interception Loss,Ei)、土壤蒸發(Soil Evaporation,Eb)和植被蒸騰(Transpiration,Et),由于水面蒸發比例太小,數量級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不予考慮水面蒸發。 相應地,以前3 種蒸散發之和(ET=Ei+Eb+Et)作為總蒸散發量進行計算分析。 此外,Yang等[9]2017 年對GLEAM遙感產品在中國區域的適用性進行過詳細的評價分析,因此,本研究不再對其在廣東省的適用性進行單獨評價,而是直接對其和組分的時空演變特性進行研究。
研究選取了能反映植被變化情況的歸一化植被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數據作為衡量植被動態變化的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12]。 NDVI值越高,表明該地區的植被覆蓋面積占比越大;NDVI值越低,則表明該地區的植被覆蓋面積占比越小。
1.2 研究區域概況
廣東省地處中國大陸南部,屬珠江流域,簡稱“粵”,周圍分別與贛、湘、桂等省份相鄰,南臨南海。全省陸地面積為17.97 萬km2,下轄21 個地級市,是中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省份之一,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南大門”。 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和水平均居全國前列。
廣東省絕大部分地區位于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因此仍有明顯的四季,夏季炎熱多雨,冬季溫和干燥。 廣東水資源相當豐富,省內多年平均降水量為1 770 mm,境內主要分布西江、東江、北江等河流,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因此也就造成其蒸散發也存在明顯的非均勻性。 此外,廣東省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屬于高度城市化地區,其下墊面的變化勢必會影響到蒸散發的空間分布。
2 研究方法
2.1 Mann-Kendall趨勢檢驗
Mann-Kendall[13-14]趨勢檢驗是一種被廣泛用于檢測時間序列趨勢的非參數方法,其在水文氣象領域頗受歡迎。 其原理為:

其中,n 為時間序列長度,xk和xj分別取k=1,2,…,n-1 和j=k+1,…,n。 當n 大于8 時,統計量S 近似服從標準正態分布,此時統計量S 的均值為0,方差為:

之后,可得到統計量Z為:

如Z>0,表明序列呈增加趨勢,反之亦然。 通過給定顯著性水平α,檢測>Z(1 -α/2)是否成立來判斷序列是否通過該顯著性水平下的檢驗,其中Z(1 -α/2)對應p=α/2,遵循標準正態分布,本研究中選p=0.01、p=0.05、p=0.10,分別對應99%、95%、90%的顯著性水平。
2.2 Sen′s Slope趨勢檢驗
Sen′s Slope[15]也是一種非參數趨勢檢驗方法,由荷蘭計量經濟學家亨利·泰爾與美國統計學家普拉納布·森聯合提出,主要用于檢測時間序列的趨勢變化方向及量級,其計算原理為:

式中,β 為Sen′s Slope統計量,當其大于0 時,表明序列呈上升趨勢,反之呈下降趨勢。
本研究通過將2 種方法進行結合,用于分析研究廣東省的1989—2018 年近30 年的蒸散發量及組分變化情況。
3 研究結果
3.1 蒸散發及其組分的時間變化特征
通過對廣東省1989—2018 年GLEAM 網格數據統計分析,得到近30 年廣東省多年平均總蒸散發量為874.6 mm,其中最大值出現在2016 年,其值為949.1 mm, 最小值出現在 1999 年, 其值為824.0 mm。 通過一階線性趨勢分析可知,總蒸發量在近30 年雖有波動,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上升速率為1.5 mm/a。 將蒸散發量各個組分(植被截留,土壤蒸發和植被散發)分別進行分析,同時繪制出各個組分比例的年際變化情況,得到圖1。

圖1 廣東省總蒸散發量及各組分的年際變化(點線圖為蒸發量,條形圖為比例)
從表1 得知,近30 年的多年平均植被截留量為97.5 mm,多年平均土壤蒸發量為26.4 mm,多年平均植被散發量為750.7 mm。 從組分占比不難看出,總蒸散發中的主要成分為植被散發,占比高達85.87%;其次為植被截留,比例為11.11%;土壤蒸發占比最小,僅為3.02%。

表1 廣東省1989—2018 年多年平均蒸散發及其組分占比
從圖1 分析各組分及比例變化趨勢可知,植被截留量和植被蒸散發量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增加趨勢,相比之下,植被截留增加的趨勢為1.1 mm/a,略高于植被散發的增加趨勢(0.5 mm/a)。 然而,土壤蒸發卻表現出輕微的減少趨勢,減少速率為0.1 mm/a。
之后,對總蒸散發的各個組分和比例進行Mann-Kendall和Sen's Slope趨勢檢驗發現,廣東省總蒸散發量表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其顯著性通過了99%(p<0.01)水平的檢驗。 對于其組分,植被截留同樣也表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其同樣通過了99%(p<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土壤蒸發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減少趨勢,其顯著性通過了90%(p<0.1)水平的檢驗。 相比之下,植被散發雖然占比較大,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態勢,但其變化并不顯著,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此外,植被截留和土壤蒸發比例的年際變化趨勢與其蒸發量趨同。 值得注意的是,占據高比例的植被散發量和它的比例出現了相反的變化趨勢。 從2012—2016 年植被散發量的變化不難看出,其數量上變化并不大,但其比例卻明顯低于多年平均。 同一時期,發現植被截留表現出明顯地高于多年平均的變化趨勢。 植被截留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植被散發的減少,因此同期的總蒸散發量變化并不明顯。
3.2 蒸散發及其組分的空間分布變化特征
基于0.25°×0.25°的GLEAM數據,繪制出廣東省1989—2018 年的蒸散發空間分布,以及各個組分比例的空間分布格局,見圖2。

圖2 廣東省蒸散發量及各組分比例空間分布

續圖2 廣東省蒸散發量及各組分比例空間分布
從圖2a可知,廣東省總蒸散發量分布不均,其中以800 ~1 000 mm的區域居多,它們貢獻了大部分的總蒸散發量。 粵東地區和粵西南部分地區較高,粵中部分地區出現了低值,其主要的城市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核心所在區域。 從植被散發、土壤蒸發和植被截留等組分的比例可以看出,植被散發占據主要成分,所有網格均在60%以上,其中粵南地區的雷州半島等地的占比更是高達90%以上。對于土壤蒸發而言,其分布情況則相對均勻,中部地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所在區域呈現出明顯的高值以外,其他區域的土壤蒸發比例差異非常小,當然這也和它本身比例小有關系。 植被截留的比例則表現出沿海地區略低,內陸略高的分布趨勢。
為研究廣東省蒸散發及其組分的變化趨勢的空間分布,研究采用Mann-Kendall和Sen's Slope趨勢檢驗方法,對每個網格1989—2018 年的蒸散發量及組分進行計算,得到2 種方法的統計量Z值和β 值的分布情況,見圖3、4。 其中值越大,表明網格的變化趨勢越明顯,β 值的正負則表示網格序列的變化趨勢,正為增加,負為減少。 將2 種方法得到的結果進行疊加,可以得到各個網格在不同的顯著性水平下的空間分布情況,得到圖5。

圖3 廣東省蒸散發量及各組分M ann-Kendall趨勢分析統計量Z分布

圖4 廣東省蒸散發量及各組分Sen's Slope趨勢分析統計量β分布


圖5 廣東省蒸散發量及各組分綜合趨勢演變分布
從Mann-Kendall趨勢檢驗結果可知,總蒸散發量(圖3a)的統計量Z值分布較為不均,總體表現出粵北向粵南遞減的分布特點,然而,也出現粵港澳大灣區個別網格的Z值也較大的例外情況;相較而言,植被散發(圖3b)和土壤蒸發(圖3c)的空間不均勻性則更為突出,網格的Z值分布較為離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所在地區的植被散發則呈現出明顯的低值區域,相應地,從Sen's Slope趨勢分析結果(圖4b)顯示,該區域β 值也明顯較周圍地區小,表明該區域為減少態勢。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核心所在地區的土壤蒸發(圖4c)則表現出相反增加態勢。
將2 種趨勢檢驗的方法相結合,分析得到廣東省的99%、95%和90%顯著性水平下的蒸散發量及組分的空間分布,得到圖5 和表2。 從圖表可知,對于總蒸散發量,空間上有67.46%區域呈現出顯著增加的趨勢,且可以通過了90%(p<0.1)顯著性水平檢驗,同時這些區域基本分布在廣東省北部的大部分區域;然而,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廣州市的個別網格,則有明顯減少的趨勢,該網格的顯著減少能通過99%(p<0.01)顯著性水平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該現象,對蒸散發各組分也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地區的植被散發和植被截留出現顯著減少的范圍要更大,且均能通過較高的99%(p<0.01)顯著性水平檢驗。 除了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的植被散發和植被截留表現為顯著減少趨勢外,其余有顯著變化的區域基本上都為顯著增加趨勢。 然而,對于土壤蒸發而言,上述規律則表現出相反的態勢。

表2 廣東省1989—2018 年多年平均蒸散發及其組分變化趨勢的顯著性區域占比
總體上,在90%(p<0.1)顯著性水平下,超過2/3 的區域的總蒸散發和土壤蒸發表現出顯著性變化趨勢,接近一半區域的植被截留和植被散發呈現顯著性變化趨勢;即使在99%(p<0.01)顯著性水平下,也有接近一半區域總蒸散發和土壤蒸發表現出顯著性變化趨勢。 由此可推測,近30 年的全球變暖和劇烈的人類活動2 種作用正在深刻地擾動著地表水循環過程,而作為水循環中重要環節的蒸散發也不可避免地被時刻影響著。
3.3 蒸散發變化成因分析
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總體蒸散發中比例較高的組分為植被散發,植被散發也稱作植被蒸騰,是指被植物根系吸收的水分經由植物的莖葉散逸到大氣中的過程。 因此,該部分的變化必然會受到地表植被覆蓋的影響,植被面積的增加會導致植物莖葉輸送更多的水分到大氣中,從而使散發量增加。
因此,為進一步探索蒸發量增加的原因,將1999—2018 年的廣東省NDVI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并選擇了2000 年、2010 年和2018 年3 個時間進行繪制,見圖6。 結果發現,在近20 年間,廣東省NDVI表現出明顯的增加態勢,整個省份的NDVI的平均值由1999 年的0.703 增加至2018 年的0.785,增加了12%。 從圖6 的2000 年、2010 年和2018 年等3 個年份的空間變化可以看出,整體“變綠”成為明顯的動態特征。 此外,雖然廣東省的蒸散發總體呈現增加的趨勢,但上述研究中發現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部分的蒸散發量卻呈現出明顯減少的趨勢。通過圖6 也不難發現,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的NDVI值則表現出明顯的“變紅”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結果的合理性。 同時,這也意味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和擴張正深刻影響著地表下墊面分布格局,從而影響著蒸散發的變化。

圖6 廣東省1999—2018 年NDVI指數變化

續圖6 廣東省1999—2018 年NDVI指數變化
4 結論
a)廣東省1989—2018 年蒸散發總量為874.6 mm。在各組分中,植被散發占據最大比例,多年平均高達85.87%,土壤蒸發比例最小,多年平均僅為3.02%。各組成比例在年際變化上存在一定差異。
b)在時間變化上,廣東省1989—2018 年蒸散發量總體呈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增加速率為1.5 mm/a,其增加趨勢通過了99%(p=0.01)的顯著性水平的檢驗。 植被散發和植被截留同樣表現出增加趨勢,而土壤蒸發則呈現減少趨勢。 在空間分布上,蒸散發量在廣東省中部以北的大部分區域呈現出顯著增加的趨勢,南部變化則不顯著。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地區則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
c)廣東省近20 年的NDVI值呈現出一定的增加趨勢,這可能是引起植被散發增加,進而導致蒸散發增加的主要下墊面因素。 相比之下,粵港澳大灣區部分地區的高度城市化使該區域的NDVI表現出明顯的減少趨勢,表明城市化對蒸散發的時空演變產生了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