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主要影響因素的相關性研究
周毅先 趙艷紅 王愛玲 馬姣媚 楊偉娟 孫瑤瑤
(1.空軍軍醫(yī)大學第二附屬醫(yī)院兒科,陜西 西安 710038;2.西安交通大學附屬西安市兒童醫(yī)院呼吸內科,陜西 西安 710003)
兒科重癥監(jiān)護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是兒科集中救護危重癥患兒的醫(yī)療單元,患兒從PICU轉出到普通監(jiān)護病房通常是其病情穩(wěn)定或好轉的表現(xiàn)。在患兒轉出過程中,醫(yī)護人員常常將與患兒主要照顧者溝通的重點放在患兒轉出后的治療和護理上,故往往忽視了患兒轉出對其主要照顧者照護負擔、心理壓力和情緒改變的影響[1]。有研究[2]顯示,患兒從PICU遷移到普通病房時,其主要照顧者在心理準備不充分的條件下,極易產生恐懼、焦慮,甚至抑郁等負面情緒,該應激現(xiàn)象即為遷移應激 ,遷移應激的產生不但影響患兒主要照顧者的身心健康,還會延誤患兒后期的治療康復進程。賀秋平等[3]的研究表明,我國PICU患兒轉出過程中,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均處于高水平狀態(tài)。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社會活動中獲得的來自家庭、朋友等物質、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4],朱孟欣等[5]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能夠提升患兒家屬自我效能,緩解其焦慮癥狀;社會比較傾向是指個體對他人與自己相關聯(lián)信息進行比較和思考的程度與頻率上差異,吳文峰等[6]的研究顯示,社會比較傾向對抑郁的進程具有顯著預測作用,即社會支持和社會比較傾向對遷移應激的主要癥狀群——焦慮和抑郁均有影響,但目前尚無研究報道二者是否對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產生直接作用。本研究擬調查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分析社會支持和社會比較傾向對其影響作用,旨在為PICU遷移應激的預防和干預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橫斷面調查,便利選取2019年12月—2020年8月在空軍軍醫(yī)大學第二附屬醫(yī)院兒科治療,并從PICU轉入普通病房的134例患兒主要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PICU入住時間≥72 h的患兒主要照顧者。(2)計劃轉入我科普通病房的患兒主要照顧者。(3)患兒主要照顧者年齡≥18歲。(4)患兒主要照顧者為患兒的直系親屬。(5)有多名主要照顧者時,選取照顧時間最長者。(6)患兒主要照顧者能夠獨立完成問卷的填寫。(7)知情同意并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1)患兒主要照顧者有嚴重認知障礙或患有神經(jīng)精神疾病。(2)患兒主要照顧者有溝通交流障礙。
1.2調查工具
1.2.1一般情況調查問卷 筆者自行編制,調查內容包括患兒的性別、年齡、PICU入住時間、疾病類型、疾病預后、醫(yī)療支付類型;患兒主要照顧者的性別、年齡、職業(yè)類型、婚姻狀況、與患兒關系、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月收入。其中疾病預后判斷采用兒童格拉斯哥預后量表進行評定,該評定共分為5級,4~5級為預后良好,1~3級為預后不良[7]。
1.2.2ICU轉出患者家屬遷移應激量表(Family relocation stress scale items,F(xiàn)RSS) 該量表由Oh等[8]于2015年編制,用于評價ICU轉出患者家屬遷移應激水平,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30,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680~0.880。王永華等[9]于2018年將其漢化,并用于評價我國ICU轉出患者家屬遷移應激水平,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57,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00~0.858。賀秋平等[3]于2019年12月對其進行修訂并用于評價我國PICU轉出患兒家屬遷移應激水平,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970。本研究采用賀秋平版量表,共包括家屬壓力(4個條目)、遷移準備(5個條目)、患者自護能力(4個條目)、遷移滿意度(2個條目),共4個維度15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賦1~5分,總分范圍為15~75分,總分越低說明患兒家屬遷移應激水平越高,其中15~44、45~59、60~75分分別代表遷移應激的高、中、低水平。本研究量表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34,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15~0.861。
1.2.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d Scale,SSRS) 由肖水源[10]于1986年編制,用于評定個體的社會支持情況,Cronbach α 系數(shù)為 0.810。共包含客觀支持(3個條目)、主觀支持(4個條目)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個條目),共3個維度10個條目。其中條目1~4、8~10為定向選擇題,4個選項依次賦分1~4分(1~4分);條目5有5題4個選項(定向選擇題),每個項從“無”~“全力支持”分別賦分 1~4 分,計所有題項總分(5~20分);條目6、7為不定項選擇題,當選擇“無任何來源”選項時賦分0分,選擇其他選項時,選幾項則得幾分(0~9分)。各維度分及總分范圍分別是:1~22分、8~32分、3~12分、12~66分,分值越高,說明調查對象在該維度的社會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量表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16,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07~0.845。
1.2.4愛荷華-荷蘭社會比較傾向量表(Iowa-Netherland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Measure,INCOM) 由Buunk等[11]于1997年編制,用于評估個體的社會比較傾向情況,兩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780、0.850。王明姬等[12]于2006年將其漢化修訂,并用于評價我國在校大學生社會比較傾向情況,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80,兩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40、0.810。本研究采用王明姬版量表,共包含觀念社會比較傾向(4個條目)、能力社會比較傾向(7個條目),共2個維度11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依次賦分1~5分,兩維度分及總分范圍分別為:4~20分、7~35分、11~55分,分值越高說明調查對象社會比較傾向性越強。本研究量表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41,兩維度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15、0.856。
1.3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由經(jīng)過培訓的2名兒科主管護師于患兒由PICU轉出前1 d向患兒主要照顧者發(fā)放問卷,并向其告知本研究的目的和問卷的填寫方法,由研究對象自行填寫,問卷均當場發(fā)放和回收。共發(fā)放問卷134份,回收問卷134份,回收率為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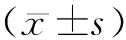
2 結果
2.1一般資料 134例調查對象中, 男78例(58.2%)、女56例(41.8%),平均年齡(7.89±3.42)歲。PICU入住時間(12.37±4.86)d;疾病類型:消化系統(tǒng)疾病46例(34.3%)、呼吸系統(tǒng)疾病37例(27.6%)、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21例(15.7%)、循環(huán)系統(tǒng)疾病17例(12.7%)、泌尿系統(tǒng)疾病13例(9.7%);疾病預后:良好103例(76.9%)、不良31例(23.1%),醫(yī)療支付類型:醫(yī)保118例(88.1%)、自費16例(11.9%);患兒主要照顧者性別:男62例(46.3%)、女72例(53.7%),平均年齡(33.71±7.39)歲,職業(yè)類型:腦力勞動49例(36.6%)、體力勞動85例(63.4%);婚姻狀況:單身21例(15.7%)、存續(xù)113例(84.3%),與患兒關系:患兒父母89例(66.4%)、患兒(外)祖父母45例(33.6%),文化程度:大專以下45例(33.6%)、大專及以上89例(66.4%),居住地:農村51例(38.1%)、城鎮(zhèn)83例(61.9%),家庭月收入:低于10 000元54例(40.3%),高于10 000元80例(59.7%)。
2.2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得分情況 本組134例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量表總分為(37.79±7.62)分,各維度得分分別為:家屬壓力(11.28±3.47)分、遷移準備(13.62±3.79)分、患者自護能力(8.16±2.84)分、遷移滿意度(4.31±1.15)分。
2.3不同特征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得分比較 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評分比較
2.4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評分與社會支持、社會比較傾向評分的相關性分析 本組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各維度得分分別為:客觀支持(14.26±3.27)分、主觀支持(19.88±5.32)分、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5.71±2.04)分;愛荷華-荷蘭社會比較傾向量表各維度得分分別為:觀念社會比較傾向(12.23±3.15)分、能力社會比較傾向(21.48±5.79)分。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本組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評分與客觀支持(r=0.512,P<0.001)、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r=0.678,P<0.001)評分呈密切正相關;與觀念社會比較傾向(r= -0.524,P<0.001)、能力社會比較傾向評分呈負密切相關(r= -0.633,P<0.001)。
2.5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見表2。

表2 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n=134)
3 討論
3.1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處于高水平 本研究結果顯示, 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量表總分為(37.79±7.62)分,按照15~44、45~59、60~75分分別代表遷移應激的高、中、低水平的評價標準[3],本組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處于高水平,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歸因于患兒主要照顧者自身心理準備度的不足,患兒入住PICU期間,其主要照顧者承受著心理和經(jīng)濟上的多方壓力,且無法在身邊陪伴患兒,對于患兒救治的參與度較低,而患兒的突然轉出則意味著主要照顧者在治療中角色的又一次轉變,此時往往會造成患兒主要照顧者未能充分調整心態(tài),做好心理上的準備[13];其次歸因于患兒主要照顧者對于自己照護能力的擔憂,患兒轉出PICU后,主要照顧者將深度參與到患兒后期的治療和護理當中,而自己是否能夠按照醫(yī)護要求配合好治療、護理工作,是否具備照護好患兒的能力等一系列問題又使其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14];最后,則是患兒主要照顧者對于新的治療環(huán)境和治療團隊缺乏信任和理解,轉出PICU說明患兒病情的好轉,但監(jiān)護等級的下降就意味著患兒得不到醫(yī)護人員全方位的監(jiān)護,由于普通病房醫(yī)護人員救治和護理的患兒較多,工作量較大,無法及時關注到每個患兒及其主要照顧者的需求,故患兒主要照顧者信任和理解度也會降低[15]。
3.2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影響因素
3.2.1患兒年齡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兒年齡是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0.764,P=0.032),即患兒年齡越小,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越高;與McKinney等[16]的報道相似。其可能的原因是,轉出PICU意味著患兒主要照顧者要開始承擔大部分照護工作,而年齡越小的患兒,其自護能力就越差,其主要照顧者的照護負擔和壓力也就越大,故其遷移應激水平也就越高。Perez等[17]的研究還表明,患兒年齡越小,其主要照顧者的疾病不確定感就越強,及時做好轉出準備情況就越差,故其遷移應激水平也就越高。此外,李忻宇等[18]的研究還表明,患者年齡越小,其主要照顧者的康復期望也就越高,而過高的康復期望會誘導其產生焦慮、不安等負性情緒。因此,對于年齡較小患兒的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在轉出前就應向其詳細解釋轉出的原因,溝通患兒目前病況,獲得患兒主要照顧者的全面理解;還可通過設立聯(lián)絡護士的方法,在患兒轉出后對其主要照顧者進行及時隨訪和心理疏導,降低其遷移應激水平[19]。
3.2.2患兒PICU入住時間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兒PICU入住時間是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1.286,P<0.001),即患兒在PICU入住時間越長,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越高;與Brodsky等[20]的研究結果相似。究其原因,一方面,入住PICU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反映了患兒病情的嚴重程度[20],而病情越嚴重,患兒主要照顧者就會越認為PICU完備的監(jiān)護儀器、先進的診療技術和及時的監(jiān)護救治更有利于患兒的治療,更令其放心,故轉出造成其應激水平更顯著的變化;另一方面,患兒在PICU入住時間越長,其主要照顧者對PICU治療環(huán)境的依賴性也就越強[21],PICU的治療環(huán)境對于患兒主要照顧者來說就是一種安全環(huán)境,隨著治療的深入,患兒主要照顧者對于該種安全環(huán)境的依賴性也就越強,一旦轉出就意味著安全環(huán)境的打破,更意味著患兒主要照顧者要開始承擔主要照顧責任,故其遷移應激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對于入住PICU時間較長患兒的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在轉出前要提前做好心理引導,及時進行轉出后照護方法的宣教工作,建立患兒主要照顧者對醫(yī)護人員的信任感,從而幫助其改善遷移應激狀態(tài)。
3.2.3患兒疾病預后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兒疾病預后是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1.072,P<0.001),即患兒疾病預后越差,其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越高;究其原因,一方面,預后較差的患兒主要照顧者在心理上會產生患兒轉出是因為誤解治愈希望較小的想法,患兒的轉出對其心理期望造成了一定的沖擊,故其應激水平較高;另一方面,由于患兒病情相對的嚴重和預后的不良,主要照顧者對于患兒今后的治療會產生更多的擔憂[20];此外,預后較差的患兒主要照顧者更希望患兒能夠得到PICU的監(jiān)護和治療,而患兒的轉出則使得其意愿無法得到滿足,故疾病預后較差患兒的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更高。因此,對于疾病預后較差患兒的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應給與更加準確、易懂的信息傳遞[22],對患兒的預后及后續(xù)治療情況給與詳細說明,幫助其打消顧慮,樹立積極的治療信心。
3.2.4主要照顧者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要照顧者性別是其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3.297,P=0.001),即女性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更高;與Brodsky等[20]的研究結果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女性相比男性,情感上更為敏感、細致和脆弱,壓力承受能力也相對較差,對于兒(孫)女罹患重病心理上更為敏感,情感上更加難以接受,易誘發(fā)焦慮和抑郁等情緒反應,在患兒轉出時也會出現(xiàn)更多的不安和擔憂,故其遷移應激水平也相對較高[23]。另一方面,女性在傳統(tǒng)的家庭結構中通常扮演著家庭照顧者的重要角色,這種傳統(tǒng)的角色往往會給其帶來更大的情感壓力和更多的不良心理壓力風險[24],故當其面對患兒轉出這一應激事件時,表現(xiàn)出了更高的應激水平。因此,對于女性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應給予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及時的心理疏導,同時對其提出的問題也要耐心、細致地解答。此外,劉潔等[22]的研究還表明轉出指導手冊的應用能夠顯著降低遷移應激水平,也可適當應用。
3.2.5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是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2.763,P<0.001),即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越低,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水平就越高。一方面,部分主要照顧者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低的可能原因是,其難以領悟和感知到社會支持的存在[25],故社會支持就無法有效發(fā)揮緩沖作用,緩解患兒轉出對主要照顧者帶來的壓力和應激反應,導致其遷移應激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焦杰等[26]的研究則表明,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越高的個體,其心理彈性就越好,在面對患兒轉出的問題時,情緒和心理調節(jié)能力也越強,越能夠利用社會支持來解決問題,故其轉移應激水平也越低。此外,社會支持還能夠提高個體對應激事件的應對能力[26],在患兒轉出時,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越高的主要照顧者越會傾向于以積極的應對方式進行應對,故其轉移應激水平越低。因此,對于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低的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給與其更多的人文關懷,主動對其伸出援手,并鼓勵其在遇到問題時向自己尋求幫助,并進行積極利用。
3.2.6能力社會比較傾向 本研究結果顯示:能力社會比較傾向是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B=-2.725,P=<0.001),即主要照顧者越傾向于能力社會比較,其遷移應激水平就越高。究其原因,從比較對象上看,社會比較分為與相對于自己較優(yōu)者相比的“上行社會比較”和與相對于自己較劣者相比的“下行社會比較”,前者會使個體產生負面自我評價,而后者則相反。在患兒即將轉出PICU時,主要照顧者在外等候過程中通常會與其他患兒家屬交流,將自己孩子的病情與其他患兒進行比較,這種比較可能更多的是一種上行社會比較。而Swallow等[27]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上行社會比較中,如果將自我劣勢歸咎于能力不足,就會導致更強的負面自我評價,進而造成更高的應激水平。此外,馬佳佳等[28]在對ICU轉出患者家屬的研究中還分析到,能力社會比較傾向越高的主要照顧者,在比較中越容易受到比較信息的影響,獨立性也越差,越難以獨立解決患者轉出后生活、護理等問題,也易造成遷移應激水平的上升。故綜合來看能力社會比較傾向越強的主要照顧者,其遷移應激水平越高。因此,對于能力社會比較傾向較強的主要照顧者,建議醫(yī)護人員要引導其正確認識患兒病情,幫助其理性篩查和判斷獲得到的比較信息,規(guī)避錯誤上行比較信息對其帶來的負面自我判斷。
綜上所述,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處于高水平,患兒年齡、PICU入住時間、疾病預后、主要照顧者的性別、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能力社會比較傾向是PICU轉出患兒主要照顧者遷移應激的主要影響因素。針對患兒年齡較小、PICU入住時間較長、疾病預后較差,主要照顧者為女性、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低、能力社會比較傾向強的主要照顧者,醫(yī)護人員可以采用轉出前給與其準確、易懂的信息傳遞,向其詳細解釋轉出原因,獲得全面理解,引導其正確認識病情,理性判斷比較信息;轉出時發(fā)放轉出指導手冊,設立聯(lián)絡護士,并建立其對醫(yī)護人員的信任感;轉出后及時進行隨訪和心理疏導,鼓勵其主動尋求幫助,對其提出的問題耐心、細致解答,同時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等方法,降低其轉移應激水平。本研究還存在單中心研究、樣本量較少等不足,且未對轉移應激水平高的主要照顧者進行干預,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