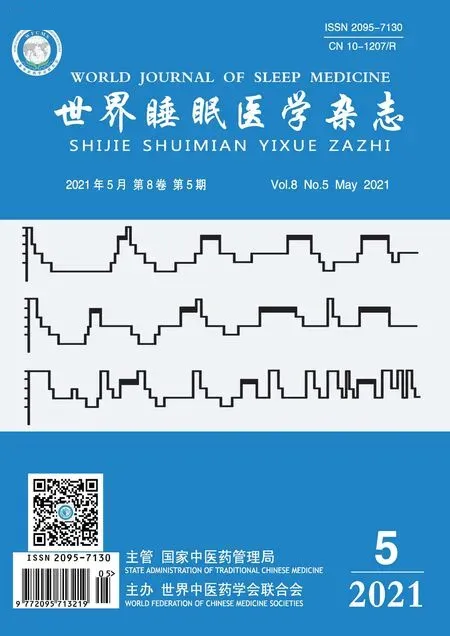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技術研究中醫治療發作性睡病的組方配伍規律
蘇曉艷 王金鳳 呂鑫 顧志榮 宋軍 謝宇平
(1 甘肅省人民醫院睡眠醫學中心,蘭州,730000; 2 甘肅省人民醫院藥劑科,蘭州,730000; 3 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學實驗中心,北京,100700)
發作性睡病(Narcolepsy,NRL)是一種罕見的睡眠障礙,主要表現為不可抗拒的睡眠發作[1]。《睡眠障礙國際分類》第三版(ICSD-3)將其分為:1型發作性睡病(NT1)和2型發作性睡病(NT2)。2種類型共同診斷包括[2]:慢性過度嗜睡持續≥3個月;平均睡眠潛伏期≤8 min,并且有兩個或多個睡眠起始快速眼動期,多次睡眠中的REM期(SOREMP)潛伏期測試(MSLT)(夜間PSG在入睡的15 min內發現SOREMP取代MSLT上的一個SOREMP)。NT1診斷標準還包括出現猝倒和/或腦脊液下丘腦分泌素1(Hypocretin-1,Hcrt-1)濃度降低。NT2標準包括無猝倒;腦脊液中Hcrt-1濃度正常或未測;不能用其他原因(包括藥物治療或停藥的效果)來解釋上述結果。NT1型多青少年起病,發病率約為0.05%[3],病理生理機制主要與遺傳有關,也與腦脊液降鈣素/食欲素缺乏有關[4]。NT2型腦脊液降鈣素/食欲素水平處于中級水平,患病率及確切病理生理機制尚不清楚。目前治療NRL暫無特效藥,主要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對癥治療,如莫達非尼、阿莫達非尼、哌醋甲酯、安非他命,國內市場較小;較新的有羥丁酸鈉和Pitolisant,目前僅在歐洲銷售[2]。且西藥治療NRL療效有限,停藥后易反復、臨床適用范圍小,故越來越多的臨床工作者正在尋求新的中醫治療方法和思路。
中醫認為日間嗜睡主要責之于濕、痰、瘀、虛。濕性粘膩、重濁,濕易困脾,脾陽受困,陽氣虛損,中陽不振,則疲乏無力,嗜臥多眠;痰阻氣機,氣道不通,久病致瘀,痰瘀互結,發為昏撲。治療以益氣補虛,燥濕健脾,化痰祛瘀為主。中醫藥針對病機辨證施治,個體化治療,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癥狀,療效顯著,不良反應小,受到廣大患者的喜愛。但治療思路及用藥卻是不盡相同。數據挖掘技術依托中醫傳承輔助平臺(TCMISS V2.5)構建相關數據庫,全面收集中醫治療NRL的文獻資料,統計文獻所用藥物,對藥物關聯規則及核心藥物組合進行關聯規則、改進的互信息法、復雜系統熵聚類分析,采用無監督的熵層次聚類分析新處方,可探索中醫治療NRL的遣方用藥規律。因此,本研究采用數據挖掘技術對于中醫治療NRL進行研究。以期總結各家治療NRL的用藥規律,進而整理NRL的治療思路及處方,可以指導臨床辨證用藥。
1 資料與方法
1.1 處方來源 檢索國家知識基礎設施數據庫(CNKI)、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CSPD)、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CCD)、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服務系統4各數據庫建庫時間截至2020年8月31日發表的中醫治療NRL的所有文獻。
1.2 文獻檢索與去重 限定“標題或主題詞或關鍵詞”為“發作性睡病”或“Gelineau綜合征”或“NRL”,并且全文包含“中醫”或“方劑”或“復方”或“湯藥”或“中藥”,檢索得到原始文獻。對檢索出的所有文獻采用Endnote X8.2軟件去重。
1.3 處方篩選
1.3.1 納入標準 處方來源于療效分析或病例對照研究;限定處方治療有效率≥70%;診斷、病歷納入與排除標準明確無誤;處方完整,中藥組成、劑量及用法明確無誤;觀察組病例數≥20例。
1.3.2 剔除標準 剔除動物實驗、個案、驗案、綜述、理論探討等來源的處方;剔除病例中合并其他嚴重疾病或并發癥者所用處方;剔除重復發表、同方異名、同方重復報道處方。
1.4 數據錄入 提取納入文獻中的方劑名、藥物組成、劑量、用法等信息,在錄入過程中參考2015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5]規范中藥名稱,如粉甘草、甜草、粉草、國老規范為甘草;芎規范為川芎;云苓、云茯苓規范為茯苓;山菖蒲、水劍草、香菖蒲規范為石菖蒲等。進入“平臺管理系統”→“數據管理”→“方劑管理”→“經驗方”項下,將納入的所有處方以人工“雙錄入”(由1人錄入、另1人核對)模式逐一錄入,完成后進入“數據分析系統”→“方劑分析”功能模塊開展用藥規律挖掘。
1.5 數據挖掘 在“方劑分析”功能模塊下,采用“頻次統計”功能進行用藥頻次分析并導出結果。在“組方規律”功能模塊下,采用關聯規則挖掘組方規律,設定支持度閾值為“≥30%”、置信度為“0.8”,分析常用藥對、藥物組合及用藥關聯規則;采用復雜系統熵聚類,以改進的互信息法的藥物間關聯度分析結果為基礎,設定相關系數為“5”、懲罰系數為“2”分析核心組合。在“新方分析”功能模塊下,在核心組合提取的基礎上采用熵層次聚類法,使用“提取組合”功能分析新組方,得到網絡可視化展示。
2 結果
2.1 用藥頻次分析 共篩選出符合條件的方劑251首,涉及中藥186味,總頻次2 178次,平均每個方劑使用中藥8.7味。其中使用頻次≥20的中藥有33味,排名前5位的依次是茯苓、石菖蒲、甘草、陳皮、白術,使用頻次均超過70次。見表1。依據第十版《中藥學》[6]歸納藥物功效可知,中醫治療NRL的方劑主要由補虛藥(補氣、補血)、解表藥、化濕藥、活血化瘀藥、利水滲濕藥、溫里藥、清熱藥、化痰止咳平喘藥、安神藥等組成,表明這幾類中藥在配伍應用中占有重要位置。

表1 方劑中使用頻次≥20的中藥
2.2 基于關聯規則的組方規律分析 支持度閾值設為≥30%,“置信度”(“A→B”表示當A藥物出現時,B藥物出現的概率至少為80%)設為0.8,共有41條記錄,即41種藥物組合,包含中藥12味。根據藥物組合出現的頻次由高到低列出,排名前5位的組合依次是茯苓-石菖蒲、陳皮-茯苓、陳皮-石菖蒲/白術-茯苓/甘草-茯苓、陳皮-茯苓-石菖蒲、甘草-石菖蒲。見表2。共得到35條用藥規則。見表3。關聯規則的網絡展示見圖1。可知,中醫治療發作性睡病的方劑中,核心藥對及組合之間互相關聯緊密,其中石菖蒲、茯苓、陳皮、半夏等在多個藥物組合中多次出現,因此是關聯網絡的核心。

圖1 關聯規則的網絡展示

表2 方劑中出現頻次≥30的藥物組合

表3 處方中藥物組合的關聯規則
2.3 基于熵聚類的組方規律分析
2.3.1 基于復雜系統熵聚類的藥物間關聯度分析 依據處方數量,結合經驗判斷和不同參數提取數據的預讀,設置相關度為5,懲罰度為2,此時較符合臨床實際。進行熵聚類分析,得到處方中藥對的關聯度,將關聯系數≥0.03的藥對列表,共有41組。見表4。

表4 基于改進的互信息法的藥物間關聯度分析
2.3.2 基于復雜系統熵聚類的核心組合分析 以藥物關聯度分析結果為基礎,設定相關度與懲罰度,點擊“聚類”→“提取組合”按鈕,得到核心組合14個。見表5。核心組合的網絡展示見圖2。

圖2 藥物核心組合的網絡展示

表5 基于復雜系統熵聚類的藥物核心組合
2.3.3 基于無監督熵層次聚類的新處方分析 在以上核心組合提取的基礎上,運用無監督熵層次聚類算法,得到7個潛在的新處方,分別為:熟地黃-山藥-菟絲子-山茱萸-牡丹皮、青黛-金銀花-大青葉-辛夷-太子參、大棗-石菖蒲-生姜-郁金、附子-細辛-桂枝-淫羊藿-厚樸-干姜、佩蘭-藿香-厚樸-淫羊藿-杏仁-草豆蔻、遠志-合歡皮-制何首烏-焦山楂-西洋參、龍膽-大黃-天花粉-羚羊角。新處方的網絡展示見圖3。

圖3 潛在新處方的網絡展示
3 討論
NT2屬于中醫學“嗜睡病”,NT1屬于中醫“厥證”。《靈樞·營衛生會》曰:“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即營衛之行失其常,則晝不精夜不瞑,發為嗜睡。《靈樞·大惑論》云“邪氣留于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于陰而不行,故猝然多臥”,即猝然多臥為營衛失調,陽虛陰盛所致。李東垣[7]《脾胃論·肺之脾胃虛論》中提出:“脾胃之虛,怠惰嗜臥。”《丹溪心法·中濕》指出:“脾胃受濕,沉困無力,怠惰好臥”說明脾虛濕困,蒙蔽清竅,即嗜睡。趙估[8]《圣濟總錄》中云:“膽熱多睡者,膽府清凈,決斷所自出。肝膽俱實,榮衛壅塞,則清凈者濁而擾,故精神昏饋,常欲寢臥也。”說明肝膽濕熱,蒙蔽心神,亦出現嗜睡。結合文獻[9]對NRL的病機歸納,總結NRL的病因病機為情志不暢,飲食不節等致肝郁氣滯,脾虛濕盛,痰濕淤阻,心竅失養,精神昏饋,發為嗜睡。中醫治療NRL目前尚無統一的證型分類。查閱文獻,目前臨床治療NRL多分虛實[10-14],證候主要為脾虛濕盛,肝郁氣滯證,痰蒙心竅證,以及氣虛、陽虛、血瘀、胃熱等;結合本研究對于藥物及組方的分析,NRL主要病性為痰、濕、虛、瘀,主要病位在脾、肝、腎、心、腦。因此主要治療應該疏肝理氣、健脾補虛、化痰祛濕、活血化瘀、開竅醒神。
對文獻251張處方中的藥物進行頻次分析,結果顯示單味藥最常使用的是依次是茯苓、石菖蒲、甘草、陳皮、白術,與之前王雪峰團隊文獻研究結果相近[15],這些中藥均有祛痰之功。本研究得到的候選新方進一步佐證了“主要健脾溫陽化濕,部分清熱活血化瘀”的臨床治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