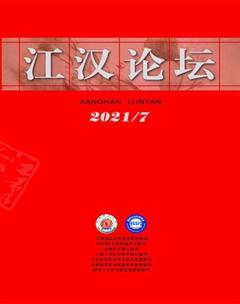唯物史觀何以被遮蔽
趙磊 趙曉磊
摘要:晚近以來,隨著西方經(jīng)濟學(xué)深度嵌入我國經(jīng)濟學(xué)的教學(xué)和研究之中,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地位已然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不從唯物史觀去認識市場經(jīng)濟,不從“存在決定意識”的邏輯去把握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才是導(dǎo)致對市場經(jīng)濟“劍走偏鋒”的認識論根源;用抽象的“公平”“正義”和“道義”來把握分配關(guān)系,這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分配觀,不如說是庸俗經(jīng)濟學(xué)的分配觀。不能撇開“勞資雙方的矛盾”來剖析“社會排斥”和“數(shù)字窮人”,只有最終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才是解決智能社會“新異化”問題的根本路徑。馬克思不會把生產(chǎn)力從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剝離出來單獨研究,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動力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只能在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中得到說明,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實踐范疇科學(xué)地揭示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內(nèi)在機制。如果說《資本論》的研究結(jié)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那么,唯物史觀的“唯物”性質(zhì)在《資本論》中也就無從立足了。
關(guān)鍵詞:唯物史觀;《資本論》研究方法;市場經(jīng)濟;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
中圖分類號:F011? ? 文獻標(biāo)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7-0031-08
如何應(yīng)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分析經(jīng)濟問題并把握經(jīng)濟理論,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學(xué)界也存在著重大分歧。其中有三個理論分歧亟待澄清:其一,分析市場經(jīng)濟應(yīng)當(dāng)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其二,為什么“生產(chǎn)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其三,《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分歧和爭論是推動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力量,若不澄清并祛除由于分歧所導(dǎo)致的對唯物史觀的遮蔽,那么,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努力就只能是南轅北轍了。
一、唯物史觀抑或唯心史觀
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jīng)不是假設(shè),而是科學(xué)地證明了的原理。”① 換言之,唯物史觀不僅是指導(dǎo)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方法論,而且還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工作以及社會實踐,唯物史觀的理論邏輯得到了科學(xué)檢驗。檢驗唯物史觀的偉大成果,就是《資本論》。遺憾的是,在運用唯物史觀來把握經(jīng)濟實踐和經(jīng)濟理論時,有不少學(xué)者展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與“存在決定意識”的邏輯卻并不一致。我們注意到,這種“不一致”在當(dāng)下學(xué)界已然成為普遍現(xiàn)象。
(一)對市場經(jīng)濟的分析
在談到“把握經(jīng)濟學(xué)”的方法論時,韓慶祥先生說:“以往,一些人著重于從經(jīng)濟學(xué)角度認識和理解市場經(jīng)濟,認為市場經(jīng)濟就是追求經(jīng)濟利益和利潤最大化,因而,往往把‘利益看作市場經(jīng)濟之‘道。對市場經(jīng)濟的這種認識和理解是產(chǎn)生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的認識論根源,也是實踐上使市場經(jīng)濟‘劍走偏鋒的認識論根源。”② 我們認為,韓先生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對市場經(jīng)濟的認識是否會出現(xiàn)“劍走偏鋒”,其原因并不在于人們的認識是否“著重于從經(jīng)濟學(xué)角度”,而是在于“經(jīng)濟學(xué)角度”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方法論是基于唯物辯證法的唯物史觀③,唯物史觀之所以“唯物”,就在于它是從社會存在(生產(chǎn)方式和經(jīng)濟基礎(chǔ))的角度去把握市場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目的。馬克思說:“生產(chǎn)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chǎn)方式的絕對規(guī)律。”④ 市場經(jīng)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這并非市場經(jīng)濟在實踐中出現(xiàn)了“劍走偏鋒”,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拜物教)的產(chǎn)生,其認識論根源不是人們誤解了市場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目的,而是市場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目的在人們意識中的必然反映而已。至于如何正確引導(dǎo)、依法管控資本的逐利本性,那是另一個問題。倘若不從唯物史觀視角去認識市場經(jīng)濟,不從“存在決定意識”的邏輯去把握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產(chǎn)生的原因,那才會導(dǎo)致對市場經(jīng)濟“劍走偏鋒”的誤讀。
由于遮蔽了“存在決定意識”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所以韓先生極力主張從“哲學(xué)層面”,即基于“理性自覺”去理解“市場經(jīng)濟之道”,他說:“其實,‘利益并非市場經(jīng)濟的真正之‘道。要真正認識和理解市場經(jīng)濟之‘道,必須進入哲學(xué)層次。如果從哲學(xué)層次來認識和理解市場經(jīng)濟之‘道,那么,市場經(jīng)濟就是追求‘利益—能力—理性—自立四者的有機統(tǒng)一……。我們要追問:獲取經(jīng)濟利益‘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據(jù)是什么?……我們再進一步追問:怎樣才能保證從事經(jīng)濟活動的人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能力?就必須有一種能體現(xiàn)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必須基于人的理性的高度自覺,此可謂‘理性最大化;從事經(jīng)濟活動的人在體現(xiàn)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能力,作出相應(yīng)的業(yè)績或貢獻,從而獲取經(jīng)濟利益和經(jīng)濟利潤的最大化,此可謂‘自立的最大化”。⑤
不難看出,由于韓先生主張的“哲學(xué)層面”與唯物史觀的邏輯已經(jīng)相距甚遠,所以他力圖在市場經(jīng)濟的“社會存在”之外、在市場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方式和經(jīng)濟基礎(chǔ)之外去尋求抽象的“理性最大化”。從抽象的“理性”出發(fā),韓先生進一步追問了分配制度中的公平:“分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一個核心問題,它涉及人的根本利益。如果僅限于經(jīng)濟學(xué)視閾的理解,分配自然首要指向的是經(jīng)濟領(lǐng)域基于‘效率的分配,……這實際上就是經(jīng)濟學(xué)家所講的第一次分配,它體現(xiàn)的是‘實然意義上的基于‘市場中的能力和業(yè)績的‘應(yīng)得性,即比例對等或相對平等,亦即哲學(xué)理念上的‘公平。”⑥ 超越經(jīng)濟學(xué)的“哲學(xué)理念上的公平”,或許是一個令人向往的美好追求目標(biāo),然而在唯物史觀看來,“權(quán)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以及由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⑦;“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chǎn)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jù)說它不公平。”⑧ 所以,從來就不存在超越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公平”,所謂“超越經(jīng)濟學(xué)”的“哲學(xué)理念上的公平”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幻覺罷了。
針對市場經(jīng)濟的貧富懸殊,韓先生說:“政府要基于哲學(xué)理念上的‘正義原則,……對人們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合理調(diào)節(jié)……支撐這三次分配的‘哲學(xué)之道或‘哲學(xué)理念分別是‘公平‘正義和‘道義,三者共同構(gòu)成哲學(xué)意義上的所謂整體性的‘分配結(jié)構(gòu)。”⑨ 調(diào)節(jié)過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是市場經(jīng)濟保持正常運行的題中之義,但是,馬克思絕不會從抽象的“公平”“正義”和“道義”出發(fā)來演繹市場經(jīng)濟的分配原則和分配結(jié)構(gòu)。在《哥達綱領(lǐng)批判》中,馬克思無情地嘲諷了“社會主義宗派分子”力圖超越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公平的”分配觀:“難道資產(chǎn)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xiàn)今的生產(chǎn)方式基礎(chǔ)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jīng)濟關(guān)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diào)節(jié),而不是相反,從經(jīng)濟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出法的關(guān)系嗎?”⑩ 由此可見,從抽象的“正義”理念來演繹市場經(jīng)濟的分配原則,這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分配觀,不如說是庸俗經(jīng)濟學(xué)的分配觀。
在談到“資本”這個范疇時,韓先生強調(diào)“我們所講的‘資本,從根本上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nèi)運作,被合理引導(dǎo)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發(fā)揮積極作用的‘資本,而不是馬克思當(dāng)年所批判的那種具有‘吃人本性的‘資本。”{11} 其實,韓先生的這個觀點并不新鮮。早在21世紀初期,胡培兆先生就撰文說:“在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xué)說中,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特有范疇和統(tǒng)治范疇,是剝削手段,吸血鬼。今天資本范疇已經(jīng)走出社會制度禁區(qū)被普遍使用,它不過是發(fā)達商品經(jīng)濟即市場經(jīng)濟的一般范疇。對資本家的理念也要轉(zhuǎn)變。現(xiàn)代資本家是經(jīng)營資本的專家,和各行各業(yè)一樣,是褒稱。現(xiàn)在世界的財富,主要是由資本家籌資、投資和組織、經(jīng)營、管理創(chuàng)造出來的。沒有他們,哪能有今天這么多企業(yè)和這么多的職工就業(yè)?不能再一言以貶之:‘剝削者。”{12}
在我們看來,與胡培兆先生一樣,韓慶祥先生也是在用道德標(biāo)準(zhǔn)評價資本家。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討論{13}。必須指出:用道德標(biāo)準(zhǔn)來評價資本以及資本家,這與唯物史觀的邏輯背道而馳。資本追不追求剩余價值,存不存在剝削,這只是在表述一個事實,屬于事實判斷;至于資本剝削是善還是惡、是好還是壞,則屬于道德評價范疇。尤其要強調(diào)的是,我們不能把資本的性質(zhì)與資本的功能混為一談。即使要對資本作出道德評價,也應(yīng)當(dāng)與資本在既定發(fā)展階段的具體功能以及人們對這種功能的歷史評價有關(guān),并非如唯心史觀認為的那樣,是出于抽象的“公平和正義”。馬克思在對待資本以及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的時候,從來不主張,也并沒有用道德評價去代替歷史分析。《資本論》的理論邏輯不是道德評價,而是唯物史觀的歷史評價。
(二)對智能社會“新異化”的分析
在分析人工智能發(fā)展將導(dǎo)致人的“新異化”問題時,孫偉平先生憂慮地說:“它比馬克思當(dāng)年揭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勞動異化更不人道。因為它……正在吞噬人作為勞動者的根本”;“‘勞動是幸福的源泉之類基本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當(dāng)智能系統(tǒng)承擔(dān)了越來越多的工作,包括以往被斷定為‘專屬于人類的工作,而人被大量替換下來、變得越來越悠閑時,勞動實踐本身是否專屬于人的本質(zhì)性活動,就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和追問了。”{14}
孫先生把人的休閑活動與“人的本質(zhì)性活動”對立起來,把“人的本質(zhì)性活動”僅僅等同于謀生的體力和腦力工作(馬克思把這種勞動稱之為“直接生產(chǎn)勞動”),我們認為值得商榷。在唯物史觀的邏輯中,勞動價值論并非永恒范疇,而是一個歷史范疇{15}。因為隨著自然力逐漸替代人力,“表現(xiàn)為生產(chǎn)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的勞動時間”{16};“正如隨著大工業(yè)的發(fā)展,大工業(yè)所依據(jù)的基礎(chǔ)——占有他人的勞動時間——不再構(gòu)成或創(chuàng)造財富一樣,隨著大工業(yè)的這種發(fā)展,直接勞動本身不再是生產(chǎn)的基礎(chǔ)”。{17} 總之,隨著自然力逐漸替代人力,直接勞動在財富生產(chǎn)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小,最終不再構(gòu)成創(chuàng)造財富的基礎(chǔ)。
隨著直接勞動在生產(chǎn)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休閑活動在“人的本質(zhì)性活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正如馬克思所說:“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yīng),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chuàng)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shù)、科學(xué)等等方面得到發(fā)展。”{18} “‘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真正的財富,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chǎn)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fā)展開辟廣闊天地。”{19} 從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趨勢看,在人類“直接生產(chǎn)勞動”逐漸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智能社會,休閑活動將日益成為與“人的本質(zhì)性活動”并不沖突的主要活動——我們可以將這種活動稱之為“間接形式的勞動”,亦即馬克思所說的基于休閑時間增長而發(fā)展起來的藝術(shù)和科學(xué)等較高級活動{20}。
在唯物史觀看來,孫先生所憂慮的智能社會日趨嚴重的數(shù)字鴻溝、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等問題,乃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導(dǎo)致勞動異化的必然結(jié)果。遺憾的是,孫先生卻得出了與此并不一致的結(jié)論:“新的實踐將包括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在內(nèi)的一切理論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21} 在討論消除“新異化”的路徑時,孫先生悲觀地說:“智能化的經(jīng)濟和社會體系對‘?dāng)?shù)字窮人的‘社會排斥,以及智能機器人對人的本質(zhì)、人的主體地位的挑戰(zhàn),新型人機關(guān)系和文明形態(tài)的構(gòu)建,都明顯超出了既有理論的視野和‘邊界,甚至不可能在馬克思當(dāng)年所設(shè)想的消滅私有制、實現(xiàn)無產(chǎn)者的解放、消滅階級和國家的層面上徹底解決。”{22} 為什么“新異化”不可能在消滅私有制的層面上得到根本解決呢?孫先生說:“智能化的經(jīng)濟和社會體系將‘?dāng)?shù)字窮人排除在外,這種‘社會排斥將工業(yè)時代勞資雙方的矛盾和對立撇在一邊,導(dǎo)致‘?dāng)?shù)字窮人淪為無人雇傭、喪失勞動價值的‘無用階層,存在變得虛無和荒謬化。”{23} 在我們看來,“導(dǎo)致‘?dāng)?shù)字窮人淪為無人雇傭、喪失勞動價值的‘無用階層”的根源,恰恰在于資本主義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撇開“勞資雙方的矛盾”來談?wù)摗吧鐣懦狻焙汀皵?shù)字窮人”;只有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才是解決智能社會“新異化”的根本路徑。這個路徑所貫穿的唯物史觀邏輯,筆者已有專文討論{24}。
為什么意識不到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的根本作用呢?在我們看來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對智能社會的分析應(yīng)當(dāng)堅持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還是堅持唯心史觀的方法論。雖然孫先生說:“作為一種超越農(nóng)業(yè)社會、工業(yè)社會的先進的技術(shù)社會形態(tài),智能社會與馬克思熱情暢想?yún)s尚未實現(xiàn)的追求人的徹底解放、真正消除異化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具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和一致性”{25},但遺憾的是,這種分析智能社會的邏輯與唯物史觀并沒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和一致性”。孫先生提出的解決“新異化”的設(shè)計理念,其要義并不是他象征性地提到的“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曾經(jīng)設(shè)想的共產(chǎn)主義原理,消滅私有制,讓廣大人民擺脫經(jīng)濟依附和階級統(tǒng)治”,而只能訴諸道德的呼喚,即“對人工智能進行理智的價值評估和必要的道德規(guī)范,基于智能科技興利除弊的選擇性應(yīng)用,通過建構(gòu)以人為本、高度發(fā)達、人機協(xié)同的智能社會,鏟除人工智能異化產(chǎn)生的技術(shù)和社會基礎(chǔ)”;“其目的是使價值、倫理成為制約人工智能研發(fā)、應(yīng)用的內(nèi)在維度,創(chuàng)造能夠通過‘道德圖靈測試的‘道德機器,讓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嚴,理性、友好、富有德性地為人類服務(wù),確保人類(特別是‘?dāng)?shù)字窮人)永遠有資格、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26} 問題是,如果遮蔽了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如果不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解放的根本路徑,那么,依據(jù)“道德規(guī)范”建構(gòu)出來的“道德機器”又何用之有?
二、生產(chǎn)力為什么最革命
對于“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學(xué)界存在著諸多爭議{27}。其中的一個爭議是馬克思究竟有沒有“生產(chǎn)力發(fā)展動力”的理論?相當(dāng)多的學(xué)者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比如,針對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關(guān)于唯物史觀的經(jīng)典表述,安啟念先生認為,“這一表述把全部社會生活的變化歸結(jié)于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但是沒有回答生產(chǎn)力又是怎樣發(fā)展的,其動力從何而來,因而在邏輯上不完整。這個邏輯缺環(huán)事關(guān)重大。” {28} 由此引申出來的困惑是:為什么生產(chǎn)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不少學(xué)者認為唯物史觀對技術(shù)創(chuàng)新并未作出進一步抽象,因而無法回答這個困惑。
就《資本論》的主要內(nèi)容而言,馬克思或許并沒有專門研究“技術(shù)創(chuàng)新”。然而在我們看來,這并不是馬克思的疏忽,而是與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對象有關(guān)。馬克思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yīng)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交換關(guān)系。”{29} 這是唯物史觀的邏輯使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定的生產(chǎn)方式或一定的工業(yè)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lián)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chǎn)力 ;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chǎn)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yè)和交換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研究和探討。”{30} 換言之,只有把生產(chǎn)力置于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聯(lián)系之中來研究,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動力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才能得到辯證的解釋。根據(jù)唯物史觀的邏輯,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體,既不存在離開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生產(chǎn)力,也不存在離開生產(chǎn)力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馬克思絕不會把生產(chǎn)力從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剝離出來單獨研究,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動力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只能在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中得到說明。因此,那種認為馬克思“沒有對技術(shù)創(chuàng)新作進一步抽象”并將其視為唯物史觀缺陷的看法,其實并未真正理解唯物史觀的要義。某些自詡為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局限性而“專門研究”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經(jīng)濟學(xué)理論,其方法論大多或已經(jīng)背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尤其是基于“制度決定技術(shù)”的假設(shè),并用“制度第一性”的邏輯來解釋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制度經(jīng)濟學(xué)”,則更是唯心史觀的典型范式{31}。
令人不解的是,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機制的問題上,安啟念先生將唯物史觀逐出了實證科學(xué)之外,他說:“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以及社會形態(tài)的更替,是對經(jīng)驗事實的總結(jié)概括,是客觀規(guī)律,當(dāng)然屬于科學(xué)。然而一旦提出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機制問題,我們便無法在經(jīng)驗事實中找到現(xiàn)成答案,而必須借助思辨的力量尋找唯物主義的解答。”{32} 換言之,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機制”不可能得到實證科學(xué)的驗證,而只能得到哲學(xué)思辨的證明。為了強調(diào)唯物史觀在分析“生產(chǎn)力發(fā)展動力”問題上所具有的“思辨性”(即“非科學(xué)性”),安先生進一步補充說:“只有當(dāng)提出并著手解答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動力問題時,作為社會科學(xué)的唯物史觀才超出科學(xué)的領(lǐng)域,上升到(或者說回到)思辨的層面,成為哲學(xué)唯物史觀。”{33} 安先生的這個看法值得商榷。事實上,不僅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可以從經(jīng)驗事實得到檢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機制也同樣可以得到經(jīng)驗事實上的證明。比如,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有關(guān)科技發(fā)展的論述中,恩格斯提供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機制的大量經(jīng)驗事實。
在唯物史觀的分析框架中,雖然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不可分割的對立統(tǒng)一體,但“不可分割”并不意味著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地位沒有區(qū)別。在“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這對范疇中,生產(chǎn)力具有“本體”的性質(zhì)。也就是說,相對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而言,生產(chǎn)力具有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要素。對此馬克思指出:“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xiàn)存生產(chǎn)關(guān)系或財產(chǎn)關(guān)系(這只是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guān)系便由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chǎn)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chǎn)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在它的物質(zhì)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34} 在唯物史觀的語境中,生產(chǎn)力的決定作用被定義為:生產(chǎn)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對于生產(chǎn)力的革命性質(zhì),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過相當(dāng)深刻的闡述:“在一切生產(chǎn)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chǎn)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chǎn)生的全部生產(chǎn)力的存在為前提的。”{35} “手推磨產(chǎn)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chǎn)生的是工業(yè)資本家的社會。”{36} “蒸汽、電力和自動紡織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37} “17世紀和 18世紀從事制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tài)發(fā)生革命”。{38} “無產(chǎn)階級是由于工業(yè)革命而產(chǎn)生的,這一革命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發(fā)生于英國,后來,相繼發(fā)生于世界各文明國家。工業(yè)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機械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fā)明而引起的。”{39} 對于生產(chǎn)力的革命性質(zhì),毛澤東也有著更為明確和通俗的解讀:“生產(chǎn)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chǎn)力發(fā)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chǎn)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chuàng)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破壞舊的社會關(guān)系。”{40}
為什么生產(chǎn)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呢?唯物史觀給出的回答是:因為“實踐”。在闡述唯物史觀出發(fā)點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們首先應(yīng)當(dāng)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yōu)榱四軌颉畡?chuàng)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chǎn)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chǎn)物質(zhì)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41}? 在有關(guān)唯物史觀出發(fā)點的論述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追問了“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這是一個關(guān)乎“社會本體論”的問題。從“第一個前提”出發(fā),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diào)物質(zhì)生產(chǎn)(勞動)即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才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所謂“第一個前提”和“第一個歷史活動”,也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本體”。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實踐這個范疇科學(xué)地揭示了生產(chǎn)力演變發(fā)展的內(nèi)在機制。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實踐活動,只要人類必須展開“實踐”,必須進行“活動”,那么為了節(jié)約勞動時間從而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工具的改進、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以及勞動者知識技能的提升,就必然是實踐活動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正如林崗教授和張宇教授所說:“人們在生產(chǎn)過程中必須考慮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問題,必須要對勞動的消耗和勞動的成果進行比較。節(jié)約勞動時間,用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的勞動成果,被馬克思稱作為人類社會首要的經(jīng)濟規(guī)律。……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是人類勞動過程的必然要求,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的普遍規(guī)律,這個規(guī)律不會因為社會制度的變化而消失,改變的只是它的實現(xiàn)方式。因此,社會生產(chǎn)力由低到高的發(fā)展具有必然性。”{42} 我們不能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就把實踐活動解釋成唯心的范疇。在實踐活動中,意識并不是第一性的、先在的東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離開了意識賴以存在的物質(zhì)肉體,離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環(huán)境,意識什么都不是。因此,唯物史觀把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終極動力歸結(jié)于實踐,是對唯心史觀把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動力歸結(jié)于人的“理性”“意識”和“智慧”的徹底否定;馬克思的“實踐”與唯心史觀所鐘情的“知識發(fā)展”“人類智慧”“個人理性”等{43} 顯然不是一個層面的范疇——盡管它們之間有著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生產(chǎn)力的革命性質(zhì),“技術(shù)自主論”也給出了理論上的論證。“技術(shù)自主論”也稱“技術(shù)自主性理論”,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國技術(shù)哲學(xué)家埃呂爾和美國技術(shù)哲學(xué)家蘭登·溫納。技術(shù)自主論認為,“技術(shù)最終依賴于自身,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趨于封閉和自我決定的有機體。技術(shù)自主性強調(diào)其主導(dǎo)力量是技術(shù)的內(nèi)在邏輯。”{44} 這個邏輯也被稱為技術(shù)的“相對自主性”。埃呂爾從技術(shù)系統(tǒng)的自增性、技術(shù)前進的自動性和技術(shù)發(fā)展的無目標(biāo)性相互交織的三個方面,對技術(shù)自主性進行了分析;蘭登·溫納提出了“技術(shù)命令”的概念,力圖揭示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及其形成的外在要求{45}。在技術(shù)自主論看來,“技術(shù)增長路線的確立是自動的,技術(shù)的增長路線是由技術(shù)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所決定的,技術(shù)發(fā)展定向是純粹的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內(nèi)部事務(wù)”,因此,“人在這個具體化過程中已不再是發(fā)明者,而是操縱者;或者說,如果人仍然扮演發(fā)明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員一樣聽從物體本身提供的臺詞,遵循物質(zhì)的念白”,比如,“四級管的發(fā)明是三極管的內(nèi)在必然,技術(shù)具有對自身起源的自主性。”{46}
技術(shù)自主論無視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作用,這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們將技術(shù)的“相對自主性”置于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對立統(tǒng)一中來考察,那么,對于唯物地理解“生產(chǎn)力最革命”的原因,技術(shù)自主論還是具有啟發(fā)意義的。生產(chǎn)力及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相對自主性”(當(dāng)然這種自主性不可能游離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外),人類只能盡力去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的“相對自主性”邏輯,從而不斷變革生產(chǎn)關(guān)系以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這就是生產(chǎn)力之所以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的根源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生產(chǎn)力的演化歷史中,人的主觀意志所具有的功能與其說是“發(fā)明者”,不如說是“順應(yīng)者”和“利用者”;在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機制中,人的主觀意志所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導(dǎo)演”,不如說是“演員”。在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中,技術(shù)與科學(xué)同屬于生產(chǎn)力的范疇,都是制約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決定性因素。技術(shù)與科學(xué)當(dāng)然有區(qū)別(技術(shù)屬于“操作”層面的生產(chǎn)力,科學(xué)屬于“理論”層面的生產(chǎn)力),然而與技術(shù)一樣,科學(xué)也有著不斷發(fā)展的內(nèi)在必然性。“技術(shù)自主論”似乎并未討論科學(xué)的“相對自主性”問題,不過從其對技術(shù)自主性的分析邏輯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結(jié)論:科學(xué)發(fā)展的趨勢和方向仍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必然性。在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歷史中,雖然科技往往有著依賴于靈感而“突變”的演化特征,但是科技的發(fā)展以及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機制,本質(zhì)上都是一個基于實踐活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演化過程。晚近以來,不少學(xué)者試圖用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相互作用的所謂“二元論”來抹殺生產(chǎn)力的決定作用。由于這種“二元論”遮蔽了唯物史觀“存在決定意識”的邏輯,故而衍生出一系列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必然性的唯心史觀的論點。在我們看來,唯物史觀之所以堅信歷史具有必然性,就是因為在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理論框架中,生產(chǎn)力發(fā)展所具有的“相對自主性”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
三、《資本論》研究方法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
學(xué)界對《資本論》研究方法的誤讀,是唯物史觀被遮蔽的又一典型表現(xiàn)。雖然馬克思對《資本論》研究方法有過專門說明,但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到底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演繹法,還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歸納法,學(xué)界一直存在著認識分歧。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前輩巫繼學(xué)先生斷言,《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歸納法,而是演繹法。他說:“馬克思正是在對17世紀經(jīng)濟學(xué)家走過的這條迷惘、錯誤道路的批判上,確定了正確的研究方法:從抽象到具體。”{47} 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就是“演繹法”,把演繹法作為《資本論》研究方法,這個觀點不僅在經(jīng)濟學(xué)界廣泛存在,而且在非經(jīng)濟學(xué)界也廣泛存在。比如,中國著名數(shù)學(xué)家、馬克思《數(shù)學(xué)手稿》主要譯者、北京大學(xué)教授江澤涵在讀了《資本論》第1卷之后說:“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方法同我們研究數(shù)學(xué)的方法是一樣的,《資本論》的論證方法同我們的數(shù)學(xué)論證方法一樣,都是嚴密地從邏輯上一步步推理和展開,真是無懈可擊,令人信服。”{48} 在很多人眼里,《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數(shù)學(xué)的論證方法一樣,都是邏輯演繹的過程,即從抽象范疇到具體結(jié)論的推導(dǎo)過程。換言之,《資本論》是馬克思“憑空演繹”出來的。問題是,如果《資本論》的結(jié)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方法論的唯物史觀,其“唯物”的性質(zhì)在《資本論》中又何以立足?
把《資本論》的研究方法界定為演繹法,其原因既與《資本論》的敘述方法有關(guān){49},也與馬克思關(guān)于《資本論》研究方法的一段論述有關(guān)。在談到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方法時,馬克思說:“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xiàn)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jīng)濟學(xué)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chǎn)行為的基礎(chǔ)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50} 馬克思這里講的“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即歸納過程。這既是典型的實證方法,也充分展示了唯物史觀的“唯物”性質(zhì){51}。問題在于,如果說《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實證的歸納法,那么,為什么馬克思又說這種“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歸納法“似乎是正確的”而其實“是錯誤的”呢?正是馬克思的這句話,令很多人困惑不已,以至于學(xué)界普遍認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具有思辨性的“演繹法”,而并不是具有實證性的“歸納法”。其實,馬克思說“這是錯誤的”,并不是指“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xiàn)實的前提開始”的研究方法是錯誤的,而是指“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敘述方法是“錯誤的”。換言之,馬克思說的“錯誤”指的是把“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歸納法當(dāng)作“敘述方法”來運用了,而并不是說歸納法作為“研究方法”是錯誤的。對此,馬克思在后面補充說:“第一條道路是經(jīng)濟學(xué)在它產(chǎn)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17世紀的經(jīng)濟學(xué)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guān)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52} 也就是說,把歸納的“研究方法”當(dāng)作“敘述方法”來運用,即“從實在和具體開始”敘述,這正是17世紀的經(jīng)濟學(xué)家的錯誤所在。
馬克思強調(diào)“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歸納法不是正確的“敘述方法”,而是正確的“研究方法”。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關(guān)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guī)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guī)定。”{53} 所謂“從人口著手”以及“從表象中的具體”出發(fā),指的是歸納或抽象的起點;所謂“越來越稀薄的抽象”,指的是歸納過程或抽象過程(這個過程是“研究過程”而并不是“敘述過程”);所謂“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guī)定”,指的是歸納或抽象之后的結(jié)論。在“越來越稀薄的抽象”完成之后,馬克思緊接著說:“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guān)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guī)定和關(guān)系的豐富的總體了。”{54} 所謂“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指的是《資本論》的敘述過程。問題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這個“那里”指的是哪里呢?顯然,這個“那里”指的是“越來越稀薄的抽象”之后的“一些最簡單的規(guī)定”,即“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這些抽象范疇。《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就是從“最簡單的規(guī)定”(即抽象范疇)開始的,而并不是從實實在在的“人口”(即具體現(xiàn)象)開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隨后的一段論述中,馬克思寫下了極易引起歧義的一段話:“后一種顯然是科學(xué)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guī)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xiàn)為綜合的過程,表現(xiàn)為結(jié)果,而不是表現(xiàn)為起點,雖然它是現(xiàn)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fā)為抽象的規(guī)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行程中導(dǎo)致具體的再現(xiàn)。”{55} 問題在于,馬克思所說的“后一種顯然是科學(xué)上正確的方法”,這“后一種”是哪一種呢?要知道“后一種”指的是哪一種,就必須厘清馬克思在這句話之前的相關(guān)論述。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是這樣說的:“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一個關(guān)于整體的混沌的表象,并且經(jīng)過更切近的規(guī)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guī)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guān)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guī)定和關(guān)系的豐富的總體了。”{56} 馬克思的這段話講了兩層意思:(1)從人口這個具體表象入手,“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guī)定”。這個抽象過程就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2)從最簡單的規(guī)定出發(fā),“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這個“回過頭來”的過程就是《資本論》的敘述過程,《資本論》的敘述過程所運用的方法就是演繹法。
可見,馬克思說“后一種顯然是科學(xué)上正確的方法”,這“后一種”指的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歸納法)和“從抽象再到具體”的敘述方法(演繹法),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說,“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加上“從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法,這“兩條道路”所構(gòu)成的“后一種”方法才是科學(xué)上正確的方法!{57} 正因為如此,在“后一種顯然是科學(xué)上正確的方法”這段論述中,馬克思特別強調(diào)了“兩條道路”各自的功能:“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fā)為抽象的規(guī)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行程中導(dǎo)致具體的再現(xiàn)。”{58} 什么是“蒸發(fā)”?蒸發(fā)就是“抽象”,就是“研究”;什么是“再現(xiàn)”?再現(xiàn)就是“表達”,就是“敘述”。馬克思在談到《資本論》敘述過程的起點時說:“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xiàn)為綜合的過程,表現(xiàn)為結(jié)果,而不是表現(xiàn)為起點,雖然它是現(xiàn)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59} 這里的“它”,指的是《資本論》中的抽象范疇(比如“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這句話有三層含義:其一,作為《資本論》敘述過程起點的抽象范疇,它是思維的結(jié)果,但并不是思維的起點,即并不是“研究起點”;其二,雖然抽象范疇并不是研究起點(研究起點是大量的具體表象——比如生產(chǎn)價格、地租、利潤和利息等等),但它卻是敘述起點,即“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其三,抽象范疇不僅是《資本論》的敘述起點,也是資本主義真實歷史的起點,即資本主義“現(xiàn)實的起點”。比如在《資本論》第1卷中,商品這個范疇雖然是一種抽象規(guī)定,但這個抽象的商品范疇正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歷史起點。所以,馬克思辯證地指出商品范疇“是現(xiàn)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由此可見,認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演繹法的學(xué)者,顯然是誤把《資本論》的敘述方法當(dāng)成了《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我們之所以必須澄清這種誤讀,之所以必須強調(diào)《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不是演繹法而是歸納法,其問題導(dǎo)向在于:如果《資本論》的研究方法離開了經(jīng)驗歸納和實踐檢驗,如果《資本論》的研究結(jié)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那么,唯物史觀的“唯物”性質(zhì)在《資本論》中又將何以立足呢?
注釋:
①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②⑤⑥⑨{11} 韓慶祥:《以哲學(xué)把握經(jīng)濟的基本方式》,《哲學(xué)研究》2020年第11期。
③{49} 趙磊:《“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論意蘊——基于〈資本論〉的方法論》,《政治經(jīng)濟學(xué)評論》2018年第6期。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頁。
⑦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361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頁。
{12} 胡培兆:《從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重視角看〈資本論〉——紀念〈資本論〉出版140周年》,《中國經(jīng)濟問題》2007年第7期。
{13} 趙磊:《為〈資本論〉一辯——與胡培兆先生商榷》,《當(dāng)代經(jīng)濟研究》2008年第6期。
{14}{21}{22}{23}{25}{26} 孫偉平:《人工智能與人的“新異化”》,《中國社會科學(xué)》2020年第12期。
{15}{20} 趙磊:《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學(xué)術(shù)月刊》2005年第4期;趙磊:《“勞動決定價值”是勞動異化的結(jié)果》,《學(xué)術(shù)月刊》2019年第12期。
{16}{17}{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4—105、101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 281 頁。
{24} 趙磊、趙曉磊:《世界處在巨變的前夜——一個馬克思主義觀察視角》,《江漢論壇》2017年第1期。
{27} 孟捷、趙磊:《生產(chǎn)力一元決定論的超越與辯護——關(guān)于〈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對話》,《天府新論》2017年第4期。
{28}{32}{33} 安啟念:《關(guān)于唯物史觀的“經(jīng)典表述”問題》,《社會科學(xué)輯刊》2010年第2期。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30}{35}{36}{39}{4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655、602、676、531頁。
{31} 趙磊:《經(jīng)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制度抑或技術(shù)?》,《哲學(xué)研究》1997年第10期。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頁。
{40}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9頁。
{42} 林崗、張宇:《生產(chǎn)力概念的深化與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發(fā)展》,《教學(xué)與研究》2003年第9期。
{43} 趙磊:《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的得與失——與孟捷教授商榷》,《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報》2017年第2期。
{44}{46} 吳國林:《量子技術(shù)哲學(xué)》,華南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頁。
{45} 梅其君:《技術(shù)何以自主——技術(shù)自主論批判》,《東岳論叢》2009年第5期。
{47} 巫繼學(xué):《世紀末議〈資本論〉的方法論》,《學(xué)術(shù)月刊》1995年第6期。
{48} 孫小禮:《馬克思的數(shù)學(xué)手稿:寶貴的歷史文獻》,《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第2期。
{5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
{51} 趙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何以“實證”》,《政治經(jīng)濟學(xué)評論》2020年第1期。
{52}{53}{54}{55}{56}{58}{5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5、24、25、25頁。
{57} 有人據(jù)此用“科學(xué)抽象法”來定義馬克思所說的這“兩條道路”,并把《資本論》的方法定義為“科學(xué)抽象法”。我們認為把《資本論》的方法統(tǒng)稱為“科學(xué)抽象法”未嘗不可,但必須指出“科學(xué)抽象法”實際上包含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而并非僅指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趙磊,西南財經(jīng)大學(xué)《財經(jīng)科學(xué)》編輯部常務(wù)副主編、博士生導(dǎo)師,四川成都,610071;趙曉磊,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xué)凱瑞商學(xué)院,亞利桑那菲尼克斯,85281。
(責(zé)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