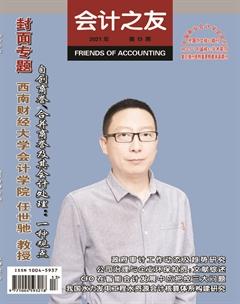自創(chuàng)商譽、合并商譽及其會計處理:一種觀點
任世馳



【關鍵詞】 自創(chuàng)商譽; 合并商譽; 企業(yè)并購價格; 商譽會計方法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1)13-0002-09
始自2018年末中國證券市場的“商譽風暴”,不僅成為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中一個諱莫如深的“雷區(qū)”,同時也掀起了我國商譽會計爭論的熱潮。事實上,商譽會計一直是困擾國際會計理論與實務界的“世紀難題”,自19世紀末商譽進入會計視野以來,對于商譽會計的多種處理方法一直存在分歧;近20年來,隨著商譽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向減值測試法的統(tǒng)一,以及由于商譽減值測試法暴露出來的諸多缺陷,商譽會計的國際分歧更加明顯,并且成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修訂)中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
從經濟學和會計基本理論的角度來看,商譽會計存在著一些基礎性或者常識性的理解錯誤(悖論)。本文嘗試從基礎理論出發(fā),重新分析認識商譽,對于準確把握商譽本質及恰當修訂商譽會計準則,不無裨益。
本文首先從不同學科對商譽的認識進行討論,然后結合微觀經濟學理論(企業(yè)理論)分析“自創(chuàng)商譽”不予確認的原因,再從會計基礎理論角度討論合并商譽會計中存在的常識性認識誤區(qū),進而從合并商譽來源角度分析合并商譽性質,最后以合并商譽性質為基礎討論合并商譽會計處理方法的恰當選擇。
一、什么是商譽——不同學科中的商譽概念
“商譽”一詞在學界和實踐中被普遍使用,但其含義各不相同。根據英國會計學家P.D.Leake[1]的研究,“商譽”一詞最早是一個法律用語,出現(xiàn)在1571年英格蘭人的遺囑中:“……我把采石場的全部利益和商譽……都給了約翰·斯蒂文”;此后,商譽又被稱為“商譽權”,其含義類似專享權或者專屬權,大多使用于法律判例中。
經濟學者對商譽的認識,在形式上又有不同。經濟學家王則柯[2]曾說,商譽就是市場信譽,“商譽是保證的一種形式”,良好的商譽(信譽)不僅能夠激勵公司或廠商提供優(yōu)質商品,而且還是市場競爭中的一種“進入障礙”,對公司或廠商(在多次博弈中)保持或獲取長遠利益至關重要;而“商譽受損時會失去一些東西。這些‘東西首先就是利潤”[3]。這種對商譽的認識,側重強調企業(yè)誠信對持續(xù)經營和長遠獲利的重要性。
營銷學中不提商譽概念,與之類似的是“品牌”概念。營銷學中將“品牌”定義為“名稱、術語、標志、符號或設計,或者是它們的結合體,用以識別銷售商的產品或服務,并使其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區(qū)分開”,并且認為品牌是一種資產,“品牌資產是向產品或服務賦予的附加價值”,它“來自消費者反應的差異”,而品牌的價值可以歸結為品牌自身未來預期收益的凈現(xiàn)值,這與會計中將商譽歸結為預期未來超額收益的凈現(xiàn)值是相似的。營銷學還進一步將品牌資產和“顧客資產”聯(lián)系起來,認為二者“有很多共同主題”,“品牌(的價值)離不開顧客,顧客也少不了品牌”[3]。就如會計中不能確認“顧客資產”一樣,營銷學中的所謂品牌“資產”與會計學中的資產不是同一個概念。
商譽概念最廣泛而且普遍地運用于會計領域。會計中對商譽性質的認識,先后形成了“好感(或善意)價值觀”“無形資源觀”“總計價賬戶觀”“協(xié)同效應觀”“商譽動量觀”等多種觀點,E. S. Hendriksen[4]曾對上述觀點進行總結,并概括為“超額收益觀”“總計價賬戶觀”“好感價值觀”,稱為商譽的“三元理論”。
楊汝梅[5]曾說,“商譽足以影響于賣價者端,在同業(yè)者有競爭之時,蓋商譽之功用,能使消費者工人及投資者,對某一企業(yè)家或其所經營之事業(yè)減少疑慮而發(fā)信仰之心,……于是種種特殊利益遂得由是而生,而其營業(yè)得較其他同業(yè)為發(fā)達焉”,所謂“減少疑慮而發(fā)信仰之心”,與經濟學家眼中的“企業(yè)市場信譽”或者營銷學者眼中的企業(yè)品牌類似,就是會計中所謂商譽的“好感”;而這種“好感”影響了賣價,使“在看重商譽的市場中,競爭不會導致價格下降”[2],“遂得由是而生”的“種種特殊利益”,就是會計中所謂商譽的“超額收益”。而會計準則將商譽(專指合并商譽)定義為“購買方的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6],實際上就是“總計價賬戶觀”的直接表現(xiàn)(購買方長期股權投資賬戶,即購買方支付的并購價格與被并企業(yè)凈資產賬戶之間的差額)。因此,商譽會計的“三元理論”,某種程度上存在這樣的關系:商譽是客戶對企業(yè)的好感價值,它使客戶愿意給出更高的價格,從而使企業(yè)獲取超過同業(yè)的“超額收益”;這個好感的價值就是“總計價賬戶”之間的差額。因此,會計理論中一般又將商譽與企業(yè)超額收益聯(lián)系起來,認為企業(yè)的商譽是“企業(yè)相對于同行業(yè)其他企業(yè)的超額盈利能力,是企業(yè)的一項不可辨認資產”[7]。
二、經濟學理論中的超額利潤——從會計為什么不能確認企業(yè)自創(chuàng)商譽談起
商譽問題幾乎從來就是和企業(yè)超額利潤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那么,經濟學理論(主要是企業(yè)理論)是如何認識企業(yè)超額利潤的呢?
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yè)理論將企業(yè)視作一個生產函數,行業(yè)內所有企業(yè)都被假設為同質性的,是行為完全相同的最優(yōu)化的專業(yè)生產者;在長期均衡狀態(tài)下,行業(yè)內所有企業(yè)的利潤均為零(筆者注:此處的利潤指超額利潤或經濟租金,意即所有企業(yè)都只能獲取行業(yè)平均利潤,不存在超額利潤);但是,現(xiàn)實中企業(yè)之間不僅存在超額利潤,而且存在持續(xù)的利潤差距[8]。新古典經濟學認為,這種持續(xù)的利潤差距,來自企業(yè)面臨的不同經營風險[9]或者外在市場結構的不完全性[10]。因此,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眼中,企業(yè)超額利潤不是商譽帶來的,而是企業(yè)經營風險差異或者外部市場結構不完全性的產物。
現(xiàn)代企業(yè)理論認為,企業(yè)超額利潤的最主要來源,是企業(yè)因內生資源稟賦不同而以更具效率和效能的方式來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這種能力上的差異帶來企業(yè)利潤的差異[11]。其中,資源基礎理論認為,能使企業(yè)獲得并保持卓越績效的根源是該企業(yè)已控的、獨特的資源束[12];企業(yè)成長理論則認為,企業(yè)所控制的、包括企業(yè)家才能在內的廣義的生產性資源束有顯著差異,同行業(yè)的企業(yè)本質上是異質的;企業(yè)資源的不同使用或者用以提供不同服務(資源的異質性),是企業(yè)利潤差異性和超額利潤的根源[1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會計著力將超額利潤歸結于“商譽資產”并進行會計反映不同,企業(yè)理論并不認為帶來超額利潤的這些內生資源稟賦需要進行單獨計量和反映。恰恰相反,資源基礎理論認為,“(無形)資源本身并沒有任何價值,僅當其用于實施戰(zhàn)略的時候才能創(chuàng)造價值”[14];企業(yè)成長理論也認為,企業(yè)異質性或者資產異質性并不體現(xiàn)在企業(yè)所控制資源的價值差異,而是體現(xiàn)在資源所提供服務的不同(即企業(yè)資源或資產的異質性),從而帶來不同的產出效果[13]。用更加直白的表述,并不是不同企業(yè)資產數量或資產價值不同帶來了企業(yè)的超額利潤,而是同樣的資產在不同企業(yè)的異質性配置和使用,帶來了企業(yè)之間的利潤差距(超額利潤)。無論新古典經濟學將企業(yè)超額利潤歸結為同質性企業(yè)之間經營風險差異或者外部市場結構不完全性,還是現(xiàn)代企業(yè)理論認為企業(yè)資源稟賦不同帶來效率與效能差異,進而形成企業(yè)超額利潤,它們都不承認企業(yè)“商譽資產”的存在,這就是“自創(chuàng)商譽”不能進行會計確認的經濟學根源。
從會計基礎理論來看,“商譽”會計的誤區(qū)源自對資產與利潤關系的誤解。第一,會計將資產定義為“企業(yè)過去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由企業(yè)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yè)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15]。資產能夠給企業(yè)帶來經濟利益,是一個“充分條件”;但是,會計卻慣性地將“資產帶來收益”等同于有一份收益就應有一份資產與之相對應,從而把“充分條件”不自覺地理解為“充要條件”,因此要為企業(yè)超額收益尋找它的資產來源;第二,在這種慣性思維中,資產帶來的收益,又被進一步理解為平均收益;企業(yè)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獲取平均收益以后,超過這部分平均收益以上的收益(超額收益),無法用既有的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來解釋,那就將其歸屬于人為設定的不可辨認“無形資產”——“商譽”,“商譽”無形資產就這樣產生了。
經濟學理論不承認商譽與會計慣性思維下確認商譽兩種情形下的企業(yè)總資產和利潤,可以分別表述為:
(1)經濟學理論不承認商譽情形下的企業(yè)總資產與利潤
企業(yè)總資產=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
企業(yè)利潤=(企業(yè)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企業(yè)利潤率
在這里,企業(yè)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的異質性使用,形成不同企業(yè)的不同利潤率水平和不同超額利潤。
(2)會計慣性思維確認“商譽”情形下的企業(yè)總資產與利潤
企業(yè)總資產=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不可辨認無形資產(商譽)
企業(yè)利潤=(有形資產+可辨認無形資產+不可辨認無形資產(商譽))×行業(yè)平均利潤率
在這種情形下,企業(yè)所有資產都獲取行業(yè)平均利潤,任何企業(yè)都沒有超額利潤存在。因為只要存在超過有形資產與可辨認無形資產平均利潤以上的那部分利潤(超額利潤),會計就人為地設定“商譽”資產,作為該超額利潤的產生來源。有多少超額利潤,就相應增加多少“商譽”資產;增加“商譽”資產后的企業(yè)總資產,就始終獲取行業(yè)平均利潤。
三、合并商譽會計:準則變遷與理論上的根本問題
(一)合并商譽會計準則變遷
會計中真正付諸實施的,是合并商譽會計。早期的合并商譽會計,始自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于1944年發(fā)布的《第24號會計研究公報——無形資產》(ARS No.24:Intangible Assets),其中對合并商譽及其會計處理做出了詳細規(guī)定:
全部商譽以使用期限為標準,分為A類商譽和B類商譽。A類商譽為使用年限有限的商譽,其成本在估計的使用年限內攤銷計入損益;B類商譽為使用年限無限的商譽,可以永久保留在賬上;但有證據表明B類商譽使用年限已受到限制時,應在剩余使用年限內攤銷;或當有證據表明B類商譽已完全貶值,則在當年全部注銷。
ARS No.24實際上允許商譽處理采用攤銷法、永久保留法和當期注銷法,企業(yè)可以根據合并商譽的特征選擇使用不同的處理方法。
1953年,CAP發(fā)布《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對第1至42號會計研究公報的重新闡述和修訂》,其中商譽部分對B類商譽的處理進行了大幅修改,取消了當期注銷法,同時對永久保留法進行修訂,只要企業(yè)認為B類商譽不是在整個經營周期內發(fā)揮作用,也可以系統(tǒng)攤銷,計入當期損益。
1970年,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發(fā)布《第16號會計原則委員會意見書——企業(yè)合并》(APB Opinion No.16:Business Combinations)和《第17號會計原則委員會意見書——無形資產》(APB Opinion No.17:Intangible Assets),規(guī)定企業(yè)合并可以采用權益聯(lián)合法和購買法進行會計處理,購買法下確認的合并商譽應在不少于40年內攤銷。
這一時期,不同國家的合并商譽會計處理方法各不相同。比如英國推薦在取得合并時對合并商譽采用一次性沖減所有者權益(當期注銷法)的方法;日本稅法則允許企業(yè)合并商譽可以在合并后的5年內分期攤銷。美國認為,美國規(guī)定的合并商譽40年攤銷,導致商譽對合并后的企業(yè)收益產生了長期影響,從而使美國企業(yè)在并購中不敢出價,因此在并購市場上總是處于不利地位。為了消除合并商譽對并購企業(yè)利潤的長期影響,2001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fā)布《第141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企業(yè)合并》(SFAS No.141:Business Combinations)和《第142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SFAS No.142: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s),規(guī)定企業(yè)合并商譽不再使用系統(tǒng)攤銷法,而采用減值測試法,每期末(計量日)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減值的那部分商譽價值計入當期損失,增值不予確認。
受美國商譽會計準則修訂的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2004年發(fā)布《IFRS 3:企業(yè)合并》(取代原來的《IAS 22:企業(yè)合并》),并于2008年再次對《IFRS 3:企業(yè)合并》進行修訂,全面與美國商譽會計趨同。IFRS實施后,IASB開展了實施后評價,各方爭議很大。2018年IASB發(fā)布的《會計準則咨詢論壇第8號議程文件:商譽及減值》和2020年發(fā)布的《企業(yè)合并——披露、商譽及其減值(討論稿)》(IFRs Standards Discussion Paper:Business Combinations-Disclosures,Go-
odwill and Impairment)中,IASB繼續(xù)堅持減值測試法,認為不應重新引入商譽攤銷,但留出了改進的空間:一是應簡化商譽減值測試方法,并提供更多有關收購及其后續(xù)業(yè)績的信息;二是歡迎利益相關者就攤銷法提出新證據或新論據。
財政部1995年發(fā)布《合并企業(yè)會計報表暫行規(guī)定》(財會字〔1995〕11號),要求對企業(yè)并購支付的買價與所取得股權份額價值之間的差額,作為“合并價差”,列作“長期投資”項目的調整項目。2001年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CASC)發(fā)布的《企業(yè)會計準則——投資》,曾將權益法下的初始投資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作為“股權投資差額”,要求在規(guī)定的投資期限內攤銷;沒有規(guī)定投資期限的,在不超過10年內攤銷。2006年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CASC)發(fā)布的《企業(yè)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yè)合并》規(guī)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yè)吸收合并中,并購成本大于被并購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以及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中,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成本大于所取得持股比例對應享有的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金額,應確認為合并商譽;合并商譽至少應當在每年年終進行減值測試。至此,我國商譽會計實現(xiàn)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全面趨同。
合并商譽會計準則的邏輯基礎和發(fā)展脈絡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將商譽看作一種資產,逐漸成為商譽會計的“共識”和制定商譽會計準則的基礎;二是對商譽的會計處理,逐漸演變?yōu)閿備N法和減值測試法之爭,而近20年來,減值測試法已成為主流的方法。
(二)合并商譽會計:理論上的根本問題
合并商譽出現(xiàn)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yè)合并中。從會計準則對合并商譽的界定來看,“購買方對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應當確認為商譽”,合并商譽是企業(yè)合并中形成的“合并價差”;對這個“合并價差”的認識,涉及到會計中的資產界定與計價這樣的會計基礎理論問題,進一步還涉及到商品價值構成與交易價格確定問題。
不妨從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yè)合并過程和企業(yè)合并后的合并報表談起(本例中假定A企業(yè)100%并購B企業(yè))。
非同一控制下,企業(yè)合并前,被并B企業(yè)獨立于企業(yè)集團而自行設立。B企業(yè)購建資產、聘任員工、確定商業(yè)模式、組織生產經營,成為一個生產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獨立“資產組或者資產組組合”(類似于《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所稱“現(xiàn)金產出單元”),意指產生的現(xiàn)金流入能夠基本上獨立于其他資產或資產組的、可以認定的最小資產組合[16]。如圖1。

假定企業(yè)集團中A企業(yè)并購集團外的B企業(yè)100%股權。在合并過程中,無論立足A企業(yè)還是立足集團公司來看,都是將B企業(yè)進行整體估值,當作一項組合資產整體購入。如圖2。

但是,在并購后的合并報表中,又回到了會計慣性思維,認為B企業(yè)也是由一項項單獨的資產構成,因此,合并報表應重新將B企業(yè)分拆為一項項單項資產分別進行計價、反映。這就帶來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資產邊界問題——究竟應該將B企業(yè)作為一項整體資產計價、反映,還是應該分拆為一項項單項資產計價、反映。遵照會計反映的“交易觀”,會計應該以“交易或事項形成的”“交易價格”,對“取得的資產”進行計價、反映。在企業(yè)合并交易中,無論站在A企業(yè)(合并時的會計主體)還是站在集團公司(合并報表會計主體)立場,交易“取得的資產”歸被并企業(yè),“交易形成的”“交易價格”是被并企業(yè)的價格;即被并企業(yè)始終是作為不可分割的單一、整體交易對象(“現(xiàn)金產出單元”或組合資產)、從會計主體外部購入;交易價格是被并企業(yè)(“現(xiàn)金產出單元”或組合資產)這一整體資產的價格。或者更深入地說,在企業(yè)并購交易中,購買方并不是購買被并企業(yè)的一項項資產(如果僅僅著眼于購買一項項資產,主并方完全可以在商品市場上完成,企業(yè)并購就沒有發(fā)生的必要),而是著眼于購買被并企業(yè);并沒有“交易或事項形成”B企業(yè)各項資產的價格,而是“交易或事項形成”B企業(yè)的價格;但是,合并報表“為了反映母公司整體財務狀況”,卻舍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B企業(yè)這一整體資產(“現(xiàn)金產出單元”或組合資產)的交易價格,而把交易對象B企業(yè)進行分拆,按B企業(yè)內部各單項資產的價值進行計價、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B企業(yè)的資產價格是B企業(yè)交易取得資產時的價格,而不是A企業(yè)或者母公司合并取得這些資產的價格)。那么,在會計中,是否不論何種情形都應該以單項資產作為被計量和反映的資產“單元”,而不考慮“交易和事項形成的”交易對象究竟是單項資產,還是組合資產?或者說,應該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資產的定義?
第二,企業(yè)整體價值是否等于組成企業(yè)的各單項資產價值之和(為方便,假定被并企業(yè)負債為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根據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商品價值(W)由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三個部分構成,即W=C+V+M。其中,不變資本(C)是生產中投入的物化勞動的價值,如固定資產、原材料、燃料等;可變資本(V)是生產中投入的活勞動的價值,如生產工人工資;剩余價值(M)是由活勞動創(chuàng)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如果把被并購企業(yè)看作一項交易商品,那么,遵循剩余價值理論,被并購企業(yè)的價值W是由被并購企業(yè)組建時投入的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期待獲取的剩余價值(M)構成,即(C+V+M)構成了被并購企業(yè)的價值;而被并購企業(yè)中各單項資產的價值,僅約略相當于組建被并購企業(yè)時投入的不變資本(C),如固定資產、原材料等有形資產和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的投入,(V+M)部分——即被并購企業(yè)組建中投入的可變資本如開辦費和期待獲取的剩余價值,并不包含在被并購企業(yè)的單項資產價值之中。
按照馬克思價值規(guī)律理論,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因此,被并購企業(yè)的(C+V+M)決定了被并購企業(yè)價值,但被并購企業(yè)的交易價格(支付對價)并不一定等于它的價值,而是圍繞其價值(C+V+M)上下波動;其交易價格(支付對價)最終取決于并購雙方的并購交易博弈;被并購企業(yè)通過成功交易實現(xiàn)“驚險的一躍”,在交易博弈中形成的并購交易價格(支付對價)的高低,則決定了被并購企業(yè)這一交易商品中(V+M)的實現(xiàn)程度;按照會計準則中對合并商譽的定義,這個(V+M)就相當于合并商譽。
四、合并商譽:來源與性質分析
那么,被并購企業(yè)的交易價格(支付對價)究竟是怎樣確定的?合并商譽又是怎樣形成的?這就要從企業(yè)并購交易中被并購企業(yè)的估值進行考察。
被并購企業(yè)的估值屬于資產評估的范疇。資產評估的基本方法有成本法、市價法和收益法。各種企業(yè)價值評估的方法,比如相對估值法、絕對估值法甚至實物期權法,歸根結底都可以歸結為這三種基本方法的變形或衍生。而在這三種方法中,考慮到市價法需要參考相似企業(yè)的市場價格,而相似企業(yè)市場價格的確定,其實最終還是依賴于成本法或者收益法,所以,企業(yè)價值評估的終極方法,可以歸結為成本法和收益法。
實際上,企業(yè)并購中通常要求同時使用收益法與成本法對被并購企業(yè)進行估值。收益法以被并購企業(yè)預期未來收益為基礎(真正使用的是預期未來現(xiàn)金流,二者的差別表現(xiàn)在一個依據權責發(fā)生制確定,一個依據收付實現(xiàn)制確定,但拉長到資產或企業(yè)的整個壽命周期,二者是一致的),選擇某種貼現(xiàn)率進行貼現(xiàn),確定被并購企業(yè)的價值,并將其作為被并購企業(yè)的交易價格(支付對價)。用公式表示為:
式中,V是被并購企業(yè)的估值,即并購交易價格(支付對價);NCFt是被并購企業(yè)預期未來凈現(xiàn)金流;i是貼現(xiàn)率;t是期限。
成本法在企業(yè)價值評估中又被稱為“資產基礎法”,顧名思義,它是站在被并購企業(yè)凈資產取得、購建的角度,對并購企業(yè)各單項資產進行估值,這種估值確定了被并購企業(yè)凈資產的公允價值;它意味著在估值時點上如果重新購置或建造被并購企業(yè)各項(凈)資產,這些(凈)資產的重置成本是多少,可以用COSTFV來表示。
顯然,商譽就是二者的差額(假定并購取得100%股權):
式中,Goodwill表示合并商譽。
在t>1的多期復雜模型下,上述公式和公式中的差額(合并商譽)計算較為復雜。可以將上述公式高度抽象、簡化,分析這個差額(合并商譽)的來源與經濟性質。
為此,做如下假設:
第一,權責發(fā)生制與收付實現(xiàn)制保持一致,因此未來收益就是未來凈現(xiàn)金流。
第二,被并購企業(yè)生命周期為1期,即期初成立,期末終結;于期初成立即被并購。
第三,被并購企業(yè)初始投資成本為(C,即COSTFV),假設初始投資成本即被并購企業(yè)組建時的各項有形資產和可辨認無形資產投入,無負債,那么,被并購企業(yè)初始投資成本(C)約略相當于被并購時其凈資產的公允價值(C=COSTFV)。
第四,并購時,預期被并購企業(yè)的收益率為r,行業(yè)平均利潤率為i,假定r>i,被并購企業(yè)存在超額利潤,并假定被并購企業(yè)并購估值使用行業(yè)平均利潤率i作為貼現(xiàn)率。
第五,并購取得100%股權。
(1)并購發(fā)生時,預期被并購企業(yè)未來現(xiàn)金流(預期未來收益)=C(1+r),預期凈收益為C×r。
(2)被并購企業(yè)并購估值(交易價格或支付對價)為V=。
(3)合并商譽GoodwillV=-C=C(-1)。
從高度抽象、簡化的合并商譽公式可以看出,并購商譽實際上是被并購企業(yè)預期未來收益大于貼現(xiàn)率代表的收益(二者之差即超額收益)的部分;它與被并購企業(yè)的凈資產公允價值一起,構成被并購企業(yè)交易價格(支付對價),由購買方支付給被并方,即:
得到:V==C+Goodwill。
被并購企業(yè)估值、被并購企業(yè)凈資產公允價值、合并商譽的上述關系,可以示例如下:
假定A企業(yè)并購B企業(yè),并購過程中采用通用的收益法與成本法(資產基礎法)對B企業(yè)進行估值。B企業(yè)具體情況及相關假設如下:
(1)年初B企業(yè)設立,購置資產一項,一次性投入,市場價100萬元;B企業(yè)無負債。該資產使用期限1年,年末全部耗用完畢,無殘值;無其他成本費用發(fā)生。B企業(yè)存續(xù)期限1年。
(2)假定年初A企業(yè)并購B企業(yè);1年末B企業(yè)預期獲得收入現(xiàn)金流120萬元;無稅。
(3)同時假定B企業(yè)所在行業(yè)平均利潤率10%。
(4)假定并購雙方博弈的結果,認可B企業(yè)未來1年內預期收入現(xiàn)金流為120萬元,并同意按照行業(yè)平均利潤率10%進行估值。
(5)A企業(yè)購買B企業(yè)100%股權。
對B企業(yè)并購估值和“合并商譽”的初步計算如表1。

從收益法的估值原理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合并商譽”,僅僅是并購雙方對被并購企業(yè)預期未來現(xiàn)金流的分成,并由購買方把被并購方獲得的分成部分,在并購發(fā)生時由購買方支付給被并方而已。分析過程如表2。
因此,從并購交易過程來看,所謂“合并商譽”,其實就是B企業(yè)的全部預期利潤中,保證了購買方按照并購交易價格(它是購買方的投入成本)獲取貼現(xiàn)率代表的利潤水平(本例中就是行業(yè)平均利潤水平10%)以后,對被并方B企業(yè)未來預期利潤的剩余部分,由被并方獲得、由購買方A企業(yè)在并購時支付給被并方,構成B企業(yè)交易價格的一部分(交易價格的另一部分是B企業(yè)凈資產的公允價值)。所以,“合并商譽”不過是被并購方獲取的并購后自身預期利潤的分成而已,是購買方對被并購方獲得的這部分預期分成利潤的預付款項。

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fā)現(xiàn),是否存在合并商譽,并不是由被并購企業(yè)是否存在超額利潤所決定,而是取決于被并購企業(yè)預期收益率(r)與并購估值中貼現(xiàn)率(i)之間的關系。分析過程如表3。

同樣可以進一步證明,即使被并購企業(yè)存在超額利潤,也可能不會存在并購商譽,甚至出現(xiàn)“負商譽”(即雙方并購博弈中出現(xiàn)i>r的情形;過高的貼現(xiàn)率i甚至會導致并購交易價格低于被并購企業(yè)凈資產公允價值)。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并購交易中使用的貼現(xiàn)率(i),一般規(guī)定采用市場利率,意味著購買方應該以獲得市場收益率作為并購出價的基礎。為了避免交易定價中濫用貼現(xiàn)率、過高或過低主觀定價,中國證監(jiān)會專門制定了評估機構折現(xiàn)率計算指引,對貼現(xiàn)率進行規(guī)范[17]。
回到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公式,實際上可以這樣理解:被并購企業(yè)交易價格,圍繞著被并購企業(yè)的價值(C+V+M)上下波動;被并購企業(yè)估值(并購交易價格)更高或者更低,代表著在補償了被并購企業(yè)價值構成中的不變資本(C)以后,(V+M)的實現(xiàn)程度;它是由被并購企業(yè)并購后預期收益率(r)與估值貼現(xiàn)率(i)之間的相對關系來決定的,歸根結底取決于并購交易雙方的定價博弈。
五、合并商譽會計處理方法:基于合并商譽來源與經濟性質的恰當選擇
(一)關于合并商譽來源與經濟性質的總結
從企業(yè)合并過程來看,并購商譽作為“購買方對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來源于企業(yè)合并交易價格確定過程中,對被并購企業(yè)預期利潤在購買方和被并購方之間的分成。其中,合并商譽就是被并購方獲得的那部分分成,構成并購交易價格(支付對價)的一部分,由購買方在并購交易完成時支付給被并方。因此,合并商譽本質上是購買方的一種預付款項,理論上將隨著并購后被并購企業(yè)預期利潤的實現(xiàn),逐步得到回收。被并購方獲得分成比例的高低,取決于貼現(xiàn)率(i)的大小,i越大,并購交易價格越低,被并購方獲取的分成也就越少,“合并商譽”也就越小(甚至為負)。
(二)從合并商譽來源與經濟性質看合并商譽會計處理方法選擇
從購買方的角度看,購買方支付的這部分所謂“合并商譽”,是企業(yè)并購交易中通過“交易或事項”取得被并企業(yè)這一組合資產的成本的一部分,應該根據組合資產成本的轉移方式,按照組合資產的成本流轉核算方法進行會計處理。
在當前分拆計價反映、單獨確認合并商譽的情況下,由于合并商譽是購買方對被并方獲得的利潤分成的預付,理應隨著并購后經營的持續(xù)和利潤的逐步實現(xiàn),逐漸得到補償、回收。鑒于合并商譽的“預付款項”性質,恰當的合并商譽會計處理方法是攤銷法,攤銷期限和每期的攤銷額度取決于企業(yè)合并過程中被并購企業(yè)交易價格(支付對價),以及支付對價確定過程中所選擇的貼現(xiàn)率(i)和貼現(xiàn)期(t)。
【參考文獻】
[1] LEAKE P D.Goodwill:Its nature and how to value it[J].The Account,1914(1):81-90.
[2] 王則柯.信息經濟學平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54-156.
[3] 菲利普·科特勒,凱文·萊恩·凱勒.營銷管理[M].14版.王永貴,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65-298.
[4] HENDRIKSEN E S.Accounting theory[M].Homewood Illinois,Richard Irwin Inc,1982.
[5] 楊汝梅.無形資產論[M].施仁夫,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26.
[6] 財政部.企業(yè)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yè)合并[A].2014.
[7] 謝德仁.商譽這顆“雷”:減值還是攤銷?[J].會計之友,2019(4):1-5.
[8] 楊瑞龍,劉剛.企業(yè)的異質性假設和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內生性分析[J].中國工業(yè)經濟,2002(1):88-95.
[9] 富蘭克·H.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M].王宗,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0] BAIN J S.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11] DEMSETZ H.Industry structure,market rivalry,and public policy[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1-9.
[12] RUMELT R P.Towards a strategic theory of the firm[Z].In Competi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ed.R.Lamb.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84.
[13] 伊迪絲·彭羅斯.企業(yè)成長理論[M].趙曉,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 杰伊·B.巴尼,德文·N.克拉克.資源基礎理論[M].張書軍,蘇曉華,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 財政部.企業(yè)會計準則——基本準則[A].2006.
[16] IASB.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A].2004.
[17] 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監(jiān)管規(guī)則適用指引——評估類第1號[A].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