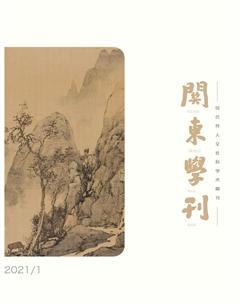無、規定與否定
[摘 要]“無”作為邏輯學、也是思想開端的環節之一,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相關文本的簡略與晦澀,要恰當地理解無是相當困難的。討論無,便離不開無與有的關系,離不開有無與開端的關系,離不開開端與規定的關系。本文將結合這三重關系,以深入解析無在開端中的內涵,并進一步探討其與“否定性”這一貫穿黑格爾哲學的概念的關聯,從而揭示無之為思想的內容規定和推進動力這一重要價值。
[關鍵詞]黑格爾;邏輯學;無;否定;規定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一般課題“走出《美學》:黑格爾整體思想視域下的美學思想再研究”(2017BWY008)。
[作者簡介]李鈞(1969-),男,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黑格爾思想中的“否定”是其思想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對于后世思想最有影響的部分。這個“否定”,是在他的《邏輯學》中嚴密地建立起來的,《邏輯學》從開始即有“有、無、變”的范疇變化,其中,“無”即是后面范疇發展中“否定”的根源。在黑格爾研究中,《邏輯學》的闡釋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在諸多闡釋著作中,對于“有”和“無”這兩個開端的范疇(也包括“變”)都很簡略,沒有深入發掘范疇的含義和與其他范疇的關系。本文試圖在《邏輯學》文本的基礎上,對“無”這一范疇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有與無在開端處的意義歧變
“邏輯學”是科學的思想的形式,邏輯學講述的,其實就是走出意識以后完全在客觀狀態下與世界的主體——精神合一的思想形式。在邏輯學的開端處,黑格爾非常簡略地描述“無”,與“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規定”的“有”一樣,無也是純粹的無,是沒有規定性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是一個談不上規定的“空”。其次,按照黑格爾的說法,“無”和“有”一樣,也還是一個對于思想的直觀。此時,有和無都沒有進入思維里面,沒有進入邏輯,只是思維形式(邏輯)整體的形式,是思維的一個整體方面。既然是思維從整體來看的方面,所以也可以說它表達思維本身和整體。黑格爾說,因此,有和無是同一的。有就是無,無就是有,因為對它們的言說都是一樣的。“無和有是同一的規定,或不如說是同一的無規定。”黑格爾:《邏輯學》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70頁。以后凡引本書,在引文后標出頁碼,不再出注。那么這個思想的開端是怎么來的呢?在《邏輯學》開始的一章“必須用什么作科學的開端”里,他講了一個思想從意識到科學的發展過程,指出,當人的意識發展到最高處——“純粹知識”時,因為這個純粹知識的性質,它可以把此前全部認識一起籠括在自己里面,或者說自己“外化”為一個整體,并且使這個整體指向一個自身。于是,超越整個意識的“科學”出現了,這個科學是作為整個意識整體的指向出現的,這個整體所代表的,就是科學,科學在這個整體上以外在的方式出現。于是,這個整體上性質是直觀的整體,就是科學——其形式就是邏輯學——的開端。也就是說,整個《精神現象學》所揭示的人類認識的整個過程,因為最終揭示了超越自己意識的客觀真理的存在,因此整體上成為開端。因為在這個時候,那個真理,還沒有顯示任何內容,僅僅只是一個指示(形式),所以它是尚未規定的“無”(換言之,這個真理所呈現的內容沒有任何具體的內容,所以從內容上說,它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規定:“有”)。
同時,他又在另外的地方,指出思想其實可以在整體上是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它自己展開后,必然會設置出自身與自身特性的關系,而那個自身生發出來的特性,從整體上都是一個性質,都是對于自己的達到過程,也就是達到自身的開端。他說:“進展,這是理念被設定起的判斷。……這樣,開端的否定的東西,或者說,它的規定性中始初的東西,就被設定起來。”
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1830年版)》,薛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9頁。
因此,“有”和“無”,它們不是隨便想象出來的東西,而就是思想“開端”本身因為自己的發生和位置所顯示出的意義。
在最初,有和無最重要的特點是沒有規定性,它們作為思維的外在整體,并沒有進入思維。所以,對于有和無,不用去想象它們是什么,而是要根據它們邏輯的意義去確定——也正因為這樣,它們是相同的。然而沒有規定性不是絕對的否定(盡管它們在相對于別的東西時必然會是絕對的否定,但這是下一步的事情。)而是還沒有規定性,它是一個混沌。“空”不是毫無生氣,而是充滿生機,但卻不可識別。但這樣出現的開端也是不穩定的,當它和自身,即它作為科學的“尚未”與科學的“已經”相比較時,就會顯出自己作為開端的特點來,也就是會有規定性,就要下降和分裂,因此會形成“有”、“無”、“變”這個開端的一體三位。
我們注意到,在邏輯學的開端處,黑格爾就提出了“規定”(DasBestimmte)在活動,因為“規定”,思想開端才顯示為被規定的“有”“無”“變”以及它們各自的規定性。這是他未曾明言的邏輯學里最重要的塑造力量。關于“規定”,《邏輯學》后面“實有”節有關于斯賓諾莎“規定就是否定”的話有提,在“某物”范疇里,它也是某物的一種內在規定性。但是,這些都是對于最根本的規定行為次生痕跡的解釋。最根本的規定,從邏輯學的一開始就是主角。也就是說,盡管黑格爾一直強調哲學必須是“無前提的”,即思想不能夠有任何自然態度、做任何預先設定,但他至少設定了一個“規定”在思想的始終,在黑格爾看來,精神(思想在達到超越意識的高度后與精神合一)本身的一切范疇和環節都是從自身中必然地演繹出來,精神(思想)不會預先帶著外在賦予的內容,但是,它至少有一個預先設定的,或者說是本來的內容,那就是規定,一種肯定性、設定性,也就是說,精神(思想)天然就是規定,除此之外,再別無他物。由于規定總是對象性或者意向性的,所以在最初,規定自己對自己進行規定,把自己當作最初的形式和內容。有了這個出發點,精神(思想)就展開自己為整個世界。
回到“無”的問題上來,我們會發現,有與無的出現中卻含著一個矛盾。按照有和無的內涵,它們僅是開端,就它們是開端而言,它們應該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但是它們在出現時,必然要以一種有規定性的方式出現,因為它們之作為沒有任何規定性的開端,必須要在于目的、本身對比才能明確自己是這樣,于是,它們又不得不在對比中被規定。所以當我們說它們是沒有規定的時候,其實已經規定它們為“沒有規定”了,而這時,我們說出的它們其實并不是它們了。因此,黑格爾在說它們的時候,雖然力圖擺脫規定來還原它們在本意上的沒有規定這個性質,故而有自身同一、不與他物對立等表述。但是,有和無在有沒有規定的一面的同時,卻無法避免地有具有規定的一面。于是,在規定的基礎上,不被規定和被規定,就成了邏輯真正的起點和動機。
首先,有無的無規定性天然含有規定性。因為有無作為開端,本身就是與非開端的對比。它們之定位于無規定性,本身就是與規定性對比。有無的絕對的無規定性,是從它們和規定性對比的相對無規定性中抽取出來的。黑格爾說:“這種無規定性,只是在與有規定的或質的東西的對立之中,才自在地屬于有。規定了的有本身與一般的有對立,但是這樣一來,一般的有的無規定性也就構成了它的質”。(第68頁)規定不能用于有、無,但是,規定卻可以通過排斥有、無來規定有無,規定把有、無從它所有的應用中排除出去,從而在另一方面反向規定了有、無。所以有、無總是處在“被規定為無規定性”和“絕對的無規定性”之間。所以,要真正地把握有無的純然絕對的無規定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甚至可以說在思維里面是無法把握的,因為任何思維都是規定的。因此,有、無純然絕對的無規定性,是超出思維的,在思維之外。當然,如前文所言,在有無還是開端、還是“尚未”的意義上,它們當然也還不是思維。因此,要把握有和無純然的無規定性,只能借助于“直觀”。“開端在直接存在的意義上,是從直觀和感知采取的。”
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1830年版)》,薛華譯,第159頁。就有和無的純然無規定的方面來說,它們整體上對立于規定。所以,有無可以說是“直觀”,還不是思維而僅是思維的整體直觀。
其次,開端除了無規定的一面,其實也有有規定的一面。其實,純然絕對的無規定性,應該是在有規定和無規定之間的“不二”,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純然的無規定。否則,那種無規定是相對的無規定。現在,除了對這含混的無規定進行了無規定的想象以外,就必須面對開端有規定,和規定有關系的一面。邏輯學在這里呈現出一個隱蔽的含混。開端的意義(無規定性),確實通過對比得出的,否則一切無可進行、無必然性。但開端作為開端,它又必須擺脫這個對比,呈現出純然的無條件性。開端如果完全和結果沒有關系,那么這個開端是漠不相關的,沒有作為“開端”的意義。然而,如果開端是相對、有條件的,那么它也不能是開端。開端的本意就應該是“是的非”。我們可以用這么一個例子來幫助理解,那就是我的開端。我的開端是我出生之時的小嬰兒,再小,他也是我。但是,相對于我的成熟或完全發育來說,他又還不是我。
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從開端開始的,命名為“有”在于它就是一個“有”,一個總體上還是含混的“存在”。這個開端作為開端應該是“不是自己的自己”,這是開端本來的必然含義。開端應該是自己,但又沒有達到自己。這個含義就決定了“有”的所謂“無規定性”到底是什么樣子。中國人容易想象一個萬物之初的“混沌”,或者由一個絕對的無開始,逐漸混沌,然后裂變。但這畢竟只是想象。思想必須固定想象,把想象建立在概念上,而且,它的變化也不是隨意或者詩意的,每一個變化都必須變之有據。也就是說,有必須內在于無。
規定的有無在這里是關鍵的。開端介于規定的有無之間,這個有和沒有規定,導致了“有”和“無”的互相顯現和糾纏。如黑格爾所言:“在第一個開端自身以內,必定包含著能夠使他物在那里發生關系的東西。”(第85頁)先是“有”的出現,然后“無”因為“有”而被映照出來,因此第二個出現。“當在邏輯中把有本身作成開端時,過渡在這個開端的純粹反思中,還是掩蓋著的;因為有只是直接建立起來的,無也只能由它那里直接出現的。”(第89頁)
有是沒有規定性的,它是一個混沌的存在,但是,對這個沒有規定性的東西卻無可避免地要進行規定。只要一規定,它就要規定為“沒有規定性”,也就是一個“非有”。在規定中,它被推向去除了任何規定性一端,成了絕對的空白。但反過來,這種無規定如果保持為不規定,那它永不能是思想的范疇,它將抽象的同一,沒有任何意義,也是一個空白。因此,有既是有,但它又同時就會顯示為非有,“非有”是有的內容,但在這個時候,內容和形式是不分開的(規定和實有的分開,要在本質論里),所以,有就是非有。于是“無”通過“有”映照了出來。
沒有規定的有,是超然的一個混沌,介于是否之間,故而是直接性的。但規定不是外來的,而是本來就內在于有中,超然的有本來就是介于無規定和規定之間的,它就是一個自我規定的精神的雛形。這個內在的規定力,一旦發生作用,它就會把有呈現為無。黑格爾關于有無的一節,其實涉及到了形式和內容的問題。有里面的規定把有自身規定為無(非有、否定),于是就有了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規定起作用,于是就有了內容,有了內容,于是就有了形式),然后再轉化為有和無的關系。有和無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也是規定和未被規定的關系。當我們把那個超然命名為有時,我們不得不把另一端命名為無。其實我們也可以用形式和內容來命名。
不過,在這個最初的直接性層次上,規定與未規定之間的關系是直接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也是直接的。因此,形式就是內容,內容就是形式。有就是無,無就是有。我們可以聯想到一個例子,正如身體和靈魂,人是什么?人既是這個身體,又不是這個身體;人既不是這個身體,又是這個身體。是和不是的這個關系,也許本來不是問題,因為它們來自更原始的超然一體的異變。
在開端這里,無、否定和規定顯示出了一種關系。這個關系不建立,邏輯學后面所有的精彩都失去了根據。開端的無規定性是在被規定和不被規定關系之外的。因此,任何被規定和不被規定的情況,都是對開端的否定。開端退縮在規定問題之后,但又始終關聯著規定問題。因此,規定是開端的表現,開端無法不被規定,規定就是開端的存在。但是,相反的情況也同樣存在,那就是,規定是開端的否定,規定歪曲了開端,遮蓋了開端。這么一個模式,直到海德格爾將“真理”解讀為“解蔽-遮蔽”的模式才清晰起來。但是,黑格爾關于開端、關于有的說法,確實反映了這么一種關系。
二、無與開端的內涵
我們在前面一直有個問題需要問:為什么在有之外,還要一個無?這個無一方面看起來是作為有的內容的無,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獨立于有,和有同時出現的意義?為什么有和無相同,但又是不同?
上節所言,一個“有”字其實并不能講完開端的內涵。開端作為直接性,首先是被定位為有的。因為,開端就是目的自身,它是對于目的的肯定,“理念的自我規定……發生判斷,并把自己建立為它自身的否定物。這樣,那種對于開端本身顯現為抽象肯定的存在,就毋寧是否定,是被設定的存在。”
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1830年版)》,薛華譯,第158頁。這個有,就是目的自身,它是目的還沒有發展自己為實體和實現自己為全體的外在樣子。但是,不管目的有沒有發展和實現自己,它畢竟還是它。在《哲學全書》的另外一個地方,黑格爾談到從精神向上帝的上升,他說:“關于這種上升的出發點,康德所采取的,就他把對上帝的信仰看作來自于實踐理性而言,大體上是最正確的。因為這個出發點含蘊地包含有構成有關上帝概念的內容或材料。”
黑格爾:《哲學科學百科全書3:精神哲學》,楊祖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6頁。這里,撇開不同文本中的用詞的不同,黑格爾其實是強調開端就是目的。開端不是無關目的(內容)的東西,而就是目的的潛在存在。
謝林在他的《近代哲學史》中,花了很多篇幅分析黑格爾邏輯學的開端,他認為這個開端是一種“純粹的思維”,但它不是一種“現實的思維”,它其實是缺乏內容的。謝林:《近代哲學史》,先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0頁。很多研究者特別是英美研究者出于對本體論的謹慎態度,將自己的立場限定在康德理性批判的主觀范圍內,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當作一種形式的東西,一種思維方式。但是,這種態度,恰恰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序言”里所批判的,將認識和對象割裂的“空的只是現象”是一樣的。在黑格爾看來,盡管邏輯學是在形式上描述世界,但思想哪怕在最初最簡單的形式性的形式里,都含有形式性的內容,內容從來就在形式里,哪怕這個內容為“無”。邏輯學是形而上學,并非主觀思維方式論。這個始終和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內容哪怕就是無,卻并不是無關緊要的,而恰恰是最重要的本身和本體。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它甚至要顛倒過來,無是形式,而有是內容。
這個有,就其為目的本身的一種整體方面來說,是可以被稱為規定本身的,因為精神或思想本身就是規定。它還可以被理解為目的的投影,是一個框子,是一個指向,它把所有有關目的的東西都籠在里面。可以說,它是最大一個“定在”(被規定的存在)——因為“有”還有另外超越的一方面,所以,黑格爾無法把“有”稱為定在,但是在后面,他明確指出,“有”在規定的一方面,就是定在,因此,“有”是最有限的有限物,它沒有一點內容,它是有限物的本身,因而也就是有限物的框子,有限物的概念。在后面,它就成了一個有限物內在的精神(概念),有限物的自在。就其是一種指向,并引導者有限物向著目的轉化來說,它是“應當”、一種壓力和義務。
所以我們說,邏輯學的開端,就是一個發生,一個規定的發生。這個規定,是自身對于自身的規定。因為理念本身就是一個判斷、一個規定,這個規定不對別者作規定,只是對自己作規定。在形式意義上,開端就是這個判斷的一端,而目的是另一端。可以說,開端就是真理本身對自己的顯現。開端里,就有一個部分與整體的結合,有一個自我異化為自我的對象的行為。也正是因為這樣,開端會呈現為“最空的有”這樣的形態。這個形態是比較而產生的。沒有比較和關系,開端不能獲得“有”的意義,也不能獲得“無”的意義。
從意識的角度來說,如果說世界都在人的意識里,那么真理是意識的本身。意識向來是存在的,但是,唯有它有了自我意識它才真正地存在,否則它便只是一個不能被自己意識到的沒有意義的東西。黑格爾在解釋“小邏輯”時說:“當我們把思維認為是一切自然和精神事物的真實共性時,思維便統攝這一切而成為這一切的基礎了……自然界不能使它所含蘊的理性得到意識,只有人才具有雙重的性能,是一個能意識到普遍性的普遍者。人的這種性能的最初發動,即在于當他知道他是我的時候。”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1頁。黑格爾并不認為“思維-意識”是主觀的人的,他把思維當作一切存在的實體,但是,當思維沒有自我意識時,它只是一個被動的自然物,它沒有意義。只有當它能夠意識到自己,有了自我認識的時候,它才是一個真正的思維、完整的思維。我們可以把邏輯學的開端看作是思維之作為真正的思維的開始,而真正的思維就在于自我關系—自我意識。這里面就是有一個自我比較、自我異化的開始。我們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把這個當作是認識的開始、意識的開始。而“有”“無”正是在這個比較中的位置(開端)獲得。
前面說過,“有”的沒有規定性在被規定與不被規定之間,沒有規定性在面對被規定的時候(被規定為沒有規定性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將出現非有或者無。因此,開端在超然中,亦有與規定和不與規定相衡量的區別。在不與規定衡量時,可以是有,在與規定衡量時,則是無。后面的情況,特別在對有進行規定的時候顯示得比較清楚:如果對有進行言說,則無法對有說出什么來,有被規定為沒有規定性,有的規定性就是沒有。在面對言說(規定)時,開端似乎在拒絕,這份拒絕,讓開端退縮在規定性之下;同時,這份拒絕,也拒絕一切除了它以外的言說。因此,可以說,開端也有“無”和拒絕的一面。
無的出現是多線索的,前面講過,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有的內容(無規定性)衍化出來,大多數對于《邏輯學》“無”的解說是這個思路。但是,黑格爾在“必須用什么作為科學的開端”里面卻傾向把“無”定位在更深的來源上。“有”沒有規定性,沒有內容,換言之可以說,開端拒絕了規定,還沒有進入規定,它只把規定放空,讓它什么也規定不到,在這個意義上,開端是“無”。因此,開端可以說是一個什么內容都沒有的“有”,也可以說是僅有一個形式的“沒有(無)”。因此,無并不是有推演出來的,而是同時出現的開端的意義。只不過“無”不可被顯示,一旦顯示,它總要被規定,而一旦被規定,它總是被規定為一個“非有”,因此,它只能出現在“有”之后,它要被“有”映照出來,但絕不是被它生產出來。在這過程中,無進一步顯示了與規定以及否定的關系。注意,無是有的平行范疇,也就是說,無是有的另一個面貌,也因此是開端的另一個面貌。無是有映照出來的,沒有第一個,第二個不能顯現,但這并不意味著第二個是第一個的產物。(變是開端的第三個面貌,因為有或無,或有和無而顯現,但它并不是他們的產物。)無也是開端。開端除了是有,還必然是無。無的出現,明確了開端的另一種特點,也通過對比明確了有。
也因此,有和無是相同的,因為它們內涵相同。但它們不是僅僅的相同,僅僅的相同意味著它們完全沒有規定性,就連它們自己“沒有規定性”的規定性都保不住。有和無又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在跟規定相關時出現了分歧。但它們又不是僅僅的不相同,僅僅的不相同意味著它們總是相對的。而相對的,就降低了它們的層次,它們也會失去“沒有規定性、不在規定性之中”的規定性,并使它們失去了開端的意義。
三、無作為“拒絕”與“否定”的本體
開端之為開端的特點開始,黑格爾邏輯學的奧秘即開始醞釀。而無的出現,是邏輯學內在運動的核心機制的出現。對于無,《邏輯學》的條目正文是簡單的,但是在附釋的闡述中揭示了它的豐富含義。
首先,無是開端的另一個面貌。它是由有映照出來的。
無是開端面對規定時的面貌,這里,無有兩重意義。一是無就是開端。無是開端的樣子,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是開端,一個東西和一個東西的樣子,對于規定來說,本來就是同一的。但是,一個東西和一個東西的樣子畢竟又不是同一的,它們一個是形式,一個是內容。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一個是“規定”,一個是“規定性”(在規定中的樣子、性質)。前面曾引黑格爾說:“進展,這是理念的被設定起的判斷。直接的普遍性東西作為自在的概念是那種在其自身將自己的直接性和普遍性降低成一個環節的辯證法。這樣,開端的否定的東西,或者說,它的規定性中始初的東西,就被設定起來。這是與一相應的,是有區別東西的關聯,亦即反映的環節。”
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1830年版)》,薛華譯,第159頁。許多讀者會將這一段看作是對于本質論的描述。但它其實是對于所有離開同一性的非同一性的描述。在黑格爾看來,在最開始的同一里面,其實就含有不同一的。而這個不同一性,就來自于這個東西和目的的關聯。關系始終在,所以,映現始終在。只不過,在整個存在論階段,映現關系沒有成為主要的。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無已經是有的“進展”。而這個進展,必然是從有,從有之為有(開端和目的的關系)映照出來的。這個映照出來的進展,必然是否定。為什么是否定呢?因為,開端看起來是有什么,但其實就是目的的還沒有,是目的的還沒有發展和實現。因此,對于規定來說,也就是開端就其與目的的關系來看,它是否定性的。
無是一種拒絕。還是這段話:“理念的自我規定……發生判斷,并把自己建立為它自身的否定物。這樣,那種對于開端本身顯現為抽象肯定的存在,就毋寧是否定。”這個拒絕首先是對于規定的拒絕,因此,我們可以說,規定本身與存在本身是對立的,它們之間互相否定。但是,進一步,如果規定是無所不包的力量,哪怕拒絕,它也要把它包括其中的話,開端就把自己的否定交給規定,或者說,規定把存在包括進來,但是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包括它,只能把它規定為“非有”(否定——無)。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不僅開端的規定性是無,而是規定和規定性本身就是無。我們還可以看到,規定對于開端來說是無,反過來,開端對于規定也是無。兩者都是無(從另一個方向來看,兩者又各自是有)。
其次,這個拒絕也是對不是它擁有東西的拒絕。開端對于規定的拒絕,也暗含了開端對于不是它的擁有的東西的拒絕。盡管這兩個拒絕其實是相同的,但在某個層面上是不同的,分別表現為是自身的拒絕和他物的拒絕。
因為無顯示出來的開端和規定的這個復雜關系,我們看到,無一方面是開端本身,它是一種存在的顯現,是直接性、外在性的。但另一方面,無又是拒絕顯現的,所以,無又代表著那個開端所要代表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講,無又是本身、是內在。總的來說,無是一種內在的外在顯現,可以說它是外在,也可以說它是內在。
在關于無限的一節里,講無限與有限的關系的段落再次提到了“無”:“無限是有限物的無。”(第137頁)在更具體的環節里,無的意義顯示得更為清楚。按黑格爾的意思,有限物是存在的進一步物化或者進一步規定。但是在規定過程中,規定把原來的東西異化和對立化了,而與此同時,這個被規定的有限物中還含有原來的維度,叫無限,這個無限就是對于異化和他物化的抵抗,故而顯示為“無”。這一節更為清楚地顯示了在黑格爾這里“無”和“有”是怎么來的,它們是關系性地獲得自己的內涵的。
黑格爾的邏輯學將在以后的發展中,以“否定”的形式展示無的復雜發展和變化。這一部分,是邏輯學中最復雜幽妙的內容。在各種變化中,否定在某個主含義的基礎上,也呈現出多重含義。這些含義,都在有無關系中得到發軔。因此,對于有無關系,對于無,尤其需要注意把握它的多重義項。
黑格爾談到西方哲學的起源時,提到了巴門尼德的“有”,這種將有進行“抽象的同一性”(第72頁)的規定,就得出這種和無區別開來的單一的有。換言之,對于一個混沌,人們將之規定一下,不管它是什么內容,總是規定為存在,“有”。“有”是對發生什么的最簡單的規定。但是,黑格爾其實自己并不這樣規定有,在他看來,那樣的規定,是“空洞的思想物”(第73頁),是知性的產物,如果有和無都是這樣被空洞地規定,那么有和無的關系就不是“不同”,而是“分離”了。他自己規定的有,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定在”,即有的規定性,即有一旦被規定,它的豐富性就片面的凝固為一個單一的“有”,而這時,它就不應該稱作“有”,而是定在了。另一個方面就是“肯定”。他說,肯定存在于任何現實的具體事物中,“是已經建立的、已被反思的有”。(第73頁)
關于無,黑格爾說得更多。首先,在無的未被規定的一面,它是未被規定的無規定性。他強調“無”的重點是“在于抽象的和直接的否定,純粹自為的無,無關系的否定;——假如有人愿意,也可以用單純的‘不字來表示它”。(第71頁)也就是說,直接性的無,除了沒有規定性和直觀本身以外,黑格爾還強調它是純然的否定。其實,“否定”已經帶有很強的規定性的色彩,但是,黑格爾在不規定情況下仍然忍不住強調無的否定性,可見他對于無的這一方面的重視。至于被規定的無,也是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和定在結合在一起的規定性本身,也就是隨著存在的豐富性被凝固為一個片面的有時,無就化為這個定在的規定性。就定在的規定性還不具體而言,定在的規定性就是規定性本身。另一方面,無就是“否定”,否定存在于任何現實的具體事物中,“是已經建立的,已被反思的無”。(第73頁)
四、無的意義與否定的優先性
在所有環節里,黑格爾都強調否定的優先性。“出發點的本質內容借以擺脫其有限性并因而自由地產生出來的那個否定的環節,必須特別予以注意。”
黑格爾:《哲學科學百科全書3:精神哲學》,楊祖陶譯,第316頁。似乎,存在就是否定,而否定是存在自身的主導性力量,更是他物的創生性力量。存在是有肯定和否定兩方面的,但否定更重要。對于存在下降為個體性以后有多樣性、有這個世界來說,否定是他物的根本要素,也是事物之間關系的根本要素。具體而言,否定的優先性有下述三個方面:
首先,當有與無被科學地、概念地建立起來時,無呈現出一種優先性。因為,存在、有、無都是作為開端被定位的。它們是作為一個前提的開端。正因為它們是開端,所以,它們的根本特點其實來自于跟那個前提的比較和跟那個前提的區別,那就是它們都是那個前提的“尚未”。有的內涵首先也是“沒有”規定性。看起來,前提是一個既定的但是還未達到的有,一個目標、一個理念,而開端是這個理念的尚未達到。開端中的“有”更像是這個前提的影子,是那個遠還未達到的目標向出發點延伸的影子,但是,這個“有”終究還是“沒有”規定性。而且,我們看到,“有”-肯定性更多地作為一個依托點而存在,在定在以后,有-肯定性在完成了“跳板”的使命后,關于存在的所有內涵都集中在否定性產生的運動和關系中,它漸漸地消失了。所以,在被建立的意義上,開端主要的內涵是無-否定。
其次,整個邏輯學、特別是“某物”環節之后(相當于物被創生之后)的邏輯學,更像一個“否定”一貫和創生的游戲。從一個和前提的區別開始,就是否定,然后以否定結合各環節,創生其他環節,最后達到一個核心是否定的復雜形式為終結。
第三,否定,不是消極的否定,它更是創造力。它因為否定他物而創造了他物,因為要區別他物而創造了他物。于此同時,它自己也因是他物的否定而創造了自己。
對于這樣一種“否定”一以貫之并且成為內核的邏輯學,我們必須負責地確定,否定為什么具有這樣的中心位置和功能。它從某物開始,就始終伴隨后面的環節。某物的否定,來自質的否定性。而質的否定性,不是外在添加在實有上面的,它必然內在于實有的來源中,而黑格爾說它來自無。那么這個無,是并立于有嗎?它是添加到有上面去的外在反思嗎?為了理解否定的優先地位,我們需要在有無環節里看到有無不相同和相同的關系,無如何作為有的否定性和規定性。
如本文第一節所言,有和無都是“無規定的自身關系”,而且是直接的自身等同關系。有和無的區別,就在于這個自身關系,一個是肯定的路徑,一個是否定的路徑。但是,無必須在有的后面,因為無應該是被有映照出來的。作為開端,它總是這個路程的開端,而不可能和這個路程沒有關系,因此,先是有關系,然后才是這個開端還沒有顯示任何東西的狀態。有和無是互相揭示的,所以有和無是對立的,不同的。
有研究者在論及《邏輯學》時說:“黑格爾認為,如果解釋一個初級的形式要素,不使用其他要素,靠自己解釋自己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人類認知中這些要素的相互關系,來自于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相互關系,即,各要素不僅不能單獨被感知,而且也不能獨立地存在。”
Stanley Rosen,“The Idea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2014,p17.同樣,有和無是交互關系著的,它們的不同只是因為規定,是規定造就了這個不同。在規定之外,有和無無所謂不同。實際上,規定就是有和無的來源。有和無是規定的有或無。但是,規定應該來自作為那個目的的思想或世界本身,是這個本身自我生產的。思想或世界本身就是規定,它自己發生規定行為,只能說,原始的狀態就是內含分裂的。有對于規定為只是一個空的內容,而無對于規定之所以為無,在于它只剩下一個形式。也因為這樣,當有無從整體上看成是變,然后再把變規定為一個有時,這個有就是“定在”了,這個定在里面的有和無都確定地表現為各自被規定的意義,有就是這個定在,因為它被限定了,所以它帶著一個形式了,于是它等待著一個具體的性質;而無,則內在于定在之中,成為這個形式,它是一個被限定的有,等待著具體規定性的規定性本身:質。有和無是最簡單的要素,它們之間必得相互解釋。但定在不是了,它不再是最簡單的東西,它可以自身解釋自己,即用內在于自己的質(否定)來解釋自己,而無須借助一個他物。有映照出無,無內化入有——這一理論環節,可以說是整個邏輯學最重要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