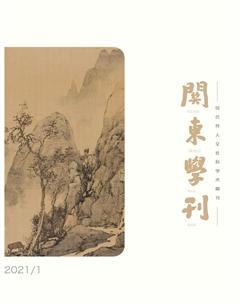“二史館”藏陳寅恪、顧頡剛佚信及相關史料考釋
[摘 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里藏有陳寅恪和顧頡剛書信各一封,未見于《陳寅恪集》和《顧頡剛全集》,當為佚信。由陳寅恪的這封信可約略知道他彼時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軌跡;此外,檔案里還保留了陳寅恪為劉銘恕《中外交通史論叢》寫的“審查意見”,陳寅恪在意見書里對劉氏的學術能力很是贊賞,體現了他對后輩學人的提攜和肯定。檔案所見的顧頡剛佚信及推薦語、評語則顯示了顧氏對學術和公共事務的巨大熱情,以及他對邊疆問題的持續關注。
[關鍵詞]陳寅恪;顧頡剛;檔案;佚信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 ‘ 學衡派 年譜長編及文獻數據庫建設研究 ” ( 17AZW016 ) 。
[作者簡介]曾祥金(1990—),男,文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西安 710049)。
一
筆者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稱“二史館”)查閱檔案的時候,意外發現陳寅恪和顧頡剛的佚信各一封。先說陳寅恪的信,這封信是陳氏寫給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的,為保存史料,照錄如下:
敬啟者
茲寄上審查意見書及原審查文件(104A 五種共六冊),請即將酬金寄下為感。此致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
陳寅恪敬啟
12月16日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信里沒有標明具體的寫作年份,從后附的《審查意見表》可知此信寫于1946年。陳寅恪于1946年春天離英歸國,10月由南京轉上海再返回清華大學,陳氏的這封信就是在清華大學寫的。彼時的陳寅恪雙眼完全失去復明的希望,心情自是沉重。八年抗戰雖已結束,國共內戰卻隨之繼起,陳氏經濟上陷于困窘,所以才會急著寫信說“請即將酬金寄下為感”。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成立于1940年,成立的目的是“審議學術文化事業及促進高等教育設施”,任務包括審議全國各大學之學術研究事項、建議學術研究之促進與獎勵事項、審核各研究院所研究生之碩士學位授予暨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事項、審議專科以上學校之重要改進事項、專科以上學校教員資格之審查事項、審議留學政策之改進事項、審議國際文化之合作事項和審議教育部部長交議事項。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章程》,全宗號:五,案卷號:134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940年5月11日—13日在重慶召開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決議案第4條即為《補助學術研究及獎勵著作發明案》;接著,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又通過了常會提出的《請討論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規則案》,教育部學術評獎活動開始步入正軌。教育部學術評獎活動的實際操作從1941年開始,該獎勵是當時最高級別的學術獎,并有高額的物質獎勵。它設有文學、哲學、社會科學、古代經籍研究和自然科學等類別,每類設一等獎1名、二等獎2-3名、三等獎4-8名不等。從1941年到1945年,該評獎活動每年舉辦一次,1946-1947年兩年合并為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教育部學術評獎活動的評委均為各領域的頂級學者,陳寅恪即為其一。
陳寅恪審閱的就是1946-1947年度的評獎作品,信里所說的“審查文件”即是劉銘恕
劉銘恕后來成為著名的敦煌學家,編有《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斯坦因劫經錄》,影響頗大。的《中外交通史論叢》,從檔案里的《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以下簡稱《說明書》)可知劉銘恕畢業于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后又至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研究院歷史科學門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部進行深造。曾在山東省圖書館任編輯,當時(1946年)正就職于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該所專任研究員兼文學院副教授。他所寫的《中外交通史論叢》內容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史、中外交通史及文化之交流、外來宗教之新的考說等,具體有《南詔來襲與成都大秦景教之摧殘》《蘇萊曼東游記證聞》《宋代海上通商史雜考》《元人雜劇中所見之火襖教》
《元人雜劇中所見之火襖教》一文后收入2013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劉銘恕考古文集》。《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作者在《說明書》里這樣講述本書的成書經過:“民國卅年春來蓉為金大文化研究所整理研究金石文字,而中外交通史為淺學所素喜者,于時賢此類論著故所未嘗釋手加之,與中國古代以及近世有密切關系之南洋風云日急,隨不期而草成鄭中貴航海事跡數篇。今春因為歷史系諸生說中國南洋交通史,披覽舊籍,偶有以為心得者,遂又輯為宋代通商史一文。”
《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由此可知,《中外交通史論叢》的成書與作者對時局的關注有極大關系,這也是彼時諸多學者所追求的目標,他們希望將自己的學術與戰亂的時局結合起來,發揮學術著作的“時效性”。杜甫和李清照等人成為戰時的學術熱點即基于此。同時,劉銘恕認為這本書在學術上的特殊貢獻在于新史料的發現,這些新資料對既往的學說“自偶有糾正、補證以及創通之處”
《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陳寅恪對劉銘恕的這部著作頗為贊賞,他在《審查意見表》里寫道:“所呈請獎之五種著述,皆為中外交通史范圍。考證材料甚為詳瞻,所列諸條中頗有創獲之處,唯以限于所論之范圍及取材之性質,故未能達到一極有系統之理想境界。然即就所得到之成績而言,亦可謂好學深思,難能可貴,不得不加以獎勵者矣。”
《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并擬為《中外交通史論叢》請第二等獎。陳氏在評語里肯定了《中外交通史論叢》的取證詳瞻和頗有創獲,同時也指出它由于論述范圍的限制導致缺乏系統性這一缺點,體現了一個前輩學者對后來者的鼓勵和期望。另外一位史學大家陳垣也參與了此書的評審工作,他對此書更為推重:“右五種六冊,細讀一遍,欽佩無已。著者對于搜集材料方法,似有充分練習,故凡子部集部有關本題材料,均能鉤稽摭拾,運用自如。足見曾下苦工,確有心得,顧亭林所謂采銅于山者,庶爾近之。不徒乞靈于圖書集成等類書,抄錄成文而已。至于考訂方法,亦極精密,有左右逢源之樂,無牽強附會之談。即內采用前人學說,亦能沿流溯源,觸類引伸,補充新證,時有青出于藍之處。此等著作,至少應予以二等獎。”
《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劉銘恕的這部著作能得到兩位大家如此高的評價,說明它確實是有價值的。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一、二、三等獎的標準有明確規定,“一律嚴格審選,給獎名額,寧缺毋濫”,對于一等獎的要求則是必須“具有獨創性或發明性對于學術確系特殊貢獻者”。
《教育部學術審議各項油印資料》,全宗號:五,案卷號:1429(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在這樣的給獎標準下,大量的參評著作很少有得一等獎的,獲二等獎的也不多見,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三等獎和不給獎之間徘徊。《中外交通史論叢》最終獲得了學術審議委員會給出的二等獎獎勵。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和劉銘恕在此前就已相識。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原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借書記錄簿,記錄簿有陳寅恪的三次借書記錄,其中一次記錄為“1944年1月21日,《廿五史》二冊、四冊,共兩冊。陳寅恪(劉銘恕代)”。陳寅恪于1943年12月來到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學,后兼任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導師。劉銘恕此時正就職于金陵大學,陳寅恪就通過劉銘恕代借了兩冊《廿五史》。兩人還有另外一層關系,劉銘恕的哥哥劉盼遂
劉盼遂(1896-1966),名銘志,字盼遂,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河南信陽人。早年就讀于山西大學,后就讀于清華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曾執教于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晚年任職于北京師范大學。在清華研究院就讀時曾師從陳寅恪。劉銘恕在其兄的引薦下于1930年首次見到陳寅恪。時間來到1957年,劉銘恕任職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從事《斯坦因劫經錄》的編撰,他對這批英藏敦煌漢文文書的卷子做了學術價值很高的提要式說明,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著名敦煌學家施萍婷就指出:“劉銘恕先生用很短的時間就編就《斯坦因劫經錄》,……《佛母贊》僅十一行,劉先生寫了130字說明,充分反映了先生的博聞強識。劉銘恕先生在編《總目》時,設‘本文一項,乃是創舉。有時,‘本文并不全錄,既省篇幅,又有利于讀者。”
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頁。劉銘恕將他在1957年第1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上發表的《英國博物館所藏卷子》一文寄奉陳寅恪指教,陳寅恪回函表示贊賞:“頃讀大作,甚佩。”同時請劉銘恕幫他留意遁倫語錄和唐玄奘詩等相關材料,接著在信里寫了一段經典性的話:
弟今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游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輟,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陳寅恪:《致劉銘恕》,《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9頁。
學者姜伯勤就指出這封信的重要價值,“不僅是對劉銘恕先生的工作有所肯定和指導,更重要的是,在一位老朋友面前,寅恪先生對本人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作了清晰說明。這封信中所說的‘試驗,無疑是陳先生本人的一種學術史、史學研究的‘試驗”。
姜伯群:《論陳寅恪先生“新方法”、“新材料”之史學“試驗”》,《史學月刊》2009年第5期。陳寅恪愿意和劉銘恕就自己的學術動向進行如此深入的交流,兩人的關系確實是非同一般。晚年劉銘恕在《憶陳寅恪先生》一文里回顧了他與陳寅恪的交往。1999年11月,中山大學召開“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年近九旬的劉銘恕撰寫《陳寅恪與別國異族語言》準備參會,后因故未能成行,不久即與世長辭。
關于陳寅恪與劉銘恕關系考察參考了姜慶剛:《陳寅恪與劉銘恕交往考略》,《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1月18日,第9版。
二
接著說顧頡剛的佚信,它是顧頡剛給劉公任的復信,此前劉公任寫信給顧頡剛,請求顧氏為他的新書《三國新志》寫序,顧頡剛就回了這樣一封信:
公任先生文席:
十載暌違,戰亂之中不復能相聞問。去冬華翰下頒,無任欣忭,并讀大著序言,就稔研究三國史事,創立體裁,勒為新著,足與歐宋齊驅,曷勝欽佩。剛自歸后,公私事冗,仆仆京滬道上,煩勞之甚。以是親友來函,每未能一一作答,既慚且歉,敢請曲宥為感。辱承囑為作序題簽,敢不應命。惟作序實不得暇,又不肯草率成文,致貽佛頭著糞之譏。敬涂一簽條塞責,幸為鑒原。出版后祈早日見寄,以快先睹,至所企盼。
專此即頌
撰祺
弟 顧頡剛
二月廿五日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顧頡剛在信里先是表達了對劉公任新著的認可,“創立體裁,勒為新著”,至于“足與歐宋齊驅”,顯然是客套話。接著說自己沒有時間寫序,希望對方原諒云云。從整封信來看,顧氏和他的關系似乎并非十分密切。顧頡剛的這封信之所以會出現在教育部學術評獎活動的檔案里,是因為劉公任在提交《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的時候《三國新志》還未出版,又因時間迫促不及央人介紹。于是劉公任就想把顧頡剛的這封信作為介紹語,并給學術審議委員會寫信做了說明:
敬啟者
頃奉七月三十日42775號大示,敬悉種切,茲遵命將顧頡剛先生致公任原二頁檢呈備核。惟拙著《三國新志》尚在滬上,已函世界書局于出版后立即直接寄上三冊,當不至延誤也。申請書三份已于日前寄呈,想已遞到。顧先生函審議完畢后,仍以賜還為禱。
此上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
劉公任敬啟
八月十四日
附顧頡剛先生原函二頁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誰知學術審議委員會的人似乎并不買賬,工作人員在便條里寫道:“本件曾呈送顧頡剛先生與作者之通信,而以顧先生為介紹人,但事實上并未得顧先生允諾,似未便寫入。”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他們認為作者把顧頡剛作為推薦人并沒有得到顧氏本人的認可,因而不方便寫進去。
由《專門著作申請獎勵說明書》可知,劉公任為湖南衡山人,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畢業,后就讀于北京大學研究院,歷任湖南大學、廣西大學教授。《三國新志》出版于1947年8月,作者這樣介紹它的成書經過:“民國三十三年夏,家鄉淪陷,棲伏嚴谷,以避禍難。每于喘息稍定之際,撰著此書,不以顛沛造次輟其素業。亂平以后,賡續為之,歷時三載,乃得完成。”全書內容分為世系、政治、經濟、學術、職官、軍備、地理七志,每志更各分細目若干,其取材于陳壽《三國志》暨裴松之注外,復引他書以相參證。劉公任認為《三國新志》在學術上的貢獻體現在:“陳壽所作,雖名曰志,實為列傳。三國之典章制度漫無可稽,故通考序書錄解題,皆以是短之。自宋迄清數百年間,從事增補編訂者已不乏人,然或作一志或作一表或書已失傳或傳而不全,后人考古,深以為病。本書自立體裁,務求明實,且盡正陳壽偏頗隱諱之弊,欲為研究三國史事者之一助也。”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呂思勉、柳詒徵和繆鳳林負責了此書的審查工作,呂思勉提出了兩個可以更正的地方:一、九品中正之制似應補附職官志之后(因選舉材料少,不別立一志);二、劉備為漢中王,起館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似系為交通軍事起見,非侈宮室,原書議論似可斟酌(六十一頁)。并在總評里寫道:“此書于三國史事,用力甚深,搜剔既精,條理亦密體例不泥于古而亦不背于舊。”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因而應該給予二等獎獎勵。柳詒徵的評價就沒有那么高了:“三國世系職官郡縣,前人皆有詳表,考訂精密,無須再改為志。華陽國志于劉先主后主皆立志,巴蜀漢中南中皆曰志,是為人與地并稱,志之例,作者亦未稱引。又政治志中雜及刑律,蓋未喻前史政載紀傳刑別為志之誼,似宜博考諸書,再求精當。序稱陳書未標紀以別于他篇,又稱漢書百官志因于百官公卿表,皆未細考。”“就陳書裴注分類抄撮,略參通考等書,以為治史初基則可,未便即稱新著。欲事獎勵,僅可列之第三等。”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繆鳳林更是認為本著作無任何特殊貢獻,且中多錯誤,不能予以任何等獎勵。三位著名歷史學者對于同一本著作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見,亦可見當時學術大環境里個性與活力的存在。
顧頡剛真正作為介紹人推薦的是李安宅的《邊疆社會工作》,顧頡剛在推薦語欄目里寫道:“作者夙習社會學,又每歷邊疆考察,以本身實地經驗,社會之實際需求,融會貫通,寫成此書。有見解,有例證,實是解決許多現實問題,為邊疆工作者所必讀。政府欲決定邊疆政策,亦必取作參考。雖一小冊,其益處殊不少也。”
《一九四五年度學術獎勵著作申請書及審查意見》,全宗號:五,案卷號:1360(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顧頡剛之所以愿意為此書做推介,除去他與寫作者的私人關系外,也跟他彼時對邊疆問題的持續關注大有關聯。另外一位推薦人陳達也認為著者憑實地觀察搜集有關邊疆社會的資料,加以分析及解釋,對于學術有相當貢獻,實為關于本問題不可多得的作品。最終《邊疆社會工作》經芮逸夫、柯象峰等人的審查后,獲得三等獎獎勵。作為評論人的顧頡剛則出現在朱祖尼的《中尼睦鄰記》中,顧氏的審查意見寫得頗為認真:“一、觀點及思想尚正確。二、參考材料未能盡量搜集,外文者尤感不足。三、結構嫌駁雜不純,敘次繁兼亦多未當。例如一章之中,忽而編年,忽而紀事,本末未竟,不能一致。四、缺乏創見。五、本文不過整理舊史料,自亦無所謂獨立體系或一家學說。六、敘述系統時欠明白,乾隆以前數章尤多首尾不清。第六章第七八兩節敘尼泊爾親美及中尼親善之增進,次序顛倒。七、引用書籍,多有未明出處者,以引查原文代替正文敘述,尤多不能貫串,不如自制提綱,而以引書為細目。”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尼泊爾屏藩西藏,自屬我國邊疆重要問題之一。本書命意甚佳,唯內容龐雜,實不足以副之。其體例駁雜,又往往羼以議論,妨礙文字統一,更不符近代著述之通例。原文中別字脫文觸目而是,尚其余事,故不擬獎勵。”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全宗號:五,案卷號:1359(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此外,顧頡剛還作為評議人審查了石永楙《論語正》、羅正緯《大學廣義》、宋嗣恂《孝經大義徵》、胡樸安《周易古史觀》、徐松石《泰族僮族粵族考》、施之勉《漢史考》和楊明照《漢書顏注發覆》等著作,由此亦可見顧氏精力之旺盛以及他對公共事業的支持。這些評語和推薦語能夠讓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一時期顧頡剛的學術路徑和學術旨趣,進而推動對顧氏的相關研究,再加上它們并沒有收入到已經出版的《顧頡剛全集》中,因而值得引起學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