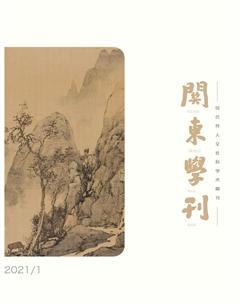清史視野下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說中的“大臣奴才化”現象考察
林晨 張睿穎
[摘 要]二月河在“帝王系列”小說中塑造了大量威名醒目的將相疆臣形象,他們活躍于儲位爭奪、軍事決策、政治改革等諸多環節,同時,二月河卻屢屢賦予他們另一個醒目的身份:皇上或皇子的奴才。這個現象與史實頗有出入,更多的是來自作者的夸張和渲染。結合清史史料和現有歷史研究成果考察二月河的小說文本,可見二月河以“大臣奴才化”的筆法構想康雍乾三代的君臣關系,使權力的爭奪、皇權的鞏固與擴張顯得更為合理正當,亦從側面推高了帝王的形象。此種書寫姿態,迥異于新文學的歷史小說傳統,也不見于古典文學甚至傳統通俗文藝的清史書寫,二月河在一些方面棄新文學傳統而去,其實卻亦未回到古典文學的流脈,而是創造了一個他想象并為之神往的“過去”。
[關鍵詞]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說;“大臣奴才化”現象
[作者簡介]林晨(1977-),男,文學博士,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張睿穎(1997-),女,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二月河(1945-2018)耗時十余年創作的十三卷五百余萬字的“帝王系列”小說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包括《康熙大帝》(共四卷)、《雍正皇帝》(共三卷)及《乾隆皇帝》(共六卷)。版本較多,但每個版本都沒有“再版說明”。本文依據的是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985-1999)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會歷史為背景,以三位帝王的政治生活為中心,勾連了多起重大歷史事件,是新時期以來長篇歷史小說的重要作品。1990年代中期后,二月河聲名漸起,先后榮獲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和湖北省暢銷圖書獎,1999年獲“海外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獎”。同年,隨著《雍正皇帝》(1991-1994)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后在央視一套熱播,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引起了讀者和評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掀起一波“二月河熱”。“帝王系列”小說不僅在海內外多次再版,銷量突破千萬冊(截至2014年),亦引發了中國影視的清宮劇和宮斗劇的熱潮,至今未曾停歇。二月河文學成就之高下雖有爭議,但他無疑堪稱當下最具時代意義的歷史小說作者。
二月河本人在清代史料方面頗下功夫“寫這幾部書,僅僅讀清史是絕對不行的,我對中國的歷史基本上是兩頭熟。小時候讀《史記》、《后漢書》、《晉書》,以后在部隊里又重點讀近代史。就清史而言,不僅要透視重要歷史人物,還要熟悉當時的典稅制度、風土人情。大量的清人筆記,我都購置、研究了,還有些別人不注意,讀起來非常枯燥的東西,如《銀譜》等等,我都細細研究。”(阿琪:《蒼涼悲壯的二月河》,吳圣剛編:《二月河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頁。),也被譽為“根據歷史的真實面目,創造出了一個勤政親民的新皇帝形象”梁樺整理:
《最愛〈雍正皇帝〉這個女兒》,馮興閣、梁樺、劉文平主編:《聚焦“皇帝作家”二月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頁。。“帝王系列”小說中有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清史上威名赫赫的將相疆臣如中樞相臣張廷玉、劉統勛,封疆大吏李衛,統兵大將年羹堯、岳鐘琪都被二月河賦予了另一個微妙而醒目的身份——奴才。雍正朝的三大模范督撫之一的李衛,在小說中的身份卻是被雍正收留的家奴“狗兒”;進士出身的年羹堯則成為胤禛門下的旗奴;就連張廷玉、劉統勛、岳鐘琪等既非仆役甚至亦非旗人的世家出身之漢族重臣,也被寫成動輒磕頭下跪、自稱“奴才”甚至“老奴才”的帝王奴仆。本文力圖從“大臣奴才化”現象入手,將清史史料與相關歷史研究成果與二月河的文學文本進行比照分析,通過研究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說與歷史文獻之間的裂隙,考察二月河書寫和渲染歷史的姿態、分寸與效果,揭示其在文本中寄托的欲望與流露的焦慮。
“奴才”一詞在清朝歷史上本有其特定的含義與用途,涉及滿漢之別、公私之界。滿語里表達主奴關系中下位者的詞匯主要有“阿哈(aha)”、“諸申(jusen)”與“包衣(booi aha)”,其中“阿哈(aha)”對應漢語中的“奴”“奴仆”“奴才”。據學者考證,清入關前“阿哈(aha)”一般指被賞賜給各級將領官兵使役的私屬丁口和因犯罪而被罰入辛者庫的人
祁美琴、崔燦:《包衣身份再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地位極其低下。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直至順治朝,臣下奏事都未以“奴才”自謂。據學者研究,在君臣語境中自稱“奴才”的情形最早出現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滿洲正白旗出身的山東巡撫佛倫的奏折中
參見祁美琴:《清代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此時已是康熙朝中葉,因此,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也很難說是“滿洲舊習”。其后“阿哈(aha)”與“奴才”在滿、漢文奏折中才漸成旗籍大臣的自稱,但終康熙一朝,使用都較混亂亦無定規。雍正皇帝登基伊始即對此問題頒布上諭,明確批評了臣下動輒自稱“奴才”的現象:“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勅諭》,《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65頁。此后,雍正在批閱奏折時,有時甚至會把臣下所寫的“奴才”字樣改為“臣”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中,雍正將“云貴總督卑職留任效力行走奴才高其倬謹奏為奏”中的“奴才”改為“臣”,并寫“向后書臣字得體一樣的”;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改毛文銓折“貴州巡撫奴才毛文銓謹奏為謹陳行伍情形仰祈”中的“奴才”為“臣”并寫“用臣字得體”。([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二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8年,第180、715頁。),以起糾正之效。乾隆皇帝繼位后,對“臣/奴才”的稱謂問題亦屢加界定并敲打臣下,規定旗人公事稱臣,私事稱奴才,漢族文官稱臣,武官稱奴才,這一具銜稱謂問題才基本固定下來。清朝兩代皇帝如此用心界定,可見“臣/奴才”的稱謂并非枝節小事,亦涉及滿漢、公私、文武的界限而不可亂用。但曾對清史頗下功夫的二月河卻不分滿漢、文武與公私,將奴才的身份泛化。這樣的書寫姿態與基本的歷史面貌相左,頗顯刺目,其文學效果也值得進一步分析。
一
“帝王系列”小說中有一批和主人關系極其密切的家奴,包括包衣奴才和賣身給主人的仆役
清代,家奴主要是非包衣籍奴仆的專稱,前者是賤戶,包衣奴才則大多為正戶或有科舉資格的獨立戶口者。(參見祁美琴、崔燦:《包衣身份再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5頁。)二月河既稱魏東亭等包衣奴才是康熙的家奴,又寫李衛這樣被買來的叫花子是胤禛的家奴,與史實有出入,且按小說所寫,李衛的身份應屬于更為低級的“賤戶”類。,如魏東亭、李衛、戴鐸等,他們深受信任,執行著不能通過正常官僚體系完成的隱秘之事。
《康熙大帝》(1985-1989)中的魏東亭是二月河筆下最早的一個醒目的奴才形象,其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二月河自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我的小說《康熙王朝》中有一個人物叫魏東亭,這個人物形象就是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為原型進行創作的。”(張麗:《文學經典中的經典——著名作家二月河談〈紅樓夢〉的價值與啟迪》,《人民政協報》2015年1月26日,第9版。)。曹寅是內務府包衣、正白旗旗鼓佐領下人、康熙乳母孫氏之子,約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入內務府鑾儀衛當差,獲得康熙皇帝賞識,歷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曹寅是直屬于康熙的包衣人,但亦是清代的“官員”,他在奏折中皆稱自己為“臣寅”而非“奴才曹寅”
史景遷指出:“曹寅更多地視自己為漢人,因而自稱‘臣。”([美]史景遷:《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陳引馳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第247頁。)筆者翻閱《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也未見曹寅稱“奴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5年。)。二月河則突出魏東亭的“奴才”屬性而遮蔽他的“官員”身份。他濃墨重彩地書寫魏東亭在康熙身邊做侍讀與侍衛時期的活動,而很簡略地寫魏東亭后期任海關總督之事,并把魏東亭作為臣子的述職活動轉化為奴才與主子重逢的情節。在《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二十六回《魏東亭述職走京師 康熙帝北巡獵猛虎》中,魏東亭回京匯報工作,康熙沒有詢問他作為總督的職務事宜,而親切地問到“家里老小如何?朕的孫阿姆呢?吃得動東西么?”
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70頁。在此,回目和敘述內容之間形成張力:“述職”本應有政務方面的奏對,但主奴時隔多年相見則只親切地拉家常而不談政事。作為和皇帝關系密切的包衣家奴,魏東亭頗得主子賞識與恩典,他也不負主子的栽培,為康熙除鰲拜密謀策劃。在此,二月河打造了一條主明、奴忠、事成的鏈條:唯有被信任的家奴才能參與關乎主子安危的機密事件,也唯有忠心不二的家奴,才能悄無聲息地完成主子交付的差使。奴才的忠誠,亦烘托出主子御下之術中“仁”的一面。康熙皇帝常以“內圣外王”自勵,小說中魏東亭這個赤膽忠心的家奴,正可作為最好的佐證。
同樣承擔密謀與監視職能的還有雍正的家奴李衛。歷史上的李衛本是捐納出身的漢臣,雍正朝三大“模范總督”之一,善治盜,曾在浙江推行“攤丁入畝”,堪稱政績赫赫。李衛既為捐納出身,其家境自然不會太差,二月河卻將李衛改寫成因饑荒而流浪,最終被四阿哥胤禛收為家仆的叫花子“狗兒”,這本身即是一個隱喻:李衛對雍正恰如狗一般忠誠。小說中他無論官職多大,從不“忘本”,始終忠于主子一家,他把自己的兒子命名為“李忠四爺”,對乾隆說“奴才是主子的狗”
二月河:《乾隆皇帝·風華初露》,第32頁。。李衛絕口不提自己在何李鎮救過胤禛命的往事,只強調自己被四爺從苦海拯救,是四爺的奴才——“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
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東逝》,第394頁。,“更”字意味著家奴身份優先于大臣身份。二月河筆下,李衛雖學問不高,但貴在不忘出身,不結黨營私,深得胤禛信任。“九王奪嫡”時期,四爺薦李衛到四川成都府任縣令,實有監視年羹堯之意,李衛果不負所托,專門寫信給胤禛如實報告年羹堯的動態。《雍正皇帝》第三卷第四十六回,雍正又密諭李衛和弘晝秘密設局除掉道士賈士芳。歷史上,雍正時期三位“模范總督”中,鄂爾泰(滿洲鑲藍旗)、田文鏡(漢軍正藍旗,后抬入漢軍正黃旗)都是旗人,按說身份上遠比漢人平民出身的李衛有更正當的做奴才的理由,但二月河卻熱衷鋪敘家奴李衛與主子胤禛及少主子弘歷之間的主奴之情。同時,相較于鄂爾泰之驕傲和田文鏡之隱匿,小說中的奴才李衛能把密事辦理得干凈利落,并對主子永葆忠心,是“模范”中的“模范”。如此書寫,也使皇帝重用自家奴才變得十分正當。
家奴在“九王奪嫡”的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月河小說中皇子的“門人”各為其主密謀策劃,活躍于奪嫡的種種隱秘而關鍵的環節。如十三爺命家奴文七十四照料廢妃鄭春華以防其有不利于太子的輿論;雍正的包衣奴才戴鐸設計查封任伯安的鋪子以打擊八爺黨;九爺的門人任伯安為八爺黨斂財;三阿哥的門人孟光祖游說于陜川廣鄂稱道誠郡王。雖曰各為其主,但二月河筆下皇子們的奴才也有分別:四爺(即雍正)、十三爺的門人往往都是他們從苦海中拯救的,這些家仆門人對主子忠心不二也幾乎都能把機密要務辦得妥帖完備。與之相對,八爺黨的皇子與其門人更多的則是利益聯結,最終也常常反為門人所累。如任伯安雖然是八爺黨的財路子,卻也私抄百官檔案,以此要挾八爺不處置自己“宰白鴨”的罪行;孟光祖過于招搖,為康熙所察,以至連累了三阿哥。二月河有意營造的這種對比彰顯了唯有真的仁德皇子才能得人心以成大事,進而使雍正奪嫡顯得理直氣壯。
二月河反復搬演“主子清明仁慈、奴才忠誠事主、主奴合力成事”的情節,以奴才為橋梁,使主子謀求權力的“大業”鋪展得合情合理。計除權臣、監視官員、謀殺道士、輔助奪嫡,“帝王系列”中家奴所執行的密謀任務,本來皆是權斗過程中最具陰謀色彩的情節,但密事被托付給赤膽忠心的家奴后,小說書寫的重心則轉向了主奴相親之情,原有的權謀陰影被主奴互信的面紗輕巧地掩蓋了。家奴對密事運作的必要性也體現出二月河對專制狀態下權力運作的一種想象:上下位者的私人關系遠比利益關系甚至制度關系更為牢固可靠。
二
八旗制度下皇帝統領上三旗,宗室王公分管下五旗,各旗主與其所統領的旗下屬人具有主屬關系。在“帝王系列”小說中,不少叱咤風云的將軍都被放置在主屬框架中書寫,如王輔臣、年羹堯、傅恒等。有趣的是,年羹堯本為正身旗人,卻被二月河塑造為胤禛門下沒有獨立戶籍的“旗奴”;王輔臣是漢人平民出身,卻被二月河“抬”入漢軍正紅旗成為康熙皇帝的奴才。其中年羹堯是二月河最濃墨重彩塑造的人物。
歷史上年羹堯之死是雍正朝觸目驚心的大案。雍正即位之初,對年羹堯倚重有加,但短短三年后,就以九十二條大罪賜其自盡。幾乎所有歷史研究都把年案視為雍正朝權力斗爭殘酷性的體現,有些研究者甚至以此案推論雍正的性格:韋慶遠教授就認為從中“可看到雍正多疑、擅用權術和手段狠刻。”
韋慶遠:《論雍正其人》,《史學輯刊》2000年第3期。即使是力主為雍正“翻案”的馮爾康教授也指出,雍正殺年羹堯的性質是君主與大臣的權力分配斗爭:“雍正作孽于前,后又專尚殘酷打擊,表現了君主權力的絕對性和他本人的殘忍性”
馮爾康:《雍正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127頁。。因此,對二月河而言,如何書寫年羹堯之死,直接影響對雍正形象的塑造。二月河選擇了一條輕便的路徑:將年羹堯塑造為一個驕縱且有二心的“旗奴”,把“鳥盡弓藏”的政治斗爭轉化為事主不忠誠的旗奴的咎由自取,遮蓋了權力斗爭的殘酷性與胤禛性格的陰暗面。這種改寫相當特殊,無論是嚴肅的歷史研究還是“帝王系列”小說之前的有關年羹堯事件的評書、小說、戲曲等通俗文藝,都從未曾強調年羹堯的奴才身份,二月河則另辟蹊徑,濃墨重彩地渲染了年羹堯的旗奴身份及其與胤禛的主奴關系。
歷史上,年羹堯原為漢軍鑲白旗人
《清史稿·列傳八十二 年羹堯》中記“年羹堯……漢軍鑲黃旗人”(趙爾巽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355頁),是就最終身份而論。《四川通志》“年羹堯,鑲白旗進士,康熙四十八年任(巡撫)”,“年羹堯,鑲白旗進士,康熙六十年任(總督)”(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職官》,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0冊,第654頁)的記載說明,年羹堯在康熙朝是鑲白旗人,結合雍正元年年希堯的謝恩折所說:“皇上天恩將奴才一族……俱調入鑲黃旗”(《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年希堯奏謝將合族調入鑲黃旗折》(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一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頁),可見年家在雍正即位后被抬入鑲黃旗。,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皇子胤禛被封雍親王,并充任鑲白旗屬主,年家所在的旗分佐領被劃撥到雍親王門下,年羹堯作為旗下屬人,與屬主雍親王的隸屬關系其實相當松散,談不上明確的“主奴關系”,這從雍親王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致年羹堯信中也可窺知一二,此信中雍親王即借年羹堯在信中稱職位而不稱奴才而痛斥他不守規矩、不尊本主:“國朝祖宗制度,各王門旗屬,主仆稱呼,永垂久遠,俱有深意,爾狂昧無知,具啟稱職,出自何典?……又何必稱我為主!既稱為主,又何不可自稱奴才耶!”
《雍親王致年羹堯書真跡》(康熙五十六年),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第一輯,北平:和濟印刷局,1930年,照片頁。年羹堯在給胤禛的私人書信都不稱奴而稱職正顯示出當時胤禛與年羹堯并非緊密的主奴關系,年羹堯以封疆大吏自居而并不十分認同自己是胤禛的奴才。但“帝王系列”小說中的胤禛和年羹堯則有明確的主奴關系。《康熙大帝》中,康熙五十八年,胤禛在訓斥年羹堯時說:“說到底,你是我門下旗奴”
二月河:《康熙大帝·亂起蕭墻》,第325頁。,后又提到:“他(高福兒)本來能學年羹堯、戴鐸,脫去奴籍為我門下,出去做官。”
二月河:《康熙大帝·亂起蕭墻》,第331頁。可見,小說中年羹堯不僅僅是隸屬于雍親王旗下的寬泛意義上的“奴才”,還是低賤的有“奴籍”的奴才;雍年二人的主奴分界甚至是“造化安排的”:《雍正皇帝》第一卷,“年軍門”回京述職,先去拜見八爺而沒有先去雍親王府,惹怒了胤禛,四阿哥在年羹堯上門謝罪時一邊啜著奶子泡著腳,一邊發作:“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腳吃奶子,你畢恭畢敬站著回話,這原本不公道,但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你回京述職,見了萬歲就該見我,見不著我,你還有三個少主子,還有福晉,怎么就想不起來?”
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奪嫡》,第365頁。
“帝王系列”中年羹堯不僅是胤禛的“旗奴”,其得以升遷,也全仰仗主子之力。歷史上,年羹堯在結識胤禛之前就已是一個少年得志、靠自身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前途大好的文官。他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中進士,并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經“散館”考試授翰林院檢討。庶吉士是二、三甲的進士中的佼佼者,“一旦被留館為翰林,即有當宰輔的希望”。
吳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對比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庶吉士出身并入選翰林的年羹堯出路優越,前程遠大。此后,年羹堯的晉升也確實相當迅速,據清史稿記載,他“迭充四川、廣東鄉試考官,累遷內閣學士”
趙爾巽編:《清史稿》卷二九五《列傳八十二 年羹堯》,第10355頁。。因此,在年家所在佐領被劃歸到雍親王統領之前,不到三十歲的年羹堯就已經是憑借個人能力獲得較高地位的朝廷新貴了。但“帝王系列”小說中的年羹堯科舉上的出色經歷被抹去了,而變成在成為胤禛的旗下屬人之前只是葛禮門下的一個普通的下級軍官,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御駕親征準噶爾時,年羹堯也才是一員參將,直至在四爺藩屬當差受到胤禛的提攜后,年羹堯才得以從寒微處起步,一路扶搖直上,繼而擔任四川巡撫和提督等重要職位。《康熙大帝》第四卷,二月河寫道:“胤禛、胤祥明面兒上幫胤礽料理部務,一邊兢兢業業辦差,不知不覺的已將年羹堯晉為四川巡撫。”
二月河:《康熙大帝·亂起蕭墻》,第238頁。《雍正皇帝》第一卷更是將年羹堯受任四川提督的原因寫為年羹堯“幫助”四爺和十三爺在桐城辦好了鹽務差使:“萬歲爺說桐城的差使辦得好,給太子爺和四爺露了臉。因四川提督出缺,就補了上來。”
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奪嫡》,第108頁。簡言之,二月河筆下的年羹堯是被胤禛一手栽培出來的,他獲得晉升并非因為個人努力,而是受益于和胤禛的主奴關系。故小說中雍正即位時年羹堯算不上先朝功臣,只是雍親王的藩邸奴才,對新君有絕對的人身依附關系。借此,二月河強化了雍年關系中的私人聯結。清代“在朝廷稱君臣,在本門稱主仆”
《雍親王致年羹堯書真跡》(康熙五十六年),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第一輯,照片頁。的通行常例意味著“君臣/主仆”不僅僅是稱謂問題,還顯示出公私分際的微妙之處。歷史上雍正即位后頒布的“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勅諭》,《欽定八旗通志》,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4冊,第165頁。的諭令則有防止臣子稱奴以媚上的意圖,事實上遍檢雍正時期年羹堯的滿漢奏折,年羹堯也無一處自稱奴才
筆者根據季永海、李盤勝、謝志寧翻譯點校《年羹堯滿漢奏折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所提供的奏折統計。即使是謝恩折、請安折年羹堯也具銜稱“臣年羹堯”。,但二月河在小說中不厭其煩地渲染年羹堯的旗奴身份以及他依憑和主子的私人關系獲得的恩賞,重新勾勒了雍年關系及二人形象。“帝王系列”中,年大將軍既是雍正的藩屬又因主子胤禛提拔才得以升遷,就理當感念君恩、忠心不二。然而,年羹堯在九王奪嫡時期就與八爺黨過從甚密,雍正三年在汪景祺和九爺胤禟的策動下又意圖謀反,可謂大逆不道,是一驕縱犯上背主負恩的“逆奴”。因此,雍正定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并勒令其自盡,并非是兔死狗烹枉殺功臣,而是主人對叛主奴才的合理懲罰。
二月河將年羹堯定位為“奴才”,看似只是改寫了他科舉仕途和大將軍的身份,實際上起到了淡化權力斗爭殘酷性與美化皇帝形象的作用。皇帝與武將之間的權力爭奪是傳統中國政治活動中最常見的斗爭類型之一。二月河通過強化大將軍的奴才身份將殘酷的權力收束轉變為主人對逆奴的懲戒,使本來陰鷙詭譎的權斗和權術,變得情理俱足,消解了功臣被誅的悲劇色彩,也回避了對皇權專制殘酷性的反思。同時,二月河用曲折的文學筆法把罪過轉移到奴才一方,磨洗掉皇帝主子性格里的陰暗面。他不無繾綣地抒寫雍正皇帝在誅殺奴才年羹堯時的內心掙扎與不忍:“他不肯自盡,朕終是不忍下辣手啊!他與你們不同,和朕是有私交的”
二月河:《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第438頁。,原來,奴才雖然忤逆但主子卻畢竟深情,從而竟可召喚出“歌頌”
“帝王將相不可以歌頌嗎?歌頌他們便是反民主?……只要在歷史上曾經對改善當時人民生活,對推動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對鞏固當時國家和平一統文學藝術昌明,對當時民族團結曾經作出過積極努力和貢獻的人……就是要歌頌,管你說什么!”(二月河:《由蔡東藩歷史演義所思》,《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帝王的主題。
三
在“帝王系列”小說中,張廷玉、劉統勛、劉墉等在朝廷中樞里鼎足輕重的漢族大臣也被二月河塑造為動輒跪下謝恩謝罪的奴才。歷史上,康雍乾三位皇帝從未要求漢族文臣稱奴才,乾隆皇帝更是屢次對臣子奏折里稱臣、稱奴才的問題加以界定,不允許漢族文臣自稱奴才
參見:《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諭》,《清實錄》第2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影印版,第21019頁。。事實上,歷史上漢族文官稱“奴”往往是“自賤其身”
歷史學家杜家驥(1949-)指出:“奴才本是一種對主子私人而言的低賤身份,同時又因這種私人色彩的關系而可得到皇帝的特殊恩惠,那些口口聲聲在皇帝面前自稱犬馬奴才的官員,就不無這種意思。而有些漢人官員也不惜為此自賤其身,對皇帝而自稱奴才,仰其鼻息,乃至遭到皇帝的制止,無恥至極。”(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第556-557頁。)。同樣是歷史小說作家的高陽(1922-1992),素以精通史實著稱,他在《慈禧全傳》(1984)中對此還特意寫到一筆,漢臣鮑超在慈禧太后面前自稱奴才便引起了反感,太后認為他“有意自附于旗下”
高陽:《慈禧全傳·清宮外史(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72頁。。但二月河對歷史上皇帝對“臣/奴”稱謂的界定及其背后的滿漢沖突問題似乎并不在意,在他筆下,岳鐘琪、張廷玉、劉統勛等漢族大臣自稱“奴才”或“老奴才”,非但與“自賤”“媚上”無關,反而還是和皇帝皇子關系親密、深得主子信任愛重的證明。
在被二月河改寫為“奴才”的漢臣中,三朝宰相張廷玉的形象格外醒目。歷史上,張廷玉家世清華,其高祖張淳明朝時官至陜西布政使,曾祖張士維官至中憲大夫,父親張英于康熙六年中進士,后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進士,歷任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要職,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廟的漢臣。張英張廷玉二代為相,素有“父子雙學士,老小二宰相”的美譽。這樣一位出身儒學士大夫世家的漢族相臣,在“帝王系列”中,竟也難逃被奴才化的命運。首先,二月河把張廷玉的出身改寫為“恩蔭進士”
“張廷玉是恩蔭進士,不過沾了祖上的光罷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奪嫡》,第51頁。),并非憑個人能力考取功名,而是沾了祖上的光才被賞賜了進士出身。其次,屢屢敘述甚至渲染張廷玉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比如張廷玉在議論任伯安案時,不小心多言觸了康熙霉頭,便撲通一下跪倒在地,喊道“奴才該死!”
二月河:《康熙大帝·亂起蕭墻》,第224頁。又如康熙二廢太子后宣布永不再立太子,一旁的方苞還沒言聲,張廷玉就趕忙贊頌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大清太祖、太宗皇帝也沒有預立太子,國家反而日臻隆治,奴才以為皇上想得很對!”
二月河:《康熙大帝·亂起蕭墻》,第249頁。到了雍正朝,張廷玉面對當時還是皇子的弘歷向其求字時,也“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老奴才怎么當得起?爺的字比奴才的強十倍呢!”
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東逝》,第254頁。既是“老奴才”,也就難免昏聵而不識大體,小說中張廷玉在乾隆朝政事一團亂麻時卻接連登殿奏本,要求身后配享太廟,并要乾隆寫字據為證頒發天下,而被乾隆斥責。把漢族宰相寫成“奴才”和“老奴才”本已與史實有出入,二月河在《乾隆皇帝》(1995-1999)中竟還借紀昀之口說:“張廷玉是抬了旗籍的,訥親就是旗主。”
二月河:《乾隆皇帝·秋聲紫苑》,第121頁。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歷史材料可以證明漢人張廷玉曾入旗。有趣的是,二月河對張廷玉的“旗籍”也只在此提了一句,前文并無鋪墊,后文也再無回應,這既無所來又無所去的莫名其妙的一筆,文學上頗顯突兀,卻給張廷玉鎖定了“旗奴”的身份。
乾隆朝的劉統勛本是翰林出身的一代名臣,在吏治、河工治理方面都貢獻頗大,歷史上乾隆皇帝曾贊揚他“如統勛乃不愧真宰相”
趙爾巽編:《清史稿》卷三百二《列傳八十九 劉統勛》,第10466頁。,但二月河對此只字不提,卻花大量篇幅寫劉統勛與皇帝皇后之間的主奴互動。小說《乾隆皇帝》中多次寫皇后賜劉統勛吃食與衣物,如在元宵節劉統勛巡街前賜魚頭豆腐火鍋,在劉統勛出外辦差時賜貂裘,端午節考慮到劉統勛心脾不受用,特賜紫金活絡丹……劉統勛每次受到賞賜,都感激涕零,伏地叩頭,流淚謝恩:“謝主子,謝主子娘娘……”
二月河:《乾隆皇帝·風華初露》,第181頁。既然娘娘是“主子”,那么自己當然就是“奴才”。值得說明的是,“主子娘娘”并非清代大臣對皇后的應有稱呼,而出于二月河的臆測。據學者研究,只有太監、宮女們才對皇后當面稱“皇后主子”,背后則稱呼為“主子娘娘”
朱家溍:《德齡、容齡所著書中的史實錯誤》,中央文史研究館編:《崇文集二編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72頁。。二月河讓劉統勛等大臣稱皇后為“主子娘娘”,不但把大臣擺在“奴”的位置,甚至卑下如同宮女太監。皇后既然是“主子娘娘”,那么,“真宰相”劉統勛自然還要以皇子為“小主子”,小說中乾隆在轉劉統勛閱的奏事折下加了一行朱批小字:“皇后亦甚惦記汝,賜貂裘一襲,行將馳送。你小主子要一件民間百衲衣,你可代主子娘娘留心物色。”二月河:《乾隆皇帝·夕照空山》,第396頁。二月河把討論金川之役的公務和主子對奴才的家事囑托共置在一份奏折中,國與家的界限、公與私的分際模糊不清,參與朝政的官員不再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0頁。的大臣,而是皇帝的私屬奴仆。清代文人謳歌康雍乾三朝君臣同心、創造盛世的筆法本已肉麻,二月河顯然更進了一步:不僅是君臣一心,原來竟是“主仁奴忠”。
“帝王系列”小說中,有資格稱“奴才”的漢臣大部分是與皇帝關系親密、同心同德的近臣乃至中樞宰相。相反,郭琇、史貽直、竇光鼐這類不在中樞核心且不分時宜、直言犯諫的漢臣就從未獲得“奴才”身份,他們冒死犯顏的勸諫行為也屢屢被皇帝指責為沾染了“漢人的壞習氣”——“沽名釣譽”
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169頁。。尤有意味的是,皇帝總能識破諍臣狂妄的忠言里意欲留名青史的私心,總是偏不加諸酷刑而是溫言撫慰,劍拔弩張的氣氛一旦解除,郭琇等人就不再直犯龍顏,反倒哽咽著膝行君前徐徐提出維護統治的懇切建議
康熙在郭琇進諫時先是大怒后召其入正廳講話,郭琇建議把“天下實得于李自成之手”的道理頒之學官,曉諭天下。(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212頁。)。如果身處大清朝權力核心的漢族相臣也不過是皇族的奴仆,莽撞好名的諍臣只是要以大不敬之言吸引皇帝的恩寵,那么傳統儒家“從道不從君”的道統就在無形中被消解了。歷史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努力通過編輯理學典籍、堅持經筵日講及晉謁孔廟等舉措,漸以“治統”兼并“道統”,使“君”與“師”的身份集于皇帝一人,其中頗有深意
關于清代帝王“道治合一”的具體舉措,可參見南開大學劉方玲2010年的博士學位論文《清朝前期帝王道統形象的建立》。。但二月河在“帝王系列”中并不費心描繪清代帝王兼并“道統”的復雜過程,而采取了一種更為輕巧的辦法解除“道統”對“治統”的制約作用,令漢臣“失聲”:將宰相塑造為奴才,從而抹殺了儒家士大夫的相對獨立性。
結語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小說中,從未有人像二月河這樣普遍、大量、夸張地書寫奴才形象。凌力(1942-2018)、唐浩明(1946-)、高陽的清史敘事也只是依史實將太監宮女和一部分旗人官員寫作奴才,未曾跨出歷史上“奴才”本來的界限,更未津津樂道地鋪展主奴之情。有清一代,君臣關系確實伴有一定的主奴特性。八旗制度中,上三旗由皇帝親自統領,隨著中央集權加強,本非皇帝領屬的下五旗人也漸漸統屬于皇帝之下,成為皇帝的奴才
“隨著八分體制的瓦解,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這些旗人(下五旗旗人)也與他們的主子宗室王公一樣,都已成為皇帝的臣仆”(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第310頁)。。不過,相較于史實,二月河更為夸張地泛化了“奴才”的范疇,不分滿漢、不論文武、不顧出身,以至從統兵大將到朝廷的中樞宰相,無處不見“奴才”,無處沒有濃厚的主奴之情。主奴互信的面紗遮蔽了皇帝與權臣、皇子與皇子之間權力斗爭的陰謀意味,“逆奴”叛主而咎由自取淡化了君王的殘酷與陰謀,中樞相臣被籠入溫情脈脈的主奴關系則漸次消解了儒家士子們秉持的“道統”,由此,權力的爭奪、皇權的鞏固與集中都似乎顯得合情合理。
“帝王系列”小說里帝王成就偉業的過程中,人格獨立的大臣近半并不可靠,自家的奴才則最是得心應手,“人治”甚至專制的色彩,在“大臣奴才化”筆法的推動之下,可謂達至頂峰。這一書寫結構亦從側面推高了帝王的形象:家奴的忠心不二成為皇上乃仁慈之主且知人善任的絕佳注腳;大將軍年羹堯原來不過一叛主逆奴,則自然抹去了雍正帝的權謀與陰鷙;奴才化的漢族相臣亦使清朝帝王之兼作君師合情合理。更重要的,奴才與主子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系,為奴才者為主子肝腦涂地是“造化”定出的本分。他們不是需要以禮相待甚至三顧茅廬的“士”,唐太宗名言“驅駕英材,推心待士”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六十三,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9冊,第574頁。所標志的為君美德用不到他們身上,奴才即使出將入相也不可以凌煙閣名臣自居——“老奴才”張廷玉不就因為強求配享太廟而觸了霉頭?因此,奴才們所建立的所有功勛都以更直接的路徑歸功主君一身。
但是,這樣將名臣大將紛紛寫成奴才的筆法,非但與史實不符,也是新文學傳統下的歷史小說中所未有,甚至不見于曾為新文學摒斥為“非人的文學”的通俗小說、評書、戲曲等傳統文藝——即使是清末《劉公案》那樣的通俗公案小說,亦未曾將“劉公”寫成奴才。“帝王系列”小說中盡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自得,而與“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思想南轅北轍。若以魯迅《燈下漫筆》的范式觀之,“帝王系列”小說中康雍乾三代圣君腳下匍匐著的盡是奴才身份的大臣,這是否算得更為夸張的“人肉的筵宴”?從對二月河筆下“大臣奴才化”這一不見于此前任何一種文學傳統的書寫姿態的考察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二月河在一些方面棄新文學傳統掉頭而去,其實卻亦未回到古典文學甚至是傳統通俗文學的流脈,而是創造了一個他想象并為之神往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