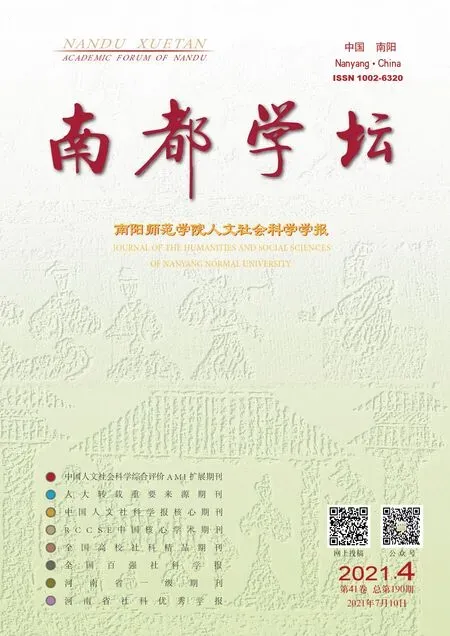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創作的一體性
李 明
(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中文系,陜西 西安 710054)
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特點,古代文論界曾有很多總結。有的學者總結古代文學批評的特有方法,如意象批評、人化批評等;有的學者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立論,指出古代文學批評思維具有直覺思維、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等特點;有的學者從話語方式上入手,指出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模糊性,以及缺少體系性等特點;有的學者則聚焦文體問題,揭示古代文學批評文體的演變過程和文備眾體的特點(1)對古代文學批評的方法、思維方式、話語方式和批評文體等方面研究的綜述,可以參考黃念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東方叢刊》2004年第3期)、蔣述卓等《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陳水云《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術檔案》(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論著。。值得注意的是,羅根澤、朱東潤、彭玉平等學者已經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另外一個本質性特點,即文學批評與創作實踐的一體性。他們雖然強調了這一特點的重要性,但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本文試圖從以下幾方面來論述這一特點的具體內涵和啟示意義。
一、批評家與作家身份的一致性
西方一向有獨立的批評家職業。羅根澤先生如是總結西方批評史:“他們自羅馬的鼎盛時代,以至18世紀以前,盛行著‘判官式的批評’,有一班人專門以批評為業,自己不創作,卻根據幾條文學公式,挑剔別人的作品。由是為作家憎惡,結下不解的冤仇。19世紀以后,才逐漸客氣,由判官的交椅,降為作家與讀者的介紹人。”[1]13但羅先生所說并不準確。按照法國批評家蒂博代的判斷,西方的職業批評在18、19世紀之后恰恰達到了頂峰,他在其《六說文學批評》一書中即總結了自18世紀伏爾泰以來職業批評的發展史,認為:“就職業批評而言,這個批評如此普及和如此強大的十八世紀,只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段罷了。”[2]“這個偉大的時代,應該等到十九世紀。”[2]總之,西方獨立批評家的歷史是由來已久了。
與西方極為不同的是,中國古代的批評家往往就是文人。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了這種批評家與作者身份的一致性。如羅根澤先生說:“在中國,從來不把批評視為一種專門事業。”[1]13“所以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沒有多少批評專家。”[1]13朱東潤先生也指出:“吾國文學批評家,大抵身為作家,至于批判今古,不過視為余事。”[3]美國學者李又安則從中西方文學批評比較的角度來談論這種差別:“中國批評家本人是詩人或是散文家,他們有意識地實踐著這一藝術,他們針對這一藝術帶來自己的批評力量。在西方,我們可以想到詩人批評家如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和艾略特等眾多人士,或小說家批評家弗斯特等人。然而我們也對西方這一現象十分熟悉,即批評家并不對他所評論的文類加以實踐。而這類人在中國就十分罕見,劉勰即屬此類,他僅以《文心雕龍》而著稱于世。”[4]如李又安所說,西方批評家除了少數兼任作家外,大部分是屬于獨立的批評者。而絕大部分的中國古代批評家往往就是作家。李又安舉劉勰作為例外,但實際上劉勰并不例外。《梁書·劉勰傳》謂劉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劉勰制文。”[5]又言其有“文集行于世”[5]。可見,劉勰亦非不能文者也。
批評家與作者身份的一致性,是緣于古人的這樣一種觀念,即只有諳熟創作之甘苦,才有資格評論詩文。如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所說:“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如果文章寫得不好,是沒有資格評論作者的,所以他反對的是“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6]。對于其中的道理,清人徐增解釋得比較清楚:“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棋力酒量,不可勉強也。”[7]442又說:“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腳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個個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7]442對詩文的創作原理有長時間的深切體驗,才能達到“一覽眾山小”的批評家的地位。方孝岳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所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批評家固然站在旁觀的地位,但是天下事往往要身歷其境的人才能說得清楚;隔岸觀火,終不能得其究竟。我們時常聽見人家說‘眼高手低’,又有人說‘眼有神,筆有思’,這就是說只能批評而不能動筆。這種人比較既能評又能作的人,就不免相差一籌了。”[8]寫得好才能評得切,這種觀點在職業批評家看來,顯然是不必要的要求。職業批評家只需要判斷作者是否符合自己認為正確的批評觀念和理論體系,而古人則認為批評的內容應該是創作上的得失。對“批評”的不同理解也就導致了對批評家資質的不同要求。
中國古代很多詩話的作者在自道寫作淵源的時候,都往往強調自己是經過多年學詩而深得其甘苦的。清代黃子云在《野鴻詩的》序言中說:“余經三十年困苦中研出,故不得不以授人。”[7]879又如張謙宜在《繭齋詩談》卷三中的自敘:“吾嘗與高大將軍語,囑曰:‘君輩慎勿談兵,非身歷行伍,九死一生,豈知此中消息。’噫!吾十三學詩,今五十五稔矣,刀痕箭瘢,遍體鱗皴,然后敢為后生言。”[9]809在古人看來,沒有扎實的創作經驗就率而談詩,無異于紙上談兵了。很多人在為他人的詩話作序跋的時候,也往往以作者的詩學創作功夫作為詩話值得信賴的原因。如王鐸序李東陽《麓堂詩話》:“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騭折中,如老吏斷獄,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于是亦云。”[9]1399鮑廷博在為《麓堂詩話》所作的跋中亦云:“李文正公以詩鳴成弘間,力追正始,為一代宗匠。所著《懷麓堂集》,至今為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中議論,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9]1400
作為重要批評形式的詩注也是如此。古人認為,必須要對詩學有深厚的體驗,才能做好詩的注釋。錢大昕序許寶善《杜詩注釋》云:“故嘗謂注詩者,必深于詩。未達乎詩教之源,未究乎詩律之細,未討論乎詩人出處本末,性情旨趣之所屬,雖日從事于鉛,猶無當也。”[10]錢大昕所說的“深于詩”應包括善寫詩。當代詩學大家陳永正先生在其《詩注要義》中總結歷代注者之擅詩:“古代注家多能文擅詩,《山谷詩集注》作者任淵早年曾受黃庭堅指導詩歌創作,《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作者趙次公曾‘且注且和’蘇軾詩,《王荊公詩注》作者李壁‘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現代注詩大家黃節、瞿蛻園、王蘧常、錢仲聯、白敦仁等更是杰出的詩人,他們既能詩,又熟悉所注釋對象的創作風格,為其詩作注,優自為之。”[11]由陳先生所言可見,創作經驗對于注詩之重要。
好的選本也需要選家對詩有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理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指出:“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12]1376清初人沈荃《莼閣詩藏·序》也認為:“予謂必胸羅萬卷,具八叉七步之才,玉衡冰鑒之識,然后揚榷品題,不差累黍。否則蒙瞍之操埏埴耳。”[13]“八叉七步之才”即出色的創作才華。有足夠的創作才華才能有李東陽所說的足以選詩的“識”力。
如上所論,批評需要一定的創作能力。但另一方面要說的是,從事創作也需要高超的批評能力。創作是需要建立在對前人作品學習的基礎之上的,尤其對于中國古典詩文來說,模擬前人是一個必經階段(2)程千帆《文論十箋》卷下《模擬》篇、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論》第二章第三節“古代文學史上的模擬之風”等文章對古代文學中的模擬之風有詳細分析,可以參考。。而以什么樣的作品為學習和模擬之對象,乃至如何學習、模擬,都需要對前代詩文的體制和演變進行一番辨體。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14]136關于“家數”,清代何世璂《燃燈記聞》記王士禎語有詳細舉例:“為詩要窮源流。先辨別諸家之派,如何者為曹劉、何者為沈宋,何者為陶謝,何者為王孟,何者為高岑,何者為李杜,何者為錢劉,何者為元白,何者為昌黎,何者為大歷十才子,何者為賈孟,何者為溫李,何者為唐,何者為北宋,何者為南宋。”[7]123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徑,不可墮入魔道。”[7]123當然,古人學習和模擬前人,最終是希望能夠通過模擬達到“脫化”而形成自己的面目。但即便如此,學習和模擬也是達到“脫化”的必要過程。如葉矯然《龍性堂詩話》謝天樞序引葉氏語所言:“詩不能自為我一人之詩,為之何益?然非盡見古人之詩,而溯其源流,折中其是非,必不能自為我一人之詩也。”[9]933可見,識古今體制源流、雅俗的文學批評能力,是創作的前提條件。
這種創作所需的評鑒能力也就是古人常說的“正法眼”“具眼”或所謂的“識”。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中指出以“正法眼”來辨別“第一義”的重要性:“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14]11盡管嚴羽以魏晉盛唐詩為“悟第一義”的觀點可以商榷,但對初學者來說,具有對前代詩史的判斷力還是很重要的。又如清代薛雪論“具眼”:“讀書先要具眼,然后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為率俗,纖弱為工致,悠揚婉轉為淺薄,忠厚懇惻為粗鄙,奇怪險僻為博雅,佶屈荒誕為高古,才是學者。”[15]95在這段話中,薛雪所說的“具眼”則指學詩者應該能夠正確把握風格,避免詩病。古人學詩又常常強調“識”的重要性。如吳雷發《說詩菅蒯》:“筆墨之事,俱尚有才,而詩為甚,才與識實相互表里。”[7]933“詩須多做,做多則漸生才識也。然必有才識者方許多做,不然,如不識路者,愈走愈遠矣。”[7]933葉燮《原詩·內篇下》中所論才、膽、識、力四種“在我者”的主體要素中,特別突出“識”的重要性:“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為體而才為用,若不足于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15]24“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為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響于耳,含糊于心,附會于口,而眼光從無著處,即歷代之詩陳于前,何所抉擇?何所適從?”[15]24“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此地前哲,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15]24學詩者要學習前人,必須練就能夠通古來作者之意和古今詩家之論的“識”力,這也就是要求詩人必須要具備很高的批評能力。
二、批評與創作之循環
批評與創作互為前提,形成一個循環。這包含著兩個層次的意思。
第一,批評從創作中來。西方文學批評的命題與體系,多從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學科中衍生而來。如柏拉圖的“模仿說”即從他的“理念”哲學而來,茵加登的文學理論是從現象學而來,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從索緒爾語言學發展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則以其社會學為基礎,等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也受到經學思想、道家思想、理學思潮等方面的影響,但主要的源動力則來自于各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如鐘嶸所提出的“直尋”命題即是針對當時用典繁縟的文風而言,殷璠的“興象”和“風骨”論則是對盛唐詩風的總結,江西派詩人的“活法”詩論也是針對江西派末流詩風過于生硬晦澀的弊端而提出。正如羅宗強先生所總結的:“中國古代許多文學批評范疇的出現,都和創作中某種文學思想、文學思潮有關。”[16]
第二,批評的目的是為了指導創作。對于中國古代的詩文評而言,批評不是為了客觀的裁判,也不只是為了促進對作品的理解,而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后進詩人提高寫作水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小序論詩文評之功能云:“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歟。”[17]“有裨于文章”正是詩文評的重要意義所在。在這種批評目的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內容以探討創作技巧得失的“創作論”為主,就不足為奇了。羅根澤先生就曾指出:“西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理論。”[1]12他所講的“文學理論”不是指作為當代學科的“文學理論”,而是指詩文創作的原則和技巧之類。孫紹振先生也指出:“中國古典詩論與西方之根本差異,在于其基礎為創作論。”[18]如《文心雕龍》的主體是“論文敘筆”的20篇文體論和“剖情析采”的19篇創作論,都以指導創作為目的。唐代流行的詩格詩式類著作,也都是以作詩的聲律、對仗、句法等法式為主的,備陳法律,目的是以曉初學。從宋代開始大興的詩話,除了“旁采故實”和“體兼說部”之外,也在于通過技巧的談論來啟發后學。如姜夔在《白石道人詩說》中點明用意曰:“詩話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19]683其實,不要說“不能作者”,即使“能作者”,又何嘗不能得益。又如清人李沂《秋星閣詩話》張潮跋曰:“有以評古人詩為話者,有以教今人作詩為話者。夫古人之詩,即微我之評,亦復何損?若夫教今人作詩,則其話為有功矣。”[7]943其實張潮所說的“評古人詩為話者”又何嘗不是給學詩者以門徑呢?
批評從創作中來,又指導創作,由此,批評與創作就形成了一個循環,略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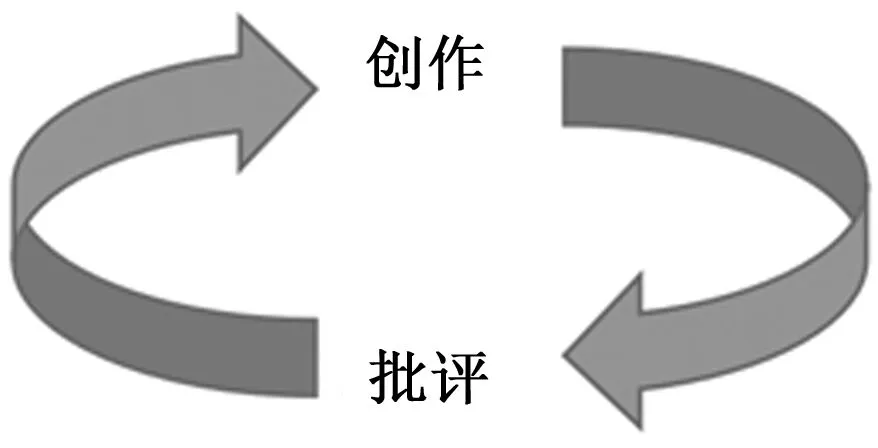
三、創作與批評的文體同一性
西方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在文體上大多具有各自的獨立性。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等古希臘羅馬的批評著作開始,西方文學批評的主要文體就是以成體系的理論篇章為主,與文學作品是斷然不同的。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卻與文學文體緊密交融在一起。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首先,古代文學批評的很多篇章都是以文學的體式存在的。《文心雕龍》是以精美的駢文寫成,陸機的《文賦》則是以賦的形式出現。自杜甫的《戲為六絕句》《解悶五首》等論詩絕句以來,歷代的論詩詩又蔚為大觀,如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等。這些篇章既是文學創作,也是文學批評,可謂一體而兩用。
其次,就言說方式而言,古代文學批評大多不是抽象式、邏輯式的,而是形象的、隱喻的,是詩性的批評。如鐘嶸在《詩品》中評價范云和丘遲詩的風格:“范詩輕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19]15《南史·顏延之傳》載鮑照評論謝靈運與顏延之詩:“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雕繢滿眼。”[20]又如敖陶孫《詩評》用隱喻的方式評論歷代二三十位詩人的風格,如評論曹氏父子:“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21]在語言批評的層面,古人也往往用隱喻論之,如唐代詩格中用“芙蓉映水”“龍行虎步”等“勢”來言句法,又如金圣嘆用“烘云托月法”“草蛇灰線法”等比喻論篇法,等等。這樣的意象式批評在古代文學批評的各種文體中俯拾即是。從根本上說,這種話語方式的形成是由古人對“言”“意”關系的看法決定的。《周易·系辭》中說:“言不盡意。”又說:“立象以盡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也進一步發揮,認為:“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22]“盡意莫若象”[22]。同樣,文學作品之“意”也是無法用分析性的“言”來論說的,而以“象”來言,更能得之。
四、從“知行合一”到“作評合一”
詩學上創作與批評的合一性正是中國思想“知行合一”的呈現。西方哲學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知識。亞里士多德將理智分為“沉思的理智”和“實踐的理智”:“沉思的理智同實踐與制作沒有關系。它的狀態的好壞只在于它獲得的東西是真是假。獲得真其實是理智的每個部分的活動,但是實踐的理智的活動是獲得相應于遵循著邏各斯的欲求的真。”[23]可見,西方思想注重追求與“行”無關的純粹之“知”。而中國傳統思想卻多認為“知”和“行”是一體的。
中國人秉持著一種“實用理性”,并不以與行動無關的純粹之“知”為最高追求。中國傳統思想認為,相對“知”來說,“行”是最終的目標。《荀子·儒效》篇云:“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圣人。”[24]劉向《說苑·政理》也說:“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25]可見,對于中國思想來說,“知”不是純粹之知,而是找到“行”的方向和方法。另外,與“行”無關的“言”,古人認為是空說,墨子稱為“蕩口”:“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尚)之,是謂蕩口也。”[26]可見,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尚用是重于求知的。
“知”離不開“行”,“行”也離不開“知”,由此有宋明儒學所提倡的“知行合一”之說。他們認為,只有“行”了才是真“知”,如《二程遺書》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27]朱熹也主張“知”和“行”是一體的,是互相促進的:“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28]148又云:“知與行,功夫須著并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28]281在這種思想傳統下,才有了王陽明著名的“知行合一”之說。《傳習錄》云:“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9]19
在“知行合一”的思想傳統下,古典詩學中創作與批評合一的特點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尚用重于求知,所以古代的文學批評大多不是為了建立理論體系,而是為了指導創作。因為“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所以古代詩人初學時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批評鑒別能力和前代批評家的指引;因為“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所以文學批評需要批評者具有深厚的創作經驗作基礎。由此就造成了古代作家與批評家在身份上的合一現象。而西方哲學追求純粹之“知”的傳統,則造成了西方文學批評注重建立獨立體系,追求客觀裁判,以及身份上職業批評家的流行。
五、古代文學批評“作評一體性”的當代啟示
明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創作的一體性,可以給當代的批評史研究以很多啟示。
由于古代文學批評的范疇和命題往往從創作潮流中總結而來,因此在研究文學批評的時候,不能忽視對文學創作的考察。正如羅宗強先生所說:“研究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離開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想、文學思潮,都難以做出更接近歷史原貌的解釋。”[16]羅先生所開創的文學思想史研究范式,將文學創作與批評結合考察,正是出于對古代文學批評這一特點的認識。因為古代文學批評的內容以創作論為主,因此確切地闡釋批評范疇、命題的內涵,需要研究者對創作有一定的體驗和心得。古代文學批評往往用點到為止的印象式的批評方法,而不是邏輯式的詳盡言說。如果缺少對作品的領悟,是很難確切體會到批評者的用意的。比如古代詩學中所說的“瘦硬”,如果沒有對黃庭堅、陳師道等江西詩人作品的研讀,是很難領會其意味的。其他如“平淡”“神韻”等范疇皆是如此。所以,程千帆先生說:“從事文學批評工作,完全沒有創作經驗是不行的。研究詩最好能夠寫點詩。”[30]
古代批評家往往就是從事寫作的作家,這一事實被彭玉平稱為批評史研究的“邏輯起點”。在其所著《詩文評的體性》一書中,他指出:“批評家是以作家的身份兼有的。這一基本事實是如此清晰,它不容我們坐視不顧,也當然應該成為批評史研究的一個基本的邏輯起點。”[31]12因此,他認為批評史研究應該以作家為本位,而非以批評家為本位來建構理論體系:“所謂的‘批評史’并不純粹是‘批評家’的理論批評的發展歷史,原生形態的批評史——也許用‘詩文評’更為恰切,應當以作家的本位為邏輯起點,從中演繹出其學術觀念和思維特點。匆匆忙忙去構建什么理論體系,或者以當代的學術意識去框架古代文學的批評文獻,也許就顯得過于功利了。起碼現在是如此。”[31]14彭先生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