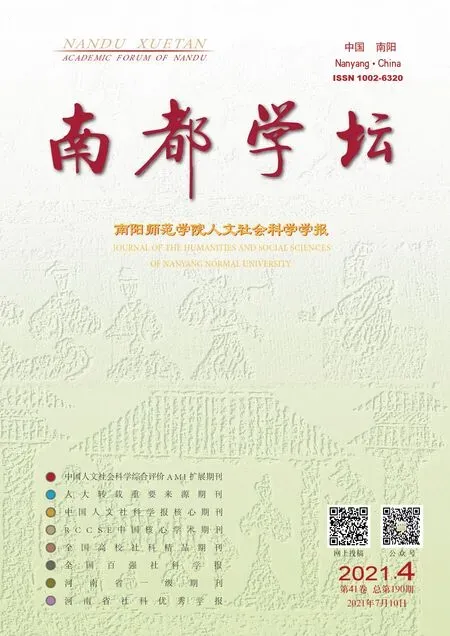論非法經營罪中兜底條款的適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為視角
樊建民, 劉祥蕊
(河南大學 法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由于政策落實的不夠完善和部分民營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時常遭遇諸多壓力。為擺脫壓力,民營企業時常會實施一些法無明文規定或規定模糊的新型經濟行為。這些行為可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或違法性,但鑒于刑法沒有為這些行為設置明確的罪狀,導致司法實踐中多依照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來認定其為非法經營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了許多新的輕刑罪狀,其中增設的第134條之一將“擅自從事礦山開采、金屬冶煉、建筑施工,以及危險物品生產、經營、儲存等高度危險的生產作業活動”設定為獨立的罪狀,并對之設置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刑罰;而之前的該類行為只能依據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認定為相對較重的非法經營罪。此時,如果出現與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列明的行為同質性、同害性的行為,司法實踐中若無法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的輕罪來定罪處罰,司法者就會選擇適用非法經營罪這一重罪條款來處置,這不但與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違背,也與社會通識常理不符。而且,本罪兜底條款的適用一直存在相當大的爭議,學者意見不同,不同司法機關的判定也大相徑庭,很難達到司法裁判的正當性和公平性。為保持立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提高法律適用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應限制本罪兜底條款的司法適用。
一、非法經營罪及其兜底條款評析
(一)非法經營罪設立的背景和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當時的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物資供應匱乏,部分資本家趁機囤積居奇(投機)、操縱價格(倒把)來謀取暴利,導致市場劇烈波動,故而1952年中共中央的“五反”指示、1964年《關于“五反”運動中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將其認定為“政治罪名”,其羅列的非法經營對象幾乎包括所有物品,表現形式幾乎包括所有違規行為。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規定了投機倒把罪,設置的刑罰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單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當時的刑罰設置屬于輕刑類型。1997年刑法將1979年之后諸多單行刑法中的非法經營條款加以總結歸納,設定為非法經營罪,并將其法定最高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至此本罪的法定刑已然屬于重刑范疇。刑法修正案(七)將組織、領導傳銷行為從非法經營罪中單列出來,但法定刑并無太大變化(僅設置沒收財產的刑罰);刑法修正案(十一)將非法經營罪中的一些行為單列出來(如第134條之一),設置輕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沒有附加刑的規定),體現立法者對該類行為的輕刑主義傾向及限制非法經營罪適用的意旨。
(二)兜底條款設置的必要性
1.法律自身的缺陷
“法律一經制定出來就是落后的”,成文法的穩定性和滯后性之間的矛盾從法律產生之初就存在。我國的刑事立法采用的都是成文法,作為保護社會公正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以強制性和嚴厲性而著稱,以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為基本原則,未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而及時、不斷修正。為了解決上述矛盾,具有巨大涵括性、彈性的兜底條款成為刑事立法無奈的唯一理想選擇。
2.立法技術的局限
法律是由人創設的,由于人類自身局限性,無法預料未來會有什么新類型的行為方式出現。法律不僅體現立法者的價值追求,也要使司法者有法可依,更要讓守法者能夠規范自己的行為。固定的詞語表達理解起來可能更顯生硬,為了盡可能地使法律涵蓋內容更加周全、更易理解,在立法描述某一罪狀本質之后,再設置一個兜底條款,可增加法網的嚴密性。
3.法律預防功能的需求
良法應該留有國民可預測的空間。兜底條款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刑法能夠對新出現的犯罪行為預留規制空間[1]。一方面,通過設置兜底條款,彌補立法者預見能力局限之不足;另一方面,設置兜底條款讓社會公眾明白還有其他可能因該兜底條款而受到懲罰的行為,從而對其起到威懾作用,使其自覺規制自己的行為,達到刑法一般預防功能的實現。
(三)兜底條款設置的合理性
1.增強刑法用語簡潔性
刑法作為最后的保障法,只有通過適用才能將靜態的法律規定轉換為動態的司法,起到保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作用。如果法律規定事無巨細、語言表達過分詳盡具體,會導致刑法典篇幅過長、體系繁雜,同時可能存在立法空缺與遺漏,與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背道而馳,適用時也會產生問題。兜底條款可以通過簡潔的文字概括出某一犯罪的具體要義[2]。通過規定兜底條款,提高刑法條文表達能力,縮減刑法篇幅,適用更為便捷。
2.增強法律適用靈活性
社會生活正在迅猛發展,新型行為方式層出不窮,法律規定越詳盡,適用范圍就越狹窄,很可能與社會生活脫節。面對此情形,如果不加節制地修改刑法,會破壞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而“兜底條款”剛好能夠彌補這一不足之處。面對異常豐富的社會生活,兜底條款可以防止法律過度僵化,高度概括性的語言表達可以防止法律適用面過窄的尷尬局面[3],既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又增強了法律的適用性。
二、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刑法第225條兜底條款的適用,仍然需要同時具備本條第一款“違反國家規定”和“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兩個前提條件。相對該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類型化的規定,兜底條款規定的內容更為概括和抽象,必須通過嚴格認定“違反國家規定”“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來加以限制。司法實踐中,正是因為對該兩個前提條件的認定不同導致了同案不同判或類案不類似判決的司法亂象,損及司法的尊嚴和權威。
(一)不適當擴大“國家規定”的范疇
案例1: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恩宏等人未獲互聯網出版批準、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其經營管理的廣州凡天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公司名下的“煙雨紅塵”營利性網站出版發表網絡文學、刊登淫穢性質的文章牟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構成非法經營罪和出版、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周恩宏等人未經許可非法從事出版活動,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1)參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1刑終1162號刑事判決書。。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非法經營罪不成立。
上述案例中認定被告人周恩宏等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理由是其經營的網站未獲批《網絡出版服務許可證》(2)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令第5號公布的《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第7條規定:“從事網絡出版服務,必須依法經過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取得《網絡出版服務許可證》。”,但該許可證所依據法律的效力層級是部門規章,并不符合刑法第96條的“國家規定”;一審法院是對“國家規定”進行了不適當的擴大解釋。二審法院也是基于此原因撤消了一審對被告人做出的非法經營罪之判決。諸如此類的案件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各級、各地法院對類似的行為經常作出大相徑庭的裁判結果。
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經營罪時,常常對“國家規定”做擴大解釋,一是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單行條例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中的“國家規定”;二是將市場登記管理類或一些非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以及一些與限制經營或專營專賣無關的法律規定,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中的“國家規定”。依立法本意,本罪中的“國家規定”指的是國家關于專營專賣或限制經營、特許經營的規定,而不是指與此無實質關聯的法律、法規規定。
(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認定的嚴重形式化和僵化
1.“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認定的形式化
案例2:被告人倪某春、劉某曉、孔某春等人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許可,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擾亂市場秩序。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構成非法經營罪(3)參見興城市人民法院(2017)遼1481刑再3號刑事判決書。。被告人孔某春提出申訴,經再審查明,被告人孔某春持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只是在未取得煙草專賣批發許可證的情形下,多次實施批發業務。再審認定被告人應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處理,而不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本案的一審在認定非法經營罪時,只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了形式審查。只要無證經營或者即使有證卻超范圍、超地域經營的非法行為都一律認定為“擾亂市場秩序”,進而可以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實質上,“非法經營”中的“非法”一般是指沒有取得經營許可證而從事經營活動的“非法”,而非沒有進行工商登記或超出工商登記范圍的“非法”[4]。
關于對“市場秩序”的理解、如何認定“市場秩序”均需要主觀裁量,而由于司法者個體的知識、經驗、素質的差異,導致“市場秩序”的認定時常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只要在市場中進行未獲批準的交易行為,便被認定為“擾亂市場秩序”。這種將“市場秩序”理解為政府對市場的管理秩序,不僅有擴大犯罪的嫌疑,更有司法僵化之弊端。
在司法實踐中,若某一行為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卻不符合非法經營罪前三項列舉的情形,又不符合其他獨立罪狀,就會一律納入第四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中,導致對本罪的把握只看重表象,忽視行為危害性的實質。
2.“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認定的僵化
案例3:被告人關某某、關某甲、郭某某在未取得《營業執照》《成品油零售經營批準許可證書》等手續的情況下,在銅川市印臺區某村合伙經營柴油,向銅川市印臺區玉華石料有限公司車輛、個人運輸車輛等出售柴油,最終三人都被判處非法經營罪(4)參見銅川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陜02刑終45號刑事判決書。。
實踐中在認定行為是否“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時,常以數額多少進行認定。在該類犯罪處理中,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非法出版、擾亂電信市場秩序等行為,在認定“情節嚴重”時也都以經營數額或造成損失的數額多少為標準,只要數額達到,一律認定為“嚴重擾亂市場秩序”。
(三)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設罪狀的適用困境
在當代積極刑法思潮下,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設第134條之一、第293條之一、第334條之一、第336條之一等,以及修改的第213條、第217條、第219條等,將特定的非法經營行為規制為獨立的罪名或歸入特定的犯罪范圍之內。
司法實踐中,部分司法者仍然秉持重刑理念,堅持重法優先的觀念,特別是過于考量社情民意、輿論政策的因素,仍然將該類行為歸入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內容之中,從而對其做出重刑裁判。當代積極刑法觀的興起,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上述裁判的傾向。筆者認為,積極刑法觀與謙抑刑法觀并不矛盾,其并不主張充分發揮刑法的作用而一味擴大刑罰適用范圍,而是主張其他法律效力不佳或者無效時重視和強化刑罰的功能,因為刑罰適用的過度或不及都不能有效發揮刑罰的功能。罰當其罪、以刑制罪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不是一味從嚴、一味從重或一味從輕。
司法實踐中若這些特定罪狀能對某非法經營行為進行調整,便應依據特別法優先的法條競合基本理論,以特定的輕罪定罪處罰;而不應適用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將其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34條之一將涉及安全生產的危險品的經營特設輕罪加以規定,對諸如此類的非法經營行為,只能按照新設的輕罪進行處理,而不能依據兜底條款進行重罪處理。如果司法實踐中出現司法解釋沒有涉及的事項以及刑法沒有特別規定的事項,按照非法經營之重罪進行處罰,將明顯導致對行為人的不公,難以達成司法活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三、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適用之限制
(一)解釋主體的限制
立法者既然設定了兜底條款,則兜底條款的內容就應該由立法者自己來界定,其他人包括司法者均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認定兜底條款的內容;因為立法者的意圖只有立法者自己才最清楚。故而立法者通過設定兜底條款留下的空白理應由立法者在完善立法時加以具體規定,或由立法者通過立法解釋進行補充規定,即兜底條款的解釋主體應是立法者,而不應是任何其他部門或其他人。在我國現實立法、司法狀況下,可以考慮由最高司法機關根據各地、各時段的具體情況,在體系解釋和同質解釋、同類解釋的基礎上,統一行使關于兜底條款的司法解釋權,對具體的非法經營行為、對象進行先行的羅列和規制,待時機成熟后再通過修訂立法來進行最終確認。
據筆者梳理,目前最高司法機關共對26種非法經營的行為方式或物品進行了司法規制(5)分別是:非法經營文物、非法經營外匯或非法從事支付結算、非法經營出版物、非法經營電信業務、非法買賣進出口證明等經營許可證明、非法傳銷、非法生產或銷售瘦肉精、非法經營食鹽、非法哄抬物價(傳染病期間)、非法經營網吧,非法發行或銷售彩票、非法經營證券業務、非法使用POS機對信用卡套現,非法經營煙草、非法發行基金份額募集基金、非法買賣麻黃堿類復方制劑、非法生產煙花爆竹、非法從事生豬屠宰或銷售,非法生產或銷售國家禁止用于食品生產、銷售的非食品原料和國家禁止生產、銷售、使用的農藥、獸藥、飼料、飼料添加劑或者飼料原料、飼料添加劑原料,非法采挖、銷售、收購麻黃草,非法信息網絡有償服務,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非法販賣麻醉和精神藥品,非法生產、銷售電視網絡接收設備軟件和提供相關下載服務,非法高利放貸、非法經營興奮劑目錄所列物質。。如此,在司法實踐中,只要刑法、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對任何超出立法范圍以及司法解釋范圍的行為,均不應依據兜底條款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限制
兜底條款之所以受到詬病,就是因為其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然而實際上,兜底條款的存在和適用,并不以犧牲罪刑法定原則為代價。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明確性原則,通過限制司法機關的權力,保障國民自由,有利于保護法益[5]。明確性原則既有實質要求也有形式要求,法條規定得越明確,越符合該原則的要求;但是絕對明確的法條也許適得其反。經濟轉型背景下,社會關系日新月異,絕對確定的法律不僅不能有效懲處犯罪,反而會延誤對嚴重違規行為的管制與約束。法的滯后性和語言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成文法不可能涵蓋所有新型犯罪,也不可能超前對某些行為進行“絕對明確”的規定,而“相對明確”能最大限度保證刑法功能的實現[6]。因此,兜底條款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反而有助于該原則的解釋與完善。在對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進行解釋時,必須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認定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必須首先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違“法”、違反的是否是“刑法”等問題,考慮這一大前提后才能繼續其他要素的認定,不能前后倒置。
(三)解釋方法的限制
1.堅持體系解釋方法
司法解釋的價值除了體現在指導定罪量刑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內涵——即在司法權內部建構起一張適度且謙抑的網絡,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的不當行使。因此我們要從整體性和限制性的角度認真解讀非法經營罪的相關司法解釋[7],解讀非法經營罪中兜底條款的真正內涵。在刑法內部體系中,在解釋兜底條款的時候,有必要參照刑法第96條“國家規定”的定義,參考本罪前三項明文規定情形中行為的性質及危害程度,考慮刑法中具體特殊罪名能否對行為進行合理規制。在刑法外部,還要考察整個法律體系,尤其要參考行政法中行為性質的認定,如果行為違反行政法但不足以受刑罰處罰,給予行為人相應的行政處罰即可。對個別新型行為的擴大解釋將導致整個法律體系紊亂、失衡,將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2.堅持同類解釋方法
同類解釋規則是指如果一項法律條文列舉了幾種應該入罪的行為之后還有一個概括式的詞語,例如“以及”“其他”,就意味著只限于包括未列舉的同類情況,而不包括不同類情況[8]。為了避免解釋的隨意性,解釋時應當根據類比的對象而定。同類解釋規則是例示主義立法模式經常采用的解釋規則,在解釋兜底條款時該解釋規則運用最廣泛。在用同類解釋規則對兜底條款進行解釋時,必須首先明確規范保護目的。若法律對某概念的規定并不明確,應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作出最有利于實現具體條文規范保護目的的解釋[9]。刑法設立的各罪狀都有各自的規范保護目的。例如:交通肇事罪保護的是機動車輛行駛過程中人的安全,受汽車喇叭驚嚇心臟病發作而死不是本罪保護范圍。因此在對兜底條款進行解釋時,不能超出該罪名的規范保護目的。從條文外部看,可以大致明確具體條文規范保護目的的范圍,從條文內部觀察,可以細化其范圍[10]。
(四)“國家規定”的范圍限定
非法經營罪的首要前提是“違反國家規定”,至于哪些內容屬于“國家規定”的范圍,可以從刑法第96條找到依據。我國《刑法》第96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11]。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發布的《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第1條規定: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制發的文件,符合以下條件的,亦應視為刑法中的“國家規定”[12]。因此,本罪所違反的法律必須是由最高權力機關或最高行政機關制定或公布的。
首先,既然“罪刑法定”,要成立犯罪,行為必須同時違反行政法和刑法的規定,觸犯一般行政法的行為不能以本罪定罪處罰;二次授權委托制定的部門規章或規范性文件效力低,也不是本罪可依據的“國家規定”。
其次,本罪適用的“國家規定”只限于調整市場秩序類的法律。刑法第96條規定的主體可制定和頒布的法律類型多種多樣,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但本罪既是非法經營罪,在刑法第三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中“擾亂市場秩序”一節中加以規定,觸犯的必然是國家關于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這部分法律。觸犯其他社會關系的法律可依據其他規定進行處罰,與經濟秩序無關的法律不是本罪的“前置性”法律規定[13]。
(五)“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范圍界定
對非法經營罪中第4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進行解釋時,尤其要堅持同類解釋規則,從本罪保護的規范目的出發,處罰擾亂經濟關系的經營行為。因為法律規定的不夠詳細,司法解釋又容易擴大規范保護目的的范圍,具體表現為對行政犯做形式化判斷以及對刑事政策過度回應[14]。行政違法并不必然等于刑事違法,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也不一定值得以犯罪論處。因此,對“其他擾亂市場秩序”進行解釋時,行為必須具有與非法經營罪中前三項行為同等或類似的危害性。
首先,在目前司法解釋規定中,非法從事國際海上運輸經營、經營非法出版物、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物,疫情期間哄抬物價等行為都被納入了非法經營罪的處罰范圍。司法實踐中,若討論非法經營食鹽、煙草等問題是否構成本罪并無太大爭議,因為非法經營罪的本質是侵犯了市場準入秩序或國家特許經營制度;但認定某行為是否屬于該罪“其他擾亂市場秩序”,則應遵循法律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要考察行為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特別許可制度。
其次,回歸條文本身,從概念上進行考察,既然罪名規定了“經營”二字,表明本罪“其他擾亂市場秩序”是一種有限度的續造,行為在客觀上應發生在經營活動中[15],且應具有長期性。偶爾實施的經營行為沒有刑罰處罰必要性。加之“經營”的通常含義是指市場主體以盈利為目的,從事某項能夠為自己帶來利益的活動[16],因此行為人主觀上應該具備盈利目的。
(六)“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界定
首先,在判斷行為后果是否嚴重之前,有必要討論該行為是否同時具備“情節嚴重”,即“情節嚴重”是本罪的構成要件。目前學界通說主張,為了避免實踐中本罪過度的擴張適用,應該把情節嚴重歸入構成要件中[1]。刑法第225條將“情節嚴重”規定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之前也證實了該觀點的合理性。
其次,對嚴重與否的認定不能僅依據數額多少。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環境下產生的行為必然會影響現有的社會關系。認定是否“嚴重”是非法經營罪行政責任向刑事責任轉化的關鍵,單純依靠數額進行認定,不僅是對行政法的侵犯,也是對人權的侵犯。
最后,要綜合考慮國家政策的安排。為了鼓勵民營企業等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國家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與政策。在對行為性質進行判斷時,要考慮該行為是否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處罰該行為是否有社會預防作用,是否能穩定市場秩序、帶動經濟發展。當某一新型產業模式出現時,若刑法沒有對應規定,應該堅持刑法謙抑性,堅持行政追責優先于刑事追責,先行政后刑事的追責理念。
四、結 語
為了在保持法律穩定的同時,更好地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結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公布施行,應該重新認識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對非法經營罪中的“兜底條款”做體系解釋、同類解釋,同時要全面考察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對情節較輕、僅造成輕微后果的行為科以刑事處罰;應注重發揮行政處罰的效用,恪守刑法謙抑性的要求,限縮兜底條款的過度擴張適用。最高司法機關應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發展狀況的差異,對本罪兜底條款的適用做出具體解釋,使其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并供立法者在完善立法時借鑒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