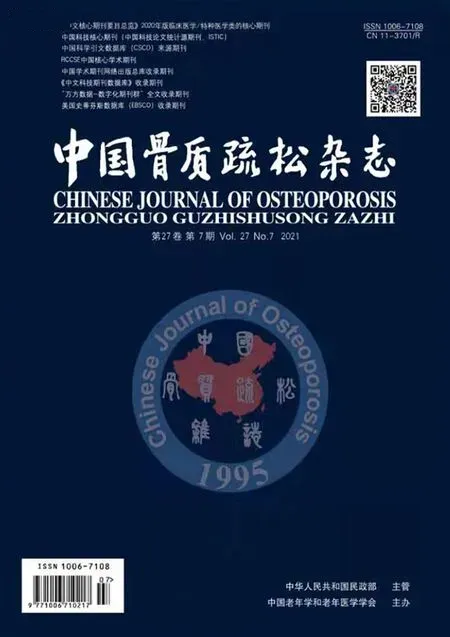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2021)
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委員會
根據國務院《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文件要求,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組織專家組對近年骨質疏松方面的共識和指南進行檢索和評價,經專家組認真研討,并結合基層醫療機構特點和骨質疏松防治的實際情況,編撰形成了2021版《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為基層醫療機構的骨質疏松癥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骨質疏松癥的定義和分類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最常見的骨骼疾病,是一種以骨量低,骨組織微結構損壞,導致骨脆性增加,易發生骨折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骨質疏松癥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大類,可發于任何年齡。原發性骨質疏松癥包括絕經后骨質疏松癥(Ⅰ型)、老年性骨質疏松癥(Ⅱ型)和特發性骨質疏松癥(包括青少年型)。絕經后骨質疏松癥一般發生在女性絕經后5~10年內[2-3];老年性骨質疏松癥一般指70歲以后發生的骨質疏松;特發性骨質疏松癥主要發生在青少年,病因未明。繼發性骨質疏松癥指由任何影響骨代謝的疾病和(或)藥物及其他明確病因導致的骨質疏松。
2 基層醫療機構防治骨質疏松癥的情況
骨質疏松癥的診斷應基于全面的病史采集、體格檢查、骨密度測定、影像學檢查及必要的生化測定。臨床上診斷骨質疏松癥包括確定是否為原發性骨質疏松癥和排除繼發性骨質疏松癥。雙能X線吸收法(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測量值是目前通用的骨質疏松癥診斷指標。對絕經后女性,建議參照WHO推薦的診斷標準,采用DXA測量腰椎、股骨頸和全髖3個感興趣區,在腰椎和髖部不能測量時,橈骨遠端1/3骨密度可作為補充,但前臂骨密度不能單獨用于骨質疏松癥診斷[4]。雖然DXA測量值作為骨質疏松癥診斷的通用標準廣泛用于各大醫院,但據調查顯示[5],基層醫務人員對骨質疏松癥診斷依據認知水平仍不足,脆性骨折史和DXA知曉率分別僅占17%和11%,醫生往往是在患者發生骨折就診時才發現骨質疏松癥。目前臨床上使用DXA對骨質疏松癥進行診斷、療效評估和骨折預測,跟骨定量超聲測定法(quantitative ultrasound system,QUS)易進行社區篩查。
骨質疏松癥治療藥物較多,基層抗骨質疏松藥物配置和醫師對其使用要求掌握迥然不同。據調查顯示[6],鈣、維生素D(含活性維生素D)、雙膦酸鹽、降鈣素類及雌激素類等相對傳統的抗骨質疏松藥物在各醫院都較普及,而相對較新的藥物如甲狀旁腺激素類似物、RANKL抑制劑等普及率不足50%。大部分醫師并沒有掌握最新的抗骨質疏松藥物及其適應證。
基層醫療服務機構是承擔骨質疏松癥早期防治工作的較合適的醫療機構,具有固定患者群、定期隨訪、較強疾病預防意識以及豐富的慢性病管理經驗,與上級醫院合作能實現骨質疏松癥的三級預防。然而,骨質疏松癥尚未納入國家慢病管理體系,其研究多為發病機制或流行病學調查,針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高危人群和普通居民開展的防治與基層骨質疏松癥的管理研究不足[7-8]。基層臨床醫生對骨質疏松癥關注度不夠、規范診治程度不高,在慢病管理服務團隊中仍存在角色模糊、職責不清的問題。骨質疏松癥的預防重于治療, 基層醫療機構不僅是骨質疏松癥預防宣教、危險因素評估、高危人群篩查的第一道關口,也是與二、三級醫院開展全專結合、雙向轉診、家庭醫生服務等重要的實施點。但目前缺乏統一、公認的骨質疏松癥防治和管理模式及切合實際和有效針對基層醫療機構診療骨質疏松癥的指導措施。
3 基層骨質疏松癥的篩查
3.1 骨質疏松癥的高危因素
(1)不可控因素:包含種族、年齡、女性絕經、脆性骨折家族史。其中種族罹患骨質疏松癥風險從高到低依次為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2)可控因素:包括不健康生活方式,影響骨代謝的疾病和藥物,跌倒及其危險因素,環境因素及自身因素[9]。
3.2 骨質疏松癥的篩查工具
(1)推薦國際骨質疏松基金會(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IOF)骨質疏松風險一分鐘測試題[10](表1)和亞洲人骨質疏松自我篩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11]作為疾病風險評估的初篩工具(表2)。(2)WHO推薦的骨折風險預測工具(FRAX?)[12-14]可用于評估患者未來10年發生髖部骨折及主要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概率。針對中國人群的FRAX?可以通過以下網址獲得:https://www.sheffield.ac.uk/FRAX/tool.aspx?country=2。(3)推薦QUS作為骨質疏松篩查工具。(4)骨質疏松癥證候分級量化標準(表3)和SF-36生活質量調查問卷也可以用于骨質疏松篩查[15]。

表1 國際骨質疏松基金會骨質疏松風險一分鐘測試題Table 1 One-minute osteoporosis risk test by 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IOF)

表2 OSTA指數評估指數Table 2 OSTA index evaluation index

表3 中醫證候量化分級評分表Table 3 TCM syndrome quantitative grading scale
4 骨質疏松癥的診斷
4.1 高危人群(具備以下任何1條)
(1)具有不明原因慢性腰背疼痛的50歲以上女性和65歲以上男性;(2)45歲之前自然停經或雙側卵巢切除術后女性;(3)各種原因引起的性激素水平低下的成年人;(4)有脆性骨折家族史的成年人;(5)存在多種骨質疏松危險因素者,如高齡、吸煙、制動、長期臥床等。(6)具有以下病史者:影響骨代謝的疾病:包括性腺功能減退癥等多種內分泌系統疾病、風濕免疫性疾病、胃腸道疾病、血液系統疾病、神經肌肉疾病、慢性腎病及心肺疾病等。服用影響骨代謝的藥物:包括糖皮質激素、抗癲癇藥物、芳香化酶抑制劑、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抗病毒藥物、噻唑烷二酮類藥物、質子泵抑制劑和過量甲狀腺激素等[4]。(7)采用IOF骨質疏松癥一分鐘測試題(表1),只要其中有一題回答為“是”,即為骨質疏松癥高危人群。(8)OSTA指數≤-4者。
4.2 臨床診斷
4.2.1臨床表現及體征:(1)脆性骨折:是骨強度下降的最終體現,髖部和椎體脆性骨折是骨質疏松癥的重要臨床表現。(2)不明原因的慢性腰背痛:是骨質疏松癥患者最常見癥狀,也是大部分患者就診的首要癥狀。常在翻身時、起坐時以及長時間行走后出現腰背疼痛、全身骨痛或者周身酸痛,且負荷增加時加重甚至活動受限。不明原因的慢性腰背疼痛為診斷骨質疏松癥的重要線索。(3)身材變矮或脊柱畸形:嚴重骨質疏松癥患者可有身高縮短和駝背等脊柱畸形。脊柱畸形會使身體負重力線改變,從而加重脊柱、下肢關節疼痛。隨著骨量丟失,脊柱椎體高度丟失,椎間盤退變,整個脊柱縮短5~10 cm不等,從而導致身長縮短。胸腰椎脆性骨折或身高減低3 cm(或1年內身高減低2 cm)或駝背的老年患者,可作為診斷骨質疏松癥的重要依據。(4)心理異常和低生存質量:骨質疏松癥患者可出現恐懼、焦慮、抑郁等心理異常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4.2.2DXA檢測骨密度: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是基于DXA測量的T值結果。測量部位主要為腰椎和股骨近端,如腰椎和股骨近端測量受限,可選擇非優勢側橈骨遠端1/3。WHO發布的DXA測定骨密度分類標準:T值≥-1,骨量正常;-2.5 4.2.3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QCT)檢測骨密度:能分別測量松質骨和密質骨的體積密度,可以較早反映早期骨質疏松的松質骨丟失,并能避免腰椎骨質增生等原因引起的DXA測量誤差,具有一定技術優勢。中國QCT骨質疏松診斷指南(2018)推薦腰椎QCT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取2個腰椎松質骨骨密度平均值(常用第1和第2腰椎),采用腰椎QCT骨密度絕對值進行診斷,骨密度絕對值>120 mg/cm3為骨密度正常,骨密度絕對值于80~120 mg/cm3為低骨量,骨密度絕對值<80 mg/cm3為骨質疏松。QCT診斷骨質疏松只需做一個部位即可,根據臨床需要選擇做脊柱或髖部[16]。 4.2.4X線攝片法:是一種方便經濟的方法,可觀察骨的形態結構,胸腰椎側位X線影像可作為骨質疏松椎體壓縮性骨折及其程度判定的首選方法。但其對骨質疏松的敏感性和準確性較低,只有當骨量丟失達30%以上時,X線攝片才能有陽性所見。 4.2.5QUS檢測:通常測量部位為跟骨、橈骨遠端,可用于基層骨質疏松篩查和脆性骨折的風險預測。 4.2.6骨轉換標志物:是骨組織本身的代謝產物,簡稱骨標志物,可分為骨形成標志物和骨吸收標志物。在正常人不同年齡段和不同疾病狀態時,全身骨骼代謝的動態狀況可通過血液或者尿液中的這些標志物水平的變化體現出來。在諸多標志物中,空腹血清Ⅰ型前膠原氨基端前肽(P1NP)和空腹血清Ⅰ型膠原C末端肽(S-CTX)是分別反映骨形成和骨吸收敏感性較高的標志物。 詳細了解病史,分析病因,重視和排除其他影響骨代謝的疾病。需鑒別的疾病主要包括:內分泌疾病如甲狀旁腺疾病、性腺疾病、腎上腺疾病和甲狀腺疾病等,類風濕關節炎等免疫性疾病,神經肌肉疾病,多種先天和獲得性骨代謝異常疾病,多發性骨髓瘤等惡性疾病,長期服用糖皮質激素或其他影響骨代謝的藥物等。 對于懷疑骨質疏松癥和已確診為骨質疏松癥的患者,需要針對性選擇合理的實驗室檢查,以利于明確診斷和鑒別診斷。 針對基層人群年齡分布、經濟能力、診療設施有限和藥物種類不全等特點,利用其現有醫療資源,制定合理的中西醫結合防治方案。骨質疏松癥的防治是一個長期、規范的過程,需要藥物、運動等綜合措施,以增加骨密度,維持骨質量,預防、減緩骨丟失的進展;同時加強肌肉質量,提高肌肉協調性,避免跌倒和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發生,從而達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瘥后防復”的目的。 5.2.1調整生活方式:(1)科學膳食:保證每日膳食豐富、營養均衡是防治骨質疏松癥的基礎生活方式。飲食上應多吃鈣和維生素D含量較高的食物,如牛奶、蔬菜、魚類、蛋類、豆腐、菌菇、燕麥、奶制品等[17]。同時還應堅持低鹽飲食,多飲水,保持大便通暢,以增進食欲,促進鈣的吸收。注意戒煙、限酒,避免過量飲用咖啡和碳酸飲料[18]。(2)充足日照:維生素D除了來源于食物,還依靠陽光中的紫外線照射皮膚而合成。一般將面部及雙臂皮膚暴露照射15~30 min即能滿足合成的需要,建議選擇陽光較為柔和的時間段(根據季節、地區、緯度等有所調整),避免強烈陽光照射,以防灼傷皮膚[19-20]。(3)合理運動:基層人群分布以中老年為主,日常運動應以負重、抗阻力運動和平衡訓練為主,不僅可以增強肌肉質量、改善機體平衡,還能改善骨密度、維持骨結構,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風險。中年人以有氧運動為基礎,配合全身肌肉力量訓練,每周3~7次,運動量逐漸增加;老年人可選擇散步、慢跑、跳舞、騎車等中強度運動,以及啞鈴、太極拳、五禽戲、八段錦等力量訓練[21]。另外,老年人還應增加手膝位、坐位、站位等平衡練習,每周3~5次。個人應根據自身狀況,選擇合適的鍛煉強度和時間,循序漸進,持之以恒,但要注意少做軀干屈曲、旋轉動作。(4)預防跌倒:中老年高危人群和家屬應提高防護意識,避免走樓梯,家庭走道保持通暢,衛生間安裝夜燈、安全扶手、鋪防滑墊;必要時使用拐杖或助行器[22]。(5)伴有影響骨代謝的內科疾病(如甲狀腺功能亢進、糖尿病、腎功能不全等),或服用影響骨代謝的藥物(如地塞米松、甲強龍等)的患者,需督促其定期至醫院檢測骨密度,必要時進行規范抗骨質疏松治療。(6)骨質疏松癥對患者心理狀態的影響常被忽略,主要包括睡眠障礙、焦慮、抑郁、恐懼、自信心喪失等心理異常。老年患者自主生活能力下降,以及骨折后缺乏與外界的交流,也會造成社交障礙等心理負擔。因此,應重視和關注骨質疏松癥及其骨折患者的心理健康評估,并視情況干預,使患者正確認識骨質疏松癥,幫助其消除心理負擔。 5.2.2基礎治療:(1)骨健康基本補充劑:鈣劑和維生素D是日常防治骨質疏松癥的基本藥物。①鈣劑:成人每日鈣推薦攝入量為800 mg,50歲及以上人群每日鈣推薦攝入量為1 000~1 200 mg。我國居民日常飲食鈣攝入量約為400 mg,盡可能通過飲食攝入充足的鈣,也可選擇合適的鈣劑予以補充。長期或大劑量使用鈣劑應定期監測血鈣及尿鈣水平,同時高尿酸血癥患者補鈣時應多飲水、多運動,防止腎結石形成。②維生素D:成人維生素D推薦攝入量為400 IU(10 μg)/d,65歲及以上老年人推薦維生素D攝入量為600 IU(15 μg)/d。維生素D用于防治骨質疏松癥時,劑量可為800~1 200 IU(20~30 μg)/d[4],可耐受最高攝入量為2 000 IU(50 μg)/d。(2)骨質疏松癥的藥物治療:活性維生素D及其類似物、雙膦酸鹽(含阿侖膦酸鈉、阿侖膦酸鈉維D、唑來膦酸、利塞膦酸等)、降鈣素、雌激素、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RANKL抑制劑、甲狀旁腺激素類似物、維生素K2類、鍶鹽、中藥。(3)藥物聯合和序貫治療。聯合使用抗骨質疏松藥物應評價潛在的不良反應、治療成本及獲益。骨健康基本補充劑(鈣劑和維生素D)可以與骨吸收抑制劑或骨形成促進劑聯合使用[4]。不建議相同作用機制的藥物聯合使用,特殊情況下為防止快速骨丟失,可考慮兩種骨吸收抑制劑短期聯合使用,如絕經后婦女降鈣素與雙膦酸鹽短期聯合使用[23]。以下情況可考慮藥物序貫治療:①某些骨吸收抑制劑治療失效、療程過長或存在不良反應時;②甲狀旁腺激素類似物等骨形成促進劑的推薦療程僅為18~24個月,停藥后應序貫治療,推薦序貫使用骨吸收抑制劑[24]。 5.2.3中藥內服:(1)肝腎陰虛證:主要表現為腰膝酸痛,膝軟無力,下肢抽筋,駝背彎腰,患部痿軟微熱,形體消瘦,眩暈耳鳴,或五心煩熱,失眠多夢,男子遺精,女子經少經絕,舌紅少津,少苔,脈沉細數。治則:滋補肝腎、強筋壯骨。推薦方藥:左歸飲、六味地黃丸、人工虎骨粉等。(2)脾腎陽虛證:主要表現為腰髖冷痛,腰膝酸軟,甚則彎腰駝背,畏寒喜暖,面色蒼白,或五更泄瀉,或下利清谷,或小便不利,面浮肢腫,甚則腹脹如鼓,舌淡胖,苔白滑,脈沉弱或沉遲。治則:溫補脾腎,填精益髓。推薦方藥:右歸飲、金匱腎氣丸、淫羊藿提取物、骨疏康膠囊等。(3)腎虛血瘀證:主要表現為腰膝及周身酸軟疼痛,痛有定處,活動困難,筋肉攣縮,骨折,多有外傷或久病史,舌質紫暗,有瘀點或瘀斑,苔白滑,脈澀或弦。治則:補腎活血、化瘀止痛。推薦方藥:補腎活血湯、青蛾丸、壯骨止痛膠囊等。 5.2.4中醫外治法:基層醫療機構可開展一些簡便、安全、有效的中醫適宜技術操作,既可通絡止痛,又可強筋健骨。(1)針灸療法:治療原則包括補腎健脾、養骨生髓、溫經通絡、祛瘀止痛等,可采用針刺、電針、艾灸、溫針灸、熱敏灸等方法,臨床主要選用腎經、膀胱經、脾經、胃經及任督二脈等,常用穴位如足三里、腎俞、三陰交、脾俞、肝俞、中脘、神闕、關元等[25-26]。(2)中藥外治法:主要針對腰背部或其他部位疼痛,中藥熱敷、溻漬、熏蒸和穴位貼敷等傳統外治法有補腎填精、益氣健脾、活血通絡、強筋壯骨之功,可有效緩解疼痛,改善運動功能[27]。 5.2.5中西醫結合治療:在單純中藥、西藥治療骨質疏松癥效果不顯著時,可依據病理特點及類型,審慎聯合應用中西藥治療,西藥的選擇應當符合用藥適應證,中藥的使用也須遵循辨證施治,臨床推薦中藥與鈣劑、維生素D等基礎治療藥物聯合使用。鑒于骨質疏松癥的發病特點,臨床防治過程中需長期服用中藥,應持續關注中藥的安全性問題,關注一般狀況、生命體征(體溫、心率、血壓),定期檢測血、尿常規,肝、腎功能,血鈣、血磷和心電圖等安全性指標。中西藥物聯合應用較復雜,目前仍需大樣本、多中心、長時間的臨床研究來驗證中西藥聯合使用的療效和安全性。 5.2.6功法:太極拳、五禽戲、八段錦等傳統功法,結合了呼吸吐納、肢體運動、自我按摩的方法,具有疏通經絡、調理氣血、舒展筋骨和強化肌力等作用,中老年人群長期練習能夠增加骨量、提升肌力、增強平衡能力[28]。 基層醫療機構應制定個體化抗骨質疏松治療方案,療程至少堅持1年,常規3~5年,多方案的聯合和序貫治療已成為基層醫生的首選[29]。 5.2.7骨折的處理:影像學檢查確診骨質疏松性骨折后,基層醫療機構可根據實際條件靈活處理,制動休息、包扎固定后轉診專科治療。 5.3.1主要療效指標:(1)隨訪患者在治療期間是否發生(髖部、椎體和前臂等部位)脆性骨折:出現兩次及以上新發脆性骨折,視為療效較差或無效;無新發或僅一次脆性骨折視為有效或可能有效,觀察時限至少為3年。抗骨質疏松治療能夠降低40%~70%的骨折風險,但不能完全消除[30]。如有新發骨折則需重新評估病情,調整治療方案[31]。(2)骨密度:根據本單位情況,選擇(橈骨或跟骨)QUS或DXA檢測骨密度(每年至少1次)。 5.3.2次要療效指標:(1)中醫證候:中醫藥療法干預前后,依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觀察中醫臨床癥狀體征及證候積分(表3)變化情況,以評估治療方案的合理性[32](1~3個月評估1次)。(2)實驗室指標:根據本單位檢驗條件,檢測血常規、血鈣、尿鈣、血磷、25-羥基維生素D、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骨堿性磷酸酶(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B-ALP)、骨鈣素(osteocalcin,BGP)、骨保護素(osteoprotegerin,OPG)、甲狀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artrate 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TRAP)、降鈣素(calcitonin,CT)、雌二醇(estradiol,E2)、睪酮(testosterone,T)等水平。骨形成標志物包括血清Ⅰ型前膠原氨基端前肽(PINP),骨吸收標志物包括血清Ⅰ型膠原交聯C末端肽(S-CTx),治療3個月后,S-CTx降低大于50%,PINP升高大于30%,說明治療有效[33]。(3)停藥期間的監測:停藥期間及停藥1~2年后均要規律隨訪、評估上述指標。(4)高質量隨訪:隨訪患者治療后的不良反應和規范服藥、生活方式管理、營養管理、運動管理以及防跌倒措施等情況,并進行生活質量評價。 基層骨質疏松癥的管理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患者、患者家庭成員、專科醫生、家庭醫生及社區工作者共同參與。基層醫療機構在骨質疏松癥管理過程中承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二級醫院連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級醫院)和三級醫院,具有特定的社區基礎,開展慢性病防治、建立慢性病防治網有顯著的優越性[34]。家庭醫生是執行全科醫療的衛生服務提供者,是初級衛生保健的“守門人”,擔負著社區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疑難復雜疾病轉診、慢病隨訪及康復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重任[35]。 大規模人群篩查需要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基層醫院參與,確定目標人群、篩查計劃、診治標準流程、健康檔案管理、隨訪管理等,設置質量控制目標,加強宣傳,使篩查對象了解骨質疏松癥的基本知識及防治重要性,提高篩查依從性。 6.1.1骨質疏松醫聯體篩查模式:前期進行醫聯體內醫務人員骨質疏松知識強化培訓,制定統一的篩查策略和流程,進行廣泛宣傳動員,對符合條件的對象進行骨質疏松相關知識及IOF、OSTA測試,同時進行DXA檢查,建立健康檔案,進行相應的治療、干預和隨訪[36]。 6.1.2家庭醫生與骨質疏松專科合作:家庭醫生與骨質疏松專科合作可提高篩查效率、明確分類診斷、規范治療及方便雙向轉診。鼓勵將骨質疏松癥篩查納入家庭醫生團隊的管理考核,調動篩查工作的積極性。 6.1.3電子健康檔案的應用:骨質疏松癥患者個人健康檔案應包括基本信息、身高、體重、過敏史、既往病史、伴發疾病、骨質疏松癥用藥記錄、運動量、吸煙及飲酒情況、骨質疏松知曉率評分、骨密度及骨代謝檢測結果等,同時有日期管理及隨訪管理功能。電子檔案資料需注意保存,注意保護患者個人隱私。有條件的地區可自行開發信息管理系統,亦可由衛生管理部門開發信息管理系統并向基層全面推廣。 分級診療是合理配置醫療資源、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重要舉措。促進患者在不同級別醫療機構有序就診,指導患者合理就醫、規范診療,從而提高醫療資源使用效率,降低骨質疏松癥及其骨折發病率和死亡率[37]。 一級醫院負責骨質疏松高危人群初篩、建檔、健教、隨訪、基礎治療及轉診。二級醫院負責明確診斷、規范治療,疑難病例轉診三級醫院,對病情穩定者可下轉一級醫院。三級醫院負責疑難病例診治,待病情穩定后轉診到一、二級醫療機構進行后續治療、康復、隨訪。 有的地區在骨質疏松醫聯體模式下成立了骨質疏松專科,配備DXA設備和骨代謝檢測及全面的抗骨質疏松藥物,社區負責篩查及上轉,骨質疏松科負責確診及規范診治,穩定后下轉社區后續治療、隨訪、康復,提高了轄區骨質疏松癥診斷率、治療率[36]。 規范管理骨質疏松癥患者,可提高患者對骨質疏松的認知水平,增強信念,提高治療的依從性,具體方式可參照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同伴管理等方式[38]。 基層骨質疏松癥管理的隨訪內容包括:(1)復查骨密度及骨標志物;(2)二次和二次以上骨折發生情況;(3)發生脆性骨折后生存狀況;(4)是否有脊柱變形、身高變短;(5)是否有長期服用類固醇激素;(6)是否出現絕經現象;(7)是否進行骨營養劑補充;(8)是否全程規范治療;(9)健康宣教;(10)跌倒風險評估及防跌倒指導;(11)是否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12)是否伴發新診斷糖尿病、甲亢、甲旁亢等影響骨代謝疾病。 隨訪形式可采用電話隨訪、上門隨訪、微信或移動APP等移動終端隨訪,有研究表明微信隨訪可提高骨質疏松癥患者依從性和認知水平[39]。 骨質疏松癥是臨床常見骨代謝疾病,基層醫療機構作為診治骨質疏松癥的前沿陣地,在骨質疏松癥防治工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針對基層醫療機構在防治骨質疏松癥過程中面臨的診斷、治療、管理問題,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委員會組織國內骨質疏松領域知名專家制定出《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該共識全面梳理了既往國內骨質疏松癥診療共識和指南,提出基層骨質疏松癥的篩查和診斷建議,推薦基層骨質疏松癥的治療方案和管理辦法,以方便基層醫務人員理解學習和掌握使用。該共識的推出提供了國內基層醫療機構缺少診治骨質疏松癥的針對性共識,具有重要的基層臨床指導意義。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基層醫療機構骨質疏松癥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編寫委員會 組長:黃宏興(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委員:史曉林(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李盛華(甘肅省中醫院),馬勇(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孔西建[河南省洛陽正骨醫院(河南省骨科醫院)],梁江聲(佛山市順德區倫教醫院),萬雷(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王志榮(江蘇省張家港市中醫院) 學術秘書:李雪松(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黃佳純(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討論專家(按姓氏拼音排序):邊平達(浙江省人民醫院),陳超(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陳小波(贛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陳慶昭(佛山市禪城區中心醫院),樊效鴻(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黃谷(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何永濤(佛山市順德區倫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金立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姜紅衛(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孔令俊(甘肅省中醫院),劉海全(廣州中醫藥大學惠州醫院),劉明明(江蘇省連云港市第二人民醫院),呂晶(杭州市西湖區文新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帥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孫艷格(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復興醫院月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王凡(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楊利學(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朱曉峰(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章恒(廣西醫科大學附屬埌東醫院),鄭福增(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4.3 鑒別診斷
5 基層骨質疏松癥的治療
5.1 治療目標
5.2 防治措施
5.3 療效判定
6 基層骨質疏松癥的管理
6.1 立足篩查、數據建檔
6.2 分級診療、雙向轉診
6.3 規范治療、定期隨訪
7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