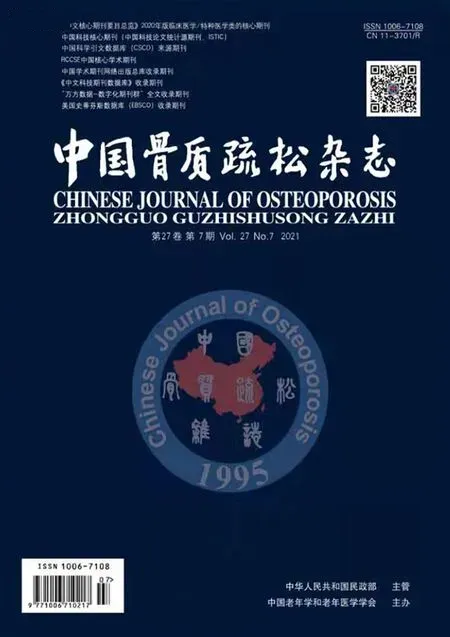應用德爾菲法確定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評估工具及評價指標
孫繼高 趙偉 朱瑞征 傅繁譽 譚彪 李文龍 薛志鵬 王榮田 陳衛衡*
1.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 北京 100102
2.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北京 100029
3.貴州中醫藥大學, 貴州 貴陽 550005
骨質疏松(osteoporosis,OP)是一種以骨量減低、骨組織微結構損壞,導致骨脆性增加、易發生骨折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2006年我國骨質疏松癥患者近7 000萬,骨量減少者已超過2億人,而2016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骨質疏松患病率達36%,說明骨質疏松已成為我國面臨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2-3]。骨質疏松癥可防、可治,要加強對高風險危險人群的早期篩查與識別[4]。本研究的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指年齡40~70歲、具有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的骨量正常或者骨量減少人群,特別是低骨量的人群。骨質疏松的評估工具與評價指標眾多,目前未有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篩選流程與監測評價的統一描述。德爾菲法又稱專家調查法,就某一領域問題對一組選定的專家進行征詢,經過多次調查統計和反饋修正,使專家意見集中趨于一致,是獲得共識意見的有效方法[5-6]。因此,本研究運用德爾菲法研究和篩選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評估工具和評價指標,為臨床辨識篩選高風險人群、設計干預計劃提供指導。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在方法學專家指導下,查閱國內外骨質疏松防治指南及有關評估工具、影響因素、評價指標的文獻,結合專家咨詢意見以及課題組前期研究成果,設計調查問卷。
1.2 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主要包括:(1)項目介紹、填寫說明和專家知情同意;(2)專家基本資料:姓名、年齡、性別、工作年限、單位、職稱、研究方向、聯系方式等;(3)問卷選擇部分主要包括篩查工具、輔助檢查、中醫辨識條目、評價指標,同時問卷留有空白項供專家補充問卷未提及的內容和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1.3 第一輪問卷
根據前期文獻研究結果及專家意見,初步建立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辨識篩選調查問卷,讓專家根據自己的經驗賦值,并補充其他重要的骨質疏松評估手段、輔助檢查和評價指標。
1.4 第二輪問卷
通過對第一輪問卷的整理分析,根據專家意見增加專家補充的內容,形成第二輪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辨識調查問卷。
1.5 指標計分與量化
問卷調查中的指標選擇均采用9分Likert評分系統,其中1~3分代表“不重要”,4~6分代表“一般重要”,7~9分代表“非常重要”。
1.6 專家遴選
參加問卷調查的專家均為國內三甲醫院或高等科研院所長期從事骨科、內分泌科、老年病科、放射科及藥學專家,包括中醫、西醫及中西醫結合專業,具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副高級及以上職稱,并在骨質疏松領域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一定知名度。
1.7 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問卷發放及回收情況
第一輪調查為現場紙質版問卷,共發放問卷20份,回收20份,專家積極系數為100%;第二輪調查為電子問卷,共發放問卷30份,回收28份,專家積極系數為93.33%。
2.2 專家基本信息
參與兩輪調查的專家來自北京、上海、廣東、福建、陜西、吉林、湖南、湖北、黑龍江、河南10個省市的20余家醫院或科研院所,在骨質疏松領域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學術造詣。第二輪參與專家均參加了第一輪調查,兩輪調查專家信息基本一致。第二輪專家中男性23名(82.14%),女性5名(17.86%),平均年齡53歲(36~79歲),平均工作年限29年(11~54年),參加專家多為工作20年以上的主任醫師或教授。執業中醫師14名(50.00%)、西醫師9名(32.14%)、中西醫結合醫師5名(17.86%),研究方向骨科18名(64.29%)、內分泌科5名(17.86%)、其他方向5名(17.86%),參與專家來自不同學科與不同專業,地域分布廣泛,具有良好的權威性和地域代表性。
2.3 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評估工具的選擇情況


表1 專家對風險評估工具的意見集中程度和協調程度Table 1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xperts’ opinion on risk assessment tools
2.4 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輔助檢查的選擇情況


表2 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輔助檢查的意見集中程度和協調程度Table 2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xperts’ opinion on auxiliary examination for high-risk population of osteoporosis
2.5 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評價指標的選擇情況


表3 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評價指標的意見集中程度和協調程度Table 3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xperts’ opinion on outcomes for high-risk population of osteoporosis
3 討論
3.1 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辨識篩選
人體骨量水平自35~40歲開始下降,我國也將骨密度檢測項目納入40歲以上人群常規體檢內容[8-9]。本研究基于中醫“治未病”思想,重點關注骨質疏松癥的“未病”人群,根據課題組前期研究成果和專家咨詢意見所確定的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指年齡40~70歲、具有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的骨量正常或者骨量減少人群,特別是低骨量的人群,若不及早發現和早期防治,容易發展為骨質疏松癥甚至發生骨松骨折等嚴重后果。根據問卷結果及專家意見,IOF一分鐘測試題陽性[10]或絕經后女性OSTA[11]判斷為中、高風險者應視為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應進行骨密度檢查進一步確定。本研究根據專家的寶貴臨床經驗確定IOF一分鐘測試題和OSTA作為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初篩工具,也與我國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和專家共識[4,12]中的推薦情況一致。
本研究雖僅納入IOF一分鐘測試題和OSTA為風險初篩工具,但其他風險評估工具和檢測設備在臨床中也有一定的意義。定量超聲(quantitative ultrasound system,QUS)作為骨質疏松風險的初篩設備,具有一定的診斷和預測骨質疏松骨折作用;骨折風險預測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FRAX)用于評估患者10年髖部骨折及主要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概率;此外,骨質疏松自我測評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OST)、骨質疏松危險評價工具(osteoporosis risk assessment instrument,OARI)、簡易計算的骨質疏松危險評價工具(the simple calculated osteoporosis risk estimation,SCORE)等風險評估工具在評估骨質疏松風險上具有積極作用。臨床中可根據實際情況,參考相應的指南或指導原則選擇使用[13-14]。
中醫學將骨質疏松歸屬為“骨痿”“骨痹”等范疇,研究基礎深厚,中醫學的癥狀體征辨識對骨質疏松的早期預測具有一定價值。有研究顯示下肢抽筋、下肢骨痛作為骨質疏松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有研究報道目眩可以嘗試作為早期預測骨質疏松骨折發生的中醫癥狀之一[15-17]。根據專家對于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中醫證候辨識的選擇情況,腰痛、背痛、周身疼痛、腰膝酸軟、駝背、身高變矮、下肢拘攣、倦怠乏力、下肢困重、足跟痛這10個指標可嘗試作為辨識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中醫評估條目,臨床上若出現上述癥狀體征的2條或以上,應警惕為骨質疏松的高風險人群,建議進一步檢查。
3.2 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監測與評價
對于評估為骨質疏松高風險的人群,應該進一步檢查。專家意見調查結果提示,應重點行DXA檢查骨密度,骨轉換指標及血鈣血磷檢測。DXA是目前臨床和科研常用的骨密度測量方法,也是國內國際指南公認的骨質疏松診斷標準[18-21]。中醫證候積分采用癥候分級量化表進行評分[22]。骨轉換指標包括骨形成標志物和骨吸收標志物,空腹血清Ⅰ型前膠原氨基末端肽和空腹血清Ⅰ型膠原交聯C-末端肽分別為反映骨形成和骨吸收代表性標志物[4,23]。基本檢查中,應重視血鈣、血磷,有助于鑒別骨質疏松。其他的血、尿常規、肝、腎功能等基本檢查,胸腰椎側位X線、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QCT)等檢查手段,甲狀旁腺素、維生素D3等鈣磷代謝調節指標及激素等生化指標,可根據臨床實際情況進行選擇[14]。
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與骨質疏松癥患者不同,其骨量正常或為低骨量,所以干預方法以調整生活方式等基礎措施為主,根據專家意見也建議進行太極拳等傳統功法進行早期防治。專家對評價指標的意見較為集中,選擇的指標較多,其中骨密度是最受關注的指標,用于監測高風險人群的骨量變化情況,是處于骨量維持還是骨量降低或增高狀態。生活質量評分可采用健康測量量表SF-36(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 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24],中醫證候作為評價指標也被骨質疏松癥專家共識推薦[8],平衡能力選擇“起立-行走”計時測試(timed up and go test,TUG)[25]。此外,血鈣血磷、骨轉換指標、VAS評分、跌倒與骨折次數也是專家較為關心的評價指標。目前的臨床研究中,對不同干預措施的評價指標選擇雖沒有“金標準”,但研究之間的評價指標差異難以進行數據的合并和進一步分析,造成了研究數據的浪費[26-27]。本研究中,專家對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評價指標雖然選擇較為集中,但評價指標數量較多、仍不統一,未來或可參考慢性腰背痛、股骨頭壞死、非瓣膜性房顫等疾病的核心指標集[28-30],建立骨質疏松的核心指標。
本研究運用德爾菲法,基于骨質疏松領域專家的寶貴經驗,確定了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評估工具和篩選流程,明確了輔助檢查手段及監測評價指標,為臨床骨質疏松高風險人群的辨識和防治提供參考。但由于專家人數、專業的限制及德爾菲法本身的缺陷,仍需要臨床的進一步驗證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