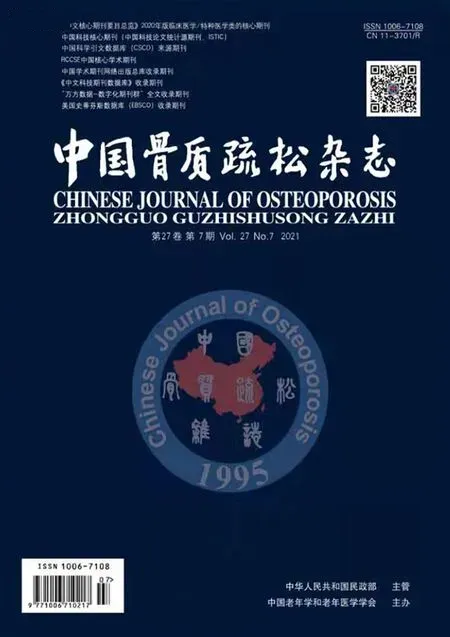肌少癥患者外周血炎性因子的Meta分析
黃安樂 卜子涵 薛夢婷 李青云 杜世正 徐桂華
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肌少癥(sarcopenia)的概念于1989年首次提出,與增齡相關的骨骼肌肌量下降,肌肉強度和(或)軀體功能低下為特征[1]。2018年歐洲老年肌少癥工作組(European Working Group on Sarcopenia in Older People,EWGSOP)正式將肌少癥定義為一種進行性、廣泛性,與跌倒、骨折、身體殘疾和死亡不良后果發生的可能性增加有關的骨骼肌疾病[2]。目前,肌少癥正影響著全球約5 000萬老年人,預計未來40年患病人群將高達5億[3],不僅降低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且與糖尿病、心臟病、心肺功能不全和認知障礙等疾病的不良預后有關,導致社會及家庭負擔加重[4]。
目前肌少癥肌量和肌質診斷的測量工具主要依靠成像技術,包括CT、MRI、超聲、雙能X線吸收測量法、人體成分分析、生物電阻抗等[5]。然而這類技術價格高昂,技術要求高,只能在設備完善的醫療場所使用,不符合當前肌少癥高患病率的現實需求。因此,EWGSOP建議開發一組生物標志物對肌少癥風險進行分層診斷,從而識別病情惡化的因素,監測治療效果。其中炎性因子被指出參與蛋白質分解代謝和肌肉合成等過程,吸引眾多學者探索其與肌少癥的相關性[6-7],然而少有循證證據支持該觀點。因此,本研究借助Meta分析對國內外肌少癥患者的炎性指標進行整合,為進一步探討肌少癥的發生機制,為尋找獨立、可靠、敏感的生物標志物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觀察性研究,包括橫斷面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或隊列研究;②病例組需按照明確標準確診為肌少癥,對照組為骨骼肌正常人群;③能直接提取或計算樣本量、炎性因子的均數和標準差;④中英文文獻。排除標準:①文章明確限定研究對象為罹患某種疾病的人群,具體包括肝硬化患者、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腎臟移植術后患者等;②體外和動物實驗類文獻;③重復發表;④數據不完整。
1.2 文獻檢索策略
確定中文檢索詞為“肌肉減少癥”“肌少癥”“骨骼肌減少癥”“肌肉衰減綜合征”“炎癥因子”“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干擾素”“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C-反應蛋白”,英文檢索詞為“sarcopenia”“sarcopenic”“inflammation”“inflammatory” “cytokine*”“chemokine”“IFN”“interferon*”“TNF”“tumor necrosis factor” “IL”“interleukin”“CRP”“C-reactive protein”。檢索時間為建庫至2020年5月。結合主題詞和自由詞進行檢索,并通過查詢專業期刊、最新出版的學術期刊資料和未公開發表的研究提高文獻檢索范圍。PubMed檢索策略如下:#1 sarcopenia[MeSH Terms] OR sarcopenia[Title/Abstract] OR sarcopenic[Title/Abstract];#2 inflammation[MeSH Terms] OR inflammation[Title/Abstract] OR inflammatory [Title/Abstract];#3 immune interferon[MeSH Terms] OR interferon*[Title/Abstract] OR IFN[Title/Abstract];#4 tumor necrosis factor[Title/Abstract] OR TNF[Title/Abstract];#5 interleukin[Title/Abstract] OR IL[Title/Abstract];#6 creactive protein[MeSH Terms] OR CRP[Title/Abstract] OR C-reactive protein[Title/Abstract];#7 cytokines[MeSH Terms] OR cytokine*[Title/Abstract];#8 chemokine[Title/Abstract];#9 #2 OR #3 OR #4 OR #5 OR #6 OR #7 OR #8#10 #1 AND #9。
1.3 文獻資料提取和質量評價
2名研究者獨立完成文獻篩選、資料提取和質量評價,并交叉核對結果。如遇分歧,通過討論至意見一致或與第三位研究者協商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基本信息:第一作者、發表時間、研究所在地、研究類型、樣本量、平均年齡、肌量評估方法;②結局指標:炎性因子濃度;③偏倚風險評價的相關要素。采用澳大利亞JBI循證衛生保健中心手冊和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對納入文獻進行質量評價。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羅德惠等[8]方法對提供樣本量、中位數、極值或四分位數的文獻進行均值和標準差的估算。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作為計量資料的效應值,并計算95%CI,當P<0.05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各文獻間的異質性采用Q檢驗及I2值評價,若P>0.10且I2<50%則認為無統計學異質性,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否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采用敏感性分析評估結論穩定性。采用Egger法和Begg法檢測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本研究共檢索出3 318篇文獻,剔除重復文獻后為2 187篇。通過閱讀文題和摘要初篩,閱讀全文復篩,最終納入17篇文獻[9-25],其中橫斷面研究13篇,隊列研究4篇,共計涉及9826例肌少癥患者。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Fig.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2.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見表1,記錄內容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所在地,樣本量、平均年齡、炎性因子和肌量測量方法。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literatures
2.3 納入文獻質量評價結果
納入橫斷面研究質量評價結果見表2,隊列研究質量評價結果見表3。結果發現,本研究納入文獻質量較高,存在較低的偏倚風險。

表2 橫斷面研究的質量評價結果Table 2 Qua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表3 隊列研究的質量評價結果(分)
2.4 Meta分析結果
2.4.1肌少組與正常對照組外周血CRP水平:納入13篇文獻[9-12,14-18,20-21,23,25](n=9 616),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骨骼肌正常對照組,肌少組外周血CRP水平升高,差異具有統計學
意義[MD=0.20,95%CI(0.15,0.24),P<0.01],見圖2。

圖2 肌少組與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CRP水平的Meta分析Fig.2 Meta analysis of CRP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 sarcopenia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2.4.2肌少組與正常對照組外周血IL-6水平:納入7篇文獻[10,13,17,19,22-24](n=483),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肌少組外周血IL-6水平高于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差異[MD=0.77,95%CI(0.13,1.40),P=0.02],見圖3。

圖3 肌少組與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IL-6水平的Meta分析Fig.3 Meta analysis of IL-6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 sarcopenia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2.4.3肌少組與正常對照組外周血TNF-α、IL-8、IL-10水平:關于TNF-α指標,本研究納入4篇文獻[10,19,22-23](n=279),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TNF-α[MD=5.07,95%CI(-0.42,10.57),P=0.07],見圖4。關于IL-8指標,本研究納入2篇文獻[19,22](n=78),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IL-8[MD=1.17,95%CI(-2.58,4.91),P=0.54],見圖5。關于IL-10指標,本研究納入3篇文獻[13,19,22](n=160),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IL-10[MD=0.34,95%CI(0.00,0.68),P=0.05],見圖6。這提示肌少癥患者外周血TNF-α、IL-8、IL-10差異無明顯統計學意義。

圖4 肌少組與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TNF-α水平的Meta分析Fig.4 Meta analysis of TNF-α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 sarcopenia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圖5 肌少組與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IL-8水平的Meta分析Fig.5 Meta analysis of IL-8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 sarcopenia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圖6 肌少組與骨骼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IL-10水平的Meta分析Fig.6 Meta analysis of IL-10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 sarcopenia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2.5 敏感性分析和發表偏倚
采用Stata12.0軟件進行敏感性分析,通過逐一剔除單項研究,觀察各研究對總合并效應量的影響。結果發現,單項研究對總合并效應量的影響較小,結果較為穩健可信(以CRP為例,見圖7)。由于TNF-α、IL-6、IL-8、IL-10等指標的納入文獻較少,本研究僅對CRP指標采用Egger’s法和Begg’s法檢測其發表偏倚。結果顯示,Z=1.65,P=0.100,t=-0.10,P=0.926,可認為不存在發表偏倚。
3 討論
隨著年齡的增加,老年人的細胞因子出現失調,具體表現為血液中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C反應蛋白水平上升2~4倍,機體長期處于低水平的炎癥狀態,即所謂的老年人慢性低度炎癥狀態[26]。初步研究表明該狀態與多種老年相關疾病,如糖尿病、阿爾茨海默病、骨質疏松癥、動脈粥樣硬化、肥胖癥等疾病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炎性因子也因此被認為是機體衰老過程中的生物標志物[27]。肌少癥作為新型的老年綜合征,越來越多研究指出,炎癥反應與其病理生理基礎有關。Payne等[28]研究指出,炎性因子可作用于細胞連接結構,損傷血管內皮細胞的完整性和良好耦合機制的建立,進而影響血管舒張功能和交換功能,導致局部血流調節受損,代謝需求降低,最終造成骨骼肌功能下降。von Haehling等[29]指出炎性因子與骨骼肌分解代謝途徑,包括泛素蛋白酶體系統、自噬溶酶體系統和細胞凋亡的激活有關,導致蛋白質合成分解代謝失衡,引起肌肉力量和質量降低。本研究通過Meta分析探究炎性因子在肌少癥患者和骨骼肌正常對照組中表達水平的差異情況。結果顯示,肌少癥患者外周血CRP、IL-6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而TNF-α、IL-8、IL-10等炎性因子濃度未監測到組間差異。
CRP是肝細胞合成的急性期蛋白,與年齡相關的退行性改變有密切聯系。臨床上通常把范圍在0~8 mg/L的CRP稱作為hs-CRP,因其靈敏度和準確性均較其他因子高,而且穩定性強,不易受影響因子干擾,且在疾病的早期就可以被監測,更被推薦作為老年慢性病的早期監測指標。Yang等[30]研究表明,CRP可抑制Akt磷酸化,從而導致下游的m TORc1通路開放受限,影響肌肉纖維蛋白合成。Liang等[31]研究指出CRP可激活核轉錄因子(nuclear factor-κB,NF-κB),而NF-κB是介導破骨細胞分化成熟的重要的信號通路之一,從而增加破骨細胞的生成和骨吸收,導致骨骼肌肌量下降。Dahl等[32]通過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發現,CRP與老年男性人群的骨密度呈負相關,且將非椎體骨折的風險增加了22%。多項研究也相應證實CRP指標與老年人肌力存在顯著關聯,可用于預測老年人的肌肉質量[33-35]。
IL-6是一種多效性細胞因子,在免疫調節、造血、炎癥和腫瘤發生等方面發揮著不同的生物學功能。目前關于IL-6誘導肌少癥的可能機制如下[36]:(1)IL-6可增加氧自由基(ROS)形成,從而激活FOXO3a,進而影響UPS的活性,造成蛋白質合成減少和蛋白質降解增加,最終導致骨骼肌喪失和功能損害;(2)IL-6可上調肌肉生長抑制素表達,進而負調控骨骼肌的生長,導致肌肉質量降低;(3)IL-6可抑制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I)表達,造成肌肉合成代謝的刺激減少,肌肉含量降低。此外,IL-6也被證實與肌少癥的臨床表現或體征相關。如Ferrucci等[37]通過隨訪老年婦女3.5年,發現高水平IL-6發生肌力降低和運動障礙的風險更高,更易造成肢體殘疾。Ding等[38]指出IL-6濃度升高會導致老年人全身、脊柱和髖部的骨密度下降。de Gonzal-Calvo等[39]表明老年人高水平的血清IL-6與肌肉質量降低、肌力下降密切相關。
TNF-α的生物學活性廣泛而且復雜,目前關于TNF-α與肌少癥的相關性研究結果存在矛盾。有研究指出TNF-α是誘導細胞凋亡的主要信號之一,與年齡相關的肌肉質量和力量的減少有關[40]。而來自動物和體外研究的數據支持TNF-α可通過p38MAPK、NF-κB等途徑對生肌過程發揮調節作用,表現為促進增殖和早期分化[41]。今后有待進一步研究明確TNF-α在骨骼肌中的作用機制。
本研究發現肌少癥與外周血炎性因子濃度水平存在一定相關性,但仍有一定局限性:①納入文獻以橫斷面研究居多,證據力度有待加強;②所調查的炎性因子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分析原因,可能以樣本的異質性為主要來源。目前肌少癥尚未有明確的診斷標準,各研究對肌少癥雖有明確定義,但在測量方法和各指標的診斷界值尚未達成統一。③外周血炎性因子采集過程中,人員細節上可能存在差異,包括采血部位、采血時間的選擇,壓脈帶的使用,靜脈穿刺技術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肌少癥患者外周血中CRP、IL-6的水平高于正常人群,提示這些炎癥因子介導的炎癥反應可能與肌少癥的發生發展有關,因不同研究間存在較大異質性,這些炎癥因子能否成為肌少癥早期診斷的生物標志物,未來亟待更多大樣本、高質量、更合理的證據予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