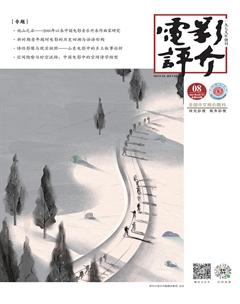后現代語境下歐美電影的碎片化影像語言重構
孫帥生

后現代視域下,歐美影片主要采用碎片化、拼接式的組織敘事模式,以多線交錯、時空重構、含混主題為其創作的主要藝術特征。此類影片巧妙而富有戲劇性地切割和串聯無序情節,以其深層次的內在關聯重構“零而不亂”的影片畫面。后現代風格電影主要借助情節交互、語言碎片化等方式,意旨影片所要呈現的核心主題。在敘事策略維度則重點涵括板塊型敘事、圓形敘事、多線索交互融合敘事等,看似充盈著混亂、斷裂等非理性特質,但循跡尋根便能夠發掘其內涵于碎片化語言中的串聯規律和線索。本文以富代表性的后現代風格歐美電影為例,探究上述三種敘事模式框架內,狀似凌亂紛雜、實為珠聯合璧的并行式多線結構敘事手法,以此體悟此類影片蘊含于碎片化語言中的集中性意旨。
后現代風格的歐美電影,在意識流、超現實維度敘事手法的嘗試和探索方面主要體現在將時間、空間的錯位互置;正敘、倒敘、插敘等多種敘事手法的相互融合及宏大視域下矛盾沖突的多元化凸顯。此種多重并列性事件橫向拼接的影片創作方式,有助于增強影片的戲劇效果[1]和藝術表達,能夠由碎片化的情節設置,層層遞進式的解密,進而深入探尋敘事主人公的復雜心理和影片試圖傳達的意旨與精神內蘊。如《東方快車謀殺案》《低俗小說》等后現代風格歐美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碎片化情節橫向拼接的特征,看似冗雜、無序、混亂的鏡頭畫面,當觀影者嘗試以核心人物為探秘的著力點而向四處輻射時,便能夠準確把握隱于多重線索中的粘合點和串聯內核,進而理解影片借助怪誕影像[2]、非理性敘事傳達的思想主旨。
一、后現代視域下的情節拼接敘事模式
(一)板塊式編排模式
后現代風格的歐美影片,以偵探、懸疑為主要題材,往往采用非常態化、意識流動的情節編排方式,富有創造性地賦予時空新的運轉方式,體現出較為濃郁的主觀化表征。此類型影片往往致力于以人為滲入點的板塊式拼接技法,替代以生活化、科學性為特征的物理時空連續流轉,將原本不同時空、不同經歷、不同性情的人、事、物以板塊的形式串聯組合在一起,以此實現影片表達主旨的目的。這種形似緊密相連的組合型板塊,實際上卻是碎片式語言及情節共同編織的非線性敘事結構。
歐美影片《羅拉快跑》便是板塊式敘事模式的代表性作品。該片核心故事情節的單一性,在某種程度上要求影片創作者在藝術創作技法方面著濃墨,這樣雖沒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復雜情節,沒有駁雜、豐富的主要和次要人物予以宏大結構的支撐,卻亦能夠于意識流敘事類型影片中獲得一席之地。該片創作者巧妙運用板塊式的編排模式,并非簡單地以單線結構描述女主人公羅拉在20分鐘內狂奔籌錢以拯救男友的完整經歷。雖然這也能體現在時間逐漸流逝的過程中,羅拉肢體神情以及內心的變化,但在敘事張力和藝術感染力方面卻有著較大不足和欠缺。
《羅拉快跑》恰如其分地融聚敘事張力和多元開放的留白式結局,將三個在敘事、故事時間方面均相同的情節板塊主觀拼接,以不同的情景模擬創設出不同的結局。相悖于單一的或悲或喜的結局,該片的三種迥異結局有助于充分調動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有效激發出觀眾聯想中超越影片三種結局的第四種結局。影片三個板塊先后呈現,在時間的起始點、情節的核心人物相同的前提下,會讓觀者產生某種情境還原和復歸的錯覺,而其中相異的遭遇又會給觀眾帶來某種落差感和陌生感。此類后現代風格板塊式拼接型影片,往往兼具熟悉感和陌生感,前者是觀者主觀臆想作用的結果,而后者則是影片所著力表現神秘感和未知感的客觀結果。
該片在板塊式敘事方面,設置了三種涵蓋悲喜意蘊的奔跑結局:第一種是羅拉求助銀行高管父親失敗,無奈和躊躇之下羅拉及其男友曼尼只能選擇另一條觸碰法律、鋌而走險的搶劫之路,很顯然,這種情境之下的壓迫、無奈和錯誤掙扎抉擇最終指向入獄的結局;第二種則更能夠凸顯激烈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情節沖突,發現父親出軌的羅拉,憤怒和不滿涌上心頭,選擇劫持父親搶劫銀行,搶劫成功后及時趕到阻止了男友曼尼的搶劫意圖,但男友卻不幸被急救車撞死。此種情境下,雖然曼尼并沒有走上罪上加罪的錯路,但羅拉劫持父親的舉動卻是嚴重違反法律的“逆行”,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劇。影片所設置的前兩個結局都是悲劇性質的,也是較為常規的大眾化思路,但是悲劇的結局往往會給觀者帶來某種惆悵與慨嘆;所以在第三個板塊情景復歸原點后,導演創新性地融入賭場這一能夠產生某種奇跡和轉機的場所,并且巧妙穿插父親出車禍后無礙的轉折性事件,最終以曼尼找回錢款、化解危機的合歡式結局收束,在某種意義上凸顯出影片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
(二)圓形記敘模式
所謂圓形記敘模式,是以線形敘事模式為參照標準而創設的新模式,此記敘模式以情節首尾相連為主要特征,故事情節在伊始和結尾處會出現近于重現、復歸和交融發展的現象。一般來說,圓形記敘模式是歐美后現代風格拼接式影片組織駁雜情節時較為常用的手法,此種起點與終點的交匯很大程度上融入詮釋了人物心理的變化發展,集中體現了內含于起點與終點中間紛繁復雜的個人、社會對核心主人公的正面與反面影響。
歐美后現代風格影片在此模式的代表作品即《低俗小說》。該片碎片化、拼接化的情節設置模糊了影片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界限和區分。總體觀之,影片可以大致分為“小南瓜”“小兔子”的搶劫行為;中間三大板塊主要圍繞黑幫人士溫特森、黑幫老大馬沙、朱爾斯、布奇等核心人物的糾葛與沖突展開情節的鋪陳和衍生。情節的混亂、人物的駁雜、場域的變更,使得該片畫面呈現出紛亂無序的特征,碎片化的語言使得前后故事情節較為松散,展現出跳躍式、突變型的視覺審美效果。
《低俗小說》中的三個核心大故事與兩個片段式小故事,各自擁有其主要人物和矛盾沖突,看似相互獨立、互不相干,但實際上在圓形敘事中串聯著朱爾斯等人的頓悟和思想嬗變。在“金表”一節中,布奇、馬沙從合作、決裂,再到最終選擇彼此諒解、冰釋前嫌,“金表”在其中作為物象標志串聯布奇與馬沙之間斗爭沖突的復雜關系;在“邦尼的處境”一節中,朱爾斯和溫特森這一對黑幫殺手,遭逢馬文的亂槍掃射卻幸運地活了下來,內心的觸動和心靈的震顫讓朱爾斯真正體悟到生命的意義,馳騁“殺”場只會加重罪孽,而無益于靈魂的解脫和身心的釋然。
影片“向善得救”的主旨巧妙地串聯起并行不悖、獨立進展的五個故事,主題的升華、圓形結構的運用,讓首、尾兩個原本凝聚力、目的性都不甚強的片段故事擁有了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此種圓形結構,能夠讓原本碎片化的語言陳述和情節編排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緊密的關聯性,不同事件對不同人物靈魂的觸動,讓原本的黑幫群體收獲了新的生活希望和堅定的生存理念,從而在意識流情節的橫向拼貼和首尾相融中消解了絕對的惡,進而真正實現惡與善的和解,促進惡向善的轉變。
(三)多線索敘事模式
后現代風格歐美電影中較為常用的敘事手法便是多線索交織的敘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不同時空之間的銜接與流轉,不同人物命運的拼接與著墨。此類敘述模式并不是各個部分分別以時間為序,從始至末、詳盡有序地對各線索展開兼具沖突與和諧的鋪陳和描述,而是各個部分同時展開、交叉進行[3],以一條核心的時間脈絡對多條分支線索中位于特定時間段的故事進行鏡像捕捉和影像剪切,從而使得影片具有豐富駁雜和意旨相通的審美價值。
多線索敘事模式的應用,有助于在時空轉換、人物更替等畫面流變中巧妙滲入影片情節發展的前因后果,進而激發觀者主動思索并嘗試串聯不同畫面中核心情節與其他分支線索之間的聯系。影片所選擇的多條線索往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線索前因后果的串聯中蘊含著某種共性和指涉意義,寄托著影片導演的創作意旨和設計目的。這種看似平行無交叉的多條線索,仿若前言與后語大相徑庭的碎片化語言,狀如毫無交集的時空情境,實則都有一條將其緊密串聯起來的無形線索,一般后現代風格歐美影片都會將這條無形線索置于某個機緣巧合或是某個深層次的共性原因。以《通天塔》和《東方快車謀殺案》為例,此二者在敘事編排中,都擁有超過3條并行不悖、相互獨立又彼此聯系的線索,前者集中記敘了11天里位于美國、日本、墨西哥、摩洛哥的四個悲劇故事,其線索的串聯點亦是呈現“零而不亂”畫面的關鍵便是日本人贈與非洲朋友的“步槍”以及作為悲劇核心沖突焦點的“語言不通”問題。后者則將集體復仇案融聚于東方快車之上,借助偵探的推理和想象,呈現出12個看似身份迥異、幾無交集的涉案兇手與遇害者之間的矛盾沖突。該片采用時空重疊的蒙太奇式拼接手法,零散卻極富內在條理地對影片進行了多條線索交互式、并列式、交疊式情景展現。人物的混雜性、語言的碎片化、矛盾的迥異性,最終融聚成共同的泄憤手段——刺殺富商雷切爾,而這其中拼接式的畫面轉化,不僅客觀還原和再現存在于富商和12位兇手之間的恩怨情仇,也以復合式、交疊性的敘事方式深入影片的核心主旨——揭露社會中的法理與人性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二、碎片化語言的多元開放內蘊
歐美后現代風格影片以“碎片化語言”作為其拼接式情節和交互式時空轉變的關鍵性推動要素,進而以“零而不亂”的畫面重構來激發觀影者尋覓串聯型線索的興趣和積極性。宏大而龐雜的人物、時空、情節結構讓此類型影片擁有更加開放多元的文化內蘊,即碎片化語言的形式之下,包含著內容維度指涉明確、意旨豐富的內在規律。多條線索交織的碎片化情節拼接不僅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挖掘圓形人物的復雜心靈特征,也能夠較為深刻地表現影片核心的人文主旨和精神內蘊。
此類影片中,語言、情節的碎片化與主旨、內蘊的集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開放多元的文化內蘊是“零而不亂”的情節網絡中最核心的一環,詮釋著影片的社會價值和時代意義。影片通常會在充滿夢幻意味和超現實主義色彩[4]的紛繁復雜情節中融入非理性精神特征,進而與現實世界進行對比和指涉,以此來揭示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此種癥結對人性的摧殘和扭曲。例如,導演大衛·林奇所創作的后現代風格電影《內陸帝國》,女主角與其所飾演的虛擬角色是具有相互嵌套特質的密切關聯體。二者都近乎雷同般發生了婚外情,但更具戲劇性和怪誕性的情節在于,女主角、虛擬角色其實都只是一位波蘭女子在遭逢丈夫無情背叛后所臆想出來的形象。這種層層嵌套式地拼接碎片化、荒誕式的故事情節[5],導演所意旨的是通過虛幻臆想的非理性婚外情事件,深入剖析后現代社會人類靈魂深處的非理性精神因子的復雜和扭曲。
相較于《內陸帝國》較為明確和直接的揭示和披露態度,《低俗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穆赫蘭道》《羅拉快跑》等后現代風格影片則體現出開放多元的意旨內蘊。以《羅拉快跑》為例,相同時間、相同境況內3種結局的編排,讓影片并沒有流于單一固定化善惡、悲喜的結局呈現方式,而是在仿若前后毫無關聯的三種板塊敘事中穿插碎片化的語言,創設出在形式與內容方面都有較大差異的3種假設情況,雖然影片并沒有言明究竟哪一種結局才是屬于羅拉和曼尼的最終結局,但很顯然觀眾在這種開放性和多元化的留白式藝術處理中,都會比較傾心于化險為夷的喜劇結局。但是,導演所要傳達的并非止于結局的開放性,其更意旨于對正確價值觀擇取問題的深入忖思,前兩種悲劇式結局都只是以惡制惡、以暴制暴式的偏激做法,而最后一種雖是喜劇結局,但是以賭博作為謀求轉機的冒險方式是否真的合理,如果曼尼沒有返回地鐵找回被乞丐撿拾的10萬馬克,那么這個結局是否又會重寫,是否賭博會以失敗收束?一系列問題在影片碎片化語言的陳述中得到了展現,也在“零而不亂”的畫面重構中留給觀影者深入而全面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結語
后現代視域下的歐美影片,致力于進行“零而不亂”的畫面重構,旨在借助圓形、板塊化、多線索等敘事手法,展現豐富駁雜的情節結構背后所蘊含的時代內蘊和審美價值。此類影片對時空結構采取或并行、或交織、或錯位的處理方式,這些近乎戲劇性的藝術處理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會讓觀影者產生混亂、費解、排斥之感,能否巧妙地引導觀眾尋找串聯多條線索中的關鍵粘合因子,是此類影片成功與否的關鍵。《低俗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等影片,均較好地于碎片化的語言中滲入對主人公非理性心理的挖掘,以拼接式的情節編排揭示富有開放多元性的核心意旨,進而實現影片的社會效益和藝術審美的統一。
參考文獻:
[1]畢躍忠.歐美推理小說的電影化敘事策略建構[EB/OL].(2020-02-26)https://www.doc88.com/p-88261139426389.html.
[2]程曉娟.歐美電影視聽語言的特征表現分析[ J ].短篇小說(原創版),2016(11):83-84.
[3]李巖.評析歐美電影視聽語言的特征表現[EB/OL].(2021-04-03)https://www.doc88.com/p-70559510810217.html.
[4]樊鵬.歐美后現代電影敘事策略解讀[EB/OL].(2018-05-26)https://www.doc88.com/p-23647833683618.html.
[5]溫玲霞.敘事重構與怪誕影像——大衛·林奇電影中的非理性精神世界[ J ].電影評介,2020(19):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