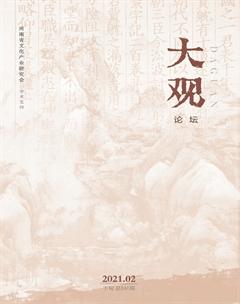符號學視角下的極少藝術“物性”美學
謝旭
摘 要:文章運用符號學的方法對極少藝術的“物性”美學進行了分析,主要簡述極少藝術“物性”的美學特質,運用皮爾斯符號學“再現體”與“對象”的理論對“物性”美學進行了分析,并借鑒海德格爾關于“物性”的思想分析了極少藝術作品的物化和符號化。
關鍵詞:符號學;極少主義;“物性”
一、極少藝術“物性”的美學特質
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有兩個重要的藝術流派,一個是波普藝術,另一個則是極少藝術。事實上,兩個流派都可以看成是對抽象表現主義的反叛①,二者都受惠于兩位重要的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勞森伯格和賈斯珀·瓊斯,但兩個藝術流派卻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②。極少藝術并不是孤立地出現于美國,同一時期的德國有“零社”,意大利有“貧窮藝術”,日本有“物派”,韓國有“單色畫”,等等。雖然各個藝術團體和流派其美學思想各異,極少藝術內部的各個藝術家的思想也有差異,但是就總體而言,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以一股展現“單色繪畫/現成品”為美學特質的藝術思潮,但是,不同于杜尚的“現成品”裝置的幽默和反諷,極少主義作品給人的感覺卻似乎是克制、冰冷,甚至死板。
事實上,極少藝術的美學特質不同于杜尚“現成品”美學特質的重要一點就在于,兩者對待“單色繪畫/現成品”的態度不同,杜尚視“現成品”為傳達觀念的工具,而極少藝術則視“單色繪畫/現成品”為一個物品本身③。最能體現極少藝術的這一美學特質的便是身為極少主義藝術家的唐納德·賈德寫于1965年的文章《具體物件》。在文中,賈德這樣寫道:“繪畫的一個主要問題在于,它是一塊平坦地靠墻放置的矩形平面。矩形本身就是一種形狀;它顯然也是整件作品的形狀;它決定并且限制了在其上或其中的內容的安排。……一幅繪畫幾乎就是一個實體、一件事物,而不是一群實體及參照物的難于明確定義的總和。”在這篇文章中,賈德首先提到,一幅繪畫首先是一個矩形、一個形狀,進而是一個實體、一件事物。
兩年后,現代主義藝術史家邁克爾·弗里德對賈德的這篇文章做出了回應——發表批判極少藝術的著名文章《藝術與物性》。在文中,弗里德提到:“現代主義繪畫已經發現了它的律令,即它擊潰或是懸擱了它自身的物性,這一事業的關鍵因素就是形狀,只不過這一形狀必須屬于繪畫——它必須是繪畫的,而不是,或者不僅僅是,實在的。而實在主義藝術④則將賭注全部押在了作為物品的既定特質的形狀上,如果還不能說作為某種物品本身的話。它不尋求擊潰或懸擱它自身的物性,相反,它要發現并突顯這種物性(objecthood)。”在這篇文章中,弗里德將極少藝術與格林伯格的現代主義對立了起來,認為被現代主義懸擱的“物性”被極少藝術所突顯,被突顯的“物性”與繪畫之間出現了沖突。沖突的結果之一,便是極少藝術的繪畫與雕塑之間的界限被消弭,此時,極少主義作品被當作一個具有實在性的“物”來看待,一個“物”就會有真實的體積和空間,而非在二維平面中創造三維空間的錯覺。
二、再現體、物質載體與“物性”
在符號學中,有兩類符號意指形態。第一類是以索緒爾、羅蘭·巴特為代表的符號學派,將符號意指關系分為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這對概念來自索緒爾的語言學,能指即聲音形象,所指即概念。第二類是以皮爾斯、翁貝托·埃科為代表的符號學派,將符號意指關系分為了“再現體”(representame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ant)。這三個概念來自皮爾斯的哲學觀點,“再現體”即符號,“對象”即所指涉的對象,“解釋項”為某符號所引發的闡釋而產生的符號。大多數情況下,“再現體”都需要物質載體來顯現。
在繪畫中,作品本身即“再現體”,作品所指涉的事物即“對象”,作品所引發的闡釋即“解釋項”。作品所棲居的墻壁、畫布、宣紙、顏料等等即物質載體。在西方美學史中,可以粗略地將后現代主義之前的美學理論分為三種:摹仿倫/再現論、表現論、形式論。從符號學的角度說,繪畫作品作為“再現體”,寫實主義繪畫的“對象”是世界的物象,表現主義繪畫的“對象”是藝術家主觀的物象或情感形式,那么,抽象主義繪畫和極少主義作品的“對象”又是什么呢?
似乎抽象主義繪畫和極少主義作品的“再現體”差別不大,只是多和少的區別。但是,兩者所指涉的“對象”差別卻是很大的。抽象主義繪畫的“對象”是繪畫的本體,或者說是由點、線、面、體等視覺因素所構成的形式美,甚至可以說,抽象主義繪畫的“再現體”和“對象”是合二為一的,抽象主義繪畫就只是要表達它自身。正如格林伯格在1954年耶魯大學的講座上所說的:“一種可識別形象的在場與否,跟繪畫或雕塑的價值之間的關系,并不比歌詞的在場與否,跟音樂的價值之間的關系更明顯。”
在抽象主義繪畫中,盡管外在對象被舍棄,但物質載體依然是被壓抑的,很多形式主義藝術史家就認為藝術作品中的物質載體應該天然地受到壓抑,例如前文的邁克爾·弗里德。正如哲學家何塞·奧特加·伊·加塞特所說:“一個認知的物除非它成為一個圖像、一個概念,一個想法,就是說除非它停止自身的存在而成為它自身的影子或輪廓,否則它什么都不是,也不存在。”只有物質因素被壓抑了,藝術作品中的其他因素才有可能顯現。在抽象主義繪畫中是如此,在寫實主義繪畫中就更是如此,物象的精巧與“物性”的表達是天然的敵人,物象越是精巧,“物性”就越被遮蔽,被不露聲色地隱藏。
然而,極少藝術的“對象”即再現體的物質載體,也就是在之前各個藝術流派中被極力隱藏的“物性”。在極少主義作品中,物質載體成為了對象,同時也打破了物質載體與再現體的區別,“再現體”、物質載體和“對象”在極少主義作品中合為一體。而英文“object”一詞,本身即有“對象”和“物”兩種含義。一件作品/物可以被分為形式和質料,在極少主義作品中,物質載體本身成為了“再現體”,形式就是質料,質料就是形式。于是,極少主義作品往往呈現出單一的形式、單一的質料、單一的色彩。在形式主義的關系構圖(relational composition)被取消掉之后,極少主義藝術家們采取了一種“一個接一個”的排列策略,正如克勞斯所說:“‘一個接一個似乎就是一天天流過的日子,沒有給予任何形式或方向,無人棲居其中,沒有生活內容,意義全無。”極少主義藝術家對于外在意義的抗拒使得他們普遍將自己的作品命名為“無題”,通過不預加任何意義的命名方式讓觀者直面作品本身的“物性”。同時,為了更好地凸顯作品本身的“物性”,裝裱的畫框也被取消,因為畫框的存在會讓欣賞者誤以為這是一個平面,進而遮蔽作品自身作為“物”的體積感。
在極少藝術風潮的早期,格林伯格是持觀望態度的,在寫于1962年的文章中他提到:“一幅拉伸或縫合的畫布已經是一幅畫了——盡管不一定是成功的一幅。”但是在1965年賈德的《具體物件》發表之后,格林伯格展開了反擊:“終于,極少主義者們似乎已經意識到,離譜(far-out)本身必須是離譜本身的目的,而這意味著最離譜(furthest-out),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格林伯格憤怒的原因就在于極少主義者走得太遠(far)了,將現代主義繪畫推到了一個無法再還原的地步,以至于離譜,甚至對“物性”的強調也將架上繪畫本身推到了一個無法再向前一步的境地,在極少藝術風潮過后,“架上繪畫終結論”席卷而來,最離譜的情況發生了。
三、物化還是符號化?
在符號學中,如果符號失去所攜帶的意義,即符號脫離了與對象的關系,那么它就不能稱之為符號了,這種情況被稱為“去符號化”(Desemiotization)或“物化”。比如,對中國人來說意味深刻的梅蘭竹菊,在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那里只是普通植物,此時,梅蘭竹菊從象征道德情操的文化符號降解為植物本身。相反的一種情況則被稱為“符號化”(Semiotization),即某物開始有了指涉對象,攜帶了意義,成為了符號。比如海邊的一個貝殼,它在海邊只是一個貝殼而已,但是如果它被當作禮物送給了別人,這個時候,它便有了意義,成為了情感的符號。
對于極少藝術來說,“對象”、“再現體”及其物質載體是合一的,物即為對象,“ object”即為“object”。此時,究竟是去符號化還是符號化呢?可以說,二者都有。我們可以借助海德格爾的思想來分析這一點。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將物之物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作品之作品因素三者并列,并認為:“所有作品都具有這樣一種物因素(das Dinghagte)。……藝術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其中這別的東西構成藝術因素。……我們的意圖是把具有物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與具有作品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劃分開來。”顯然,海德格爾將藝術作品的物因素與作品因素進行了區分,認為構成藝術作品本質的是作品因素。可見在當時,“物性”還不被認為是藝術因素之一,需要與其他被認可的藝術因素相結合才能成為一件藝術作品。
從去符號化的角度來說,在以往的藝術中,物因素都是作為工具突顯作品因素,或者說指涉對象——世界的再現、情感的力量、繪畫的本體等等。物因素是符號載體,而作品則是符號。例如,在畢加索的綜合立體主義時期,其綜合材料的運用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畫面;在杜尚的裝置中,現成品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觀念;在更早的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古典繪畫中,物的特性則是被極力壓抑和隱藏的。但是在極少藝術中,“物性”得到了突顯。此時,之前的一切指涉對象都不存在了,作品因素也就喪失了,作品只剩下物因素,即被物化、被去符號化。
反之,從符號化的角度來講,正是因為物因素得到了突顯,其他的指涉對象都不存在了,于是,物因素才成為了作品因素。此時,作品喪失指涉對象之后再度找到了它的指涉對象,即它自身,重新被“符號化”。但此時,正如上文所說,物因素與作品因素合二為一,物質載體、“再現體”和“對象”合為一體。
海德格爾也認為:“作品中的物因素是不能否定的,但如果這種物因素歸屬于作品之作品存在,那么,我們就必須根據作品因素來思考它。如果是這樣,則通向對作品的物性現實性的規定的道路,就不是從物到作品,而是從作品到物了。”在這里,海德格爾似乎道出了極少藝術的一個特點,即極少主義作品雖然是突顯“物性”本身,但依然是被當作藝術作品來觀看的,甚至可以說,物之物因素需要成為作品之作品因素才可以被觀看和凝視。
四、結語
藝術符號學作為符號學的分支,在繪畫領域,先后有福柯、蘇珊·朗格、諾曼·布列遜等學者的研究。本文運用符號學的意指三分式原理對極少藝術的“物性”美學進行了分析,極少藝術的“再現體”、物質載體與“對象”是合一的,這種合一不僅將現代主義繪畫推入無法再還原的境地,同時也昭示著“架上繪畫終結論”風暴即將到來。最后,通過對于海德格爾“物性”觀點的分析得出,“物性”只有通過將自己符號化,作為極少主義作品,才能夠被觀看和凝視。
注釋:
①甚至說,可以看作是對格林伯格本人的反叛。
②但當時有些的評論家也同樣認為,兩者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共通之處,這從極少藝術的另一個名字“無圖波普”(Imageless Pop)中可以看出。
③事實上,1963年杜尚在加州帕薩迪納藝術博物館的回顧展給了極少主義藝術家們很大的啟發。
④弗里德將極少主義稱為實在主義藝術(Literalist Art)。
參考文獻:
[1]JUDD D.Specific objects[J].Arts Yearbook,1965(8).
[2]弗里德.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M].張曉劍,沈語冰,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3]格林伯格.藝術與文化[M].沈語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4]GREENBERG C.After Abstract Expressionism[J].Art International,1962(6):30.
[5]GREENBERG C.Recentness of Sculpture[J].American Sculpture of the Sixties,1967:47.
[6]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文集:林中路[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7]克勞斯.現代雕塑的變遷[M].柯喬,吳彥,譯.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
[8]HOPKINS D.After Modern Art:1945-2017[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9]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M].趙星植,譯.成都:四川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0]JOSELIT DAVID.American Art Since 1945.[M].London:Thames&Hudson LTD,2003.
[11]BATTCOCK GGREGORY.Minimal Ar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12]福斯特.實在的回歸:世紀末的前衛藝術[M].楊娟娟,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13]朱橙.物性、知覺與結構[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6.
[14]邁耶,李云.極簡主義運動的興起[J].裝飾,2014(10):12-19.
[15]張曉劍,沈語冰.物性的誘惑:弗雷德的現代主義立場及其對極簡藝術的批判[J].學術研究,2011(10):134-140,146.
作者單位:
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