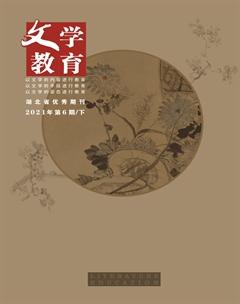《傷逝》中的子君與《逃離》中的卡拉形象比較
張學思
內容摘要:以魯迅《傷逝》中的子君與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卡拉這兩個人物形象比較,她們的兩次逃離,第一次逃離父母大家庭,第二次逃離婚姻的牢籠。比較她們逃離后面對同樣的女性生存困境:經濟困境、愛情困境、自我困境等。各自文本中的兩個寵物(阿隨與弗洛拉)也隱喻著女性由逃離走向回歸這一逃離模式。
關鍵詞:女性 逃離 困境逃離 模式
“逃離”是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不斷重復的母題,是人類面對困境時的共有選擇方式之一:逃離現有困境,尋求新天地。而在眾多的逃離故事中,關于女性逃離的故事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在近現代,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無論是現實生活中,還是文學作品中,“逃離”的女性形象越來越多,如易卜生筆下娜拉的逃離,現實生活中蕭紅的逃離等,這是女性對自身命運的覺醒,并試圖作出一些努力與嘗試,以改變現有的女性困境。本文以魯迅的《傷逝》與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兩位女性人物形象:子君與卡拉為研究對象,探析她們在各自人生中的逃離,發現她們都只實現了逃,并沒有真正地實現離。
一.女性人生中的兩次逃離
在西方與中國的歷史中,女性大多居于從屬地位。在西方,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而存在,在中國,女性作為父權與夫權的附屬而存在。在中西方的一次次婦女解放運動中,促使女性在其思想上有覺醒的意識,從而跨出“逃離”的步伐,她們試圖逃離生活中的困境,尋求新的自由天地。
(一)第一次逃離父母家庭的主動
對于女性來說,她們的第一次逃離:為了愛情,寄希望于逃離父母大家庭,從而獲得一種愛情上的自由。為此子君發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1]的逃離宣言,逃離父母大家庭,與涓生同居。卡拉也是如此,“她在桌上留了張紙條,清晨五點鐘悄悄溜出了家,在街頭的教堂停車場上與克拉克會合”[2]。她們二人為了愛情,決絕地逃離父母大家庭。但她們的第一次逃離的決絕,其實是有后盾支撐的,即愛情伴侶。子君與卡拉的逃離,實際是將女性的依附性,從一個男性(父親)轉換到另一個男性(丈夫)身上的,她們的自我是缺失的,她們的附屬性使得她們完全不能夠獨自承擔逃離的后果。
其次,她們逃離的對象是不同的。子君逃離的是父權制下的父親、叔伯,她逃離的是中國封建式的傳統包辦婚姻,她逃離的是其母親所處的婚姻命運。在子君逃離封建家長制的大家庭過程中,她的母親始終是失語的,文本中沒有出現任何其母親對于她愛情或者婚姻的言論。自始至終都是子君的父親與叔伯們在發聲。作為子君母親那一代的女性顯然已完全從屬于丈夫,失去了表達自我的聲音。而卡拉逃離的是父親(繼父)與母親,以及一種現有的生活。卡拉的繼父與母親都對卡拉的愛情婚姻發表了他們自己的見解,并試圖讓卡拉意識到真實生活的殘酷性。卡拉顯然忽視了他們的忠告與勸解,義無反顧地逃離現有的安逸舒適,尋找愛情與未知的新鮮感。卡拉對于自己丟掉的東西是清楚的,在這一點上,她比起子君,其自我覺醒意識是更為強烈一點的。她不但為了愛情,也是為了對另一種未知的生活的追尋。對于卡拉,“她唯一真正想做的,從出生以來,唯一真正想做的,就是能夠住在鄉下和動物打交道。”[3]而克拉克的出現,恰巧滿足了她的想法,既能給她愛情,也能實現她對未知生活的想象。
她們逃離父母,貌似得到了愛情上的自由,卻重蹈了母親的婚姻命運,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言:“受到雙親權威保護的少女,在反抗與希望中運用她的自由:她利用它來拒絕和超越他與此同時感到安全的境況;她正是從家庭的溫暖中向婚姻超越;既然她結了婚,在她面前就再也沒有別的未來。家庭的大門對著她重新關上:這將是她在人間的全部命運。她準確地知道,留給她的是什么任務:就是她母親完成的同樣任務,日復一日,要重復同樣的儀式。”[4]子君和卡拉的第一次逃離都是想要反抗父母家庭,通過婚姻來獲得自由。為此,她們決然的與父母、與過去割裂,由于她們自身獨立性的缺乏,附屬性的充斥,第一次逃離并沒有讓她們獲得所想要的自由,反使她們陷入了婚姻困境,于是她們又開始了第二次逃離。
(二)第二次逃離婚姻牢籠的被動
她們的第二次逃離:逃離婚姻日常生活的瑣碎。第二次的逃離對于她們來說顯然是艱難與未知的,此時的她們是沒有過多的后盾支持的,在沒有任何經濟支撐的情況下,她們的逃離相比第一次逃離,凸顯出了被動性。子君在涓生沒有決絕的說出那些不愛他的話之前,還始終不能意識到她與涓生的愛情已經在婚姻的瑣碎中消磨殆盡了,在度過了一個極難忍受的冬天之后,她終于在父親接她的時候,選擇了逃離婚姻牢籠。她的第二次逃離是被動的,不是自己主動走出婚姻家庭,而是由作為父權中心代表的父親接回了家。
卡拉的第二次逃離,也不是主動的自我意識覺醒,她是在與賈米森太太聊天中,抱怨克拉克,一開始她并沒有想過真正地逃離,“出走嗎?如果辦得到的話我早就這樣做了”[5],“只要可能,我會付出一切代價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沒有錢。在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6]在西爾維婭·賈米森的幫助下,她才開始走上逃離之路。
子君逃離婚姻的家庭,卻再次回到了父權為中心的家庭,以死結束。卡拉逃離婚姻的牢籠,卻在大巴車還未抵達自由的國度,便忍不住給克拉克打了電話,要求她接自己回家,再次回到了婚姻的家庭。她們的第一次逃離是為了愛情逃離父母家庭,卻陷入了另一個困境:婚姻的現實與瑣碎,“家庭不再保護她對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個孤獨和被拋棄的從屬者。愛和習慣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幫助,但不是拯救。”[7]為此,她們又不得不再次逃離現有的困境,但基于女性逃離之后面對的生存困境,她們只實現了逃,卻不能真正的實現離。
二.女性逃離后的生活困境
女性的第一次逃離父母家庭困境,卻陷入了另一種婚姻牢籠,面對著現實生活中的諸多生活困境。
(一)經濟困境:過度依附男性伴侶
卡拉在一開始逃離父母的信中說道:“我一直感到需要過一種更為真實的生活。我知道在這一點上我是永遠也無法得到你們的理解的。”[8]而卡拉所謂的真實生活是什么?是“她把他看作是二人未來生活的設計師,她自己則甘于當俘虜,她的順從既是理所當然也是心悅誠服的”[9]從一開始卡拉便不是獨立的,而“婚姻必須是兩個自主的存在的聯合,而不是一個藏身之處,一種合并,一種逃遁,一種補救辦法”[10]她的逃離僅僅是愛情意識的覺醒,是想要脫離自己固有的一種生活,是對新鮮生活和所謂“真實生活”的向往,真實生活回饋給她的是殘酷。第一次逃離后,卡拉與卡拉克一開始的生活是愛情的甜蜜,他們會開著車在鄉野間漫游,旅途是充滿歌聲與趣味的。但落實到婚姻現實中,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漫游不但浪費時間,還浪費金錢,他們開始感受到生活現實所帶給他們的壓力。他們的馬術學校會因為天氣不好的原因,學員少之又少,經濟壓力隨之而來。她與克拉克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生活困境。于是卡拉需要去賈米森太太家做幫傭,盡管不情愿,卻知曉她必須這么做。
子君的生活也是如此,在經濟空間的狹窄里,她與涓生的愛情被消磨殆盡。子君第一次逃離之初,他們心甘情愿的蝸居在大院中小小的破屋中。他們在愛情的初始,逃離的初始同樣是充滿甜蜜與生機。但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壓力:子君依靠涓生的微薄薪水生活,一整個家庭的開銷壓力也是聚焦在涓生身上。現實生活讓子君忙碌起來,子君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更不用說讀書和散步了。她的生活困在了蒸饅頭、做飯與洗衣服之中。而料理家務讓女性遠離了自身。
卡拉與子君在第一次逃離之后,面對最緊要的困境便是經濟困境,她們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了愛情上的自由,但這個自由如同空中樓閣,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撐,沒有根基,漂浮著。“在經濟上這個共同首腦是他(男人),因此,在社會看來,體現這個共同體的是他”[11]。卡拉與子君在經濟上,依賴的是男性伴侶。當她們自依賴的那一刻起,她們也承認了自身的附屬性,她們以男性為中心,建構自己的婚姻生活。
(二)愛情困境:愛情的消逝
卡拉面對的不僅是經濟壓力,還要隨時忍受克拉克火爆的脾氣與大男子主義。在克拉克的眼中,卡拉如同一只小寵物一般,是他的附屬物一般。在克拉克的敘述中,多次稱卡拉為“我老婆”,卡拉總是作為其附屬物的存在,而不是一個作為人的獨立個體而存在。克拉克甚至不在乎卡拉的尊嚴,企圖威脅與敲詐賈米森太太,想要從她那里獲得一筆錢來緩解自己的經濟壓力。從始至終,他沒有明確說過他愛卡拉,卡拉對于其只是他老婆,被定義為他的一個附屬物。自始至終,都是卡拉獨自訴說對克拉克的愛情,對克拉克的依賴。而克拉克的愛情是模糊的。
涓生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中與經濟生活的壓力下,他對子君的愛也漸漸消淡。涓生開始躲避子君,躲避家庭,躲在圖書館中求得寧靜與靜謐。于是他開始對子君說出那些決絕的話,“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于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12]。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有一種不幸使他們(夫妻)很少擺脫得了的:這就是厭倦。不論丈夫成功地把妻子變成他的應聲蟲,還是每個人龜縮在自己的天地里,過了幾個月或幾年,他們再也沒有什么可溝通的了。夫婦是一個共同體,其中的成員失去了自主,卻不能擺脫孤獨;他們靜止地同化,而不是互相維持生活活躍的關系。”[13]
卡拉與子君為了愛情,逃離了父母家庭。可是逃到了婚姻家庭中,當愛情伴侶愛的消逝,她們面對的是更為真實的愛情與生活的現實。為了愛情而逃離,但當愛情也消失殆盡的時候她們一無所獲,她們當初為了愛情的努力與逃離的決絕顯得空洞而無力。
(三)自我困境:獨立性的消失
在面對經濟困境與愛情困境中一系列雜亂的事件中,卡拉崩潰了。卡拉終于說出“我再也受不了了。”受不了她的丈夫,受不了這樣“真實”的生活。于是卡拉在賈米森太太的幫助下,決定開始她的第二次的逃離,但自她坐上大巴,便開始一邊想象未來獨自生活的艱辛,一邊不由自主地想起克拉克。在她逃離克拉克以及他們婚姻的的旅途中,卡拉卻不斷地提到克拉克七次……于是她再也忍不住地喊出“讓我下車”,并祈求克拉克來接自己回家。她的逃離徹底的失敗了。
子君在生活的瑣碎與伴侶的厭倦中,逃離了婚姻家庭,卻只能再一次回到了父母大家庭。她沒有留下任何字跡,徒留下了鹽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但是子君作為已經與涓生同居過的女性,逃離之后,她在嚴威與冷眼中走著所謂的人生路,回到封建大家庭后的無處歸屬,使得子君最后選擇了死亡。
卡拉與子君在逃離之后,由于過于在經濟和愛情上依賴一個男性,生活的重心全部在一個男性身上,她們的自我獨立也在逐漸消逝。作為女性,“附屬性在她們身上已經內化了:即使當她們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動時,她其實是奴隸;男人本質上是自主的,他只是從外邊被縛住。如果他感到他是一個受害者,是因為他承受的負擔更為明顯:女人像一個寄生者那樣靠他供養,而一個寄生者不是一個獲勝的主人。”[14]所以,盡管她們有著逃離的意識,但是卻不能真正地離開男性。她們的逃離陷入了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循環:逃離—回歸。
三.女性逃離模式的隱喻與重復
(一)阿隨與弗洛拉的隱喻
在這兩個文本中,都出現了一個互文性的隱喻對象:《傷逝》里子君的阿隨,《逃離》里卡拉的弗洛拉。阿隨與弗洛拉的逃離模式隱喻了女性的逃離模式的最終指向,即“逃離—回歸”。
阿隨是子君養的一只花白的叭兒狗,即使在飯菜不飽的境遇下,子君也是要先喂了阿隨,甚至有時給阿隨自己也不輕易吃的羊肉,可見阿隨對于子君來說是重要的。在子君逃離婚姻家庭后的一天里,涓生在一個陰沉的上午,“偶然看到地面,卻盤旋著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15]他發現那是阿隨。它回來了。阿隨的回歸伴隨著瘦弱與半死,顯然它的逃離,意味著失去了子君的悉心照料,在饑餓與寒冷中選擇了回歸。
弗洛拉是卡拉養的一只白山羊。在弗洛拉丟失之后,她不斷的夢見弗洛拉,弗洛拉的失蹤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她的逃離意識,在瑣碎的生活和暴脾氣的克拉克的重壓之下,她萌生了“逃離”的意識。在西爾維婭·賈米森的幫助下,她開始逃離。但真正獨自面對未知的生活,她退縮了。在大巴還未抵達目的地的時候,她便要求下車,給克拉克打了電話讓她來接自己。她回歸到了婚姻生活中。在克拉克將衣物還給西爾維婭·賈米森太太的時候,弗洛拉出現了,弗洛拉的回歸像一個幽靈一樣。但是弗洛拉在日后又再一次的丟了(逃離),直至后來,“在干完一天的雜貨后,她(卡拉)會作一次傍晚的散步,朝向樹林的邊緣,也就是禿鷲在哪里聚集的枯樹的跟前。接下去就能見到草叢里骯臟、細小的骨頭。那個頭蓋骨,說不定還粘連著幾絲血跡至今尚未褪凈的皮膚。這個頭蓋骨,她都可以像只茶杯似的用一只手捏著。”[16]這也許就是弗洛拉的頭蓋骨。弗洛拉失去了卡拉的庇護與精心照料,可能忍受著饑餓以及兇猛的野獸,在野外的生活中,喪失了生命。在弗洛拉在逃離之后的命運中,卡拉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倘若真的逃離之后的命運,于是“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帶走了。她抵抗著那樣做的誘惑。”[17]
(二)“逃離—回歸”的循環模式
逃,首先她們的逃離就是一種逃避,不能正視其所處的困境,因此她們所能實現的逃離也只是短暫的逃離,并不能長久實現自我的幸福與自由。子君如此,卡拉亦是如此。她們如果不能夠解決生活困境:經濟的獨立性的缺乏、對男性的依附性、自我獨立性的消逝等問題,她們的逃離只能陷入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循環:逃離—回歸。
卡拉與子君的逃離是希望擺脫一種現有的困境,尋求幸福與自由,但顯然她們的逃離是讓自己陷入了另一種困境,她們又不得不再次選擇逃離,于是他們的逃離模式有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逃離—回歸—逃離—回歸。兩次逃離的結局都是只能逃,卻不能離,由于切實的生存困境始終得不到解決,因此她們的逃離總是一次又一次的指向回歸。
中西方近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以及思想啟蒙運動,為子君與卡拉的逃離提供了現實土壤與可能性。子君與卡拉所象征的女性是有其心靈上的覺醒意識,也邁出了實踐的步伐:逃離。但是基于逃離之后,她們作為女性的一些生存困境:經濟空間的狹窄、愛情伴侶愛的消退、自我獨立性的缺乏等原因,她們的逃離陷入了一種“逃離—回歸”循環。而要想實現真正的逃離,實現自我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狀況的經濟演變,以及自我獨立性精神的建構。且不僅僅是個體的自我解放,更需要一種集體的解放,去建構一種解放的普遍性。
參考文獻
[1]魯迅.傷逝.魯迅:彷徨[M].上海:中華書局,2013,142.
[2][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32.
[3][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27.
[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57.
[5][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22.
[6][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22.
[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97.
[8][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33.
[9][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32,33.
[10][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98.
[1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04.
[12]魯迅.傷逝.魯迅:彷徨[M].上海:中華書局,2013,154.
[1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84.
[1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301.
[15]魯迅.傷逝.魯迅:彷徨[M].上海:中華書局,2013,159.
[16][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48.
[17][加]艾麗絲·門羅.逃離.李文俊譯.艾麗絲·門羅.逃離[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48.
(作者單位:武警士官學校文化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