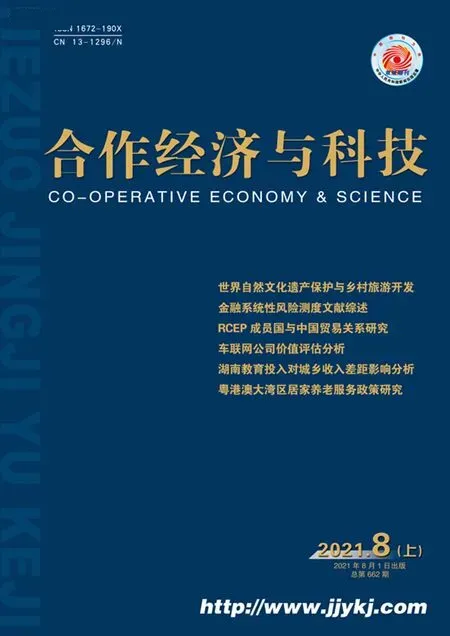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否影響企業創新
□文/焦 陽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
[提要]本文選取2008年至2019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利用Baker et al.(2016)構建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探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是否存在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且產權性質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而融資約束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中起到負向調節作用。
一、引言
國家為了保障社會穩定、實現經濟增長制定了一系列的經濟政策,政策設定和實施本應保持連續性和平穩性,但由于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各國紛紛調整原有經濟政策以減少金融危機對經濟造成的重大損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指政府在經濟運行的不同階段會靈活調整其經濟政策以適應當前經濟增長形勢,而經濟主體通常無法提前預知經濟政策的動向和變化,由此會產生諸多不確定性,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且廣泛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重重考驗,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指出,“中國要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為此我國也出臺了一系列創新扶持和激勵政策,助力我國創新事業遍地開花,碩果累累。企業作為推動創新的主力軍更應不遺余力地為我國自主創新事業添磚加瓦。而企業創新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產權性質、行業導向等,那么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影響企業創新?什么因素又會影響二者之間的關系?基于以上問題,本文進行實證研究。
二、文獻綜述
(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行為。經濟政策的變化必然會影響企業的發展前景和經營策略。結合前人經驗發現,現有研究大多關注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微觀行為的影響,如投資水平、現金持有、企業并購等,且研究結論不相一致。如李鳳羽和楊墨竹(2015年)通過研究發現,企業認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時其投資水平便會降低,且這種現象在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尤為明顯。再如Baum等(2006年)認為企業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壓力下,會選擇持有更高水平的現金從而保持一定的流動性。黃燦、俞勇等(2020年)認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會影響投資者對企業并購前景的判斷,進而抑制企業并購。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企業行為具有激勵作用。如,顧夏銘等(2018年)持有的觀點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促使企業抓緊機遇,加大創新研發力度。再如王義中和宋敏(2014年)研究發現,企業面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會通過外部需求、長期資金需求和流動性資金需求渠道來增加投資。
(二)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從企業內部角度來看,管理層的個人偏好和從業經歷是能夠影響企業創新的一大因素。唐清泉、甄麗明(2009年)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實證表明企業研發投入水平會受到管理層風險偏好的嚴重影響。虞義華、趙奇鋒和鞠曉生(2018年)通過分析董事長和總經理的發明家經歷,發現如果管理層曾經具有發明家經歷,則該企業的創新產出會顯著增長。
從企業外部角度來看,外部市場環境也會影響企業的創新行為。解維敏、方紅星(2011年)認為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則處于該地區的企業的R&D投入水平越高,且這種效應對小規模企業和私有企業更為顯著。黃德春、劉志彪(2006年)和武運波、高志剛(2019年)均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劉柏、王馨竹(2021年)研究發現同群效應對企業創新具有正向激勵作用,有效的競爭環境會促使企業增加創新產出。
三、研究假設和模型設定
(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通常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以及充裕的研發時間,然而不同理論對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后果有不同的結論。實物期權理論以投資不可逆性和不可轉移性為前提,將投資看作是一種期權。隨著時間推移,投資者可用于借鑒和參考的信息越來越多,因而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時,投資者為了降低投資風險,避免投資損失,會暫緩對企業的投資,從而企業可用于研發活動的資金減少,企業創新行為也隨之減少。而增長期權理論的觀點為企業創新不會受到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反而會增加創新活動。在市場競爭中,創新即意味著市場份額的增加,不確定性也代表了機遇,如果延緩投資或者降低投資份額即意味著將投資機會拱手相讓。因此,投資者和企業出于對投資收益和搶占市場份額的考慮,必然會加大創新研發力度。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H1a:其他條件相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正向影響企業創新行為。
H1b:其他條件相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負向影響企業創新行為。
(二)產權性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擔負著實現國家經濟增長、推動產業升級的重大使命。由于其先天的政治屬性,國有企業在面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時,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和稅收優惠。同時,由于其企業規模龐大,違約風險低,且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相較于非國有企業更能受到銀行信貸部門的青睞,從而可以獲得長期的現金流,滿足企業創新活動所需的資金缺口,激發國有企業的創新潛力,增加創新產出。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H2:產權性質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關系中起到調節作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國有企業的創新激勵作用比非國有企業更強。
(三)融資約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資金缺口一直是企業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難題,不同企業的融資渠道和難易程度也各不相同。融資約束越小的企業面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時越容易獲得及時可用的現金流并用于研發創新,相反融資約束大的企業因受到資金限制,缺乏大量現金流支撐創新活動,只能延緩投資,減少創新研發活動,以維持企業內部正常運營。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H3:融資約束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中起到調節作用。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其創新行為的正向影響要比受到融資約束大的企業更強。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2008~2019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并對原始數據做了如下處理:(1)剔除觀測期內被ST、*ST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公司;(3)剔除數據嚴重缺失的公司。最終選用我國A股上市公司1,830家,共21,140個公司的年觀測值進行回歸。同時,本文對部分變量進行雙側1%的縮尾處理以避免異常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Bakereta(l2016)構建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衡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其他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
(二)模型設計。為了檢驗假設H1,本文構造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被解釋變量Innovationi,t為公司i在第t年的創新水平。在回歸中,為了減輕內生性問題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除GDP以外)均滯后一期。EPUi,t-1表示公司i在t-1年所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δind表示行業虛擬變量,用于控制行業固定效應的影響。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為了檢驗假設H2和假設H3,構建回歸模型:

其中,上述模型檢驗假設H2時,Xi,t-1=Soefirmi,t-1,表示企業的產權性質。檢驗假設H3時,Xi,t-1=SAi,t-1,用于衡量企業所受融資約束情況。
(三)變量定義
1、創新變量。本文采用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作為衡量企業創新的指標。
2、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PU。在基本回歸中,本文采取Baker et a(l2016)構建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作為衡量我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代理變量,并將月度指標通過計算算數平均值的方式轉換為年度EPU指標;在穩健性檢驗中,則采用根據內地報紙進行文本檢索和過濾的方式,將關鍵字詞每月出現頻率標準化后,得到我國月度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標,同時也將其通過計算算數平均值的方法將其轉換為年度EPU指標。
3、特征變量。實證過程假設H2和假設H3中共涉及了2個特征變量。在假設H2中,設置虛擬變量Soefirm來反映企業產權性質情況。若企業是國有性質則令Soefirm為1,否則為0。在假設3中,將SA指標用于衡量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即:
SA=-0.737×size+0.043×size2-0.040×age
其中,size為企業規模,age為公司成立年限。
4、控制變量。本文主要選取了如下幾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賬面市值比(BM)和人均GDP增長率(GDP)。
五、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為了能更加充分了解模型中各變量特征,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一覽表
(二)模型選擇和檢驗。本文先進行F檢驗,拒絕了建立混合回歸模型的原假設,隨后進行了LM檢驗,結果顯示應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最后進行豪斯曼檢驗,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0000,拒絕原假設,因而本文回歸模型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
(三)實證結果和分析
1、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表2模型(1)匯報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LEPU的回歸系數為0.0040,且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為正,這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由此,假設H1a成立。(表2)

表2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及調節效應回歸結果一覽表
2、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影響的調節效應分析。表2模型(2)和模型(3)反映了2008~2019年間產權性質和融資約束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調節效應。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LEPU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03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說明假設H1a的正確性。同時,交互項的系數為0.0016,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這表明產權性質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即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能激起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力,從而假設H2成立。
此外,表2模型(3)還報告了融資約束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表明,LEPU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交互項系數為-0.0040,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融資約束減弱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從而假設H3成立。
六、穩健性檢驗
(一)內生性分析。由于模型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引起內生性問題,為了減少內生性問題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滯后一期的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作為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從表3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到,解釋變量依舊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驗證了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表3)

表3 內生性分析結果一覽表
(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的重新度量。為了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部分采取內地報紙構建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作為衡量我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代理變量,并將月度指標通過計算算數平均值的方式轉換為年度EPU指標并加入至回歸方程,表4匯報了回歸結果。從模型(1)可以看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前文結論一致。模型(2)中LEPU的回歸系數為0.0055,交互項系數為0.0018,且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產權性質強化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也與前文結論相一致。模型(3)顯示,LEPU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064,交互項系數為-0.0059,且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融資約束弱化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強,在面臨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其創新活動越消極,與前文結論一致。以上結果均說明了本文實證結果的穩健性。(表4)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一覽表
七、結論及建議
本文將2008~2019年間我國A股上市的1,830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構建固定效應模型,探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影響企業創新行為。實證結果表明:(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會正向激勵企業創新。(二)產權性質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二者之間呈現正向調節作用,即相較于非國有企業而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能激發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動。(三)融資約束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中呈現負向的調節作用,即受到融資約束越小的企業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其創新強度要比受到融資約束大的企業更為顯著。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一)從政府角度出發,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合乎當前的經濟形勢,注重政策對實體經濟運行的影響,避免經濟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和微觀經濟主體的經營活動帶來負面影響。同時,要堅持走自主創新之路,要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突出位置上,堅持國有企業引領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非國有企業在創新項目上的需求,為其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和政策優惠。習近平曾說:“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注重創新人才培養是煥發創新活力的重要基石。我國正處于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需要科技支撐的時代,走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創新之路,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二)從企業角度出發,要理性看待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積極響應國家的創新號召,鼓勵創新,注重創新,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做到與時俱進,結合自身業務特點和經營模式,將創新融入生產。要深度挖掘企業內部創新潛能,引進創新人才,重視員工教育,培養創新思維,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為我國自主創新之路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