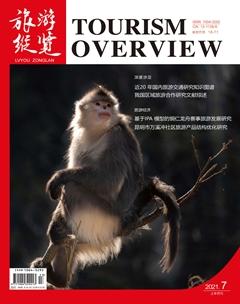不是所有的荔枝都叫妃子笑
穆齋
夏天到來,帶來的不僅僅是炎熱,還有眾多成熟的甜蜜。在夏季水果中,如果說荔枝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怕是實在說不過去。荔枝的美名在我國流傳的年頭著實夠久遠,杜牧一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給這種甜蜜的果子冠一響亮的名頭,也讓“妃子笑”這三個字在很多人印象中,成為荔枝的代稱,但是請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荔枝都叫妃子笑。
由于荔枝這種水果本身的特性和保鮮技術所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北方吃荔枝是一件相當奢侈的事情,哪怕距離楊妃時代已久,北方也很難實現荔枝自由。同時,在北方只要提起荔枝,“妃子笑”三個字就時常伴其左右,不過這可不僅僅是唐詩的意向了,而是荔枝的品種——妃子笑。
記得以前,約莫有十幾個年頭了,我這個北方人在市場、超市買荔枝,就只有妃子笑這個品種,到了近幾年才逐漸出現“白糖罌”“糯米糍”“槐枝”等品種,家中長輩感嘆,原來荔枝還真不只有妃子笑。
妃子笑荔枝雖然在北方常見,但并不代表物以稀為貴就可以忽略它的缺點,妃子笑的果子個頭兒雖大,但是口感略有些酸澀,肉的厚實度尚可,水分卻沒有那么飽滿,據一些廣東的朋友反饋,這個品種在當地并不怎樣受歡迎,充其量是早熟產品,上市早,聊以解饞罷了。同理,白糖罌等品種也是如此,這些荔枝給北方人吃,廣東人倒也有些瞧它們不上。說到這里,廣東人的高傲已盡數體現。
廣東、廣西一帶,有一種在當地人中極受歡迎的荔枝品種,叫做桂味。不同于妃子笑的外觀,桂味長得實打實像一個漲起來的河豚,小小的刺短、尖且密,像“一座座青山緊相連”。桂味的果子小小的,顏色較妃子笑鮮艷,有的也有一些綠色,這并不是沒有成熟,反而味道比純紅外皮的荔枝更好一些。桂味吃起來極甜,甜到無法描述,甜到語言匱乏。水分也極為飽滿,剝殼的時候也不像妃子笑一樣會過多地流失水分。據當地人說,這個品種的荔枝之所以叫做桂味,是因為它吃起來有一種桂花的清香。可惜我在它的甜度面前幾乎無法思考,實在沒顧上品是不是桂花的味道,不過確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清甜。
桂味在廣東、廣西兩省都早有種植,在《嶺南荔枝譜》記載:“桂味產番禺蘿岡洞(今屬廣州市郊)牛首山最盛”。據廣西欽州《靈山縣志》記載,荔枝種植始于唐朝,宋朝已有較大發展。絕對是有歷史的甜蜜。

除了桂味,在荔枝的甜度排行里,“糯米糍”也絕對是名列前茅。糯米糍的外觀較為平整,不像桂味一樣山丘疊起,它的外殼上有一些凸起,或者說隆起,并不像那種尖尖的“刺”。它的果實長得像一顆“心”,果肉厚實,汁水飽滿,口感也更綿軟,確實像是在吃那種糯米皮包裹著奶油餡兒的小吃。最令人稱贊的一點就是它的果核較小。癟癟的核雖然不怎樣圓潤光滑,看上去不怎么美觀,但對于食客來講,這才是優點,畢竟大家也不是為了吃果核或者把玩果核才買的荔枝。
如果說桂味、糯米糍都是甜掉牙的品種,那么妃子笑和白糖罌只能算是中等甜度。而接下來要說的這種荔枝就不是夸贊了,在我看來,它和荔枝標準的甜都快沒什么關系了。這種荔枝就是“槐枝”。槐枝又叫尚書懷,據《增城市志》記載,明朝尚書“湛文簡公昔從楓亭懷核以歸,所謂尚書懷者也。”這里的湛文簡公就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大儒湛若水,他曾先后擔任過禮部尚書和兵部尚書,正是他將福建游仙鳳亭的良種荔枝核帶回家鄉廣東增城沙貝(今新塘鎮),交給鄉人到四望崗上培植。十多年后,四望崗荔枝成林,人們把這種清甜爽口的荔枝叫做“尚書懷”,也就是槐枝。雖然這個品種的荔枝看起來來頭不小,但可惜的是,槐枝吃起來不僅甜度不夠,反而還有些酸澀,吃起來就不像個“正經”荔枝。但是這種荔枝卻憑借著它的一項特點在眾多荔枝中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那就是這種荔枝果木的好脾氣,它實在是太好作為嫁接的砧木了,看在它為廣大荔枝家族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的份上,提起荔枝不提它這個品種,還真是有些說不過去。
荔枝的品種還有很多,好吃的比如掛綠、新球蜜荔,不好吃的比如白蠟、黑葉等,想要詳盡地說清楚他們的特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荔枝的產地自己去品嘗一番,或許是個好主意,去嘗試一下“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豪放,感受一下嶺南人的Privi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