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生活和自我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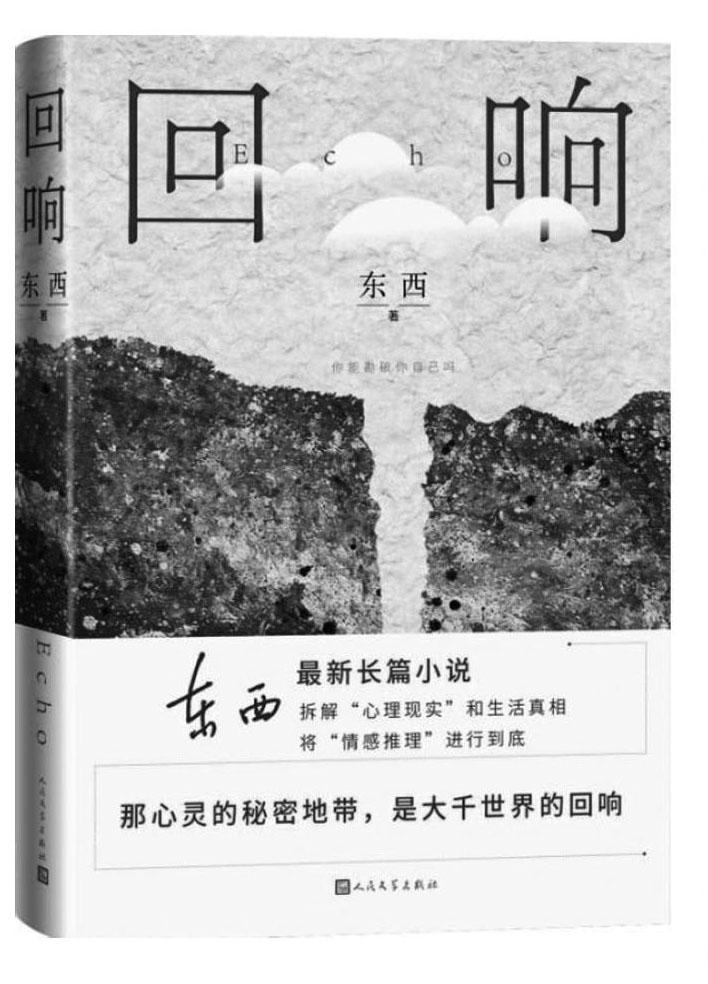
文學(xué)不是關(guān)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及人的詞典和百科全書,它是人的啟示錄。社會(huì)生活和現(xiàn)實(shí)關(guān)乎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關(guān)乎人在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中的遭遇、處境和命運(yùn),對這一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思考和表現(xiàn)的文學(xué),便是人對人的啟示錄。在此意義上,東西的長篇新作《回響》便是“啟示錄”式的寫作。小說描繪了兩種現(xiàn)實(shí)場景、兩個(gè)世界景觀:一個(gè)是社會(huì)生活世界、景觀,一個(gè)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景觀。通過兩個(gè)世界、兩幅景觀,小說形成了一個(gè)有意識建構(gòu)起來的視角,其焦點(diǎn)是“現(xiàn)實(shí)”或“事實(shí)”“真相”。作為一部虛構(gòu)性小說,《回響》在展示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同時(shí),營造了一個(gè)心靈之夢,從而超脫了普通生活狀態(tài),敞開了其沉默部分。這是一部具有強(qiáng)烈的刺痛人心、啟迪心靈、升華靈魂的“真實(shí)性”的小說。
一、現(xiàn)實(shí)、心理與“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
《回響》雖然圍繞案件偵破故事和情感故事展開,卻具有超出破案和情感故事的強(qiáng)勁的文學(xué)力量。故事背后,隱含、回響著一種巨大的回應(yīng),一種對作為整體的人和已有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回應(yīng)。
《回響》有著關(guān)注和表現(xiàn)日常社會(huì)生活的傾向。這一點(diǎn)不僅體現(xiàn)在對“大坑案”的持續(xù)偵破過程以及由此關(guān)聯(lián)的城市和鄉(xiāng)村生活故事、場景的描述,也體現(xiàn)在對人物的社會(huì)生活、家庭生活和情感婚姻生活的描繪。作者將筆觸探入較為廣闊而又細(xì)微的生活,通過細(xì)節(jié)真實(shí)地再現(xiàn)了當(dāng)下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心理觀念和價(jià)值觀念,對老年人、青年人、富人、農(nóng)民、白領(lǐng)、自主創(chuàng)業(yè)者、進(jìn)城打工者、家族產(chǎn)業(yè)繼承人、警察、罪犯等不同行業(yè)、職業(yè)、地位、身份、階層的人群,對社會(huì)物質(zhì)的發(fā)展進(jìn)步、社會(huì)階層的分化和隔膜、貧富懸殊等現(xiàn)實(shí)狀況,進(jìn)行了細(xì)致描摹,展現(xiàn)了一幅既充滿生機(jī)、活力又滿含艱難、窘迫的栩栩如生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和肌理。
在小說所展開的現(xiàn)實(shí)圖景和社會(huì)情境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作家對豐富駁雜的“人”這一生命體的體驗(yàn)和認(rèn)知,小說直面的是“人”,是有著各種性格、脾氣和經(jīng)歷、動(dòng)機(jī)和欲念的具體的生命體。“現(xiàn)實(shí)”隨著“人”的出現(xiàn)和凸顯退隱為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的背景,它不再是一種純粹平面的客觀存在,而是因?yàn)椤叭恕钡碾y以辨清必然還是偶然、理智抑或沖動(dòng)、理性還是感性的主觀意識變得模糊含混、無法捉摸。在“人”的難以捉摸的心理和無意識作用下,“現(xiàn)實(shí)”仿佛變成了憑個(gè)人的主觀意識和意念才能被體驗(yàn)、掌握和理解的存在。小說對冉咚咚和易春陽“被愛強(qiáng)迫癥”的描寫,尤其是對刑偵大隊(duì)副大隊(duì)長破案直覺的反復(fù)提及,對其丈夫慕達(dá)夫是否出軌的執(zhí)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反復(fù)試探、心理分析,包括對慕達(dá)夫與貝貞是否偷情的曖昧敘述,對慕達(dá)夫是否曾對卜之蘭始亂終棄的點(diǎn)到為止的敘述處理,都在有意識地把“現(xiàn)實(shí)”納入“心理”“感覺”中,納入人物(主要是冉咚咚)的主觀意識中,通過人物的體驗(yàn)去推理、猜測和摸索。而與此同時(shí),小說又提供各種其他的“事實(shí)”來延遲“真相”的發(fā)現(xiàn),甚至揭穿所謂的真相不過是夢境、幻覺或自以為是的臆測。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回響》堪稱是一部典型的“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作家筆下的“現(xiàn)實(shí)”包含著突出的心理體驗(yàn)的內(nèi)容。
小說精心描繪日常生活中個(gè)體相對獨(dú)立的心理活動(dòng)和潛意識。小說中的人物,無論是父母和子女、丈夫與妻子、罪犯和警察,還是男女情人,他們都會(huì)從自己的處境、地位、階層和需求出發(fā),小心翼翼、千方百計(jì)地按照個(gè)人的想法、愿望和想象、預(yù)測來設(shè)計(jì)、“塑造”自己所設(shè)想的現(xiàn)實(shí)和世界。這些個(gè)人化的、不愿公開的意識,以及自己也未必清晰把握的潛意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倫理關(guān)系之中的。與此相對的是社會(huì)的而非私人的意識和潛意識。它代表著秩序、穩(wěn)定,卻也處于清晰或不那么清晰的生成與變化中,如以戀愛、婚姻和家庭為主體的倫理道德秩序,以警察和罪犯關(guān)系出現(xiàn)的“法的秩序”。慕達(dá)夫與父母之間,冉咚咚與父母之間,夏冰清與父母之間,吳文超與父母之間,慕達(dá)夫與冉咚咚之間,劉青與卜之蘭之間,徐山川與沈小迎之間,慕達(dá)夫與貝貞、冉咚咚與邵天偉之間,夏冰清與吳文超之間,吳文超與劉青之間,徐山川和夏冰清及其他情人之間,便交錯(cuò)著各種道德倫理關(guān)系。冉咚咚與徐山川、徐海濤、吳文超、劉青等案犯之間,便是“法的秩序”的體現(xiàn)。
《回響》中對各種秩序的描述和設(shè)置,很有深度也很耐人尋味。一方面,小說對處于各種倫理道德秩序中的個(gè)體的疏離與親近、隔膜與溝通、冷漠與溫情、世故與無情等情感關(guān)系有著細(xì)致入微的表現(xiàn)。通過言語、行為與心理、情感之間的對位、錯(cuò)位、糾結(jié)、矛盾關(guān)系,小說深刻揭示了處于道德倫理秩序中的人性、人心的復(fù)雜性,以及日常生活與情感的深層復(fù)雜性;另一方面,小說對“法的秩序”中人心之真實(shí)性的揭示也有振聾發(fā)聵之力量。作家不僅深入發(fā)掘執(zhí)法者冉咚咚的性格、心理矛盾,也通過她的“心理追蹤”進(jìn)入案犯的心理和靈魂深處,描畫案犯的心理軌跡、心靈世界和人性狀態(tài)及其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及其家庭出身、職業(yè)狀況的關(guān)系。這就在“法的秩序”與倫理道德秩序和時(shí)代生活和社會(huì)心理之間,建立了密切關(guān)聯(lián)。于是,奇數(shù)章所寫的“案件”和偶數(shù)章所寫的“感情”,就始終通過心理、情感和關(guān)系、秩序聯(lián)系在一起,相互融滲而非彼此隔離:“法”中有情感、心理;“情”一則通過夫妻關(guān)系、家庭生活建立與“法”的聯(lián)系,二則通過心理和意識的試探、交鋒和剖析、“偵破”,建立了與“法”更深層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圍繞案件偵破線索的“法”敘事固然跌宕起伏,圍繞冉咚咚、慕達(dá)夫情感關(guān)系的“情”敘事雖看似靜止,卻也暗流涌動(dòng)。這使《回響》具有很強(qiáng)的“情節(jié)性”,這一情節(jié)性不僅限于圍繞案件偵破展開的顯性故事,更指圍繞情感、倫理和道德展開的隱性的“心理故事”。通過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故事”,《回響》蘊(yùn)含了兩種(兩組)不盡相同的文學(xué)力量:現(xiàn)實(shí)自身的直接經(jīng)驗(yàn)的力量和對人的熱情探索的力量;作為智性的理解的力量和作為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的力量。
但東西的小說與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這一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樣式又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重要倡導(dǎo)者和實(shí)踐者亨利·詹姆斯雖然強(qiáng)調(diào)小說應(yīng)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再現(xiàn)生活,但他所謂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并非客觀存在,而是作家對現(xiàn)實(shí)的印象和主觀性經(jīng)驗(yàn)。因此,他雖然被稱為“心理分析小說家”,但其“現(xiàn)實(shí)感”卻是具有感知力稟賦的作家捕捉“瞬間”、形成經(jīng)驗(yàn)并出之于意象的“具體陳述的可靠性”。個(gè)人的內(nèi)心感受與知覺是“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所青睞的,而個(gè)人與歷史、社會(huì),主觀愿望與客觀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則被放棄。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強(qiáng)調(diào)的“經(jīng)驗(yàn)”并非現(xiàn)實(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經(jīng)驗(yàn)是巨大的感官,它好像是一張用最美麗的絲線編織成的,延及認(rèn)識領(lǐng)域,本身包括了每一個(gè)存在的細(xì)節(jié)的碩大的網(wǎng)。這是認(rèn)識氛圍本身,而當(dāng)認(rèn)識具有想象力時(shí)——想象力在天才人物身上特別有力地發(fā)展著——認(rèn)識吸收著生活中最細(xì)微的運(yùn)動(dòng),把生活中最小的跳動(dòng)轉(zhuǎn)化為可以顯現(xiàn)的東西。”“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是最好的老師,……現(xiàn)實(shí)的空氣(典型化的真實(shí))是小說的最大優(yōu)點(diǎn),是無條件地、鄭重其事地建立在小說的一切優(yōu)點(diǎn)……之上的優(yōu)點(diǎn)。”當(dāng)小說家“展示出自己反映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的意義、色彩、凹凸、性格——人類存在的全部本質(zhì)的方法時(shí),他才真正地同生活展開競賽”①。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以虛構(gòu)挑戰(zhàn)現(xiàn)實(shí),以個(gè)人主觀經(jīng)驗(yàn)取代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以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建立一個(gè)對抗和超越生活世界的虛構(gòu)世界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dāng)代中國的先鋒寫作。
東西的小說也運(yùn)用幻覺、夢境、變形、荒誕等手法,但他始終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痛苦、苦難和生存的沉重、艱難和乖謬。這體現(xiàn)出其作為新生代小說家對先鋒小說的反思和超越意圖。《回響》情節(jié)展開雖以心理和推理為主,但他同樣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本次寫作的難度是心理推理,即對案犯、主人公以及愛情的心理推理,而這樣的題材又如何與現(xiàn)實(shí)與閱讀者產(chǎn)生共鳴?”并有意識地建構(gòu)一系列“有意思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現(xiàn)實(shí)與回聲、案件與情感、行為與心靈、幻覺與真相、罪與罰、疚與愛等”(《〈回響〉后記》)。小說圍繞刑事犯罪事件展開的偵查、走訪、問詢,密切關(guān)聯(lián)案件的推理、進(jìn)展,在生活畫面的展開和現(xiàn)實(shí)細(xì)節(jié)的捕捉中,體現(xiàn)著一種理性、智性的介入。這方面的敘事可謂社會(huì)心理和社會(huì)行為研究,通過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深層進(jìn)入,體現(xiàn)著一種置身事外卻持續(xù)追蹤和觀察案件進(jìn)展的“抽離性”快感。小說的另一部分,關(guān)乎豐富的情感、家庭、婚姻內(nèi)容,作者對這些關(guān)涉道德倫理向度的情節(jié)的表現(xiàn),是將日常生活和工作關(guān)系,轉(zhuǎn)換為“心理”關(guān)系,從心理層面抵達(dá)生活深處。相對于第一部分內(nèi)容的“抽離感”,它帶來的是充滿情感內(nèi)容的“浸入感”,這是關(guān)于愛情與謀殺、親情與疏離、信任與背叛、愛與恨、哀與痛等充滿張力和激情的、讓人沉醉其中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回響》提供了一種深度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對人的智性和心理、情感分別進(jìn)行了富有深度的發(fā)掘,延伸和擴(kuò)展了我們的人性認(rèn)知和體驗(yàn),豐富了作為整體存在的人的理解。
相對而言,《回響》雖圍繞案件偵破展開敘述,關(guān)聯(lián)城鄉(xiāng)諸多階層和群體人物,描畫變動(dòng)中的生活場景,但其主要目的卻不是要展現(xiàn)一個(gè)客觀世界,表現(xiàn)當(dāng)下中國現(xiàn)實(shí)。小說中的世界不是作為“(典型)環(huán)境”而存在的,不是我們所看到的作為客觀存在的世界。作家更多時(shí)候是通過人物包括案犯們的講述,提供了他們對這個(gè)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因此這個(gè)世界是一個(gè)“人”的世界,人所生存的(實(shí)然)世界和人想要或所欲生存的(或然)世界。由案件偵破所關(guān)聯(lián)和建構(gòu)的是“社會(huì)”“生活”,由情感狀態(tài)、心理活動(dòng)建構(gòu)的是“心靈”“情感”,前者關(guān)乎“公”,后者切近“私”,二者盡管分為并行的奇數(shù)偶數(shù)章,但實(shí)際上卻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相反,公與私、智性與心理共同表達(dá)了一種普遍的經(jīng)驗(yàn),建立了一種“闡釋”(這一點(diǎn)使小說具有明顯的智性色彩,即使對心理、情感的表現(xiàn),也呈現(xiàn)出細(xì)膩的辨析色彩)和表述經(jīng)驗(yàn)的可能的模式。
因此,《回響》具有突出的“智性寫作”特征。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為主要內(nèi)容和敘事線索,以“大坑案”偵破和慕達(dá)夫與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yàn)椤皢栴}”導(dǎo)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說。不同于常見的偵探破案故事和愛情倫理故事,小說有著嚴(yán)肅的“問題”聚焦和人性追問。它還是一部以人類理性和情感、智性與心理為主,以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為輔的小說。它關(guān)注人性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整體性觀照人的心理、情感、理性和社會(huì)性。它是小說、文學(xué)與心理學(xué)和案情推理學(xué)的“合作”。對案件的偵查、推理,對人心的推測、研究,嵌入了小說敘事,構(gòu)成其基本內(nèi)容,影響了敘事節(jié)奏的快慢。小說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著一種環(huán)環(huán)相扣、迂回曲折卻又步步推進(jìn)、深入人心的探究案件和情感真相的思維方式。小說以心理和推理作為基本內(nèi)容和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形式,對人性人心狀況進(jìn)行了較為廣闊、細(xì)致和全面的想象性辨析和考察,揭示了隱藏在日常生活、情感和倫理關(guān)系之中卻被遮掩或無法說出的“真實(shí)”,揭示了那些隱秘的不欲示人的思想和欲念在它自身軌跡上的運(yùn)動(dòng)。
當(dāng)下中國正處于劇烈而復(fù)雜的歷史轉(zhuǎn)型期,“如何在中國社會(huì)和現(xiàn)實(shí)這一復(fù)雜的意義場域中,突破帶自然主義色彩的日常化詩學(xué)和著重‘個(gè)體‘私人‘內(nèi)心的敘事模式,將‘我從流行性寫實(shí)模式中釋放出來,并重新寫進(jìn)‘我們‘現(xiàn)實(shí)以及與之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著的‘世界和‘歷史之中,重構(gòu)一個(gè)‘我/‘我們、‘生活/‘歷史、‘內(nèi)心/‘現(xiàn)實(shí)相互溝通、對話的‘大敘事,是現(xiàn)時(shí)代對文學(xué)提出的迫切命題”②。在敘事方式上,《回響》無疑提供了嶄新的具有啟示性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
二、形式感與“小說精神”
文學(xué)存在于一個(gè)以“人”為中心的世界,它關(guān)心和表達(dá)的現(xiàn)實(shí)是以“人”為中心的現(xiàn)實(shí)。19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個(gè)性意識和純文學(xué)意識的覺醒,文學(xué)往往被看作以個(gè)體為中心的人尋找一種與其“個(gè)性”“獨(dú)特性”相關(guān)的“形式”。對于年輕一代作家尤其是有過先鋒性寫作的作家來說,創(chuàng)作不再是一種社會(huì)學(xué)、政治學(xué)或歷史學(xué)的附庸或隱喻,作品(文本)形式才是文學(xué)的本質(zhì)或本身,歷史、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時(shí)代、意識形態(tài)等必須借助這一形式才能成為文學(xué)的言說。在此情況下,歷史等要么作為非文學(xué)因素被淡化、排除,要么以人性的轉(zhuǎn)喻成就某種陰郁的美學(xué)趣味。“當(dāng)日常性私人性成為文學(xué)/歷史舞臺上的唯一主角時(shí),它們就放棄了對自身內(nèi)在的省思而專注于‘展示自己的形象,文學(xué)話語的歷史性維度、政治意涵和尖銳性以及日常生活的潛在能量,被心安理得地放棄了。”③歷史、意識形態(tài)包括人本身失去了其硬度、厚度和分量,不再是寫作的立足點(diǎn)和目的地,它們被“人性”化和美學(xué)化了。
作為一名曾經(jīng)的新生代作家,東西對此類風(fēng)格的先鋒寫作進(jìn)行了反思,他對“寫什么”和“怎么寫”懷有同樣的興趣和熱情。他既是尖銳現(xiàn)實(shí)和苦難生存的發(fā)現(xiàn)者和表現(xiàn)者,也是新的形式和修辭的探索者和尋找者。為特定的生活和人尋找和構(gòu)造特定的形式,是東西一以貫之的追求。同樣,在東西那里,“人”與“個(gè)人”與特定的群體也不是隔離、對立的,他并無興趣回歸抽象的宏偉話語,同時(shí),個(gè)體意義之人雖構(gòu)成其寫作的基點(diǎn),東西卻又不完全認(rèn)同流行的卻同樣抽象的個(gè)人或私人。因此,東西對“人”的思考及其圍繞“人”的實(shí)踐,便不再是“先鋒小說”之前的社會(huì)性、政治性和歷史性的附庸式寫作,其小說中的“人”具有相對獨(dú)立性,有著屬于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和生活世界,但這一世界并不與外界隔絕,而是生活化、社會(huì)化乃至政治化的。或者說,這也是一個(gè)“歷史”之人,只不過,他不再以投入歷史、歸化歷史為歸宿,相反,他常常被迫承受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擠壓。
《回響》中的人物,或是兒子、女兒如慕達(dá)夫、冉咚咚,或是財(cái)大氣粗的老板如徐山川,或是僅能維持生計(jì)得不到尊重的打工者如易春陽,或是夫妻、戀人如慕達(dá)夫與冉咚咚、貝貞與洪安格、劉青與卜之蘭,或是刑警如冉咚咚、邵天偉。他們既是社會(huì)之人,也是內(nèi)心之人,具有社會(huì)性和心理性雙重因素,且后者才是《回響》側(cè)重發(fā)掘、“實(shí)驗(yàn)”的重點(diǎn)。無論是奇數(shù)章所寫殺人案件偵破,還是偶數(shù)章的情感故事講述,都以人的心理探測、心靈揭示和靈魂展現(xiàn)為主要內(nèi)容,以隱秘的心理動(dòng)機(jī)作為智性分析和邏輯推演的對象。在小說中,東西始終讓他的主人公在破案和情感生活中保持著一種思索、心理探險(xiǎn)和真相揭秘的熱情,為此,小說有意設(shè)置重重懸念,作為情節(jié)推進(jìn)、演變和進(jìn)入人物深層心理和無意識領(lǐng)域的動(dòng)力。被列為第一犯罪嫌疑人的徐山川在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求職面試后他究竟在包間對夏冰清做了什么,他是如何利用于己有利的證據(jù)實(shí)施犯罪行為,夏冰清留存的錄音是不是她被徐山川強(qiáng)奸的證據(jù),慕達(dá)夫與貝貞、與卜之蘭是否有過婚外情,等等。這些充滿懸疑的故事,不僅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也在逐步接近真相的過程中解開了人性和心理謎團(tuán),既有吸引讀者的魅力,也有力推動(dòng)和啟示讀者進(jìn)行思考。
東西是一位有著強(qiáng)烈“形式感”的作家,他對“怎么寫”的追求不亞于“寫什么”。他的小說既有對現(xiàn)實(shí)生活題材、內(nèi)容的選擇、掘進(jìn),又以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的富有新意的發(fā)現(xiàn)和表現(xiàn),吸引讀者并讓讀者在故事的編織、講述中進(jìn)入嚴(yán)肅的審視——對現(xiàn)實(shí)、他人和自我的反思。《回響》致力于尋找與發(fā)現(xiàn),揭示表象與真相、他人與自我、現(xiàn)實(shí)與人心之間曲徑通幽的奧秘,精神分析的意味極為突出。可以說,這是一部體現(xiàn)了米蘭·昆德拉所提倡“小說精神”的小說。米蘭·昆德拉認(rèn)為,“小說的存在理由是照亮‘生活世界,保護(hù)我們不至于墜入‘對存在的遺忘”④。為此,他提倡一種“小說的精神”,以抵抗大眾傳媒時(shí)代制造的“共同的精神”,抵抗那種被簡化、被一體化乃至被吞噬和被遺忘的生活、世界和存在之意義。昆德拉將小說的精神概括為“復(fù)雜性”和“延續(xù)性”。“每部小說都在告訴讀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復(fù)雜這是小說永恒的真理”,他用塞萬提斯說明小說的復(fù)雜性精神是“有關(guān)認(rèn)知的困難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⑤。《回響》是一部簡潔的卻并非“簡化”生活和世界的長篇。小說主要講述兩個(gè)事件——?dú)⑷思疤桨福星榧m纏和離婚,卻沒有將事件簡化為媒體新聞或街談巷議——如此作法便是背離了小說精神的不幸:文學(xué)成為作者、讀者和大眾傳媒共同制造和參與的、瞬間就會(huì)被棄之如敝屣的“桃色話題”的狂歡。東西沒有將“事件”事件化,而是以全部心智將其小說化、文學(xué)化,使其成為一個(gè)深長的思考性探尋而不是那種被窺視欲控制下生產(chǎn)出來的簡化的俗套——一種敘事精致、經(jīng)過精心包裝的陳詞濫調(diào)。
《回響》以貼近、切入人物內(nèi)心的方式描述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那些具有“認(rèn)知的困難性”的人與事,而且通篇運(yùn)用心理和推理手法去接近這些人和事,對其做出認(rèn)知和評判。在此過程中,小說恰恰體現(xiàn)了真理(真相)的難以把握性。東西意識到避免簡化和事件化的必要性,并以內(nèi)心化、心理化作為敘事對策,應(yīng)該說,這一策略是有效的,他將我們帶進(jìn)了一個(gè)情感、思考和思維的世界,發(fā)現(xiàn)了被商業(yè)化、市場化掩蓋的另一種生活態(tài)度和生命形式。夏冰清對父母安置自己生活的做法所選擇的順從與反抗,以及她對愛情、物質(zhì)、金錢的追求讓她始終陷入困擾之中無法自拔,并最終釀成悲劇,卻也不無合情合理之處。她離開父母和家庭,離群索居,孤單寂寞,卻又能在離世之前以特殊的方式“玩幽默”“調(diào)侃死亡”,表現(xiàn)出意想不到的勇敢和樂觀。夏冰清父母自得知女兒死訊開始,直至得知女兒之死的真相,其間的失望、悲傷、酸楚、悲涼、傷感和無奈、自責(zé),也得到過程性、復(fù)雜性的細(xì)膩揭示。小說對冉咚咚時(shí)時(shí)陷入案件與感情相互糾纏難以擺脫的心理困惑和生活困境的深入探究,更是通過齊頭并進(jìn)的兩條線索得到了完整而飽滿的呈現(xiàn)。她在拷問別人,同時(shí)也在拷問自己。她在認(rèn)識別人,同時(shí)也在重新認(rèn)識自己。在此,生活的意義、世界的意義被具體化、個(gè)體化和內(nèi)在化,而《回響》作為一部小說的意義,也通過這一系列復(fù)雜性的設(shè)置,體現(xiàn)出了其所在的世界的復(fù)雜性,世界的復(fù)雜性導(dǎo)致“認(rèn)知的困難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冉咚咚是破案高手,精通犯罪心理學(xué),最終她憑借出色的直覺、推理能力和心理學(xué)知識,偵破了徐山川殺人案,但當(dāng)她將心理學(xué)知識和直覺、推理能力運(yùn)用到夫妻、婚姻和家庭領(lǐng)域中,從蛛絲馬跡入手,從偽裝層到真實(shí)層再到傷痛層,深挖丈夫慕達(dá)夫的心理,使其幾近崩潰,最終婚姻、家庭破裂。這個(gè)自信而敏感多疑的女性主人公何嘗真正勘破了身邊的愛人,又何嘗真正勘破了她自己?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文學(xué)教授慕達(dá)夫的認(rèn)識倒有旁觀者清的意味:“別以為你破了幾個(gè)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歸類概括總結(jié)人類的所有感情,這可能嗎?你接觸到的犯人只不過是有限的幾個(gè)心理病態(tài)標(biāo)本,他們怎么能代表全人類?感情遠(yuǎn)比案件復(fù)雜,就像心靈遠(yuǎn)比天空寬廣。”東西以執(zhí)拗的方式在《回響》寫出了人性、世界的復(fù)雜與幽微,這也成就了小說言說這個(gè)世界的文學(xué)復(fù)雜性。
昆德拉從小說與“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出發(fā)談?wù)撔≌f精神的“延續(xù)性”:“每部作品都是對它之前作品的回應(yīng),每部作品都包含著小說以往的一切經(jīng)驗(yàn)。”他哀嘆“時(shí)下的事情”占據(jù)了太多的空間,“將過去擠出了我們的視線,將時(shí)間簡化為僅僅是現(xiàn)時(shí)的那一秒鐘。”在他看來,如果被納入這種“時(shí)代精神”體系中,“小說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種注定要持續(xù)、要將過去與未來相連的東西),而是現(xiàn)時(shí)的事件,跟別的事件一樣,是一個(gè)沒有明天的手勢”⑥。小說不僅要在小說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中確立和確認(rèn)自己,它更要超出某種狹隘的單質(zhì)的“時(shí)代精神”對自身的簡化。小說要避免成為“現(xiàn)時(shí)的事件”描述,而成為人類歷史和變化的世界的一部分或一個(gè)環(huán)節(jié)。一方面,小說具有歷史性的特點(diǎn),正如它所在的世界、現(xiàn)實(shí)是歷史性的。另一方面,昆德拉又認(rèn)為:“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說出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⑦他反對大眾化小說對“非小說的知識”的表現(xiàn)。那么,何謂“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在小說的歷史性與“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理解二者的關(guān)系?顯然,昆德拉在此強(qiáng)調(diào)的其實(shí)并非只要“小說性”(“文學(xué)性”),否則小說會(huì)失去它與社會(huì)歷史的聯(lián)系。他強(qiáng)調(diào)的關(guān)鍵在于如何言說社會(huì)歷史和現(xiàn)實(shí),而不是不要言說社會(huì)歷史和現(xiàn)實(shí)。東西的《回響》某種意義上也是昆德拉之“小說精神”的回應(yīng),他的自述專門談到了這部小說“怎么寫”的問題:“奇數(shù)章專寫案件,偶數(shù)章專寫感情。”其實(shí),不論寫案件還是寫感情,兩個(gè)方面、兩條線索的敘事,都描述了這一時(shí)代的中國城市鄉(xiāng)村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都有著作家堅(jiān)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和體驗(yàn)的有力支撐。但《回響》不是以表現(xiàn)當(dāng)今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為目的的小說,東西并非要以小說的形式記錄現(xiàn)實(shí)生活場景、描繪生活畫面。相對于對人物人性和心靈、情感的表現(xiàn),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在小說中更多是作為背景或促成人物做出選擇和實(shí)施某種行為的心理動(dòng)因。從主要人物慕達(dá)夫、冉咚咚、夏冰清到案犯吳文超、劉青、易春陽乃至沈小迎、卜之蘭,小說分別為他們營造了能顯示出其存在的處境和心理活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背景和社會(huì)文化空間。因此,與其說《回響》表現(xiàn)的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不如說是人的現(xiàn)實(shí),更深入地說,則是促成人的言語、行為和選擇的心理現(xiàn)實(shí)和情感現(xiàn)實(shí)。相對于可見的經(jīng)驗(yàn)性生活來說,《回響》著重表現(xiàn)的這種現(xiàn)實(shí)是深層的、隱秘的甚至是被刻意隱瞞或有意無意忽略的,作家細(xì)心而又迅速地進(jìn)入人物內(nèi)心,并寫出現(xiàn)實(shí)和時(shí)代的“秘密”——由特定歷史情境下個(gè)體的人共同折射出的某種集體意識或無意識。
三、“發(fā)現(xiàn)秘密”的可能性寫作
《回響》是探索和發(fā)現(xiàn)“秘密”的小說,是作家借助心理和推理進(jìn)入生活、人和自我的隱秘部分的小說。進(jìn)一步看,這是一部思考“可能性”的小說。謀殺案最終偵破,涉案人被繩之以法,天道輪回,惡有惡報(bào),真相大白,正義得償。但這只是就作為事件的案件來說,而關(guān)于人性和心靈,關(guān)于自我和他者,尚有太多難以勘測和言明的秘密。故事結(jié)束了,生活還在繼續(xù),秘密仍舊是秘密。小說描述冉咚咚通過否認(rèn)、壓抑、合理化、置換、投射、反向形成、過度補(bǔ)償、抵消、認(rèn)同、升華等方法,啟動(dòng)自我防御機(jī)制,以避免打開和進(jìn)入自己的真實(shí)心理層。當(dāng)她主動(dòng)敞開心扉,卸載部分自我防御時(shí),她感受到自己“心理向好的預(yù)兆”,恢復(fù)了見自己離婚后一直怕見的前夫慕達(dá)夫的勇氣。自信的回歸,是直面自我、發(fā)現(xiàn)那份自己一直未能意識到的歉疚的結(jié)果,但人心的隱秘與浩大,又豈是個(gè)人心智所能窺破的呢?面對慕達(dá)夫“你能勘破你自己嗎?”的提問,“她想這才是問題的癥結(jié)”。能否“認(rèn)識你自己”是關(guān)鍵,卻也是天問式的未解之謎。
小說采用了開放式結(jié)尾。冉咚咚的感情歸宿如何,是與慕達(dá)夫破鏡重圓還是在自己“準(zhǔn)備好”以后與等待著的邵天偉走在一起?未能通過邵天偉檢測的她,是否能勘破遠(yuǎn)比案件復(fù)雜的人類情感和心靈?與卜之蘭大學(xué)期間發(fā)生婚外情感的文學(xué)教授是否是慕達(dá)夫?這個(gè)卜之蘭無意間提到的往事,真相如何,是否會(huì)切入冉咚咚記憶成為一個(gè)隨時(shí)可能爆發(fā)的“炸彈”……小說多處預(yù)留了開闊的想象空間,這是生活的現(xiàn)象學(xué)描寫,也是存在之可能性的敘事征候。
開放式結(jié)尾是小說思考存在之可能性的表意形式,也是東西一直以來探尋可能性的詩學(xué)思想的延續(xù)。《沒有語言的生活》以兩個(gè)版本的開放式結(jié)尾,直接表明了這種可能性;《篡改的命》思考“底層”改變自己命運(yùn)的可能性。《回響》在延續(xù)東西對生活、人性和文學(xué)可能性之探尋的同時(shí),也具有了新的敘事質(zhì)素。東西此前的“可能性”寫作,常常描述嚴(yán)酷殘忍的現(xiàn)實(shí)對生命的擠壓和榨取,故事往往荒誕不經(jīng)卻有著讓人觸目驚心的真實(shí)感,人物被無法擺脫的悲劇性宿命糾纏,敘述具有強(qiáng)烈的無奈感、絕望感和荒誕感、虛無感。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現(xiàn)代主義敘事經(jīng)營了太多人的危機(jī),將人置于萬難拯救的殘酷境地,以此探測人的邊界和極限。”⑧在彼時(shí)的東西看來,這一切正是生活本身造成的,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以強(qiáng)硬的姿態(tài)主導(dǎo)著作家的想象。現(xiàn)實(shí)的極致性催生了極致性的想象。荒誕意味、戲擬手法、反諷筆調(diào),顯示了作家在面對如此現(xiàn)實(shí)時(shí)的絕望反抗,是作家直面生活和超脫現(xiàn)實(shí)的勇氣和智慧的表現(xiàn),但這種極致性寫作是否也暗示了作家所對抗的現(xiàn)實(shí)及其邏輯也在限制著自己思想、精神和藝術(shù)上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他在某個(gè)方向上寫到了某種可能性的極致或某種極致的可能性,使作品具有了問題表現(xiàn)的尖銳性,卻也同時(shí)喪失了更多的可能性,失去了生活和人性的寬廣度?作家是否有效抵達(dá)了他所要表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與人性的深處,是否真正抵達(dá)了人物自身的內(nèi)在性?——這里的人物內(nèi)在性不僅指人物被某種強(qiáng)烈、執(zhí)拗乃至偏執(zhí)的愿望或欲望控制的心理感覺,也指他們所在的生活環(huán)境、他們的現(xiàn)實(shí)生存以及支撐著他們生活的價(jià)值系統(tǒng)和意義體系?對于這些問題,東西有著不同于此前的思考并在《回響》中有意識地進(jìn)行了形象化的回應(yīng)。
小說深刻描述了轉(zhuǎn)型期中國社會(huì)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和消費(fèi)文化興起導(dǎo)致的整個(gè)社會(huì)情緒氛圍的變化,尤其是人與人關(guān)系所發(fā)生的微妙卻巨大的變動(dòng)。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guān)系,人們能夠共享和分享的情感也在緩慢無聲地發(fā)生著嬗變。在親情上,父母和子女之間隨著年輕一代個(gè)人自由意識的覺醒和更多個(gè)人權(quán)利的獲得,漸生隔膜、嫌隙和矛盾,如冉咚咚、慕達(dá)夫、夏冰清、易春陽、吳文超、劉青等幾乎所有的年輕一代與他們各自的父母之間,都產(chǎn)生了生活方式、生活觀念和價(jià)值觀念上的變化。在愛情這個(gè)更具私人性質(zhì)的領(lǐng)域,曾經(jīng)讓人一往情深、天長地久、甜蜜得讓人心醉又傷感得讓人心碎的浪漫美好的愛情,出現(xiàn)了明顯的現(xiàn)實(shí)化、功利化和工具化趨勢,“天長地久”未必是愛情追求的目標(biāo),“曾經(jīng)擁有”成為眾多人的“信念”或選擇。男女之間或因?yàn)榻?jīng)濟(jì)原因或地位差異而拋棄對方或被拋棄,如劉青與卜之蘭;或喪失了彼此信任、良好溝通的能力,如冉咚咚與慕達(dá)夫雖然彼此仍然相愛,但前者的敏感多疑和后者的言聽計(jì)從,卻導(dǎo)致了婚姻和家庭的破裂;或因家庭貧困、自卑心理等原因無法獲得異性青睞而陷入空幻的單相思,如患上“被愛妄想癥”的易春陽。隨著性禁忌在社會(huì)意識中的淡化和消失,男男女女或以“愛”之名行“性”之實(shí)或純粹為了“性”走在一起,如徐山川周旋于眾多情人之間,洪安格自己暗度陳倉,卻以莫須有的婚外情與貝貞離婚,與婚內(nèi)出軌對象另立家庭。夏冰清與徐山川之間則糾纏著性的暴力、商品化的交易和情感歸宿的追求等多方面復(fù)雜因素。沈小迎與徐山川本已無愛,卻默契地維持婚姻幸福家庭和諧的假象,各取所需。友情方面,劉青利用吳文超的信任,背叛友情,騙取巨款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桃源夢。在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下,理性的計(jì)算和謀劃介入感情并使之淪為商品化的存在,而利益追逐過程中的不公平不公正、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huì)分層結(jié)構(gòu)的固化,既催化了人的被傷害感、被剝奪感、挫敗感和無能無力感,也發(fā)酵了羨慕、郁悶、嫉妒、憤懣和怨恨等社會(huì)性情緒氛圍。這些經(jīng)驗(yàn)感受和情緒氛圍在東西的長篇《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等描寫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的小說中均有投射和反應(yīng)。生活的苦難、精神的磨難,冷酷的生存本相,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冷漠乃至仇恨,生活的無望和絕望等以荒誕、反諷、黑色幽默等形式表現(xiàn)出來,充滿一種敞開思考和意義空間的詩學(xué)張力。
如果說東西此前的諸部小說可稱為“絕望和反抗絕望”的實(shí)踐的話,那么,《回響》則在絕望或反抗絕望之外,點(diǎn)亮了希望,在令人失望的土壤里種下了希望的種子,讓讀者在看到愛的能力衰竭的現(xiàn)實(shí)時(shí),也感受到愛的能力緩慢恢復(fù)、生長和純粹化的可能。小說不再以戲擬、調(diào)侃、反諷、黑色幽默、荒誕等手法來言說絕望、傳達(dá)“反抗絕望”的生命意志,而是在暗黑中透出了光亮,在絕望中孕育出了希望,灰暗的調(diào)子里也流淌著溫暖的汁液。雖然小說人物的內(nèi)心在復(fù)雜的心理追索中呈現(xiàn)出復(fù)雜性和矛盾性,但這些人物都是可靠的、能立得住的,小說在案件偵破和情感追蹤過程中的理性推理,以及對更廣闊生活和人性世界的包容,在揭示人物行動(dòng)的內(nèi)在依據(jù)和人的內(nèi)在真實(shí)的同時(shí),也給他們提供了更為自然和舒展的意義體系和價(jià)值體系。人性善惡的復(fù)雜性與變動(dòng)性,不能只由罪犯來證明,即便是罪犯也并不都如徐山川一般。在帶著投案自首的劉青離開埃里的路上,“冉咚咚想劉青的罪感既是卜之蘭逼出來的,也是村民們逼出來的。由于村莊的生活高度透明,每個(gè)人的為人都被他人監(jiān)督和評價(jià),于是傳統(tǒng)倫理才得以保留并執(zhí)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凈化,埃里村也在凈化這里的每一個(gè)人”。小說結(jié)尾,一向自信正確的冉咚咚也產(chǎn)生了對慕達(dá)夫的愧疚,“她沒想到由內(nèi)疚產(chǎn)生的‘疚愛會(huì)這么強(qiáng)大,就像吳文超的父母因內(nèi)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蘭因內(nèi)疚而重新聯(lián)系劉青,劉青因內(nèi)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陽因內(nèi)疚而想要給夏冰清的父母磕頭。”這種“愛”是對絕望的超越而不是直接的對抗和反抗,東西在小說中沒有激烈地理解人性,他借助弗洛伊德、榮格等現(xiàn)代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知識觸摸和解析了人性,又用現(xiàn)代人文主義信念化解了人本主義非理性的偏執(zhí)——后者既有對無意識、潛意識和本我的洞見,也造成了對人文主義、現(xiàn)實(shí)生活和人的在世生活狀態(tài)的遮蔽。《回響》的最大啟示和意義,或許就在于,它揭示了在充滿“現(xiàn)代性”風(fēng)險(xiǎn)的陌生社會(huì)中,重建信任的可能性,在“愛”之流逝和“愛”之能力退化的現(xiàn)實(shí)縫隙中,在情感的漂移和傳統(tǒng)道德的廢墟上,重建友愛、互愛的可能性。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回響》也無疑是作家東西在世界觀和文學(xué)觀上的一次自我重建與自我革命。■
【注釋】
①[英]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shù)和社會(huì)的中心》,劉保瑞譯,載崔道怡、朱偉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工人出版社,1987,第11、12-13頁。
②王金勝:《現(xiàn)實(shí)主義總體性重建與文化中國想象——論陳彥〈主角〉兼及〈白鹿原〉》,《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2019年第4期。
③王金勝:《“總體性”困境與宏大敘事的可能》,《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2020年第6期。
④⑤⑥⑦[捷克]昆德拉:《小說的藝術(shù)》,董強(qiáng)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第23、24、24-25、46頁。
⑧陳培浩:《敘事裝置、靈的啟示和善的共同體》,《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2020年第6期。
(吳義勤,南京大學(xué)中國新文學(xué)研究中心、中國作家協(xié)會(hu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