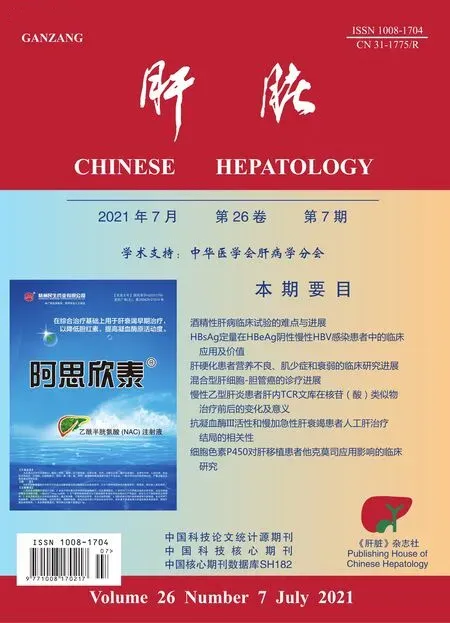HBsAg定量在HBeAg陰性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臨床應用及價值
王捷驍 干沁怡 謝青
HBV感染在世界范圍內分布廣泛,全球約有2.92億慢性感染者,其中西太平洋和非洲占近68%。每年約有88萬人死于慢性HBV相關性疾病,其中死于肝硬化和肝癌的患者接近九成[1]。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多種抗病毒藥物的出現大大改善了慢性HBV感染的結局,但很少有患者能實現持續的HBsAg消失,即功能性治愈。HBeAg陰性的慢性HBV感染作為HBsAg消失的前一階段自然成為了研究的熱點,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qHBsAg)的臨床應用也逐漸成為焦點。HBeAg陰性階段HBsAg動力學的研究進展使人們對qHBsAg的應用有了新的認識,而其比HBV DNA更低廉的檢測費用也有利于臨床進一步推廣。本文對近年來qHBsAg在HBeAg陰性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臨床應用進行了總結,旨在為精準診療提供參考。
一、慢性HBV感染的自然進程
慢性HBV感染的自然史根據自然病程一般可劃分為4期,即免疫耐受期(慢性HBV攜帶狀態)、免疫清除期(HBeAg陽性CHB)、免疫控制期(非活動HBsAg攜帶狀態)和再活動期(HBeAg陰性CHB)。成人感染HBV通常無免疫耐受期,直接進入免疫清除期。免疫耐受期患者的典型特征是年齡較輕、癥狀較少、HBeAg陽性及高HBV DNA水平,但ALT和肝組織學卻是正常的。20歲之后,>90%的慢性HBV感染患者逐漸進入免疫清除期,其特點為持續或間歇性ALT升高、有活動性肝臟炎癥改變和肝炎發作(短時內的ALT>5 ULN),以及HBeAg陽性伴HBV DNA水平的下降。ALT水平升高被視為免疫介導殺傷HBV感染的肝細胞的結果,而更高的ALT水平通常反映出更強的宿主免疫應答。這些免疫介導在時間的積累下可能最終導致HBeAg血清學轉換,即HBeAg消失和抗-HBe出現。HBeAg血清學轉換是一個慢性的過程,>95%的患者會進入非活動HBeAg陰性的持續緩解期;期間HBsAg的清除率一般為每年2%。而持續處于免疫清除期,則可能會導致疾病進展,惡化為肝硬化或肝癌[2]。
二、HBeAg陰性階段中HBsAg的動力學改變
(一)免疫控制期 血清HBsAg陽性>6個月,HBeAg陰性且ALT持續正常,HBV DNA<2 000 IU/mL被定義為免疫控制期,即非活動HBsAg攜帶狀態。2010年起,qHBsAg<1 000 IU/mL被當作一個閾值來協助判斷非活動攜帶者中未激活或低風險再激活的患者[19]。然而,關于qHBsAg對于HBsAg攜帶者判定的閾值的爭論一直存在。在一個為期5年的隨訪中,87例非活動性攜帶者中96.6%的患者維持在免疫控制期,其中19例(21.8%)患者實現HBsAg清除。在感染HBV基因型B或C的HBeAg陰性的患者中,上述標準對于識別非活動性攜帶者的陽性預測值(PPV)為83%,陰性預測值(NPV)為74%。非活動性攜帶者有1.1%/年的復發率,那些HBV DNA<2 000 IU/mL但qHBsAg>1 000 IU/mL的患者存在1.5倍的肝炎再激活的風險(血清HBV DNA>2 000 IU/mL,ALT>ULN)、2.3倍乙型肝炎暴發的風險(血清HBV DNA>2 000 IU/mL,ALT>5倍ULN),以及之后發展為肝硬化和肝癌的可能[3]。一個涉及189例HBV DNA<2 000 IU/mL且ALT正常的來自歐洲、亞洲、澳洲的8個中心患者的研究顯示,對于不同基因型有不同的PPV和NPV。這項研究同時顯示,qHBsAg<100 IU/mL比100~1 000能更好地識別非活動性感染者誰有更高的5年或10年HBsAg清除率[4]。然而qHBsAg<100 IU/mL在臨床實踐中很少見,因此診斷價值有限,qHBsAg<1 000 IU/mL可能還是一個更合適的閾值。
持續血清HBsAg消失被認為是慢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此時感染已經被消除,但仍存在少量的cccDNA。在一個為期5年對87個非活動性HBsAg攜帶者的隨訪研究中發現,年齡>40歲、qHBsAg基線低水平和逐年明顯下降的qHBsAg水平是與HBsAg清除相關的獨立因素,而血清中抗-HBc和HBcrAg含量則不是相關的獨立因素[3]。關于非活動性攜帶者的研究表明,持續穩定小幅度的qHBsAg下降,且qHBsAg<100 IU/mL可以預測未來6~10年HBsAg的血清清除。一項研究顯示,qHBsAg<100 IU/mL的非活動性攜帶者中HBsAg清除率一年后是44%,三年后是67%,而qHBsAg<10 IU/mL的非活動性攜帶者中HBsAg清除率1年后是67%,3年后是56%。在所有非活動性HBsAg攜帶者中,qHBsAg<200 IU/mL與1、3年后qHBsAg清除相關的NPV是100%和92%,PPV是36%和49%。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患者在前兩年內HBsAg下降>1 log10IU/mL,PPV將提高接近100%[5]。一項研究顯示,qHBsAg<200 IU/mL且下一年qHBsAg下降>0.5 log10IU/mL,預測3年的HBsAg清除的PPV為67%。這些研究結果提示,qHBsAg水平越低HBsAg清除率越高,而qHBsAg<200 IU/mL為HBsAg開始清除的預測值,同時HBsAg的急劇下降是加速HBsAg清除的前提條件。這些發現可用于預測1~3年內HBsAg的清除,并且比在臨床中采用qHBsAg<100 IU/mL來預測未來6~10年中HBsAg清除更有效[6]。
(二)再活動期 與免疫控制期不同,HBV DNA>20 000 IU/mL,ALT持續或反復升高的HBeAg陰性患者,定義為再活動期。與良性的、免疫控制期患者相比,那些再活動期HBV感染者每年有3%~5%的疾病進展風險,包括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17]。與免疫清除期HBeAg陽性的CHB患者相似,HBeAg陰性的CHB患者也會因為免疫介導的肝細胞溶解,而表現出持續性或間歇性ALT升高與發作性乙型肝炎暴發。乙型肝炎暴發后HBV DNA水平會發生變化,伴隨自發緩解或持續的ALT升高,而一些患者可能甚至惡化為肝臟失代償甚至肝衰竭。因此,監測血清ALT、膽紅素和甲胎蛋白水平對于ALT水平升高或ALT>5倍ULN的患者來說非常重要,建議每周或至少每兩周進行檢測,及時發現并治療肝功能失代償[7]。研究發現在乙型肝炎暴發的過程中,不論患者HBeAg是陰性還是陽性,血清HBV DNA和qHBsAg水平通常在血清ALT達到頂峰之前激增。同時,由于被感染肝細胞死亡以及未被感染細胞的稀釋,cccDNA水平會有所降低。在一些有效的乙型肝炎免疫清除的患者中,qHBsAg水平可在ALT上升的時候下降,并隨著ALT之后的緩解,qHBsAg繼續下降。相反,在一些免疫清除不足或失敗的患者,當ALT水平降低時,qHBsAg和HBV DNA水平仍會繼續增長或者維持較高的狀態,之后便是持續的ALT上升,以及肝炎暴發或更嚴重的后果[6]。
三、HBsAg在HBeAg陰性的CHB患者抗病毒治療中的動力學和療效預測
臨床上常用的抗病毒藥物有聚乙二醇干擾素(PEG-IFN)和諸如恩替卡韋(ETV)、替諾福韋酯(TDF)和富馬酸丙酚替諾福韋(TAF)等核苷類似物(NUC)[2]。持續的NUC抗病毒治療對大多數患者均有獲益,>95%的患者可實現HBV DNA低于檢測下限。而PEG-IFN則具有廣泛抗病毒以及免疫調節的特性,其可以影響病毒cccDNA,或直接抑制HBV的復制。一項對HBeAg陰性患者為期48周的單用PEG-IFN治療的研究顯示,23%患者能達到持續的臨床緩解,且5年HBsAg清除率為12%。而PEG-IFN和NUC抗病毒原理的不同,也造成了抗病毒過程中的HBsAg動力學的差異[8]。
(一)PEG-IFN治療中HBsAg的動力學和療效預測 一項對HBeAg陰性的CHB患者為期48周單藥PEG-IFN治療的研究顯示,qHBsAg下降0.71 log10IU/mL,其中21.7%的患者下降>1 log10IU/mL,11.6%的患者在治療結束后qHBsAg<10 IU/mL,后續的調查發現達到這些條件的患者與沒有達到這些條件的患者相比,3年HBsAg清除率明顯提高(30%比2.6%; 52%比2.3%,P<0.000 1)。延長PEG-IFN療程從48周至96周可以使HBsAg清除率從0%增加到5.8%(P=0.24),qHBsAg<10 IU/mL從0%增加到9.6%(P=0.06)[9]。進一步研究顯示,qHBsAg在第12周時下降≥0.5 log10IU/mL 以及在第24周時下降≥1 log10IU/mL,對PEG-IFN治療結束后24周保持持續病毒學應答有很好的預測價值。這些數據可以為早期的停藥時機提供參考,而對于HBsAg清除的預測則可以對結局有所預估并指導患者調整抗病毒治療方案[10]。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項對465例HBeAg陰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研究中,對血清HBV DNA及HBsAg定量進行檢測,同時與患者的HBV基因型和突變的位點情況進行比較,發現血清qHBsAg含量與患者的基因型或突變位點有關[11]。因此在使用qHBsAg作為標志物時,除了關注自然病程進展的影響外,仍應考慮其基因型及突變造成的影響。
(二)NUC治療中HBsAg的動力學和療效預測 真實世界的研究發現,ETV、TDF和TAF治療HBeAg陰性的CHB患者,有>95%的患者HBV DNA無法檢測到,但qHBsAg下降緩慢,約每年下降0.08~0.098 log10IU/mL,且僅有不到10%患者能達到1年下降>0.5 log10IU/mL。而第1年NUC治療后HBsAg沒有明顯下降的患者,接下來的治療只有很少的機會實現HBsAg清除[12]。值得注意的是,患者治療前ALT水平越高,qHBsAg下降越明顯。而某些患者的ALT水平在治療期間升高,但HBsAg水平有所下降,這也可以反映NUC對HBV抑制之后免疫恢復的情況。同時,HBsAg下降的速度對預后有很強的預測能力,一項納入334例患者的研究顯示,在第1年ETV治療后HBsAg下降>75%(0.6 log10IU/mL)對5年治療后qHBsAg<100 IU/mL和HBsAg清除有很好的預測效果(HR為 5.8和8.2)。然而HBsAg清除在NUC治療期間很難實現,有調查顯示,5 409例患者在接受ETV治療的6年中,每年僅有0.33%的患者實現HBsAg清除。統計數據發現,在治療第6~12個月內HBsAg迅速下降、治療前qHBsAg低水平(<730~1000 IU/mL)以及較快的HBsAg清除速率(每年>0.166 log10IU/mL)均對之后的HBsAg清除有預測作用[13]。
(三)PEG-IFN和NUC聯合治療中HBsAg的動力學和療效預測 目前,為了提高療效,各國開展了多種PEG-IFN和NUC組合的臨床試驗。早期的一些聯合治療試驗,包括PEG-IFN和拉米夫定聯合治療,效果并不比IFN單用好[18]。在一項2016的隨機對照試驗中,第48周時PEG-IFN聯合TDF治療患者的HBsAg清除率(7.8%)高于那些單用TDF(0%)或PEG-IFN(1.3%)者,第120周時聯合治療組HBsAg清除率增加到10.4%(TDF:0%;PEG-IFN:3.5%)。同時,第72周收集到的數據顯示,若第24周時qHBsAg較基線減少>3.5 log10IU/mL,則高度預測HBsAg清除的PPV為85%,NPV為99%[14]。一項納入185例患者的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在第96周接受NUC聯合PEG-IFN治療的患者,其平均HBsAg下降遠高于單用NUC治療者(P<0.004),但其在第96周時7.8%的HBsAg清除率并不比單用NUC治療患者3.2%的清除率高許多。這項研究同時發現,那些使用聯合治療并在第96周實現HBsAg清除的患者,在第12周時已有顯著的HBsAg減少,而HBsAg基線在2~3 log10IU/mL為HBsAg清除的獨立相關因素,與運用哪種NUC藥物無關[15]。一項對121例HBeAg陰性患者進行為期48周的PEG-IFN單用或聯合ETV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HBsAg清除的患者HBsAg和HBcrAg的基線及各個時間點的水平都低于HBsAg未清除患者,且數據顯示,HBsAg定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HBsAg清除,與HBcrAg聯合則預測的效果會更好[16]。因此,監測HBsAg定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抗病毒治療的效果,未來仍需更多關于抗病毒的臨床研究進行驗證。
四、總結及展望
qHBsAg作為一個補充性的血清生物標志物,而非HBV DNA的替代品,對疾病進展及療效有較強的預測能力,可以區分HBeAg陰性CHB和非活動HBsAg攜帶者,并預測HBV再激活的可能性。qHBsAg對HBsAg<200 IU/mL且HBsAg快速下降(一年中下降>0.5 log10IU/mL)患者的自然進程及NUC治療后1~3年中HBsAg消失都有預測作用。同時,在抗病毒治療時和治療后檢測qHBsAg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在確定是否要停止治療,或進行姑息療法時。對于免疫控制期的患者,建議每兩年檢測一次qHBsAg,一旦出現HBsAg快速下降(一年內下降>0.5 log10IU/mL,或兩年內下降>1 log10IU/mL)或qHBsAg水平下降到<200 IU/mL時,應進行更頻繁的檢測[6]。對于NUC治療,建議在治療開始時監測qHBsAg水平,每3~6個月以及在治療結束前后及在臨床復發時更頻繁地進行檢測[6](圖1)。為了優化HBeAg陰性慢性HBV感染患者的臨床管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從而對qHBsAg有更深的理解和應用,如qHBsAg的單用或與其他標志物如HBcrAg、HBV RNA的聯合使用等。相信未來qHBsAg會在HBV評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為HBeAg陰性HBV患者管理中更重要的一環。

圖1 血清HBsAg定量監測的時間流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