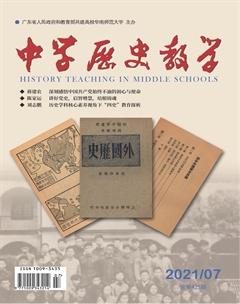運用“大歷史觀”提升高中統編教材的教學效率
袁玲
“大歷史”的英文名是Marco-history,這一名詞是黃仁宇先生所獨創,取“宏觀歷史”之意。用黃仁宇自己的話說“大歷史”就是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概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中去。“宏觀”與“放寬視野”是黃仁宇在解釋“大歷史”時的兩個要素,“宏觀”即“空間意義上的放寬視界”,黃仁宇認為“大歷史”應是打破了國家地域的限制,而使世界成為一體,以全球視野來研究歷史。在此基礎之上的“大歷史觀”則是“主張從客觀歷史的經驗出發,強調對歷史事物的理解應建立在觀察與歸納之上,不僅要注意細節,更強調要從宏觀上把握,以免陷入微觀的‘近視”[1]的一種歷史分析法。
隨著高中統編教材的擴大使用,新教材大部分課時間跨度大、內容多、知識新,課堂時間又明顯不夠用。如何提高課堂效率成為了一線教師的授課難點。視野極度寬廣而又注重分析、綜合、概括,以獲得歷史發展內在規律性的“大歷史觀”則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
本文以“明至清中葉的經濟與文化”一課為例,運用“大歷史觀”來分析相關教學內容的具體問題。
一、從“長時段”“整體性”看明清盛世
黃仁宇認為“中國大歷史”并非一般而言的中國通史,它注重歷史長期的合理性,在他看來,所謂“長時段”動輒將歷史的基點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明至清中葉(1368年至1840年)的472年間,中國的經濟、文化、科技快速發展,超越過往朝代,堪稱中國古代史上的“盛世”之一。在這四百多年中,中國經濟領域出現了多種新現象,經濟作物的區域化生產之下,吳江盛澤鎮、震澤鎮以絲織業聞名全國;新航路開辟后白銀大量流入隨后成為流行的主貨幣;大帆船貿易開啟了中國與墨西哥,亞洲與美洲間的貿易之路,“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2]可見,中國正不自覺地參與到早期全球化進程中。在1700年至1820年間,中國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為0.85%;而整個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為0.21%[3],對比西歐,中國明至清中葉的經濟之盛,可見一般。
人性之光的閃現,是這一時段思想文化的高光時刻。《中外歷史綱要》指出“陸王心學隱含一定的平等叛逆色彩。”“平等叛逆”該如何解釋?黃仁宇認為“大歷史”是由小細節組成的,“大歷史一定要架構在小歷史之上”[4],大時代下王守仁、李贄等人的個人際遇就預示著明朝思想界的革新。王守仁在平定叛亂時,通過講學批判朱熹,宣稱道德與事功互為體用,更說圣人與愚夫愚婦區別只在一念之差。王守仁在肯定孟軻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仍屬簡易可行的真“理”時,隨即又將“獲理”濃縮為“致良知”“知行合一”七字真言,這正好符合了從不同出發點否定官方理學的士人共識,王守仁在正統中蘊含著叛逆。泰州學派代表人物李贄更是指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圣人知天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為一身矣”[5]。他的思想接近了近代西方天賦人權、人人平等思想,他在叛逆中顛覆著正統。從王守仁到李贄,心學家們提倡個人的主觀努力,肯定人的價值,這是要讓個體掌握時代話語權,它體現的是濃重的人性解放色彩。就在這472年間,世界的另一端,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們正高舉“理性火炬”驅散專制與教權主義的陰霾。讓我們運用“大歷史觀”來放寬歷史的視界:同時段內中西方都出現人性解放的呼號,其共同原因是什么?黃仁宇先生指出“大歷史觀”意在改變人們的觀念,使人們對歷史理解不再局限于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狹小范圍。由此可知,其共性應是世界范圍內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因為一定時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的反映。
二、從“間架性結構”看明清困局
黃仁宇先生指出傳統中國的結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肉面包”,上面一塊面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面包稱為農民,一個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主要的治理手段是以抽象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代替法律的支撐。在這樣的“潛水艇夾肉面包”即“間架性結構”下明清盛世陷入困局,整個國家逐漸陷入僵化模式。
明清商品經濟出現新現象并超越前代,但農業工具基本沒有改進,農業技術沒有突破性的創新;有些農業先進地區甚至從牛耕退回人耕;人口激增,耕地緊張,農業生產率總體上下降。有經濟學家指出,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明清商品經濟比前代有較大發展,但勞動生產率又陷入停滯,這不就是一種悖論嗎?黃仁宇指出在“間架性結構之下”“幾百萬小自耕農,一經產生而固定化”[6]他們無法大規模地調整生產。用長時段視角來看,明清的商品經濟基本是沿著封建地主制經濟的軌道前進的,它并沒有真正脫離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軌道,與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不同的,這就預示著中國在邁入現代社會時必定困難重重。
在經濟因素作用下,明清思想界同樣陷入困境,1602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將《坤輿萬國全圖》進獻給明萬歷皇帝,《坤輿萬國全圖》所展示的地圓學說、五洲說、五大氣候帶及經緯度測量法等都對當時的中國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奇異的地圖,利瑪竇“奇談怪論”式的注解使得晚明部分知識分子感到焦慮,他們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他們斥責此圖是“邪說惑眾”,攻擊利瑪竇在描繪鬼魅“直欺以其目的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聽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7]雖然晚明的知識分子已經看到了完整的世界地圖,并且也知道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具體位置,但安土重遷、偏安一隅的中國人始終都不曾想過去遙遠的域外之邦看看,這張地圖除了在認知上拓寬了國人的視野,卻沒帶來任何實際效用。甚至在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君臣都不知道英國到底在哪里,而這卻是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標明了的。“中國兩千多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8]
三、從“數目字管理”看中西分流
明清時期,中國始終沒有邁入近代社會,依據“大歷史觀”這主要是因為明清時中國沒有同英國一樣實現“數目字管理”,即“經濟組織上的分工合作”“法律體系上的權利義務分割”“道德觀念上的私人財產不可侵犯”。不難看出“數目字管理”在本質上是提倡技術理性思路,在這一思路下,西方的現代化經驗就是“科技因經濟體制之活躍而增長”[9]。此外,西方的國家體制使整個社會因自然賦予的不平衡而繁榮,它鼓勵各地區發展其專長,這些不平衡的因素在互相競爭后,終至分工合作,在循環往復中各方面都繼續長進。從長處及大處著眼,明清的國家體制不能使中國適于現代科技,明太祖創設的“洪武型財政”作為一種“收斂型”財政制度延續明清兩代,這使中國形成了“一種大而無當而又自給自足的經濟系統”,雖然明清時期諸如“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的確使整個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一些活躍現象,但由“洪武型財政”所決定的“組織與制度體系”依然如故。
在制度性因素下,明清中國政治腐敗,不僅未采取積極措施促進經濟發展,還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打壓商業的發展;中國的統治階級對農民和手工業者殘酷剝削,占有他們全部剩余勞動甚至部分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并將剝削所得全部揮霍而非擴大社會再生產;明清中國的法律制度不保障產權……最終1800年后“大分流”出現了,英國及其他西歐國家走到了前頭,而其余地區則落到了后面。中國近代的落后早在明太祖洪武時就已埋下了因子。
王家范先生曾這樣評價黃仁宇的“大歷史”:“我覺得黃仁宇的治史路向,對我們是極具啟發意義的。治史的割裂,畫地為牢,分工過細,無疑已成為史學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障礙。拆掉圍墻,其中包括古代史與近代史的打通,中外歷史的打通,實有必要。”[10]
“大歷史”在某種意義已經不是一國一地的歷史,而是一個涵蓋了整個世界歷史范圍的概念。通過中西古今對比,是為了把握現代中國在歷史長河中的前進方向,現實中不可解決的問題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這就是歷史“以古鑒今”的現實功能。隨著高中統編教材的擴大使用,新教材時間跨度大、史實密集度高,運用“大歷史觀”解讀整合教材既可以拓寬我們的歷史視野,又能深刻揭示史實背后的規律,不妨一試。
【注釋】
[1]李席:《黃仁宇“大歷史”的現代性解讀——以<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為中心的剖析》,《淮北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第9頁。
[2]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72頁。
[3]李伯重:《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3頁。
[4]黃仁宇:《黃河青山》,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277頁。
[5]張世英:《儒家與道德》,《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第28頁。
[6]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26頁。
[7]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歷史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中外歷史綱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87頁。
[8]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自序。
[9]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183頁。
[10]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