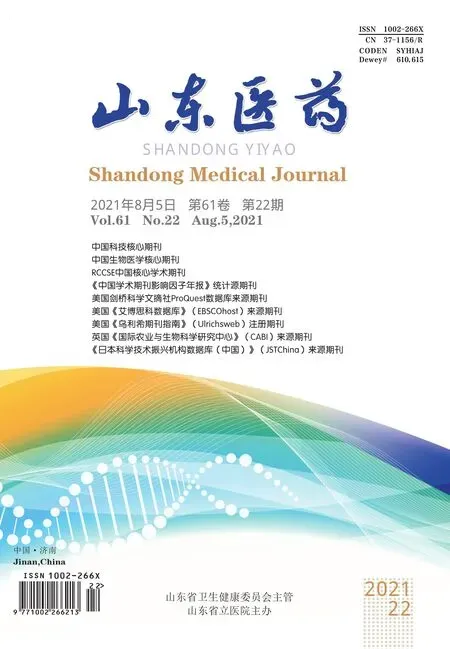血漿copeptin、IGF-1 水平對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吳高遠,倪永豐,錢洪波,潘捷,殷駿,吳問亮
安慶市第一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安徽安慶246000
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SAH)是蛛網膜下腔出血中最常見的類型,約占蛛網膜下腔出血總數的85%,多數aSAH 合并嚴重并發癥,具有極高的致死率,10%~25%患者死于住院前,即便存活亦常遺留殘疾[1]。aSAH 預后受神經損傷程度、血流動力學、腦血管穩態、血腦屏障是否完好、神經元恢復等多種因素影響。和肽素(copeptin)是內源性應激標志物,具有調節滲透壓、血流動力學、體液穩態等作用。copeptin 在體內分布穩定,對心腦血管疾病診斷、病情評估有較高價值[2]。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是生長激素關鍵調節因子,具有維持神經元存活和軸突生長功能,在神經內分泌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IGF-1 缺乏可能參與腦出血后垂體功能障礙進程[3]。本研究擬探討copeptin、IGF-1在aSAH 預后預測中的價值,以期為臨床aSAH 患者風險評估、預后判斷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神經外科收治的142例aSAH 患者。納入標準:①劇烈頭痛、腦膜刺激征陽性,顱腦CT 和MRI 提示與動脈瘤相關的出血灶;②符合2015 版《中國蛛網膜下腔出血診治指南》中的診斷標準[4];③首次診斷aSAH,既往無腦出血病史。排除標準:①顱腦外傷、高血壓導致的腦出血;②煙霧病、動靜脈畸形、假性動脈瘤;③入院48 h 內死亡患者或發生腦疝患者。本研究獲得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入組前均告知患者或其家屬本研究目的和內容,均表示同意,簽署同意書,研究期間嚴格遵循倫理學原則,保障患者隱私和安全。
1.2 臨床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吸煙史、飲酒史、基礎疾病、血壓、動脈瘤直徑、Hunt-Hess 分級[5]、改良 Fisher 分級[6]、世界神經外科醫師聯盟委員會的蛛網膜下腔出血(WFNS)分級[7]、治療方式、機械通氣、有無瞳孔擴張、并發癥等信息。
1.3 血漿copeptin、IGF-1檢測 所有患者入組后24~48 h采集清晨靜脈血5 mL,經離心(4 ℃,3 000 r/min離心15 min,離心半徑10 cm)后取血漿保存于-80 ℃超低溫冰箱(Thermo Fisher 公司)待檢。取出樣品快速解凍血漿樣品,ALISEI 全自動酶標儀(意大利SEAC公司)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血漿copeptin、IGF-1,試劑盒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4 隨訪 發病后3 個月采用改良Rankin 量表(mRS)評價患者預后情況,mRS 評分≤2 分為預后良好組 44 例,mRS 評分>2 分為預后不良組[8]98 例。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5.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以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等級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aSAH 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應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進行診斷效能分析,以曲線下面積(AUC)為主要判斷指標。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預后不良組年齡(67.19±6.34)歲,體質量指數(25.06 ± 3.03)kg/m2,收縮壓(156.35± 8.34)mmHg,舒張壓(76.33± 4.39)mmHg;預后良好組年齡(63.73 ± 6.73)歲,體質量指數(25.42 ± 3.11)kg/m2,收縮壓(145.47 ± 6.92)mmHg,舒張壓(75.42±4.02)mmHg。預后不良組年齡、收縮壓高于預后良好組(P均<0.05),女性、合并糖尿病、機械通氣、瞳孔擴張、保守治療、WFNS 分級Ⅲ~Ⅳ級、Hunt-Hess 分級Ⅲ~Ⅴ級、改良Fisher 分級Ⅲ~Ⅳ級、遲發性腦缺血、腦出血、腦血管痙攣比例高于預后良好組(P均<0.05)。兩組體質量指數、舒張壓、吸煙史、飲酒史,合并高血壓、高脂血癥、冠心病以及動脈瘤直徑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均>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例(%)]
2.2 不同預后患者血漿copeptin、IGF-1水平比較 預后不良組、預后良好組血漿copeptin 水平分別為(1.96 ± 0.35)、(0.85 ± 0.21)ng/mL,IGF-1 水平分別為(2.02 ± 0.21)、(3.51 ± 0.37)ng/mL,兩組比較,P均<0.01。
2.3 影響aSAH 患者預后的多元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aSAH預后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差異的變量為自變量:預后(Y):0=良好,1=不良;年齡(X1:1 為<65 歲,2 為≥65 歲)、性別(X2:1=男,2=女)、收縮壓(X3:1為<150 mmHg,2為≥150 mmHg)、合并糖尿病(X4:1=否,2=是)、機械通氣(X5:1=否,2=是)、瞳孔擴張(X6:1=否,2=是)、治療方式(X7:1=血管介入/開顱動脈瘤夾閉術,2=保守治療)、WFNS分級(X8:1=Ⅰ~Ⅱ級,2=Ⅲ~Ⅳ級)、Hunt-Hess分級(X9:1=Ⅰ~Ⅱ級,2=Ⅲ~Ⅴ級)、改良Fisher 分級Ⅲ~Ⅳ級(X10:1=Ⅰ~Ⅱ級,2=Ⅲ~Ⅳ級)、遲發性腦缺血(X11:1=否,2=是)、腦出血(X12:1=否,2=是)、腦血管痙攣(X13:1=否,2=是)。代入Logistic回歸方程。結果顯示,WFNS 分級Ⅲ~Ⅳ級、并發腦血管痙攣、高copeptin、低 IGF-1 是 aSAH 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P均<0.01),見表2。進一步校正WFNS分級、腦血管痙攣后,copeptin(OR=1.625,95%CI:1.504~1.905,P<0.01)、IGF-1(OR=1.823,95%CI:1.653~2.035,P<0.01)與aSAH患者預后相關(P均<0.01)。

表2 影響aSAH預后的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
2.4 血漿 copeptin、IGF-1 水平對 aSAH 患者預后預測的價值分析 ROC 曲線分析血漿copeptin、IGF-1水平預測aSAH 患者預后的AUC分別為0.739、0.770,copeptin、IGF-1 聯合預測 aSAH 預后不良的AUC為 0.905,高于單獨 copeptin、IGF-1(Z分別為2.536、2.264,P均<0.05)。血漿 copeptin、IGF-1 及二者聯合預測aSAH 預后不良的最佳截斷值、靈敏度、特異度、約登指數見表3。

表3 血漿copeptin、IGF-1水平預測aSAH患者預后的效能分析
3 討論
aSAH是臨床常見的出血性腦血管疾病,好發于女性,可能與激素水平有關。aSAH發病還與年齡有關,隨著年齡增加其發病率呈增長趨勢[1]。aSAH 對神經系統功能以及多個器官均產生嚴重影響。aSAH病因、發病機制復雜,臨床癥狀不一,病情進展快,病死率高。評估aSAH 預后有助于早期發現危險因素,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患者病死率和神經功能惡化。WFNS評分、Hunt-Hess分級、改良Fisher分級易于臨床醫師掌握,但缺乏客觀充足的影像學證據以及生物學指標,在aSAH 預后評估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尋找與aSAH 預后密切相關的分子機制有重要意義。
copeptin 是精氨酸加壓素(AVP)前體C-末端糖基化多肽,AVP 由垂體后葉釋放,具有升高血壓、收縮血管、抗利尿循環等作用,參與腦血管穩態維持。AVP 半衰期短,其臨床應用受限,copeptin 具有和AVP 相同病理生理作用,比AVP 更穩定,逐漸成為AVP 的替代生物學指標。copeptin 已被證實與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9]、冠心病、冠脈病變嚴重程度[10]等密切相關。血漿copeptin 水平在腦梗死、顱內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中明顯升高,參與腦血管疾病患者神經受損、不良臨床結局過程[2]。本研究發現,copeptin 水平與aSAH 患者發病3 個月后預后有關,高copeptin 水平預示更高的致殘和死亡風險,說明copeptin 水平越高,神經受損越嚴重,預后越差。ZHENG等[11]認為,copeptin是aSAH患者臨床結局強有力的預測因子,預測效能超過NSE、S100B 等神經損傷相關指標。copeptin 參與aSAH 預后的機制尚不明確,可能機制:aSAH后腦組織缺血缺氧,血流動力學異常,copeptin 作為神經內分泌應答的一部分生成增加,通過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促使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調節滲透壓,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12]。
IGF-1 是一種分泌型小肽生長因子,參與機體生長、組織修復、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質代謝等多種生理和病理生理過程,與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發病有關[13]。近期研究顯示,約12.1%創傷性腦損傷和 aSAH 患者血漿 IGF-1 水平明顯下降[14],提示IGF-1 缺失與aSAH 發病可能存在密切聯系。IGF-1 是否能為aSAH 預后評估提供有效信息尚不清楚。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低IGF-1 水平是aSAH 患者發病3 個月后神經功能惡化的危險因素,說明IGF-1 缺失可能與aSAH 神經功能惡化和不良預后有關。IGF-1 參與aSAH 患者病情進展的機制:aSAH可導致垂體功能障礙,影響生長激素分泌,IGF-1 作為生長激素調節蛋白其表達也出現下降,IGF-1 活性降低影響神經元生長,促使神經細胞凋亡、壞死,導致神經退行性病變和神經功能的惡化[15]。IGF-1 缺乏可引起腦血管壁病理重塑,導致管壁肥厚,彈性降低,IGF-1 水平下降可能促進了腦出血的發生。動物研究顯示,重組IGF-1 制劑可降低p-GSK3蛋白和促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表達,增加緊密連接相關蛋白occludin 和claudin-5 表達,減少腦出血小鼠腦水腫,降低血腦屏障通透性,改善神經行為[16]。
本研究ROC 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血漿copeptin、IGF-1 預測 aSAH 患者預后的AUC為 0.739、0.770,提示copeptin、IGF-1 可作為一種新的生物標志物評價aSAH患者預后。copeptin、IGF-1聯合提高了預測aSAH患者預后不良的效能,說明copeptin升高、IGF-1降低的aSAH 患者發病3 個月內神經功能惡化的風險更大,對預后不良具有提示作用。本研究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腦血管痙攣、WFNS 分級Ⅳ~Ⅴ級是aSAH 患者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之一,腦血管痙攣是aSAH 常見的嚴重并發癥,是aSAH 患者致殘和死亡的原因之一。WFNS 分級Ⅳ~Ⅴ級預示較高的延遲性腦缺血風險,是aSAH 術后72 h 延遲性腦缺血有效預測因子[17]。
綜上所述,血漿copeptin、IGF-1 水平升高與aSAH 患者預后不良密切相關,可作為aSAH 預后評估的潛在生物學指標,copeptin、IGF-1聯合檢測可提高aSAH患者預后預測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