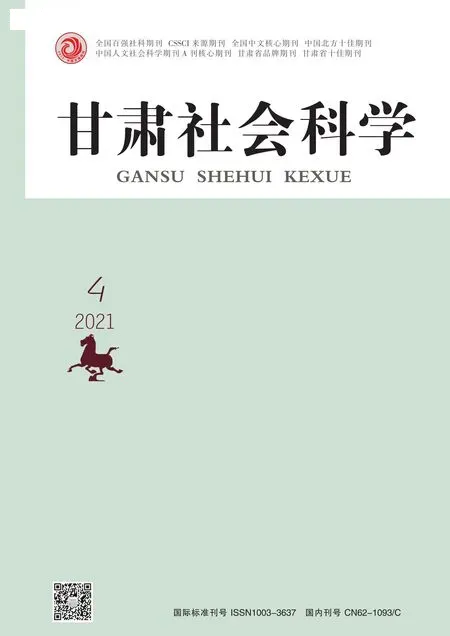杜甫的俠義人格與詩格
汪聚應
(天水師范學院 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0)
提要: 從俠義人格與詩格的文化視角審視杜甫及其詩歌創作是一個全新的角度。浸潤于唐代任俠風尚的杜甫,世情家風養俠氣,儒義劍氣鑄俠骨,詩史健筆明俠心。他崇俠尚義,歌頌游俠精神,對俠有清醒認識、選擇接受和辯證宣揚,詩歌創作充滿了任俠精神。其游俠意氣、仁俠情懷、犧牲精神成為杜甫俠者人格的重要標識,形成了他文氣與俠義相融、儒與俠互補的文化人格,賦予了他俠骨仁心的詩圣內涵。這種俠義人格精神使他敢于直面現實而不畏強權,也使詩歌創作增添了現實高度和藝術張力,洋溢著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詩學價值。
人格關乎詩格。高尚的人格是產生高尚詩格的前提,是詩歌藝術審美感染力的基礎,也是詩歌藝術的生命力。杜甫生活在任俠風氣高昂的盛唐和中唐,深受時代任俠風尚和儒家思想影響、家庭任俠精神熏陶等,人格精神充滿俠義文化色彩,詩歌創作表現出深厚的任俠精神。其溫良泛愛、重交尚義、重諾好施的仁俠情懷和利他的犧牲精神不但是杜甫俠義文化人格的重要內涵,而且形成了他儒與俠互補、文氣與俠義相融的文化人格,賦予了他俠骨仁心的詩圣內涵。杜甫以清醒的現實態度和儒家博施濟眾、仁民愛物的價值觀念認識俠,選擇性地接受了俠,這使其人格精神和詩歌創作表現著俠文化積極向上的一面,充滿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帶給人們強烈的審美感動和深沉的人格力量。
一、家風世情的俠氣浸染與俠義人格的精神特質

杜甫祖上多俠義之士,任俠家風而仁義恒傳,對杜甫俠義人格的影響自然深遠。襄陽杜氏家族在公元4世紀到9世紀約500年間,命運的跌宕起伏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形成了諸如豪爽俠義、狂放不羈等等心理和行為特征”,影響了家族成員的心理層面[2]。杜甫對俠義精神的認同、接受與歌詠都有源自俠義家風的濡染,其祖上任俠有節義者如杜叔毗、杜并及其曾祖姑、姑母等。
杜叔毗為杜審言之曾祖,慷慨有志節。《周書》卷四十六《杜叔毗傳》記載,杜叔毗兄君錫、從子映、映弟晰為曹策謀害,他“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后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另據《新唐書·藝文傳》載,杜審言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時,司馬周季重等誣構其罪,系獄欲殺。杜審言子杜并“袖刃刺季重于坐,左右殺并”[3],俠義復仇,與杜叔毗無二。杜甫家族以俠義聞者還如其曾祖姑王珪妻杜魚石女,困頓時剪發鬻酒以待長者。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中表達了對其“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杯酒”及其“愿展丈夫雄,得辭兒女丑”的崇敬,抒發了對這種俠義家風的持守與弘揚:“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杜甫姑母仁義至孝,病疫之年,自幼喪母、在洛陽仁風里姑母家寄養的杜甫感染疫病,其姑母舍子保甫之命,使杜甫刻骨銘心,稱其為唐“義姑”,將她比作 “棄子行義”的“魯義姑”載入《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中,并“嘗有說于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4]3660。
杜叔毗和杜并,俠義復仇不顧性命;杜魚石女及杜甫義姑,剪發鬻酒不失豪俠,棄子救侄舍生取義。杜氏一門可謂俠義包舉,俠行義舉貫代而傳。而任俠家風帶給杜甫心靈深處人格精神的俠義哺育是深遠的,也是深刻的。它們在文化心理、行事交友、人格追求、詩歌創作諸方面影響了杜甫的文化認同、處事原則與價值觀念,使其始終將古代任俠風氣中的“利他”的犧牲精神作為出發點,去提升自我的人格內涵,去譜寫詩歌的現實篇章。“利他”精神也就成為杜甫俠義人格的基點和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核心。
杜甫這種俠義人格的形成,除了家風世情,也有他剛直仗義、崇尚狂放豪蕩的個性與獨特的人生經歷,這使他心高氣傲,狂放不羈,平視王侯,不肯趨炎附人。他愛蒼鷹駿馬,嗜酒迷劍,俠義磊落之士他傾心交結,如李邕、李白、高適、嚴武等,他們的豪言俠行、義膽俠心,也深深影響了杜甫。其豪俠義士般裘馬輕狂的漫游生活,其狂放不羈的壯言豪語都洋溢著俠義人格的浸潤與澆灌。
對這種俠義人格風范的接受和踐行,在杜甫青壯年時期和外在氣質上的表現就是游俠少年的“意氣”“率真”和“狂放”。其《壯游》《遣懷》之章、《少年行》之篇,表現的都是唐代少年游俠的時代風貌。杜甫以性情相投、人品相高意氣結友:“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貧賤”[5]2480。其《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就是以游俠口氣的慷慨流露,希望韋左丞能引以為知己:
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5]2251—2252
而其《今夕行》抒寫早年狂放縱游的任俠生活,就是他意氣、性情的真實寫照。此詩揮寫“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的一場除夕博戲,袒臂跣足,豪放不羈。其中“劉毅從來布衣愿,家無儋石輸百萬”足見杜甫“英雄有時亦如此”的豪放,頗有少年游俠之氣[5]2254。而其“不羈”之氣,令陸游生發對后世只將杜甫看作詩人而不當俠者的感嘆。其《讀杜詩》云:
城南杜五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扶幾空嗟咨。[6]
杜甫豪氣由來塞天地。志士詩人陸游感嘆的是后世對杜甫認識的偏頗,對詩人俠義人格精神和不羈氣質稟賦的視而不見,對其濟世雄心的熟視無睹。仇兆鰲說“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簡”。而杜甫詩中自恃狂傲之句則俯拾皆是:“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杜甫一生悲天憫人,憂國傷時,俠風古義染儒身,他以一介平民身份關心民瘼國運,展示著義儒仁俠所特有的一種俠義人格。其人格構成中的俠義精神,多是將時代任俠風氣結合儒家仁義價值觀念而內化為一種超越時代的文化人格追求,這是他接受俠文化中積極因素的價值體現,也是杜甫人格精神中值得敬仰的地方。有時代俠風的濡染,更有古游俠精神的熏陶。杜甫這種俠義人格精神與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極力贊頌的古布衣之俠千里誦義、同情弱者、振窮周急、溫良泛愛的民間俠義精神同出一轍,于詩人之俠有特別的文化意義。它使杜甫在文化人格層面展示了作為極富熱腸的仁者和極有俠氣的詩人兩者的高度統一,也使他身上展現的俠義人格集中體現著中國俠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一是利他精神,突出表現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二是恩報觀念,突出表現就是“士為知己者死”;三是功名意識,突出表現就是“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四是重義信諾,突出表現就是“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而安史之亂后的杜甫,其俠義文化人格精神中增添了許多理性成分,多了強烈的正義特質和悲壯色彩。詩人的堅定、執著、敢于殉道的士君子精神風范因現實苦難的磨煉而日益深沉,脫略書氣的仁俠情懷使“士之厄困”與貧寒窘迫的底層民眾成為他俠義人格最為關注和為之犧牲的群體,也成為他俠義文化人格中道德純粹的砥石。
二、儒義劍氣的俠骨澆灌與俠義人格的精神內涵
儒者主仁重義,有原始俠者情懷和俠義人格規范。劉若愚在《中國之俠》中感言:“在強調個人尊嚴,反對國家權威方面,在寧取富有人情味的正義感而不取法律概念方面,游俠和儒家是站在一起的。”[7]章太炎在《訄書初刻本·儒俠第五》中說,儒家“殺身成仁”“除國之大害,扌干國之大患”,都是“任俠之雄所兼具的”[8]。

古之解少陵者,自為解耳。即進而有解于少陵,解其詩焉耳,孰為俠志?孰為仁音?孰為道義?孰為忠愛?孰為篤交?孰為尚友?孰從而逆之?孰從而剔之?而迥存吾少陵者,斯鈔之不可已也。[1]
子美性情,有其豪俠仗義、狂傲灑脫的一面。這里所列杜甫“俠志”“仁音”“道義”“忠愛”“篤交”“尚友”雖是就杜詩而言,但無不是從杜甫這個有俠者情懷的人格深處和骨子里探尋到的真實存在。
溫良泛愛是杜甫俠骨中流淌不絕的仁俠人格精神。在杜甫身上,詩格與人格是高度統一的。觀其一生,戀主憂民,血忱耿炯,與日月齊光。他“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流露著對朝廷明君的傾心忠愛;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充滿了對下層人民的同情與博愛,尤其是安史之亂后的漂泊生活,時代的霹靂使他成為普通的一員,生活的艱辛使他融入下層百姓并為他們俠義吶喊:“晚憩必村墟”“田父實為鄰”“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劚”。面對社會貧富嚴重不公,只有他敢于怒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博愛多施、溫良泛愛不亞于古游俠,這是杜甫儒俠人格的底色,有古游俠人格精神的濡染,也有儒家“仁愛”思想的影響,體現著超道德的俠義人格精神。這種振人不贍的仁俠之心,尤為可貴之處在于推己及人。雨及時而有潤物之喜,屋風破而生庇寒士之心;由自身除征免稅而思及遠戍之卒,因幼子夭折而念及失業之徒……王安石在《子美畫像》中感言:“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杜甫為社會底層困頓者的俠義吶喊和史詩巨篇一樣,充滿深厚仁愛和振窮周急的俠者情懷。

與其他有俠氣的文人相比,儒義精神熏陶下的杜甫,其思其行,其詩其意集中表現出中國俠文化中獨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其俠骨仁情表現出對俠清醒的現實認識和選擇性接受。
重義信諾、擔當赴難的犧牲精神是杜甫俠義人格的重要標志。中國古代俠文化有著中華民族的血性反映,突出表現就是孟子所說的“舍生取義”,以及他所說的大丈夫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與任俠的李白相比,李白詩中過分渲染游俠少年的斗雞走馬、飲酒博獵、恣縱任性,有著濃烈的功業意識和浪漫精神;而杜甫詠俠詩注重張揚古游俠的言信行果、溫良泛愛、打抱不平的俠義精神,并以儒家仁義、忠信等價值觀念詮釋任俠精神。因此,杜甫作為對俠和俠文化進行改造的唐代詩人,著重弘揚了俠文化中豪蕩俊爽的自由意識、重義輕生的犧牲精神、溫良泛愛的仁者品質、重諾誠信的人格風范。對游俠放蕩不羈、游冶博獵、斗雞走馬,甚至殺人越貨等“不軌于正義”的行為端持批判。蘇轍《詩病五事》說:“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9]故杜甫詠俠詩中稱贊的俠者,必是豪爽仗義、溫良泛愛、忠勇報國之士。對驕奢粗豪、好勇斗橫的少年,頗多微詞。如《少年行》三首之三云:
馬上誰家薄媚郎,臨階下馬坐人床。
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5]2246-2247
杜甫三首《少年行》,《唐詩類苑》卷八十五人部載入“俠少”類,《淵鑒類函》卷三百十一人部“游俠”載其三,批駁的是游俠少年的蠻橫無理。而其一寫游俠少年的豪飲無度,其二寫游戲少年的虛度年華,整體上對游俠少年的粗豪放蕩、年華虛擲和蠻橫使氣、驕奢無理等行為充滿了諷刺。
向往公平正義,是杜甫俠義人格中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內容,是儒義與劍氣交融的生動體現,也是其詩歌創作詩史精神的力量之源和詩圣人格的超道德境界。公平正義是古代游俠的精神追求,也是古代文人知識分子的處世之道、德修與追求,這其中就有俠義與劍氣的融合互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劍經過俠士的正義化、道教的神秘化與儒家的寫意洗練,被賦予了更多文化氣質和中國特有的“公平正義”崇拜與崇高地位,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劍俠文化。或表現出對自我人格理想的期待,或表達對功名的積極進取,或洋溢著詩人的豪俠氣概,或表達對社會黑暗與不平的抨擊、懷才不遇的憤懣與宣泄等等,但都蘊含著公平正義必勝的期許。對俠而言,劍就是公平正義的象征。由此,古代文人對劍俠也同樣寄予公平正義的人格期許。唐人詠俠詩中劍意象公平正義的內涵非常豐富。如李中《劍客》:“神劍沖霄去,誰為平不平。”[5]8500慕幽《劍客》:“去住知何處,空將一劍行。殺人雖取次,為事愛公平。”[5]9624呂巖《贈劍客》:“背上匣中三尺劍,為天且示不平人。”[5]9697賈島《劍客》可謂代表,詩云: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5]6616
這里不僅有俠者對打抱不平的期盼,更有詩人懷才不遇的憤懣。公平正義可期,詩心俠心可鑒。而回蕩在歷史長空中的文人俠義之士,用他們對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用他們積極進取的人生理想,譜寫了劍文化和俠文化的正義之聲。杜甫的俠意識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游俠輕生重義的人格精神、冀知報恩的知己情結、溫良泛愛的仁者品德的高度認可,這是他極力頌揚的任俠精神和信守的俠義人格規范。
唐人對俠文化的繼承和改造的突出方面,就是大力提倡“俠義”,將“義”作為俠的標志和行俠的價值核心:“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杜甫重諾信義,且非常看重“義”,既是儒家“義利”觀的影響,也是對唐人俠的義化改造的接受。他的俠義人格,真正體現了“國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職守重于生命,然諾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譽重于生命,道義重于生命”的中國之武士道精神[10]。其“好義之心”,就是將“義”作為體現人生價值的重要內容堅守一生,就是對國家盡忠義,對朋友重信義。也以說明杜甫對“義”的執著和“義”在其人格及價值觀念中的位置。甚至他還將義從任俠之士延伸到了義鳥。如《義鶻行》,活畫出仁慈義勇的義鶻形象,展現著杜甫見義勇為的俠思俠氣和路見不平的俠骨仁心。
在杜甫俠義文化人格中,對游俠的重諾輕生、言信行果,絕不停留在言語層面,而是有自身的積極踐行。他在《敬贈鄭諫議十韻》中豪言壯語:“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在《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中,更是向楊綰陳說踐行挖茯苓之諾。
自漢以來,士風中漸染俠風俠氣,頗重俠義精神。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論東漢名節士風時,將其成因歸之于游俠。其卷五“東漢尚名節”條云:
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后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11]

輕財重施,在杜甫身上也有俠性表現。大歷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出巫峽,作《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詩,將瀼西四十畝果園贈予友人。黃生《杜詩說》卷十中說:“此詩當與《園》詩四韻同看,彼以買得而喜,此以別去而惜,皆見物外高致。然始而買,終而贈,又是達士曠懷,彼視天下之物何者為我所有哉?若在俗人,果園四十畝必將襟府塞滿,在公舉以贈友,只與饋桃撲棗同觀,想見靈府空洞無物,不虛作第一詩人。”[12]仇兆鰲感言:“初寓長安,得錢沽酒,時招鄭虔,后去夔州,舉四十畝果園贈與知交,毫無顧戀。此與謫仙之千金散盡者,同一磊落襟懷。”[13]25
恩仇分明是與“義”緊密相連的任俠精神,也是所謂“俠客之義”的重要價值觀念。杜甫崇尚恩仇分明,恩報意識很重。他說:“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白刃酬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但從杜甫的思想行為和詩歌創作看,杜甫的恩仇意識和古游俠的所謂“一飯之恩必償,睚眥之仇必報”的狹義恩仇觀是不同的。
可見,杜甫人格詩格中體現出的任俠精神,使杜甫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具備了豐厚的俠義文化人格內涵,也使這位一生窮愁、功名不顯的漂泊詩人足以光耀史冊。從這一點看,充滿俠骨仁心的詩圣,他的光輝早已穿越了文學,照耀了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他以一個俠者的情懷,實踐了儒家的人文關懷和價值追求,他以整個的生命,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這一切,也豐富了杜甫的情感世界與創作畛域,影響了杜甫的詩歌創作風格,提升了面對嚴肅的社會現實主題時,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自身所需要的俠者之勇、仁者之心、正義之氣等亮劍精神和愛憎分明的藝術膽力。
三、俠義人格的俠心抒發與詩史書寫
中國俠文化的創造具有群體性特征,它是史家、文人、大眾的歷史文化共建。通過史家的法正之路、文人的義化之路、大眾的英雄之路,使中國俠成為一個歷史文化綜合體。這個綜合體也體現著文人與俠客的特殊關系:“千古文人俠客夢”,而“少年游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則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三部曲。
杜甫以史詩健筆書寫國憂家愁、抒發不平之氣。與唐代文人一樣,他在熾熱的任俠風尚中從游俠身上發現的人生價值是多方面的:特異獨立的人格精神、濃厚壯烈的功業意識和恩義深沉的知己情結,以及通脫浪漫的生活方式,并通過自我的任俠行為和對俠的崇尚詠贊,認同并內化了這些人格精神,這使其人格理想和詩歌審美理想表現出濃郁的俠義色彩,形成杜甫詩歌中獨特的任俠精神,其俠義人格的俠心抒發與詩史書寫表現出文心與良心兼備,俠義與儒仁并舉的時代人格特征。
聞一多先生說:“兩漢時期文人有良心而沒有文學,魏晉六朝時期有文學而沒良心,盛唐時期可說是文學與良心兼備,杜甫便是代表,他的偉大也在這里。”[14]聞一多把安史之亂作為唐詩轉變的界限,并認為關鍵在于詩人的成分有了大的改變,由貴族轉變為士人。他推崇杜甫,是因為杜甫恢復了兩漢文人關心民生哀樂的良心,突破了盛唐貴族詩風,開啟了中晚唐不絕的現實主義詩風。與杜甫而言,時張時隱于詩人血液中的剛正不羈的俠者人格,濟人拯物、溫良泛愛的俠者情懷成為他崇俠尚義、詠贊任俠精神的情感基礎和信念支柱,也形成了杜甫文情與俠氣并行合一的個性氣質,儒仁與俠義相融互補的人格精神。這種俠義人格精神貫穿于杜甫一生,尤以安史之亂后,其行為方式更多地拓展到了家國層面,轉向了天下蒼生。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俠心抒發與詩史書寫也因此具有了超強的史詩高度、豐厚的藝術張力和真誠的現實感動,并具有了高尚的詩格,體現著人格與詩格的高度統一。
杜甫合儒、俠為心,以詩與史為形,俠心與詩心相融,詩與史合一。其俠義人格中,能體現其俠心的是俠忠、仁情和義行。在詩歌創作中,這種俠義人格精神表現為對國家的忠義、對人民的同情,對見義勇為、冀知報恩、豪爽任性等任俠精神的謳歌等。如“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甘為國家民族視死如歸。即使如《新婚別》這樣的詩篇,詩人依然書寫的是鼓勵人民迅速平叛戰亂。對“暮婚晨告別”“妾身未分明”的新婦,甘愿“對君洗紅妝”“與君永相望”支持丈夫平叛的行為給予了肯定。漂泊西南時寫的《秋興八首》更有“夔府城高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的赤心。而《鳳凰臺》展現的是一位俠忠老臣對國家剖肝瀝膽的犧牲精神。詩人以“無母之鳳雛”比喻處于危難中的朝廷,以“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的獻身精神,抒發對朝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的期望[5]2297-2298。
杜甫以溫良之心抒發對人民的極盡同情泛愛,而能“推己及人”,能以“利他”的犧牲精神面對大眾的苦難,并常常以自己的身份處境相比來告誡人們:百姓的苦難比自己更深。這是杜甫俠者仁心的獨特之處,也是他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獨特之處,而建立在俠義基礎上的詩史書寫也就具有了獨特的感人力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慷慨陳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現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5]2310;《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悲痛相比:“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鴻洞不可掇。”[5]2266

與李白相比,杜甫雖少擊劍任俠的親身經歷,但其詩卻多敘寫漫游所見的游俠生活。如《遣懷》《壯游》等詩抒發了青年時期杜甫狂傲的意氣和對俠義精神的向往。其《壯游》云: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云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鹙鸧。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5]2358

杜甫以文人的良心抒發對眾生萬物的同情憐憫,以史家直錄精神反映現實之弊,以俠者豪健之筆抒寫俊爽之氣,始終展示著自我磊落的膽識意氣和濃烈的俠義人格精神,這種膽識意氣使其俠心抒發和詩史書寫并不是簡單地敘述一段見聞、描述幾件實事,而是以俠骨仁心滲透或流露出對人對事強烈的情感和深刻的現實揭露,俠心烈烈,正氣凜然。其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也因此獲得史詩的紀實性和詩史的深刻性,俠心抒發情真意切,詩史書寫令人肅然生畏。
杜甫的俠心抒發和詩史書寫增強了詩歌中任俠精神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的內容是杜甫詩歌研究中鮮少被探知的方面,它對于全面認識杜甫及其詩歌創作精神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作為現實主義的詩人,作為俠骨仁情的詩圣,杜甫俠者之心始終不脫離文人的社會責任感、深沉的憂患意識和犀利的批判精神,是唐代詩人中對時代任俠風尚和俠文化有清醒認識并進行義化改造的詩人。他對俠文化的利弊有客觀的認識和態度,并能立足于國家、社會、自我不同層面,加以辯證的鑒別和有揚棄的繼承。一方面,他以積極的現實主義態度冷靜對待俠和俠文化,自覺摒棄其“不軌于正義”的一面,極力弘揚俠文化中與儒家仁義精神相融的積極因素,并以此為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這是杜甫著重接受了俠文化中古布衣之俠的任俠精神。另一方面,他以正義為核心,對游俠及其行為觀念加以理性地辯證審視,肯定俠言行信果、重義好施的品格和慷慨赴難的氣節,并引以為自我克服現實人生艱難的精神力量。這是杜甫自覺以正義改造俠文化,提升了俠文化中面對國家民族大義視死如歸的擔當精神。
四、俠義人格詩格與詩史融合的詩學價值
杜甫“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他的俠義文化人格,對于全面認識和揭示其詩圣內涵的時代精神、沉郁頓挫藝術風格的人格力量,對于全面準確地解讀杜詩的人文精神和唐詩的文化精神都有極其重要的認識價值、詩學價值和社會文化意義。
杜甫俠義文化人格在人性、道德等精神層面和行為處事等實踐層面所展現的人格精神力量具有積極的認識價值,在現實主義詩歌創作和詩歌審美等文學層面所展現的詩與史的高度融合具有崇高的詩學價值。
就士風與俠風的關聯看,唐代士風與俠風深受漢魏六朝影響,兩者相互影響浸潤,這種緊密關系也使俠本身的傳承與發展受到影響,表現出某些行為理性,這種行為理性的形成在唐代有一個引導改造的過程。杜甫等一部分具有俠氣、俠行、俠情的文人以正義理性引導澆灌,使俠在唐代從陳子昂的家國引導到杜甫的精神守正,從韓愈、柳宗元的儒義灌注到李德裕“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正義旨歸,最終形成俠與義的合而為一,中國俠的義化改造得以完成。這期間,一條重要的紅線就是從曹植《白馬篇》中以國家民族大義改造提升游俠行為和任俠精神,經唐之義俠到清代輔法之俠,俠的大眾英雄化色彩漸濃,人格精神得以正義為本色。
杜甫儒與俠融,義與俠合。他身上體現的俠義精神,從行為看,表現為對朝廷的忠守有節,俠“士為知己者死”的冀知圖報;對天下蒼生之不振有仁俠的好施推義;對朋友之誼有義俠的肝膽相照,更有對俠義精神的心靈化的詩歌抒寫。杜甫俠義人格力量的認識價值所包舉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它不僅有對俠和俠文化在人性道德層面的理性哺育和正義指引,有對俠義精神的自傳化的踐行和心靈化的感悟,于己于人、于公于私、于國于家,皆能如一,并付諸現實主義詩歌創作。
杜甫以仁俠情懷書寫難民化的社會史和生活史,使其俠義人格具有了鮮活的社會歷史內涵。除“三吏”“三別”諸篇之外,“似騷似史、似記似碑”的《北征》,詩篇滲透著一個俠義詩人的難民感受;《兵車行》《悲陳陶》《悲清坂》《哀王孫》諸章,即事名篇,為時事而作,卻處處流淌著杜甫仁俠情懷的憂患與呻吟,詩人高大的人格形象展現了無畏的史官文化精神,賦予了詩篇深沉的歷史感。而對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歷史危機的體察與揭露,仁俠情懷的杜甫顯示了強大的俠義人格力量。
杜甫俠義文化人格給予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以無比深厚的人格力量,成就了詩歌創作的高尚詩格,提升了詩史的社會歷史價值,彰顯了詩圣的文化人格精神,昭示了儒與俠互補、道與義共生、詩與史融合的詩學價值。這種獨特的詩學價值在內容、藝術和審美等詩學內涵特征上表現為無比深邃的現實深刻性、高度凝練的藝術典型性、至情至真的審美形象性。其關注現實的精神風貌、沉郁頓挫的審美特征、詩史相融的詩體貢獻,不但使杜詩情感深沉、文氣沛然,而且也為杜詩詩學增添了彪炳詩史的審美價值。
仇兆鰲《杜詩詳注》說:“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詩史,謂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圣,為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13]1宋人和明人以“史”和“圣”的定位評價,直指其現實主義詩歌俠義文化人格價值的外觀和內蘊,它使杜甫的詩思表現出詩的史化和史的詩化在“詩史”思維下異質同構的統一性,這種存在著杜甫俠義文化人格的文化基因,賦予其現實主義詩歌創作史的厚實沉重和詩的藝術沉痛,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嚴肅感、崇高感和悲壯情調。建立在儒家仁義基礎上的俠義文化人格,與杜甫的人生軌跡相伴,使杜甫詩歌在表現宇宙人生等重大現實題材時,無不透露出其俠義人格的詩性感覺對時代變化的核聚變式的反應,其轉益多師、創新創變的曠代才情與堅定、獨立的凜然俠氣,在其人格層面展示了詩史內涵的博大精深、詩史精神的正義宣化和詩史藝術的審美力量,使得杜甫詩歌的現實昭示性早已穿越歷史空間,放射出時代的思想光芒。
杜甫的俠義文化人格,使其現實主義詩歌創作充滿著憂時傷世、悲己哀國的歷史憂郁感和現實崇高感,賦予了沉郁頓挫藝術風格深沉的歷史意識、崇高的藝術精神和強大的人格力量,它對于杜詩風格的鑄塑和唐詩魅力宣揚無疑是一種典范。他的現實主義巨篇充滿自傳性的生命體驗,凝結著志士的悲慨、仁者的胸懷和俠者的大義,形成了杜詩“沉郁頓挫”風格崇高剛健的藝術風骨、深沉凝重的藝術氣度和慷慨悲壯的審美力量。也使現實主義詩歌創作參與了生命力的永恒建構,更使其人格走向了永恒,并成為中國詩歌之高峰、文化之高峰、人格之高峰。
杜甫的俠義文化人格是全面認識詩人及其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不可或缺的文化視角。時代任俠風氣、儒家仁義傳統、任俠家風以及剛正不阿的個性,形成了杜甫崇尚俠義、歌詠游俠的精神力量,也成就了他書氣與俠義相融、儒與俠互補的文化人格。杜甫對俠的清醒認識、選擇接受和辯證宣揚,提升了俠義人格,充滿強烈的人文關懷,使俠超越了個人名利而上升到國家民眾的高度,使俠和俠文化超越了狹隘的快意恩仇的個人空間,成為對國家、社會、個人都能產生積極影響的精神力量,也成就了俠骨仁心的詩圣。在文化學和人格學上給予中國現代人文精神的建構以巨大的文化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