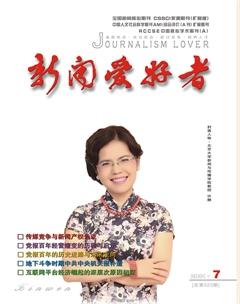媒體融合創新的文化范式與實踐路徑
劉運來 曹乾源
【關鍵詞】媒體融合;新聞編輯部;創新學習文化
自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媒體融合已經邁過“七年之癢”的關鍵時期。七年中,各類型傳統媒體根據實際情況積極探索著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范式和路徑,其中尤以技術范式最為普遍。基于技術升級改造的“中央廚房”“新聞島”“媒體云”等改革,引領了新聞編輯部迭代升級的新趨勢。伴隨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在新聞業中的應用,先進技術依然會成為媒體融合的重要驅動。也正因為新傳播技術的強大形塑能力,使得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技術革新范式,而忽略了對新聞編輯部創新學習文化的洞察。從而使得傳統媒體在融合轉型中,記者編輯群體缺乏對新聞業數字化內涵的理解,表層的技術和設備的投入上極易形成“姿態性融合”的怪圈。正如學者何瑛和胡翼青在對“中央廚房”的反思中指出,中央廚房式的“轉型”使新聞生產流程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聞的“工業屬性”得到了強化。但與此同時,新聞的“文化屬性”被削弱。這種轉型實際上是困境下的“現實選擇”。[1]
一、媒體融合創新進程中的范式困境
從早期的“報網并存”“報網互動”“報網融合”到近些年的“兩微一端”或“全媒體”,傳統媒體融合轉型的技術范式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取得與同時期的數字新媒體相抗衡的發展水平。在中國,處于傳統媒體大多數的“腰部媒體”在融合轉型中慣例性引進的大屏幕、云上采編系統等只是一種“姿態性融合”。那種提出“媒體融合,決勝大屏”[2]的觀念,只會讓傳統媒體的資源投入壓力日趨加重。因此傳統媒體在融合轉型中尋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并希望保持與受眾的相關性,那么他們還應該融入數字文化。這就意味著,傳統媒體融合轉型創新要走出技術范式的迷思,要從介質的數字化到文化的數字化。如果融合轉型中的媒體只有技術要素,那么就很難建立一種數字新聞生態,一種包含社會、文化與價值的有機系統。
因此,媒體融合轉型創新的范式應在技術的中觀層面開始向編輯部微觀層面的文化轉向,即編輯部創新學習文化的建構與實踐。究其原因,在媒體融合的浪潮中,技術范式優先的理念,遮蔽了創新文化學習的可能。尤其是在對從業者賦予全媒體復合人才的職業話語下,編輯部的文化創新與學習往往成為盲區。這種盲區的結果就是,一部分傳統媒體在融合中出現了“錯位”,即不僅把把關人的權力讓渡給了數字平臺的生存法則和算法機制,而且內卷化為數字平臺的內容勞工。
二、媒體融合進程中創新學習文化范式的提出
隨著技術要素的引入,新聞編輯部將在專業背景、性別、年齡、技術等層面出現更大的分化。在新聞生產的流程與編輯部崗位的權力分配中,技術成為重要變量。在這場重新結構化的編輯部改革創新行動中,如何讓編輯、記者、技術設計、工程師等協同工作,更好地實現“做更好的報道,講好中國故事”?這就需要在編輯部培育創新的活力與文化,并以良好的機制保障內部群體能夠認同這種創新文化,從而驅動編輯記者主動學習和實踐。對此,荷蘭溫德斯海姆應用科技大學媒體研究中心的奧內拉·波庫(Ornella?Porcu)教授在2017年提出了新聞編輯部的創新學習文化理論(Innovative?Learning?Culture簡稱ILC),并將其定義為:一種社會氛圍,它激勵人們一起工作和學習,將個人的成長與團隊、組織的成長相聯系,并鼓勵組織為人們提供靈活性、實驗性、創造性和探索激進可能性所需的自主權。在開放的領導、溝通與相互信任下,為了內部共同的目標協同發展,在開放溝通和相互信任下將階段性的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相結合。[3]
奧內拉·波庫認為文化對新聞編輯部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凝聚共識、團結協作、創新發展和形成身份認同的關鍵力量。這種力量與作為客觀工作環境的技術要素不同,它能夠深入到編輯部成員價值和意識層面。在更大的數字化背景下,傳統媒體實現更大程度上的徹底變革,需要媒體組織逃離他們長期依賴體制而形成的“舒適區”。這就意味著,僅僅投資大屏幕、開通云上系統并不能徹底地改變,也不足以保證新聞機構未來的良性發展。然而,學習與創新作為內部產生的新穎元素,可以被視為新聞編輯部變革的一部分,它具有更強的創造性、多樣化的生產力和更強的包容性。創新學習文化對于新聞編輯部來說,能夠賦予組織更強的彈性生存能力以應對外部的威脅。這種文化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組織文化,而不是技術。尤其是針對編輯部內部的內卷化、冷漠化問題,創新學習文化能夠激發編輯記者“跳出框架”,以實驗和學習的方式觸發和培養新穎和創新的想法。作為一種組織氛圍,創新學習文化賦予了整個新聞編輯部變革性的品質和創造性的潛力。
創新學習文化范式提出的另一個價值在于,它以一個新的視角來分析編輯部個體的探索性創新是如何觸發和培育的,可以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在新聞編輯部各種場域力量的影響下,個體如何超越日常工作慣例探索自身的創造能力。崇尚“有機”運轉的傳統報紙編輯文化,在新媒介技術的驅動下轉向為“原子化”的新型精英文化,激活優秀人才的鲇魚效應。[4]因此,面對傳統臃腫僵化的組織結構,創新學習文化范式更提倡以內部變革為導向,以更大的包容性激活和釋放個體的創新能力。當然,傳統媒體新聞編輯部融合轉型的創新學習文化范式在新聞業融合實踐中遭受到的障礙會比政治、經濟與技術的范式更大。
三、媒體融合進程中創新學習文化范式的多維內涵
要理解創新學習文化的內涵,就需要了解與之相關的概念:學習文化、探索創新和文化沖突。
針對新聞編輯部,我們將學習文化具體理解為以下幾個層面。首先作為編輯部員工要重視在工作場所中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如應用于新聞采寫制作、分發、互動的新媒體技術。其次,編輯部應建立一種機制用以激勵員工尋找自我導向的學習機會,如編輯部的組會、頭腦風暴、專業講座,以及外部的參觀、學習與體驗。最后,編輯部制定長短期相結合的目標以及提供相應的資源,鼓勵員工協同參與目標的完成,并在經驗與知識的分享中產生共鳴。學習文化不僅可以驗證知識獲取并預測編輯部員工在工作場所應用知識的能力,還可以激發員工的內在動力和主人翁意識。它使得媒介組織在完成自身升級迭代的同時,在外部的競爭環境中取得優勢。此外,學習文化強調的是編輯部集體的、動態的具有規范性的集體學習文化,而不是個人學習文化。對于新聞編輯部來說,只有集體學習才能調動更多員工的積極性,確保更多員工的參與。
探索創新在創新學習文化中至關重要。它反映了創新者利用已有的條件探索新的可能性。其特點表現為檢索、冒險、試驗、發現、靈活性。在新聞編輯部,探索創新可以轉化為發現和試驗接觸受眾的新方法、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和使用可能帶來新商機的技術工具。和其他行業一樣,在媒體組織中探索性創新也不是完全激進、冒險和毫無程序可言的。探索性創新并不意味著打破與顛覆,它是漸進式的,所涉及的創新領域也是較小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會從根本上挑戰已有的市場邏輯和制度紅線。當媒體融合轉型成為中國媒體不得不面臨的重要議題時,培養和激活從業者探索創新,成為融合創新中的關鍵課題。
新聞編輯部的文化沖突是轉型導致的。其表現為以下幾方面:一是模式轉變的沖突,面對互聯網的沖擊,新聞編輯部被迫在經濟上將20世紀以新聞產品供應為中心的生產模式轉變為21世紀以用戶需求為中心的分發與營銷模式。模式的轉變,使得編輯部成員賴以生存和自豪的傳統新聞業的操作系統逐漸失去了“魅力”。因此,伴隨恐懼和焦慮的增加,新聞編輯部的沖突就開始涌現。第二種也是最大的文化沖突發生在媒體組織管理層和編輯部員工之間。眾多的媒體融合實踐表明,管理層和編輯部之間對轉型發展的看法通常是不盡相同的。二者之間的沖突,既是媒體經營與新聞生產之間的“鴻溝”,也是媒體決策層與編輯部員工目標的差異而產生的隔閡。文化沖突的結果便是掣肘的融合轉型的實際成效。盡管技術的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沖突的痕跡,提升融合的信心,但當媒體組織各層次就轉型的理念、價值、操作規范、經營模式、創新機制與職業認同等方面不相容時,轉型就被認為是消極的。編輯記者本身并不反對變革和創新,他們也能夠接受新事物。但當缺乏學習氛圍、缺乏創新機制和對創新者的激勵與保護時,他們往往拒絕革新,即使他們渴望學習。
上述三個維度既是傳統媒體新聞編輯融合發展的制約因素,也是創新學習文化范式在推進融合走向深入要解決的問題。創新學習文化作為對技術革新范式的進一步補充,它專注新聞編輯部的學習和創新過程,并將二者傾注到編輯部新聞生產的整個流程。它在革新編輯部的種種桎梏過程中,從一個想法開始,到為這個想法提供發展的空間,它鼓勵編輯部員工學習、試驗、敢于試錯和敢于堅持自我。
四、媒體融合進程中創新學習文化范式的實踐路徑
第一,建設組織創新文化。創新是組織對外部環境經驗觀察的回應,當遭遇到外部的挑戰因素時,就會進行組織結構和管理層面的調整與改革,即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感知和應對外界的破壞。那么,這種回應考量的是組織的效能。有效的回應,則可以避免被外部變革的環境破壞或淘汰。一些大型媒體機構往往通過成立中央廚房、內部創業小組、孵化器或投資基金的方式,鼓勵媒體人進行內部創新創業。
第二,培養創新與學習中的學徒制。我國新聞業的歷史實踐發展過程中,通過“學徒制”培養記者的傳統由來已久。伴隨著媒體融合轉型發展,走在改革前沿的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于2016年率先探索推出了“指導老師制”。結對的師徒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工作室”,成為一個個有創意的單元,進一步激活了媒體深度融合和創新的活力。自“指導老師制”實施以來,浙報集團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有個性的骨干人才,在微信公眾號和新聞App上大放光彩。
浙報集團的師徒制實踐,不僅是為了適應媒體深度融合的需要,更是培養一種團結、創新和自我超越的文化。在師徒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既有利于新聞理想的傳承,也在編輯部種下了尊師重教的種子。和新聞傳播教育領域提倡的“雙師制”不同,新聞編輯部開展的學徒制根植于媒體的組織文化對接媒體發展的前沿需要,它注重的是員工在實踐中協同成長以及師傅自身的示范效應。
對于傳統新聞業融合轉型來說,更糟糕的事還在后面。自動化的信息搜集和分類推送,“機器人寫新聞”也從神話變成了現實。數字化與數據化,正在成為未來新聞業的技術支撐,并深層次地形塑著受眾賴以生存的媒介文化。如果未來不想被算法和機器人所替代,那就需要提前開始謀劃。因此,從選題、內容生產、制作、發布流程與軟件系統的應用,各個環節都需要更加密切的協作。基于此,主流的傳統媒體編輯部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那就是在已有板塊資源下優選出新的團隊孵化新的項目,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俠客島、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的底稿以及財新傳媒的數據新聞團隊等。這些團隊或工作坊的建立,不僅讓創新項目得以持續發展,而且提升了對項目的認同度。
五、結語
一切競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來源于文化的競爭。在媒體融合創新的內容范式和技術范式主導下,更多的傳統媒體要想走出發展的泥淖需要敢于“跳出框架”,主動向創業自媒體學習。這種學習的目的在于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探索發展的新的可能性。理解這種新就取決于新聞機構的創新、學習和具有活力的文化氛圍。但是較之于內容與技術創新的可量化而言,文化作為價值和觀念,是一種復雜而無形的問題,不易衡量。尤其作為文化創新,其遠期目標又往往難以得到管理層的認同。因此,我們也會發現融合轉型中傳統媒體新聞編輯部的學習和創新較為缺乏。不僅缺乏對創新概念的認識和創新的動力,更缺乏觸發和培育學習與創新文化的環境。在新聞業發展的歷程中,從來沒有遭遇到今日的巨大變革。如果傳統媒體還沉溺在過去的職業榮譽、社會地位、資源壟斷和權威性的“舒適區”而不自省的話,那面臨沖擊的不僅是自身的專業主義,還包括行業的尊嚴。如果將技術的迭代作為迎接這種環境改變的重要手段而忽略范式的革新,最終難以在激蕩的變革中形成自己的媒體文化和生態系統。
[本文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培育項目“新時代鄉村文化價值耦合及傳播網絡構建研究”(項目編號:31511912109)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白紅義,張恬,李拓.中國數字新聞研究的議題、理論與方法[J].新聞與寫作,2021(1).
[2]文之強.媒體融合,決勝大屏[J].傳媒,2017(5).
[3]Porcu,O.2017.“Exploring?Innovative?Learning?Culture?in?the?Newsroom.”Journalism,doi:10.1177/1464884917724596.
[4]常江.導演新聞:浸入式新聞與全球主流編輯理念轉型[J].編輯之友,2018(3).
(作者單位:劉運來,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曹乾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編校:鄭?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