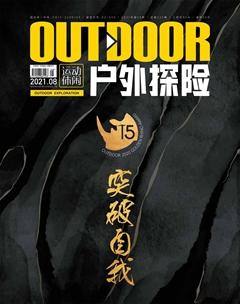最佳戶外影片

《跨越雅魯藏布》導演手記
撰文:張也
編輯:SINGING
跨越團隊: 張亮 賴張?盧鋒華 羅夢禪
攝影師: 曹希佳 王晨臣?張凱 張曉澤
提名理由
綿延的岡底斯山和喜馬拉雅山之間,形成了平均海拔約4000米的大河,世界第一大峽谷雅魯藏布。10年來,扁帶選手張亮和朋友一直夢想著走扁帶跨越雅魯藏布,但當他們終于成行并抵達這里,雅魯藏布卻在全球氣候變暖、冰川消融的影響下出現了嚴重的堰塞湖災害。導演張也詳細地研究了災害的原因,并帶領大家再次回到雅魯藏布。
影片記錄了人類通過團隊首次用扁帶跨越雅魯藏布的過程,也融入了他們對環境問題的思考,為傳統的山地戶外紀錄片,添加了新的意義。
2006年夏天,我第一次來到雅魯藏布大峽谷。當時大峽谷還沒有修建景區,派鄉還只是一個向墨脫縣輸送物資的轉運站。當地老鄉講,在雨季,神山南迦巴瓦難得一見,讓我別抱有太大的期待。那年,我拍到了南迦巴瓦的日出日落,月光下圣潔的長矛戰神,并一路走進那個中國唯一沒有修通公路的縣城。從此便對雅魯藏布留下了難以割舍的情結。
由于對自然和戶外運動的熱愛,身邊慢慢結下了不少同好的朋友。2010~2011年左右,我在國外網站上看到了走扁帶這項運動,順藤摸瓜地查到了張亮,他似乎是我在北京唯一能接觸扁帶運動的途徑。從那個夏天開始,我們將大把的時間揮灑在了天壇附近的公園里,身邊的小伙伴也越來越多。
后來張亮搬到了上海,我也就離扁帶越來越遠,幾個朋友散落在全國各地。
直到2016年,紅牛邀請他做虎跳峽的行走,我又剛好在做“班夫山地電影節”的巡展,大家又重新激起關于扁帶的暢想。我們想要一起去大自然里,完成一些扁帶的跨越挑戰,“雅魯藏布”第一時間跳脫出來。
2018年秋天,我終于找到機會,約著張亮一起去大峽谷進行了前期的勘查。雅魯藏布大峽谷是世界上最長,也是垂直落差最高的大峽谷。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個相對落差大、背景壯闊、但跨度適中的場地。但實際上大峽谷要么就是跨度超過500米甚至1公里的廣闊江面,要么就是兩岸稀疏的灌木和松散的砂石,一路從峽谷入口,到公路盡頭,都沒有安全理想的搭建地點。我們只好硬著頭皮,跨過加拉村的吊橋,徒步繼續往里探尋。
在江對岸沒走多遠,有一處小廟,走近便聽到廟堂之中眾僧人的誦經聲。出于禮貌,我們并沒有進入,而是坐在門口靠墻休息。當時那個地方特別的氣場,讓我們急躁的心一下子安靜下來。一位女僧人送來酥油茶,并告知我們再往里即使徒步也很難進入,張亮很釋然地跟我講沒關系,他感覺一定能發現更好的地方。

回程的路上,我們發現水泥橋邊有個岔路口,來時的那側路程短,但另一側貼江更近。峽谷里起了風,天上的云層逐漸散去,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壘難得一起短暫現身。我們剛剛沿著新路開了幾分鐘,便發現一處江水急轉的峽灣處,兩岸佇立著完整的大巖壁。簡直不會有更完美的場地了!望遠鏡觀察、測距、無人機拍攝大環境,再下到巖壁的凸起端查看巖質,我們在1個小時內就確定了搭建方案。夕陽時偶遇了一位舊友,我們把酒言歡,欣賞神山落日,第二天在宿醉中回到城市。
由于大峽谷氣候的特殊性,我們回家后馬上制定了活動和拍攝計劃,希望順利地完成人類首次扁帶跨越雅魯藏布江及大峽谷的挑戰。約好了賴張、鋒華、羅夢禪等幾位朋友,訂好了機票只待出征。為了保證活動的順利進行,我還特意飛了趟拉薩,跟景區和相關部門做好了活動報備。
10月17日,雅江突發泥石流,沿岸山體疏松的砂石和碎塌陷的冰川一起堵在雅江河道,下游居民安危告急,我們一下緊張起來。一方面擔心準備很久的活動還能否完成,更重要的是擔心峽谷深處的居民和那間不知名的廟堂。好在兩天后,堰塞湖開始自然疏解,隱患排除,新聞報道無人員傷亡。
與景區溝通后,我們也按計劃準備著行程。
出發的前一天,雅江再次發生了泥石流災害,二次形成的堰塞湖更加危急。那時我們比災害前更著急,想趕緊回到大峽谷,看看當地到底情況如何。大家商量后,都沒有退縮,決定一起前往災區,看看能做些什么。
落地后,越野車把我們送到索松村,一路上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喧囂。不等景區的工作人員到來,我們就自己向峽谷深處走去,車不讓進,我們就徒步往里走,但武警早已封鎖了峽谷,我們無法入內。好心的武警人員跟我們轉述了峽谷內部的情況,村民都已經安全轉移出來,但兩側山地和公路全部毀壞,進入過于危險,為了安全進行了封鎖。我們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但在峽谷深處好不容易找到的跨越地點,肯定是無法接近了。帶著遺憾,我們在索松村口嘗試搭建了一條線路,背景的南迦巴瓦和雅江十分震撼,但很遺憾的是,僅有張亮完成了這條線路,因為在搭建完成不久,民警就來到現場,把我們帶到了派出所。目標沒有完成,惦記的人和地方沒有見到,還被抓進去了,2018年,我們就這樣狼狽地離開了雅魯藏布。
回到北京后,我找到研究地質和冰川的朋友,了解到這次的災害并不完全是一場意外。全球氣候變暖不僅使兩極的冰川融化,也影響著內陸冰川。發生在雅江的災害,正是因為冰川消融導致崩塌,連同泥石一起墜落,形成了堵塞。而氣候變暖這件事情,其實是與每個遠離大峽谷的城市人息息相關的。正是因為我們過度的能源消耗、超額的碳排放,加劇了氣候變暖,影響到了全球的生態以及生活在大峽谷友善的村民。
這場災害好像冥冥中賦予了我們更多的責任,讓我們的跨越挑戰,有了實際的意義。所以我提出,希望再次回到大峽谷,通過首次扁帶跨越雅魯藏布的事件,引起更多城市人對于大峽谷、對于氣候變化的關注。大峽谷景區表示非常支持,扁帶和拍攝團隊也全員歸隊。2019年春天,大峽谷幾千棵古桃樹枝頭滿粉的時候,我們又回來了。
雅江兩岸仍舊破碎,洪水沖毀的大橋、樹木散落江岸,洪峰水位線以下的江岸滿目瘡痍,與完好蔥郁的原始林形成鮮明對比。進入峽谷后,我們第一時間申請了特殊許可,趕往加拉村深處的廟宇。加拉村是當時堰塞湖災情的核心區,新聞里并沒有關于寺廟的信息,我們十分擔心廟宇和僧人們的狀況。一路經歷了塌方、落石、斷橋、陷車,沿著臨時開出的沿江路繞了半天的時間。爬過一片坍塌的泥土,我們總算見到了寺廟,聽到了熟悉的誦經聲,我們的心也再一次安寧下來。
幾經磨難,我們終于開始了跨越挑戰。這個特別的架設地點,剛好位于兩座7000米雪山之間,雅江在此突然收窄,在雪峰間刻劃出一條牦牛角形狀的大拐彎,這也就是世界上最長峽谷的最深區域。扁帶線路跨度166米,距離江面60米高,對于團隊來說在能力范圍之內。但在這么復雜的自然環境里,光是架設就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留給我們完成線路的時間只有4天。
第二天,面對大風和多變的氣象,大家都拼盡全力地去嘗試,一次次的沖墜并沒有換來跨越的成功,突降的雷雪夾雜著冰雹終止了我們當天的行走。第三天更是降雪不斷,整片山都換成了冬裝,僅有坡間粉紅的桃花提醒我們,此時正值春季。大家去架設點看了一下,就被勸回了酒店,沉悶地窩了一天。晚飯后,夜空繁星初現,我們一起去南迦巴瓦的面前仰望銀河,朝拜神山。倒數第二天,陽光回到山谷,也帶來了不穩定的峽谷風。張亮和賴張幾次嘗試后,頂著大風走到了江的對岸,我們終于完成了心中的目標。
線路的盡頭并不是終點,我們非常享受雅魯藏布的美好,希望通過影像分享給更多朋友,也希望大家一起關注生態環境,阻止氣候變暖進一步發展,讓雅魯藏布永遠美好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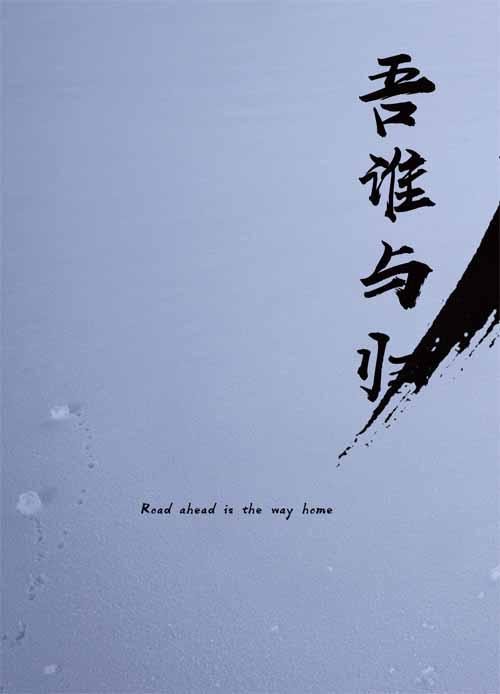
微斯人,吾誰與歸
提名理由
2019年6月,昊昕、Stanley、Ken三位年輕的中國阿式攀登者,出發前往巴基斯坦喀喇昆侖山脈。他們的目標是一座6000米級別的尖塔未登峰,位于Liligo冰川末端的群山深處。阿式攀登在中國成為一種熱衷的攀登方式不過短短十多年,但它正在吸引著一批新生代攀登者。
短片記錄了一群年輕人,他們因對阿式攀登的熱愛成為志同道合的伙伴,創造了許多精彩的攀登,共享其中歡樂和痛苦的交織。山中時光雖短,但彼此交付的所有瞬間永遠珍貴。
認識昊昕的時候,阿左還在成都領攀登山培訓學校工作。
那是2014年,在領攀學校的一個培訓中,他們第一次互相認識。那時的昊昕還在蔓峰探險帶隊,他們還不太熟識,也還不知道,今后他們將會完成如何偉大的事業。
2015年起,阿左和昊昕開始搭檔在各地進行一些攀登——去宜賓攀巖,在雙橋溝攀冰……他們喜歡去攀登一些新鮮、漂亮的線路。
大雪塘三峰,坐落于邛崍山系的南端,遠遠看去,其山脊平緩而綿延,但北壁卻如刀劈斧砍般陡峭。2016年1月,阿左和昊昕搭檔,用5天時間完成了北壁的野生動物園線路,線路難度:D/VI/M4+/雪坡60度/1100米。

完成了野生動物園之后,阿左和昊昕真正熟絡起來,感覺彼此之間可以成為很好的搭檔,完成更多的攀登。
幺妹峰,在中國的攀登界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好像是一塊試金石,凡是完成過幺妹峰攀登的登山者,毫無例外都能一戰成名,躋身頂尖登山者的行列。2016年完成了幺妹峰攀登之后,古古建議阿左和昊昕也去嘗試一下幺妹峰。
2017年9月從領攀學校離職后,阿左也有了更充分的時間來做這件事。
2017年11月10日中午時分,阿左和昊昕站在了幺妹峰的頂峰,一戰成名。
2018年1月的雙橋溝,阿左又一次回到這個地方練習攀冰。一名香港朋友Halu帶來了一個朋友,他就是Stanley。
來自香港的Stanley一直在法國的Chamounix生活,這座位于勃朗峰腳下的小鎮在世界各地的攀登者和滑雪者心中擁有著崇高的地位。背靠阿爾卑斯群山,Chamounix
可以快速到達許多非常著名的攀登路線,這使之成為了攀登愛好者的天堂。
在這里接觸攀登,Stanley很快便完成了大量的技術型攀登。來到雙橋溝攀冰的時候,Stanley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攀登者。攀登理念的相似,讓Stanley與阿左、昊昕很快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同樣成為了好友的,還有香港的攀登者Ken。
經過幺妹峰的洗禮后,阿左和昊昕看到了自己在攀登能力和技術上的不足,帶著學習的想法和計劃,他們去了Chamounix小鎮。在阿左的記憶中,那是他們在過去的幾年中最開心的一段時光,他們在Chamounix完成了很多攀登路線,也認識了很厲害的老師Yannick 和Helias。
去喀喇昆侖登山,其實一開始是Stanley和Ken的計劃。喀喇昆侖山脈的龐大、偏僻和神秘吸引了Stanley的注意力,于是他買來地圖研究這片山域,尋找可能的攀登。

一座外形獨特漂亮的尖峰抓住了Stanley的目光,百般搜索卻找不到關于這座山峰的資料。這可能是一次首登,會是一個蠻有趣的項目,Stanley心想。
慢慢的,昊昕也對這個項目產生了一些興趣,就這樣,昊昕也加入了這次計劃。
2019年6月4日,在看了3個月地圖后,他們終于來到了這座山的腳下,在冰川上建立了大本營。在4條山脊交匯之處,那座尖峰拔地而起,大家都驚嘆于它的美麗。
6月14日,天仍未亮之時,Stanley和昊昕正式出發開始攀登,留守前進營地的Ken用鏡頭記錄下了這個瞬間,黑暗之中,昊昕背著碩大的背包,掛著一捆繩子,手里拿著冰鎬,一步一步地從鏡頭前走過,進入了黑暗之中。誰又能想到,這會是他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攀登。
在ABC留守的第三天,Ken用相機拍下了一段獨白,今天是Stanley和昊昕原定計劃中沖頂歸來的日子。前一天還能看到二人的位置,現在已經消失在了視野中。Ken做不了別的什么,只有在營地等待,雖然很信任二人的經驗和能力,但他仍然很擔心。
幾天前,Stanley在大本營的時候曾說,他覺得應該害怕的是雪崩。但他可能沒有想過,自己的擔心會成為現實。
逾期兩天后,Ken呼叫了巴基斯坦軍方的直升機救援,最終在線路的下方發現了二人的遺體。6月的雪崩風險還很高,救援實施困難,當8月他們再回到這里時,遺體已經被新雪覆蓋。大家手里拿著探桿,在兩個月前發現二人的地方,一邊走,一邊探測厚厚的積雪。
兩天后,大家在厚厚的雪層下,找到了遺體。
在山下,阿左哭了。昊昕,這個曾一起完成了大雪塘,一起站在幺妹峰之巔,一起四海攀巖的好搭檔,永遠地離開了。“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地方”,阿左看著遠方的群山說。
“這個地方,我不會想再來。”Ken也如是說道。
阿左在影片的最后寫道:想念你們,昊昕,Stanley。

做一件藝術的事
撰文:在遠方的阿倫
編輯:文森
導演:在遠方的阿倫
攝影:在遠方的阿倫
提名理由
《點亮的地平線》是阿倫在自駕游歷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時所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在這短短的十幾天旅途里,他一個人到達了曾經與世隔絕的扎尕那村,并沿著洛克之路穿越探索了迭山西部少有外人知曉的古冰川遺址。
時過境遷,在這個信息發達的當代,無數曾經因為山高谷深而難以被涉足的原始秘境,已經有了走出山外被眾人所知的全新方式和契機;而地理上的地平線,或許依舊會被高山深谷所折服,但是探索發現以及向外傳播的動力和精神,會在當代持續不斷地去點亮那些曾經人類難以到達的遠方和旅途。
在這短短的十幾天旅途里,一個人到達曾經與世隔絕的扎尕那村,并沿著洛克之路穿越探索了迭山西部、少有外人知曉的古冰川遺址。在路上還遇到了一個戶外徒步主播“迷戀哥”——這個回族的穆斯林不顧全家的反對,正拉著自己的徒步車,從甘南走向青藏——這是我在路上遇到的,最拉風的男人。
為自己做一件藝術的事
從幼兒園開始,我就學習畫畫,也半吊子地學過電子琴;小時候喜歡看科幻雜志,所以作文也一直寫得還不錯;大學在四川美術學院學習工業設計,成績還算讓家人順心,但寫東西的時間越來越少,于是就組樂隊玩攝影,把文字轉化成原創歌曲和攝影照片。總之,似乎從小就開始“不務正業”。
畢業后,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名工業設計師,民企、國企、500強都待過,在我最后服務的creativeconsulting公司里,學到了特別不同的東西。簡單地說,是設計調查、設計研究和設計策略——一個多學科融合的設計思考過程。
在那里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錯,不過加班到凌晨2點是常有的事情。但在工作中學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方法和思維觀點:以人,作為思考角度來設計生活方式與產品體驗。
在我三十而立的那一年,我終于開始以個人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突然發現再繼續這么孜孜不倦,我就沒機會再走出去,為自己干一件特別藝術的事情了。就這樣,我辭掉了工作,開啟了認知圍城之外的旅途。
阿倫作品
在這段21000公里的旅途里,我最遠僅到達了拉薩,但遇到了諸多事情,不斷地刷新著我的三觀。我走到一半才發覺,也許應該悉心記錄下來,就像……去趕個集,一定要帶回些鎮上的稀奇玩意兒回村給家人一樣。
2015年還是圖文的時代,旅行結束回到上海后,我花了漫長的時間記錄下了這3個月的旅途,并以圖文游記的形式在各個旅行社區周更“環游中國”這個系列,這一更就是25章、幾十萬字和上萬張圖片。
其實2015年當我繞了中國小半圈,到達敦煌的時候,又開始盤算著去新疆,但最后我放棄了。那時我是裸辭出來旅行的。在此期間待業的所有開銷都要錢,萬一路上遇到不測,出個事情進個醫院……那時候就覺得,自己離娶媳婦可能就越來越遠了。

在《點亮的地平線》里,在遇到“網絡主播迷戀哥”之前的那個段落,就伏筆和獨白過這么一句話來描述當代的自媒體從業者——“可能,沒有絕對的純粹,但也沒有絕對的繁復”。所以等待了兩年后,有了品牌的贊助,2017年第二季“環游中國”,我就沿著新藏線穿過昆侖去了新疆。
2015年和2017年這兩次獨自駕車環游中國,每次旅途后,我都會花超過半年的時間去整理路上的所見所聞。表面上,這些人文風景和紀實故事被大家津津樂道,并以追劇的心理來進行閱讀,但其實可以窺見讀者都有一個飛躍圍城、馳騁遠方的愿景。所以無論是曾經的游記還是現在制作的旅行紀錄片,最重要的都是觀察分析——讓感性和理性相互作用,調和成我最想與你分享的遠方,和“阿倫作品”。
圍城隨筆
伴隨著成長,我們的物欲增強,開銷增多,工作變忙,時間減少,下一個“不切實際的決定”所需要的勇氣和成本越來越大。對于大部分人來說,環游中國變得越來越難,對于我自己來說,我想通過一次漫長的游歷來向讀者揭示,這圍城之外你未曾察覺過、不曾關心過的大世界和小人物——旅行只是個容器,容器里都是對大世界和小人物的好奇、關心和探索。
“圍城隨筆”系列紀錄片的預告片于2016年年末進行推送,不同于“環游中國”,它并不以一次長線旅程來作為敘述的主要線索,而是以一個具體的省市、地理坐標或是景觀、路線等作為記錄對象。這樣一來,從時間、難度以及成本上,觀眾和讀者都可以親自前往。“圍城隨筆”雖沒有環游中國那樣的雄心壯志,但它一定會成為觀眾和讀者的下一個目的地。
點亮的地平線
1933年,有本叫做《消失的地平線》的小說在西方引起狂熱的追捧,有無數的背包客前往云南尋找“地平線的盡頭”以及書中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而小說作者的靈感來源,其實來自西方探險家約瑟夫·洛克在中國云南的一系列探險故事。
本片的名字《點亮的地平線》,除了在向當年和如今的戶外探險家們致敬之外,還是在表達:在時過境遷信息發達的當代,無數曾經因為山高谷深而難以被涉足的原始秘境,已經有了走出山外被眾人所知的全新方式和契機;而地理上的地平線,或許依舊會被高山深谷所折服,但是探索發現以及向外傳播的動力和精神,會在當代持續不斷地去點亮那些曾經人類難以到達的遠方和旅途。
在《點亮的地平線》最后段落,我旁白中的“骨頭”和“刺”既代表年少輕狂時的初衷、夢想和動力,也代表人在江湖中的世故、遺憾和妥協。任何人都無法脫離“舍去”和“得到“,即便是在片中縱橫馳騁,享受美景的我,片后在剪輯制作時那些無數個難熬的日與夜,是觀眾甚至摯友都無法感知的。
所以前者的“得到”,是因為后者的“舍去”,自然我為此犧牲和付出了很多東西,既有幕后的私人時間,也有片中還未抵達過的遠方。
“這是觀眾茶余飯后,手指匆匆劃過的閑余時間;但卻是媒體人加班熬夜,風雪夜歸所付出的所有時光。”——我在微博大概說過這句話。

一個孩子的別樣成長人生
撰文:徐承華
編輯:SINGING
導演:徐承華
攝影:王振 汗斯 劉曉 呂孝波 樓梁
提名理由
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和親子陪伴的理念下,8歲的男孩辛巴攀登海拔5396 米的哈巴雪山、挑戰漂流川西大河、參加理塘賽馬節、拍攝野生動物、保護珍稀植物,在旅途中遇到的探險家、攝影師、植物學者、藏族孩子、畫家,都成了辛巴的朋友和老師。
經歷放棄與堅持、挑戰與困境、父子間沖突矛盾,辛巴逐漸成為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內心強大、懂得愛與尊重的孩子。影片由辛巴的爸爸老極擔任導演,從父親的角度進行拍攝,在注重素質培養的今天,展現了戶外對兒童的教育意義。
我是老極(徐承華),有孩子之前曾旅居西藏兩年,進疆多次,登過山、漂過流、也騎過馬。有了孩子小辛巴之后,我就想用戶外運動的方式教育他,用熱愛用自然去培養一個戶二代。兩歲半時,他說想去看北極熊,我們一家人騎著三輪摩托跨越12個國家,到達了北極。5歲的時候,我們穿越了南美洲,用時146天到達了南極。
2020年7月初,我們來到哈巴雪山腳下,徒步到大本營,經過適應性拉練的一天,在第三日正式沖頂。沒想到先是下起了小雨,接著在海拔4900多米的地方起了大霧,氣溫驟降。
這種環境的惡劣變化讓辛巴吃盡了苦頭。在雪線旁,我問辛巴,現在有兩條路,一是下撤,可以很快回到溫暖中。二是繼續慢慢往上走,繼續挑戰。沒想到的是他默默無語地用手指著山頂,然后一步步沖頂成功。從海拔4000米的大本營,歷時7小時15分登頂,這對于一個8歲孩子來說,太不容易了。
每一刻都是毅力、勇氣、堅持和實踐夢想的不易。
到了川西藏區力丘河畔,從5歲就開始訓練劃船的他準備單人單艇挑戰激流大河,爵士冰和我作為向導進行陪伴和保護。150公里的巨浪大河,冰雹的惡劣天氣,這時候卷過來一個三級大浪,一下落水翻了船。救他上來,我問他什么是勇敢?辛巴說: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后還會堅持去做。
辛巴的師父奚志農是一位野生動物攝影師,曾經六進白馬雪山將滇金絲猴展現在大眾面前,首次報道藏羚羊被偷獵的真相。辛巴一直覺得他師父是個用相機當槍的大英雄,而他師父則特別想帶著小徒弟好好看看中國的野生動物。這一老一少在青海玉樹藏區的野外跋山涉水拍攝尋找。
離別時,奚志農對著小徒弟說:“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不吃野生動物的肉就會被餓死,沒有人,不穿野生動物的皮毛就會被凍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消費野生動物。”
在第四集《尋寶記》中,好奇心比貓還重的辛巴還去拜訪了高原植物學家彭建生,一起尋找生活在第三極的奇花異草。爬上碎石遍地的刀片山,經受隨時降臨大雨的考驗,先后看到了傳說中的雪蓮、世界上最好看的花朵綠絨蒿、一生只開一次的塔黃……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于高原物種的多樣性,這是最好的了解方法。
在四川藏區理塘大草原,辛巴結識了藏族孩子桑珠一家,一個獲獎無數的賽馬世家。而在遼闊的草原上,從小就訓練騎馬的小辛巴和桑珠開始參加了當地藏族的最大賽馬節。通過辛巴比賽騎馬的故事,讓觀眾了解藏族文化民俗傳統以及少年的純真友情。
我覺得用心去陪伴孩子成長,讓他們到大自然中去,是非常重要的。2020年暑假,8歲的辛巴說他特別想看看自己祖國的雪山、河流、動物、植物和人。于是,我們自駕出發前往第三極青藏高原,去見一見那些看著他長大的叔叔們。兩個月的旅行中先創造了哈巴雪山的最小登頂紀錄,又在青海玉樹拍攝雪豹、找尋珍稀植物,在川西大河上單人單船漂流,這一切都是我們待在如今鋼筋水泥的城市中,難以收獲的寶貴經歷。

對話
OUTDOOR:這次辛巴參與到《辛巴奇遇記》的完整攝制過程中,他是如何參與的?
老極:去南北極旅行的時候,辛巴年紀小,所以行程基本上都是由我跟太太小豬決定的。但是現在他8歲了,是孩子比較能獨立思考的階段,就和過去不同了。在去第三極之前,辛巴寫了20多個關于第三極旅行的夢想,我們父子倆就一起收集資料、檢索路線、討論行程。那時候,我感覺這個故事差不多成型了,于是在他的夢想的基礎上,表達了我期望在哪些部分進行拍攝,他也同意了。
從辛巴小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拍他,所以他非常習慣鏡頭的存在。我們都覺得“記錄”很有意思,希望能給未來留下過去的記錄。但對于孩子來說,紀錄片本身是無關緊要的,玩得開心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們達成了共識,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鏡頭會一直長時間從旁記錄,去保持最真實的狀態。
OUTDOOR:《辛巴奇遇記》在播出后,您回看這部作品和觀眾回饋時,有什么樣的感受?
老極:《辛巴奇遇記》播出之后,我看到很多父母不僅是通過點贊來表達態度,更多的人是主動說出了他們對教育的看法。在今天的中國,所有的父母都在擔憂和思考教育問題,我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體驗式教育算是給出了一個嘗試性的探索方向,有非常多的人鼓勵和支持我們。用他們的話來說,雖然不會像我們帶孩子去南極、北極、第三極,但他們看到了一種可能性,認為人生和教育都擁有更多可能。我作為內容制作者、導演,看到這種思考、反思和探討,感到非常開心和榮幸。5年、10年后,我們再回頭看這部作品時,也能看到在當時的中國,有這么一群父母在努力嘗試、探索和思考。
作為孩子的父親,我很開心看到觀眾朋友對辛巴的鼓勵和認可。就像他登頂雪山之后,我哭了,因為我看到了我的孩子在成長,我看到了他不斷地去挑戰自己的巔峰和極限,不斷為了自己的夢想努力付出的過程。現在我回頭看這部作品,我認為我送了一份非常好的禮物給我的孩子。這份禮物不僅是送給他的,也是送給我自己的。
OUTDOOR:辛巴回看這部作品里的自己是什么感受呢?
老極:他看這部片的反應比我更激動,他看到自己登頂的那一刻感嘆“原來我當時那么厲害嗎”,給他自己再次帶來了一種自豪感和力量。過幾年之后他再來看,他可能會有更多感受。
OUTDOOR:有什么想對《辛巴奇遇記》的觀眾說的?
老極:每個孩子遠遠比我們成人想象中更強大,都充滿各種可能。讓孩子多去接受自然的滋養,接受戶外運動的磨礪,去野、去愛,去擁抱美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