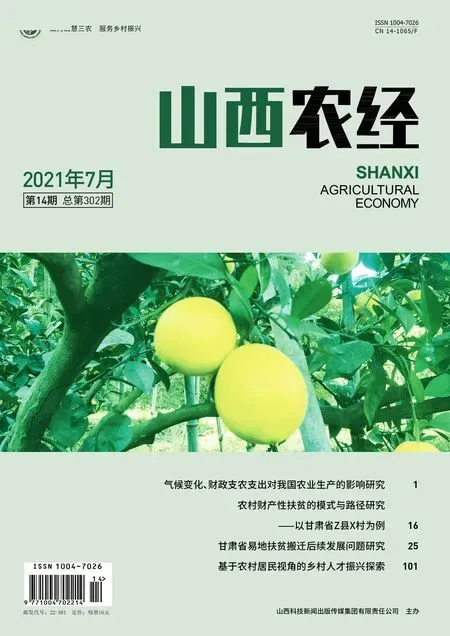“農村空心化”視角下基于NGO 模式的農村養老問題研究
——以河南省S 村幸福院為例
□劉 雯,朱華東,馬可心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4)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末中國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達到2.54 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8.1%,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1.76 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2.6%。在如此規模龐大、發展速度快的老齡人口壓力下,中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與城鎮化過程的疊加,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無疑會加大社會運行壓力。
按照黨的十九大決策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指出要“打造高質量的養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到2022 年,我國初步建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制度框架[1]。
此外,相較于經濟基礎較好、知識能力豐富、自我規劃能力較強的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的養老問題存在“空心化”、家庭結構縮小、經濟基礎薄弱、文化程度低、組織能力弱等問題。因此,如何構建新型農村養老模式,解決更多貧困地區老人“老有所依”的問題刻不容緩。
為了更好地分析農村養老問題,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貧困農村地區——河南省三門峽市靈寶市S 村進行實地調研。該村采用“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s)模式,即由非政府組織牽頭,將該村的老人、留村青年、閑置建筑、土地等資源進行整合,采用社區養老與互助養老相結合的方式,打造“養老基地”,并逐步向外拓展,吸引政府、社會的資金支持,以及鄉鎮醫院的醫療保障,現已較好地解決了該村在“空心化”背景下的養老問題,對解決廣大農村養老問題有一定借鑒意義。
1 文獻綜述
面對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不同的嘗試。
李長遠(2015)[1]把各地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劃分成為形式性購買、委托性購買和契約化購買3 種典型模式;將我國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實踐分為依附性非競爭、獨立性非競爭、獨立性競爭3 種模式。
吳紅娟(2008)[2]認為,隨著社區村民委員會的行政色彩減弱,社區中得以產生更多非政府組織和更多活動,這些活動能激發社區居民間的社會聯系和情感溝通。
胡宏偉等(2011)[3]提出了NGO 組織參與居家養老的三大成效:一是實現“老有所養”“多元養老”的有效途徑;二是有利于促進我國養老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三是可以減輕其他養老組織的負擔。
李光旭(2016)[4]在考察南京居家養老機構后提到,當地養老機構存在不可避免的服務風險、機構獨立性受到制約、可鏈接資源少等問題。
蔡云彤(2018)[5]明確指出,當前NGO 在發展中面臨服務設施不完善、使用效率低;服務內容單一,難以滿足老年人全部需求;活動形式少,老人積極性不高;人員流動性高,NGO 存在感較低;行政性過強,NGO掣肘較多等問題。河北省肥鄉縣的“互助幸福院”被稱為“村集體辦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的養老模式,全國紛紛仿效,建立了9 萬多個互助幸福院,但在廣泛推廣中,地區適用性、低效性、形式性等問題也在不斷暴露。
綜上,傳統的農村養老主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村民委員會幫扶為輔。現階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空心化”現象加劇、“空巢老人”增多,傳統養老服務的供給模式已經不適合農村老齡化現狀,受到老年群體需求多元化、需求規模化、服務個性化的挑戰,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困境。因此,亟須探索適合“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特征的新型養老模式。
2 S 村幸福院基本情況及NGO 互助養老服務運營模式
調查了該村參與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65 歲以上的老人,共有307 戶,其中包含119 位符合年齡階段的老人,有112 位老人接受了訪談。通過與社區養老負責人交流和對老人進行訪談,梳理出該村養老模式的框架:以社區養老為主,互助養老為輔,由非營利組織試運行,涉及基本的醫療、娛樂、運動等方面;前期資金來源為老人的積蓄、子女的供養,后期由政府進行引導幫扶,S 村幸福院已實現了獨立運轉和持續發展。S 村幸福院互助養老模式如圖1 所示。
現階段,S 村幸福院NGO 互助養老模式已經完全實現了自主運轉。幸福院為非營利互助養老模式,是在原有農村小學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將教室改成宿舍,可容納近200 人居住,內設健身器材室、醫療室、麻將桌等。此外,13 名組織成員對老年人進行照顧,提供生活上的幫扶,組織一系列娛樂活動豐富老年人生活。政府和村民委員會提供資金和醫療等方面的援助。大部分老人都有勞動能力,可以彼此照顧,通過種植果蔬等實現自給自足。
3 NGO 互助養老模式下S 村幸福院的優勢與機遇
3.1 S 村幸福院的發展優勢
3.1.1 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優化了養老服務的功能性河南省靈寶市S 村原有的傳統養老模式是以家庭養老為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S 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空心化”現象加劇。由于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限于家庭結構和代際支持,老年群體的生活很難得到保障[6]。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介入,在其養老服務供給更加專業化、服務內容更加多樣化的基礎上,因其非政府性、公益性的特征,能夠更加貼近村民大眾,有效彌補了村集體養老的不足,提供了養老多元便捷服務。
3.1.2 社會力量參與,群策群力,提高了養老服務的社會化水平
目前,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經過多年發展,已經逐漸得到了村民的認可和接受,但由于傳統養老觀念固化,該模式還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想改變這樣的現狀,必須提高融資渠道的靈活性、服務方式的兼容性,使社會力量多方參與,群策群力,相互協作,減弱對村集體的依賴性,有效彌補NGO 互助養老服務在運作管理上的不足。
3.1.3 注重資源整合,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資源
作為一個村級單位,S 村的養老資源、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組織、個人等資源在農村養老服務的供給方面尚處于零散化狀態,醫療保障、政策扶持、社會幫扶等方面還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
此外,NGO 模式作為非政府性、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有利于調動社會力量和資源投入到NGO 互助養老模式當中,且整合了社會養老資源,提升了養老服務的針對性。
3.1.4 福利多元主義,緩解家庭和政府的養老負擔
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對村資源的整合,使得家庭、村集體、個人等各主體都能參與到NGO 互助養老服務中,提供多元化供給養老服務,群策群力,相互協作[7]。
同時,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非政府性體現了公益服務、福利多元主義的特性,有利于凝聚社會力量,在村莊內營造尊老、愛老、敬老的良好氛圍。
3.2 NGO養老模式的機遇
3.2.1 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8 年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中明確提出,要推進農村幸福院等互助型養老服務發展;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要完善農村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支持多層次農村養老事業發展。這些文件是國家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積極探索,對政府部門職能的轉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為NGO 模式能夠有效參與養老服務這一社會領域建設提供了有利契機。
3.2.2 “農村空心化”下養老需求的迫切性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傳統養老模式已無法妥善解決高齡、空巢、獨居、失能老人的生活問題,養老困境亟待解決[8],尤其是農村地區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為2.64 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7%,其中65 歲以上老年人口1.91 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3.50%,其中大約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農村。在基礎設施薄弱、社會保障不健全的情況下,規模如此龐大的贍養群體無疑為NGO 模式助力鄉村養老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3.2.3 NGO模式的發展不斷壯大,可借鑒經驗不斷涌現
隨著我國政府在社會服務上的購買力度、參與程度不斷加大,NGO 互助養老服務方式作為一種融合社會資源參與政府合作的新型養老方式,逐漸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認可,以政府和第三方合作的養老模式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趨勢。其中,上海、南京、廣東等地率先改革養老服務模式,并通過不斷創新、不斷調整,總結出許多好的經驗做法,為NGO 模式參與社會服務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4 NGO 互助養老模式下S 村幸福院的劣勢與挑戰
4.1 S 村幸福院的發展劣勢
4.1.1 養老服務層次較低,專業服務人才匱乏
從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現狀來看,養老服務項目受制于經濟、人才、環境的限制,其服務項目的層次性不高。同時,養老服務的支柱性行業涉及醫療、護理、康復等領域,在基層農村的養老服務人員中,只有極少人接受過養老服務的專業教育,導致養老服務層次偏低[9]。
除此之外,養老護理服務對專業知識要求高,護理工作難度大,但護理人員待遇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養老護理專業人才的培養。
4.1.2 獨立能力較差,對村民委員會過度依賴
在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發展初期,對村集體資源和公共權力有很大的依賴性。理論上,NGO 模式是非政府的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是相互合作、相互依賴的雙向關系。但事實上,在NGO 養老模式的管理、項目運營等環節中,村民委員會仍處于支配地位,在財力、物力、經費的管理方面處于強勢。
同時,由于NGO 互助養老模式自身的弱勢和在村集體內部的有限號召力,導致了社會組織與村集體之間不對稱,過度依賴政府的“庇佑”,扭曲了其原本發展的路線。
4.1.3 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籌資機制不健全
目前,NGO 互助養老服務行業的發展還不成熟,且結構體系不完善。由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可以看出,其在資金籌集方面主要是政府的扶持,極大程度上制約了NGO 組織的發展。在沒有完善籌資渠道的前提下,融資來源單一,獨立能力差,對村民委員會過度依賴。
4.2 NGO互助養老模式的挑戰
4.2.1 評估和監督機制不健全,難以評估服務效果和服務質量
政府對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監督和評估機制還未完全建立,使得NGO 模式在養老服務的發展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督調控機制[10]。由于政府缺乏專業人才,難以對養老服務中的一些專業性問題進行有效評估與監督。
此外,市場上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服務水平參差不齊,難以控制養老服務的質量,從而使NGO 互助養老模式在服務質量的穩定性和有效性上無法進行科學評估和監管。
4.2.2 社會認同感較低,老年群體參與積極性不高
“養兒防老”是農村地區的傳統觀念,即普遍由子女負責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S村NGO 互助養老模式在推行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阻礙。主要是因為S 村老年群體觀念保守,對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接受程度不高。這些老年群體更愿意選擇在家養老,既能為子女在家照顧下一代,又因子女認為把父母送到幸福院是“不孝”,為父母養老送終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行為。
5 對策建議
經過實地調研發現,S 村的NGO 互助養老模式發展存在制約因素,如養老服務層次較低,專業服務人才匱乏,幸福院的獨立能力較差,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等。因此,必須針對這些問題,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提出具有較強針對性且切實可行的解決策略,促進S 村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可持續發展。
5.1 鼓勵農村老人接受并積極參與NGO互助養老模式
5.1.1 養老機構的選址應科學合理
養老機構的選址要合理,切實考慮參與NGO 互助養老的老年人的需求,盡量選在道路平整、采光良好、空氣清新的位置。
5.1.2 增加對NGO互助養老的宣傳
針對目前S 村部分老人存在對NGO 互助養老模式不了解的情況,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加強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宣傳工作,引導老年人轉變思想觀念,讓其了解養老模式并非僅有在家養老一種。在宣傳的過程中,除了依靠傳統的公告欄形式,還要深入一家一戶積極宣傳。
其次,可以為有養老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體驗,詳細地解答有意愿加入的老年人的問題。
5.1.3 服務方式要多元化,有所變通
增加養老服務的方式,應考慮具體實際情況,不應照搬其他地區的經驗。可以對參與NGO 互助養老模式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上門的服務,為喜歡安靜的老人單獨安排休息室,根據老人的不同需求,分為“全托”和“半托”等形式[11-12]。另外,應多層次滿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關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5.2 加強對NGO互助養老模式下農村養老的保障措施
5.2.1 拓寬籌資模式
首先,增加與民政部門、財政部門等資金聯系,將資金用于老人養老的日常服務、后續管理與服務中,爭取實現資金多途徑利用。
其次,村集體應立足本身,發展當地特色行業,增加村集體經濟。村集體可從中抽取資金用于NGO 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使其可以長遠運行。
5.2.2 強化個人及家庭責任,確定合理繳費比例
單靠社會的籌集和村集體經濟是不夠的,必須引導老年人個人及其家庭參與到NGO 互助養老模式中,幫助其科學籌資,緩解政府資金壓力。根據多使用、多繳費的原則,考慮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承受范圍,制定合理的個人繳費比例,盡力保證繳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