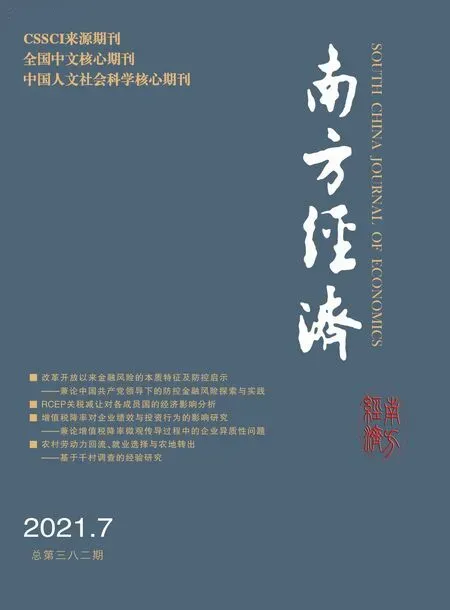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與民營企業高管腐敗
馬 駿 黃志霖 梁浚朝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其在推動經濟、增加就業和促進創新等方面均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不可否認,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中堅力量,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在制度轉型期,民營企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不合法或投機等成分,很多創業者是通過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的創業行為(Baumol,1996)來獲得生存空間并實現初始財富積累,在這一進程中也伴隨著腐敗問題的滋生,往往更容易被認定為具有“原罪”嫌疑(唐松等,2017)。據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報告》調查顯示,僅2014-2017的四年時間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案件數量為1666起,占腐敗案件總數的64.7%。頻發的高管腐敗現象成為了“做強做優做久民企”道路上的攔路虎,嚴重損害了股東和投資者的利益,阻礙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一背景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反腐風暴,民營企業家的腐敗行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僅靠“運動式反腐”成本相對較高,長期影響也相對較弱。與此同時,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處于信息劣勢一方的外部監督機構往往無法及時有效地制止企業高管的機會主義行為。那么除了出臺相關政策和加強外部監管以外,是否還有其它更為制度化、正式化和常態化的治理手段抑制民營企業高管的腐敗行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把企業……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在民營企業中,黨組織作用表現在引導、監督、維權、統戰、協調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多個方面(李少斐,2008),能有效促進企業健康發展,探索黨組織建設和企業發展間的最佳結合。
作為企業和政府溝通和聯系的重要橋梁(Chang and Wong,2004),民營企業黨組織是推動企業經營發展和促進清廉民營企業建設的重要驅動力。首先,作為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企業黨組織有義務、有責任起模范帶頭作用,在企業內部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政策和方針,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進而預防和遏制企業腐敗行為的滋生。與此同時,通過參與公司治理和決策,企業黨組織能夠在決策層面加強黨委政府的政策滲入到董事會的決策思維中,進一步推進企業反腐倡廉建設。其次,企業的文化建設是企業黨組織的重要職責之一,企業黨組織可以發揮文化核心作用,加深員工和管理層對黨的先進思想的學習與理解,樹立廉潔意識,推動廉潔文化建設融入到企業文化建設中。有學者指出,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環境對于防范企業腐敗具有積極的作用(Levendis and Waters,2009),黨組織與企業文化建設關系密切,能夠有效幫助企業塑造誠信公正、合法守紀的健康企業文化。由此引發的思考是,民營企業設立黨組織是否能夠有效發揮監督和制約企業高管的作用,從而減少高管腐敗行為?民營企業黨組織的治理參與是否能夠進一步掣肘高管腐敗行為?如果能夠,具體的渠道和效果如何?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加強和改進民營企業黨建工作,促進民營企業長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對于以上研究問題,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國上市民營企業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對假設進行驗證。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第一,豐富了民營企業腐敗相關的文獻。過去關于民營企業腐敗的文獻主要側重于企業高管腐敗的誘因,認為腐敗治理不過是實踐層面上的“對癥下藥”,故有關專門針對民營企業高管腐敗治理的研究一直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識別出民營企業黨組織抑制高管腐敗行為的影響機制和效果。進一步,過去研究發現,高效的內部控制以及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制度能夠有效抑制高管腐敗行為(Hogan and Wilkins,2008;Klamm et al.,2012;Ji et al.,2018),而本文則發現,黨組織的建立能夠作為企業內部控制和傳統治理結構的重要補充,進而發揮協同治理作用。第二,拓展了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文獻,為民營企業黨組織與企業高管腐敗行為之間建立了理論聯系。就目前研究來看,大多數文獻在探討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影響時,主要將目光聚焦于黨建對企業社會責任(梁建等,2010;鄭登津、謝德仁,2019;Yan and Huang,2017;Dong et al.,2016a)、長期導向行為(何軒、馬駿,2016)、企業績效(何軒、馬駿,2018b)、參與社會治理(何軒、馬駿,2018a)等方面的影響。基于文獻回顧可以看出,現有研究對民營企業黨組織與企業高管腐敗關系的理論分析仍較為匱乏。作為政府與民營企業聯系和溝通的重要途徑,黨組織不僅是使黨委政策方針在企業得以貫徹執行的關鍵節點,同時也是推動企業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驅動力。因此,本文聚焦于民營企業黨組織,探討民企黨組織對企業高管腐敗現象的影響及其具體渠道和機制,以期為現有研究作出有益的補充。第三,本文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全面從嚴治黨以來,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建設一直是黨建工作的重要領域,科學分析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影響有助于加強和改進企業黨建工作。與此同時,伴隨著日益復雜多變的反腐形勢,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反腐”將持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點關注的問題。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能夠為企業治腐尋找更為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態化的治理途徑,為民營企業的長足發展提供理論與經驗借鑒,同時對中國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實踐啟示。
本文接下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與理論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包括樣本選取、變量說明、數據來源、模型建立等;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及討論;最后一部分是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與理論分析
(一)民營企業高管腐敗
根據透明國際(2008)的定義,企業高管腐敗是指高層管理者為撰取私利而濫用權力的現象。在學術界,國內外學者主要從控制權私利視角來界定企業高管腐敗的內涵,認為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使得企業實際控制權往往掌握在擁有決策權力和信息優勢的管理者手中,由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存在天然利益沖突,企業高管可能通過超額薪酬、索賄受賄、在職消費、侵占資產等方式謀取控制權私利、從而損害投資者利益(陳信元等,2009;Van den Steen,2010;李殷、劉忠,2021)。盡管目前對企業高管腐敗的內涵定義并非完全一致,但學者們均普遍認為,企業高管腐敗的本質是一種以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其后果則是導致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受到損害。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者針對高管腐敗成因這一話題展開探討,這些研究都證實高管腐敗的誘因有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如高管道德水平(Luo et al.,2017)、公司治理(Yermack,2006;Brocket,2010)、企業文化(O’Reilly,1989)、制度環境(Baumol,1996;Duvanova and Dinissa,2014)等。根據已有研究和對中國現實的觀察,本文主要從三個層面探討企業高管腐敗的關鍵誘因,即微觀層面的高管個體因素、組織層面的公司治理與企業文化因素以及宏觀層面的制度環境因素。
從高管個體層面來看,高管權力是誘發其腐敗的關鍵要素之一。由于現代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使得管理者和股東的效用難以統一,加之股東不可能對擁有私人信息和掌握公司控制權的管理者進行全面徹底的監督,因此,理性的管理者會有動機地進行權力尋租,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Van den Steen,2010;Bendahan et al.,2015)。
從組織層面來看,已有學者從監管低效率、內部控制失效、激勵機制匱乏、企業文化風氣敗壞等方面展開了探討。有學者指出,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和治理機制不健全的直接表現就是企業高管腐敗(Hirsch and Watson,2010;申宇、趙靜梅,2016)。此外,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的欠缺同樣容易造成高管腐敗,其中企業對高管激勵的方式有很多,諸如薪酬機理、精神激勵、股權激勵等,而約束的關鍵在于對高管行為的監督與管控,企業高管的激勵扭曲與內部控制失效是導致高管腐敗的重要誘因。另外,企業高管的腐敗程度也與長久積淀的企業文化息息相關,不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環境是企業高管腐敗的關鍵誘因之一(Pearce and Robinson, 2003)。
從宏觀層面來看,高管腐敗的成因源于企業外部的制度環境。首先,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實施腐敗產生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與國有企業相比,因缺乏必要的市場和政策環境支持,民營企業往往面臨更加巨大的生存壓力和更加嚴格的制度約束(Zhu and Zhang,2017;Song et al.,2011)。在這一背景下,民營企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不合法或投機等成份,企業高管通過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的腐敗行為以獲得生存空間并實現財富積累。其次,也有學者指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監管效率欠缺是企業高管謀取私利的重要成因(Dyck and Zingales,2004)。
(二)民營企業黨組織與高管腐敗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黨組織都具有政治核心作用或政治引領作用。黨組織對企業的政治領導有助于增強對企業高管的監督,防止企業高管以犧牲公司利益為代價實現其個人目標。本文認為,嵌入到民營企業中的基層黨組織,影響高管腐敗行為的機制主要源于以下三點:
首先,根據《關于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民營企業黨組織肩負著“塑造積極向上的企業精神,樹立高尚的職業道德,促使企業誠信經營”的職責。誠然,引導和監督企業高管廉潔從業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方面。黨組織可以憑借其政治優勢,通過開展各項黨風黨性專題宣傳教育活動,促進黨中央的精神和理念在企業組織中傳遞,使企業能夠深入理解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引導企業和國家發展同頻共振。在實踐中,黨組織有著自上而下嚴格的監督制度和政治紀律,能對企業高管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和約束作用,確保其將合法經營、合規經營等理念落實到企業日常管理中。與此同時,黨組織可以利用自身的組織資源優勢圍繞企業生產經營等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何軒、馬駿,2018b)。通過民營企業黨組織與企業管理層溝通協商和懇談,黨組織成員和管理層成員在決策前會進行事先溝通并交換意見,將黨組織的意見及時反饋給董事會,作為董事會作出最終決策時的一個重要參考。這一工作程序進一步放大了民營企業黨組織的監督作用,有助于預防企業高管在決策層面濫用控制權以謀取私利。
其次,民營企業黨組織具有配合企業文化建設的功能。由于具備天然的政治先進性,黨組織成員有責任、有義務起模范帶頭作用,為企業群眾樹立可以效仿的具體榜樣。企業高管也正能夠從先進人物和典型榜樣的價值追求、精神風貌和言行舉止中,深刻理解廉潔企業文化的實質和意義,有利于培養廉潔自律的經營意識。另一方面,黨組織通過在企業內部開展多項黨紀黨風和反腐倡廉方面的教育專題活動,號召企業高管學習黨的先進思想,遵守黨的規章制度,能夠促進黨中央的反腐精神在企業組織中傳遞,推動廉潔文化建設融入到企業文化建設中,使組織內部形成誠實公正、清正廉潔的企業氛圍。進一步,健康的企業文化有利于企業建立清正廉潔的價值觀,進而對企業高管形成軟約束,從動機上抑制其私利行為。
最后,民營企業黨組織具有參與公司經營與治理的功能。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組織在場地設施、制度保障、指導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提高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和作用(李世剛、章衛東,2018)。在公司治理實踐中,黨組織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等方式對民營企業的治理參與,會對企業管理決策產生影響,其中就包括抑制企業高管的私利行為。首先,黨組織與董事會成員的重合與交叉任職,不僅有助于加強黨委政府的政策方針滲入到董事會的決策思維中,為黨組織抑制高管腐敗行為提供觀念層面的保障,同時也能強化董事會的監督效率,將黨組織的行政監督機制和董事會的公司治理機制有機融合起來,進而降低企業高管腐敗的概率。其次,作為企業治理核心內容的監事會與董事會擁有關于公司相對較多的“內部信息”。在民營企業中,企業高管是組織決策的主要制定者,對于奢靡在職消費、構建商業帝國等隱性腐敗行為(徐細雄,2012),往往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而無法被察覺,企業高管謊報和瞞報成為無法避免的問題。通過參與到企業治理的具體運作實踐中,黨組織能夠接觸到企業內部真實可靠的有效信息,能夠降低由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道德風險,進而會在抑制高管腐敗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降低高管腐敗發生的概率。
(三)黨組織參與治理抑制民營企業高管腐敗的影響路徑分析
上文我們分析了誘發企業高管腐敗行為的個體、組織和環境因素,這一部分則基于上文分析,剖析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如何通過抑制這三面誘發因素,最終降低企業高管的腐敗行為。具體而言,我們分別從高管個體層面(高管權力)、企業層面(家族控制型企業)以及環境層面(市場化水平)進行分析。
1.高管權力
企業高管腐敗的本質是一種濫用控制權謀取私利的行為,是控制權較大的高管人員為了獲取灰色利益而違反個人職業道德造成的(Watson and Hirsch,2010)。代理理論認為,由于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所有者追求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的目標與經營者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存在天然不一致性,掌握實質控制權的企業高管會有動機地進行權力尋租,從而引發代理問題。管理層權力理論也強調,由于不完備契約與信息優勢,高管權力能夠凌駕于企業契約之上,高管為謀取私利很可能進行權力尋租,實現個人效用最大化。由此可見,高管腐敗與企業內部權力配置之間息息相關。具體來說,現代企業兩權分離,使得高管與股東的效用難以統一,企業高管出于自利動機,在獲取控制權后更容易引發“塹壕效應”(權小鋒等,2010),進而通過各種渠道削弱董事會的監督作用,愈發增強了高管腐敗的空間(Hambrick and Msaon,1984)。特別地,在我國轉型經濟過程中,由于企業控制權市場、經理人市場、勞動力市場相關機制尚不健全及資本市場效率缺乏,企業高管更有可能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濫用控制權,進而滋生腐敗行為。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一把手”文化導致權力過于集中,從而使高管權力能夠凌駕于企業契約之上,愈發增強了高管腐敗的空間(Bolton et al.,2006;盧銳等,2008)。徐細雄、劉星(2013)和陳信元等(2009)的實證研究都發現,CEO 權力強度越大,企業越可能發生高管腐敗。
作為中國特色的一種體現,黨組織的出現必然會對企業高管的經營決策構成一定影響和制約(梁建等,2010)。在民營企業中,黨組織作為一種制度力量,能夠通過具體措施限制企業高管濫用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對管理層權力形成制衡。首先,企業黨組織具有監督和引導經營者廉潔從業的重要職能。企業高管在經營過程中行使的決策權和經營權,會受到企業黨組織的嚴格監督和有效約束,有助于減少高管腐敗現象發生的頻率。進一步,通過參與公司治理與決策,黨組織能夠進一步強化董事會的監督作用,有助于在決策層面抑制企業高管的濫用權力行為,其次,黨組織可以發揮其文化核心作用,通過舉辦反腐教育和黨建活動,能夠促進誠實守信,清正廉潔等價值觀滲入到企業管理層中,增強企業高管廉潔從業意識,進而在思想源頭上抑制高管權力對高管腐敗的誘發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弱化高管權力與高管腐敗的正相關關系。
2.家族企業
受到傳統儒家文化和家族主義的影響,中國家族企業仍然以傳統權威和魅力型權威主導,家長制、道德型領導成為主流模式,決策和管理中仍然帶有濃重的經驗主義和個人意志。同時,較高程度的家族涉入進一步使得非正式干預和關系治理得到加強。這一治理模式在外部制度環境不完備以及市場競爭較弱時,能夠幫助家族企業有效地減少代理成本、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提升家族企業的治理效率和價值(Fama and Jensen,1983)。但同時,這一典型特征使得家族企業缺乏內部和外部正式的監督和控制系統(Rand?y and Goel,2003)、雇傭更少的外部董事和管理者(Cowling,2003)、面臨更少的外部利益相關者監督和信息披露的壓力(Carney,2005)。在家族利益的驅使下,家族企業高管有可能采取一系列侵害股東集體利益的自利行為(Bassetti et al.,2015),如挪用企業資源向家族成員進行轉移支付、家族代理人搭便車問題等(Schulze et al.,2001;Schulze et al.,2002)。
此外,控制權理論認為,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以及信息不對稱,企業高管在獲取控制權后可能并不傾向于按照股東意愿形式,而是出于自利動機利用控制權攫取私利,損害投資者利益。我國家族企業在具體治理實踐中較多采用金字塔控制結構等控制權放大機制(王明琳和周生春,2006),使得控制權與所有權高度分離。此時,持有實質控制權的家族企業高管往往具有更加強烈的自利動機通過“隧道行為”侵占投資者和股東利益(Johnson et al.,2000)。最后,結合當前中國轉型時期的特殊背景,企業所處大環境下外部監督約束缺位,加之企業高管實施腐敗的機會成本較低,持有實質控制權的家族企業高管往往會為了謀取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各種機會主義行為。此外,從更宏觀的意義上來說,家族企業還可能通過集體或個人行動來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制度(Craig and Moores,2010;Dieleman and Sachs,2008;Reay et al.,2015)。在某些情況下,家族企業集團會形成寡頭控制(Fogel,2006),進而通過一系列政治尋租活動來破壞市場規則(Dieleman and Sachs,2008)。
進一步,在家族企業中,董事會的組成人員絕大多數都是家族成員,僅極少數企業設有獨立董事或家族以外的成員進入監事會。在這一情況下,縱使高管腐敗行徑敗露,出于維護企業形象、情感紐帶等社會情感財富的目的(Gomez-Mejia et al.,2007),家族成員之間可能會選擇“睜一眼閉一眼”的姑息態度,公司治理機制也因此而無法發揮作用。
在這一背景下,由于天然的政治先進性,黨組織能夠超越企業經營中追求短期或單一主體效益的局限,成為制衡家族企業高管的重要力量。首先,黨組織具備更為完善且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企業,能夠更加嚴格公正地對家族企業高管進行考核監督。此外,作為典型的二元型組織,家族企業在追求經濟目標的同時,還會追求社會情感目標(馬駿等,2020a)(如建立和維持正面的家族形象和聲譽、企業在家族成員間的代際傳承和家族對企業的控制地位等),后者有時候甚至更加重要(Gomez-Mejia et al,2007;Berrone et al.,2012;馬駿等,2020b)。高管腐敗不僅是一種違法違規行為,更是一種違背商業倫理的敗德行為。其一旦東窗事發,對于家族形象和家族聲譽所造成的損害是無法挽回的,對社會情感財富的存續也會造成重大打擊。從這個角度來看,為了保全家族的情感財富避免名譽受損(Zellweger and Astrachan,2008),家族企業可能會更加積極地支持和配合黨組織的工作,在企業決策過程中自覺接受黨組織的監督與監管, 加強對自身經營行為的規范和約束。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降低家族企業內部高管腐敗行為的發生概率。
3.市場化水平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逐步確立,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但由于地理條件、資源稟賦及國家政策等差異,我國各省份、地區的市場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異(樊綱等,2011)。學者們普遍發現,相對較差的制度環境(對應于較低的市場化水平)會導致創業者和企業高管進行更多地尋租和腐敗行為(Baumol,1990;徐細雄、劉星,2013;Dong et al.,2016b;魏下海等,2015;何軒等,2016),而較好的制度環境(對應于較高的市場化水平)則能夠抑制這些行為。這種非均衡格局為本文從單一國家背景,探討基層黨組織對不同的區域市場化進程與企業高管腐敗關系的影響提供了很好的現實素材。
在市場化進程較低的情境下,民營企業受到的外部約束相對較弱,監管法律體系的漏洞和缺陷為企業高管實施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真空地段。此時,作為內部治理的有效組成,民營企業黨組織可以彌補地區外部治理機制的缺陷,與外部治理要素共同協作,共同發揮對企業高管行為的監督與約束作用。另外,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區,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的作用有限,企業高管往往需要尋求一些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以克服企業發展障礙,其中政治關聯就是非常重要的替代性制度。但是這種在人格化基礎上建立的傳統政商關系很容易滋生腐敗,進而誘發諸如“權錢交易”、“政商合謀”、“政商利益聯盟”等負面行為(杜興強等,2010)。在這一情境下,作為一種制度化、正式化、非人格化的組織層面的政治聯系,基層黨組織有著嚴格的組織規范和紀律,能夠有效防止尋租腐敗的滋生(何軒、馬駿,2018a)。企業高管無需像以往那樣,為了獲得企業發展必須的關鍵資源而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用于政府關系的建立和維護,這有助于企業擺脫非市場化的政治關系依賴,基于傳統政商關系進行尋租性腐敗的現象會受到抑制。
當企業所處區域市場化水平較高時,由于外部治理機制更趨健全、資源可獲得性更高和市場信息更為透明,高管的機會主義行為得到了抑制和約束(Dyck and Zingales,2004)。此時,民營企業黨組織可以進一步強化正式制度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尤其是,在黨組織治理參與度較高的民營企業,黨組織會更加發揮職能,對各項權力的履行能形成較好的制衡,高管的經營與管理行為均受到有效監管,進而抑制企業高管的私利動機。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強化市場化水平與高管腐敗的負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滬深上市民營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構建了時間跨度為2004年到2017年的面板數據樣本。之所以選擇2004年為研究起點,主要是因為CSMAR和Wind數據庫從2004年開始才有較為完整且可信的高管個人資料信息的披露。本文的核心變量以及控制變量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和CSMAR上市公司數據庫,并通過多個數據來源交互印證。本文對總體樣本進行如下篩選:(1)剔除ST、SST、*ST 公司的樣本;(2)剔除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類受管制公司的樣本;(3)剔除觀測值缺失的公司樣本。經過處理,本文得到一份非平衡的面板數據一共13453個觀測值(企業數×觀察年份)。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
高管腐敗(1)我們認為,高管腐敗與企業違規是兩個不完全等價的概念,但在企業情境中,企業違規行為的核心載體和直接體現就是高管的違規和腐敗行為。或者說,企業違規的披露其實就是披露高管的腐敗行為,尤其是在中國外部治理環境不規范的情形下,高管的個人意志和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營企業的決策行為,陳信元等(2009)就指出,“違規擔保、違規借貸等行為既屬于公司的違規行為,也是高管的違規行為”。因此,從概念界定上來說,高管腐敗和企業違規是兩個不等價的概念,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沒有辦法徹底將兩者分開。在本文中,我們則將企業違規視為高管腐敗的替代變量,事實上,過去的研究也同樣進行了同樣的操作(陳信元等,2009;黃玖立和李坤望,2013;Cai et al.,2011;Khanna et al.,2015),盡管有些研究沒有直接言明。。對于高管腐敗的衡量,現有研究主要有兩類測量方式。第一類以公司(高管)違規行為的披露和處罰(陳信元等,2009;Khanna et al.,2015)為測量標準;第二類以公司(高管)的費用支出為界定標準,其中又包含兩類不同的衡量指標:一是企業的招待費和差旅費支出(黃玖立、李坤望,2013;Cai et al.,2011),二是企業的超額管理費用(陳冬華等,2005;杜興強等,2010)。
借鑒現有研究,在主效應檢驗中,本文使用公司違規作為高管腐敗的替代變量,具體而言,我們整理了目標企業在每一年披露的違規信息,并統計出目標公司目標年份的違規次數。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進一步使用三個替代變量:(1)違規的虛擬變量:是否有違規行為;(2)企業的招待費和超旅費支出:將企業招待費和差旅費的和單位化(以企業員工數為標準),然后取自然對數;(3)超額管理費用:使用企業實際管理費用與根據回歸模型估計的期望管理費用的差值衡量,具體計算過程參考杜興強等(2010)的研究。
2.自變量
黨組織參與治理。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并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其需要強制性披露公司中是否設立了黨組織,這為我們識別公司中黨組織的設立情況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現有研究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目前對于黨組織嵌入的測量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研究載體,考察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情況,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是陳仕華、盧昌崇(2014)使用“黨組織成員是否兼任董事會、監事會或高管”為衡量指標,設立“黨組織參與”虛擬變量。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將黨組織參與細分為三個0-1指標:黨組織成員是否兼任董事會成員、黨組織成員是否兼任監事會成員、黨組織成員是否兼任高管;另一類則使用企業“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情況來衡量黨組織參與治理(馬連福等,2012;馬連福等,2013)。具體而言,他們分別使用黨委委員兼任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和高管成員來測量。
借鑒以上研究,在主效應檢驗中,我們使用公司中是否設立黨組織作為自變量,使用“黨組織成員是否兼任董事會、監事會或高管”為衡量指標,設置“黨組織參與”虛擬變量。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進一步使用6個“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變量——黨委委員兼任董事會成員數/董事會規模、黨委委員兼任監事會會成員數/監事會規模、黨委委員兼任高管成員數/高管規模、黨委委員是否兼任董事長、黨委委員是否兼任監事會主席、黨委委員是否兼任總經理。
3.影響路徑變量
(1)高管權力。Finkelstein(1992)首次對高管權力做出了相對科學的衡量,根據來源將高管權力分為所有權權力、結構權力、專家權力和聲望權力。后來學者們都在此基礎上對高管權力問題進行了討論,結合數據可得性,本文借鑒Haynes and Hillman(2010)的衡量方法,從結構性權力和所有權權力維度出發,選取如下變量:兩職合一(CEO兼任董事長)、非關聯董事占比、CEO與董事持股比、CEO任期以來聘請董事數占比。其中,兩職合一、CEO與董事持股比越高、CEO任期以來聘請董事數占比越高,高管權力越大;而非關聯董事占比越高,高管權力越小。基于此,高管權力的測量方法是:(1)將以上四個變量標準化((目標變量-變量均值)/變量標準差);(2)標準化后,高管權力=兩職合一+CEO與董事持股比+CEO任期以來聘請董事數占比-非關聯董事占比。
(2)家族企業。借鑒李新春等(李新春等,2015)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即“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且實際控制人的家族成員或持有股份,或進入董事會,或進入監事會,或擔任高管成員,必須滿足上述條件之一”,本文按以下步驟獲得上市家族企業研究樣本:首先,根據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CSMAR上市公司數據庫,獲取了2004年至2017年所有“實際控制人類型”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業;然后,根據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和年報中披露的公司實際控制人、持股情況、董事會成員和高管成員等信息,確定是否滿足家族企業的定義。其中,關于家族親緣關系的確定,我們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還通過互聯網搜索引擎來進行佐證和補充。在此基礎上,本文設置虛擬變量,滿足上述條件的企業定義為家族企業并賦值為1,否則定義為非家族企業并賦值為0。
(3)市場化水平。市場化水平來源于樊綱等(2011)編著的《中國市場化指數(2011)》的以及王小魯等(2019)編著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需要說明的是,樊綱等(2011)的市場化水平數據期間為1997-2009年,王小魯等(2019)的市場化水平數據期間為2008-2016年。由此,在2010年之前樣本中,我們使用樊綱等(2011)的市場化水平數據,2010年以后的問卷中,我們使用王小魯等(2019)的市場化水平數據。
4.控制變量
借鑒現有研究(陳仕華、盧昌崇,2014;馬連福等,2012;馬連福等,2013),本文控制了CEO人口統計學變量、企業發展情況、企業治理情況和外部環境因素。CEO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CEO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任期;企業發展情況包括企業年齡、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銷售增長率、股權集中度;企業治理情況包括董事會規模、獨董比例、兩職合一、內部控制質量。企業外部環境因素包括地區、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
各變量的測量詳見表 1。

表1 變量測量與設計
四、數據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匯報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可看出,企業年平均違規次數(高管腐敗)為0.2415次,最少的沒有違規,最多的違規了11次,差異相對較大。有黨組織參與治理的公司比例為6.43%,標準差為0.2453。高管權力的平均值為0.1656,標準差為1.6543,各公司CEO之間的權力差異同樣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在所有民營企業中,超過60%的企業為家族控制。各地區市場化水平差異巨大,水平最差的為-0.2621(西藏地區),水平最高的地區則為15.7149。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變量的相關系數
表3報告了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表3可看出,本文關注的核心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顯著負相關,高管權力、家族企業與高管腐敗顯著正相關,市場化水平與高管腐敗顯著負相關。就控制變量而言,總體來說,年長、男性、任期較長的CEO所轄企業高管腐敗次數越少;成立年限越短、規模越大、資產負債率越低、資產收益率越高、銷售增長率越高、股權集中度越高、內部控制質量越好的企業,發生高管腐敗的次數越少。從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來看,本文初步證實了,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顯著抑制企業高管腐敗的發生,這一結論則需要進一步的回歸分析加以論證。

表3 變量的相關系數
(三)假設檢驗
在實證檢驗前,本文對數據做如下處理:(1)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在1%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2)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對相互項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同時,對所有進入模型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VIF)診斷,結果顯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3)為了克服面板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時序相關和橫截面相關等問題,本文采用Driscoll-Kraay標準差進行估計。
1.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關系的檢驗結果
表4報告了高管腐敗對黨組織參與治理的回歸結果。模型(1)為基準模型,模型(2)加入黨組織變量的回歸模型。模型(2)的結果顯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顯著負相關(β=-0.0627,p<0.01),表明相比沒有黨組織參與治理的企業,有黨組織參與治理的企業發生高管腐敗的頻率越低。這一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

表4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關系檢驗
2.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
本文關注的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了緩解這一問題,我們分別使用傾向匹配得分法(PSM)、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Heckman兩階段回歸、因變量滯后、樣本縮減、雙重差分法(DID)等六個步驟進行處理。
①PSM。首先使用傾向匹配得分法來處理內生性問題(Heckman et al.,1998)。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評估某一行為或特征時,通過傾向得分值找到與處理組相似的控制組進行配對分析,此時樣本選擇偏誤能夠被有效降低,同時減弱控制變量等因素對考察變量的影響,有效緩解內生性問題。首先,本文使用Logit模型對匹配變量進行篩選,參與篩選的匹配變量為上文中所有控制變量,解釋變量為0-1虛擬變量,1代表企業有黨組織參與治理,0代表企業未有黨組織參與治理,同時控制地區、行業和年度效應。其次,基于Logit模型的擬合值計算出相應的傾向得分值,并采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對處理組和控制組的PS值進行配對。最后,采用“對被處理單位的平均處理效應”(ATT)來估計黨組織參與治理對高管腐敗的影響作用。表5報告了使用PSM方法的回歸結果。其中,第二行報告了黨組織參與治理對高管腐敗的ATT回歸結果,結果顯示,ATT平均處理效應為-0.0740,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上述“最近鄰匹配方法”按照1∶4的比例進行配比,本文同時按照1∶1、1∶2、1∶3的比例進行配比,結果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這表明,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影響后,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顯著抑制民營企業高管的違規行為。由此,本文的結果相對穩健。
②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本文選擇兩個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分析。第一,本文選擇企業所在地區和行業中黨組織設立的均值(除目標企業自身)作為工具變量。選擇這一工具變量的原因是:企業經營有賴于其對環境和文化的遵從,組織結構和戰略不可避免受到同一地區和行業中其他企業的影響;同時,同一地區和行業中的其他企業無法直接影響到本企業的違規;第二,何軒、馬駿(2018b)使用企業“開辦時的資產規模”作為黨組織的工具變量,考慮到本文數據可得性問題,我們使用企業上市招股時的資產規模作為工具變量。表6中模型(1)和(2)分別報告了使用以上兩個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均顯著負相關(β=-0.275,p<0.1;β=-1.958,p<0.05),表明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6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的回歸結果:2SLS回歸分析
③Heckman兩階段回歸。本文還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差問題(Selection Bias),為解決可能存在的樣本自選擇而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構建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行控制。使用Heckman兩階段回歸過程中,加入逆米爾斯比率λ可以適當克服自選擇性偏差,如果λ顯著不為零,則表明存在顯著的樣本自選擇性。在回歸分析中,需要設置至少一個影響企業黨組織參與治理但對高管腐敗沒有偏效應的工具變量(Heckman,1979),本文同樣選擇2SLS模型估計中的兩個工具變量分別進行回歸,表7報告了檢驗結果(2)受到篇幅限制,本文沒有報告Heckman兩階段回歸中第一階段結果。第一階段的結果顯示,本文選擇的兩個工具變量均與黨組織參與治理顯著相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回歸結果。,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λ都顯著不為零,表明存在自選擇問題。進一步,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均顯著負相關(β=-0.377,p<0. 01;β=-0.295,p<0.1),表明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7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的回歸結果:Heckman兩階段回歸分析
④因變量(高管腐敗)的滯后處理。我們將高管腐敗變量分別取滯后一年、二年和三年,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_滯后一年(β=-0.0580,p<0.01)、高管腐敗_滯后二年(β=-0.0560,p<0.01)、高管腐敗_滯后三年(β=-0.0690,p<0.05)均顯著負相關,表明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8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關系檢驗:滯后1-3年的回歸結果
⑤剔除2012年以后樣本的回歸。2012年以后,國家推出在私營部門成立黨組織的號召的同時,也在加強反腐力度和巡查,所以存在黨組織和腐敗的相關性,但兩者不一定構成因果關系的潛在可能性。我們仔細查詢了中央政府對于“反腐”和“非公經濟黨建”工作的重要會議和論述后發現,其實在2012年后,中央政府就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重要部署。
首先,“非公經濟黨建”問題。2012年3月21日,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會議代表并講話。他強調,非公有制企業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和作用決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整個黨建工作中越來越重要,必須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實實抓好(3)資料來源:http://www.gov.cn/ldhd/2012-03/21/content_2096653.htm。。2012年11月8日召開的十八大再次重申了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領域黨建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非公有制企業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和作用決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整個黨建工作中越來越重要,必須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實實抓好(4)資料來源: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7/0220/c117092-29093965.html。。
其次,“反腐”問題。從2012年11月,中共中央開始加大反腐力度,至2014年,有超過18萬名黨員干部被處分,56名“老虎”落馬。近年來,中國的反腐力度也始終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因此,從以上內容可以發現,從2012年開始,國家其實已經同時開展“大力反腐”和“加快非公經濟黨建工作”,進而可能產生上文提出的問題。基于此,我們將2012年以后的樣本刪除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_當年(β=-0.0727,p<0.01)、高管腐敗_滯后一年(β=-0.0398,p<0.05)、高管腐敗_滯后二年(β=-0.0573,p<0.01)、高管腐敗_滯后三年(β=-0.0713,p<0.01)均顯著負相關,表明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9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關系檢驗:剔除2012年以后樣本的回歸結果
⑥雙重差分模型(DID)。本文進一步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來估計黨組織參與治理對高管腐敗的影響。首先,采用上文穩健性檢驗中使用的最鄰近Logistic傾向得分匹配策略,通過使用與上文一致的特征變量(在設立黨組織前三年的觀測值),將有黨組織參與治理企業與控制組中為未有黨組織參與治理的企業進行匹配,最終獲得768個樣本。該部分研究保留設立黨組織企業和控制組企業在首次識別企業設立黨組織這一時間點的前后三年(包括設立當年)的觀測值作為分析樣本,當樣本企業有黨組織參與治理時,變量treat取值未“1”,若未有黨組織參與治理,則取值為“0”。當樣本所在時間是在黨組織參與治理之后,變量post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我們所關心的是,當該樣本企業在黨組織參與治理后的年份,即自變量(treat×post)對該企業進行的違規活動是否有產生顯著的影響。結果如表10所示,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β=-0.0679,p<0.05),表明企業有黨組織參與治理之后進行違規活動的頻率越低,由此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10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關系檢驗:DID回歸結果
(2)高管腐敗變量替換
上文使用企業違規次數衡量企業的高管腐敗,我們進一步使用如下四個變量作為高管腐敗的替代變量:第一,目標企業當年是否違規,設置為虛擬變量;第二,高管的顯性腐敗。顯性腐敗是易被發現、察覺和披露的腐敗問題,是企業高管為攫取私利出現的直接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行為(徐細雄,2012;陳信元等,2009)。國泰安數據庫中將違規事件分為以下15種類型:①虛構利潤;②虛列資產;③虛假記載;④推遲披露;⑤重大遺漏;⑥披露不實;⑦欺詐上市;⑧出資違規;⑨擅自改變資金用途;⑩占用公司資產;內幕交易;違規買賣股票;操縱股價;違規擔保;一般會計處理不當。其中,⑦-是顯性腐敗的幾類具體體現,我們將其定義為顯性腐敗,統計出目標公司當年出現顯性腐敗的次數。第三,高管的隱性腐敗。隱性腐敗主要是指高管在職期間進行的非正常消費(徐細雄,2012),這一類行為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不易被察覺。具體而言,本文使用兩個變量來體現隱性腐敗:一是企業的招待差旅費用(黃玖立、李坤望,2013;Cai et al.,2011),使用員工人數單位化后取自然對數;二是超額管理費用(陳冬華等,2005;杜興強等,2010),具體計算方式參考杜興強等(2010)。
表11報告了具體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使用上述四個變量作為高管腐敗的替代變量后,回歸結果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黨組織參與治理的系數均顯著為負。由此表明本文的結論相對穩健。

表11 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腐敗的回歸結果:高管腐敗變量的替換
(3)黨組織參與治理變量替換
在上文基礎上,本文進一步使用企業“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情況來衡量黨組織參與治理(馬連福等,2012;馬連福等,2013)。具體而言,使用6個變量——黨委委員兼任董事會成員數/董事會規模、黨委委員兼任監事會會成員數/監事會規模、黨委委員兼任高管成員數/高管規模、黨委委員是否兼任董事長、黨委委員是否兼任監事會主席、黨委委員是否兼任總經理。
表12報告了具體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黨委委員兼任董事占比(β=-1.163,p<0.01)、黨委委員兼任董事長(β=-0.136,p<0.01)、黨委委員兼任監事會主席(β=-0.250,p<0.1)均與高管腐敗顯著負相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

表12 黨組織與高管腐敗的回歸結果:黨組織變量的替換
此外,我們還參考鄭登津、謝德仁(2019)的做法,使用企業黨組織活動情況(1) 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影響程度,等于黨組織活動次數的自然對數,黨組織活動次數越多則表明黨組織影響力越大;(2)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是否獲得上級黨委表彰的啞變量,黨組織受到上級黨委表彰則表明黨組織影響力較大)來衡量黨建工作。回歸結果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
3.黨組織參與治理抑制企業高管腐敗的影響路徑分析
本文認為,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通過弱化高管權力、家族企業與企業高管腐敗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以及強化市場化水平與高管腐敗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來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和治理作用,表13報告了具體的回歸結果。模型(1)、(3)、(5)的結果顯示,高管權力(β=0.00880,p<0.05)和家族企業(β=0.0305,p<0.01)的系數顯著為正,而市場化水平(β=0.0221,p>0.1)的系數無顯著性。進一步,模型(2)、(4)、(6)的結果顯示,黨組織參與治理與高管權力的交互項(β=-0.0206,p<0.05)以及黨組織參與治理與家族企業的交互項(β=-0.0641,p<0.1)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而黨組織參與治理與市場化水平的交互項(β=0.00697,p>0.1)的系數無顯著性。以上結果表明,高管權力越大、家族控制型企業中的高管發生違規的頻率越高,而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顯著地弱化它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對于市場化水平而言,其對高管腐敗的影響作用有限,且黨組織參與治理也無法進一步發揮協同作用。由此,本文假設2和假設3得到支持,假設4沒有得到支持。

表13 黨組織參與治理抑制高管腐敗的機制分析
五、結論與討論
在經濟與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企業高管腐敗問題一直是熱議的焦點話題。特別地,自黨的十八大提出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部署以來,中國形成了反腐倡廉的高壓態勢,社會各界對于反腐敗的熱情空前高漲。在這一背景下,不僅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被頻頻曝光,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組成部分的民營企業高管腐敗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和業界的關注。過去研究更多地關注了外部環境、高管個人特征以及公司內部特征和治理結構對于民營企業高管腐敗的影響作用,但忽視了民營企業內部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態化的反腐機構——基層黨組織的積極作用。
基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國上市民營公司數據,考察了黨組織抑制企業高管腐敗的具體機制和效果。結果發現:基層黨組織能夠通過“清和親”的廉潔文化建設以及參與公司治理的方式,積極推動民營企業進行廉潔組織文化建設,同時有效監督高管行為,進而實現抑制高管腐敗(包括顯性的違規行為和隱性腐敗)的積極作用。進一步,黨組織能夠弱化高管通過權力以及家族控制權來攫取私利的負面作用,進而減弱高管權力和家族涉入的不利影響。
本文具有明顯的政策啟示:首先,對于民營企業自身而言,盡管在制度轉型前期,其可以通過非正式的政治關系或非生產性的尋租行為來獲得資源、市場準入和政策優惠,但隨著制度的完善以及反腐敗的深入,過去的非正式關系和尋租行為將失去其正當性和合法性。但不可否認的是,組織惰性的存在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及高管仍然無法擺脫過去的慣性思維——通過腐敗來謀取私利。此時,除了提高道德品質以及約束自身行為以外,進一步完善現代公司治理制度變得尤為重要。在這一過程中,響應《公司法》和《黨章》的要求,滿足黨組織設立標準的民營企業應該及時響應號召,在條件允許范圍內積極推動內部黨組織的建立。一方面能夠通過黨組織具有的組織資源優勢來幫助企業獲得必要的成長空間,更重要的是利用其具有的引導、監督、協調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優勢,推動企業廉潔組織文化的形成并對高管權力進行有效監督和約束。由此,黨組織能夠作為企業內部控制機制的有效補充,發揮協同治理腐敗的積極作用。其次,對于執政黨和政府而言,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清和親”的新型政商關系的構建,從根源上消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則可以積極推進各類民營企業內部基層黨組織以及上級黨組織的建設工作,充分發揮黨組織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態化的治理功能,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進而預防和遏制企業腐敗行為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