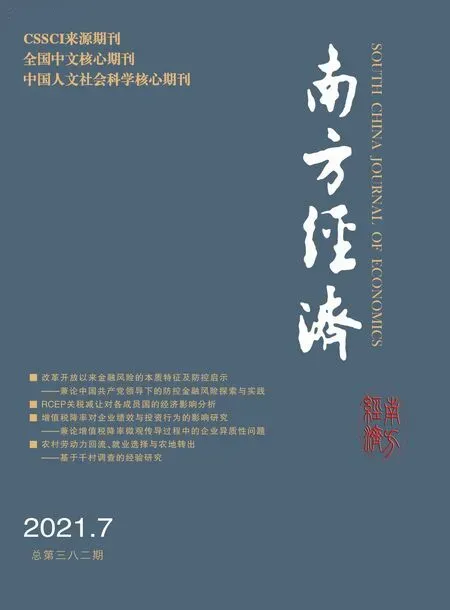女性是出色的股票交易者嗎?一個實驗研究
曹 倩 牛曉飛 李建標
一、引言
金融市場存在性別比例失衡問題。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披露的統計年鑒顯示,從2007年開始我國女性投資者占比逐年減少,由2007年的45.85%縮減至2015年的43.76%(1)由于2015年以前,我國實行一人一戶限制,并且投資者一般會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時開戶,因此,上海證券交易所提供的股票投資者狀況,基本上能反映我國A股個人投資者的整體狀況。自2015年4月13日起我國A股市場全面放開一人一戶限制,自然人可開立多個深A和滬A股賬戶。。金融市場環境彌漫著“男子氣概”文化氣息。
現有研究性別差異的行為金融學文獻,發現了與金融市場交易行為相關的三方面情形:第一,女性比男性顯得過度不自信(Barber and Odean,2001),她們交易股票的頻率較低(Fellner and Maciejovsky,2007)。第二,女性比男性更為風險厭惡(Croson and Gneezy,2009),她們傾向于投資更少比例的風險資產(Hariharan et al.,2000)。第三,女性更為規避與其他投資者競爭(Niederle and Vesterlund,2007),并且擁有較少的金融知識(Driva et al.,2016),她們不愿意參與股票投資(Bannier and Neuberty,2016)。然而,這些研究并沒有很好地回答男性與女性投資者股票交易決策是否存在差異。與男性相比,女性投資者是否是更出色的股票交易者?她們是否擁有較少的股票交易決策偏見?目前,這些問題尚存在爭議。
為此,本文以處置效應為研究視角,重點考察男性和女性投資者股票交易決策偏見特征及其影響機理,旨在回答女性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決策是否優于男性。處置效應(Disposition Effect)是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決策偏見,它是指投資者傾向于過早賣出盈利的股票、過久持有虧損的股票(Shefrin and Statman,1985)。即使盈利股票的平均超額收益率高于虧損的股票,投資者仍然會樂于處置盈利的股票(Odean,1998)。
事實上,Summers and Duxbury(2012)強調情緒對投資者處置效應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處置效應來源于正性情緒和負性情緒間的情緒平衡,既包括預期情緒,也包括體驗情緒。實驗中,他們通過改變投資者的股票購買選擇權來控制投資者的情緒體驗,研究發現感知后悔導致投資者繼續持有虧損股票。李建標等(2019)也認為感知后悔是產生處置效應的關鍵因素,他的實驗研究發現感知后悔對投資者處置效應有顯著正向作用。
基于此,本文認為投資者感知后悔對股票交易決策起著決定作用,如果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那么其內在機制可能是感知后悔(2)目前心理學文獻多局限于對情緒的性別差異進行解釋,并不關注其對行為的驅動作用。正如Elster(1998,p.47)所說,“心理學對情緒的研究并沒有關注情緒是如何驅動行為的。相反,他們嘗試識別情緒產生的根源。一定程度上,心理學家通常關注的是行動傾向,而不是觀測到的行為。”而行為金融學文獻較少關注情緒的性別差異對個體行為的潛在影響(楊曉蘭和高媚,2018;周業安,2019)。。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情緒存在性別差異(Else-Quest et al.,2012)。不論在東方文化中,還是在西方文化中,女性都被視為更為情緒化的性別(Belk and Snell,1986)。女性具有情緒識別(Hall,1978)和情緒記憶(Fujita,1991)優勢。在股票交易中,女性的情緒識別和記憶優勢,可能導致她們擁有更多的情緒體驗,從而做出非理性的股票交易決策。比如,在遭受資本損失時,女性的感知后悔程度會高于男性,因此她們更不愿意賣出虧損的股票。
為了厘清處置效應的性別差異以及影響機理,本文采用Frydman and Rangel(2014)的實驗設計。Frydman and Rangel(2014)實驗設計的關鍵是每個股票價格變化服從正自相關性,只要股票的價格上漲,理性的被試將會買入或者持有股票,這跟處置效應的交易策略完全相反。進一步,本文收集被試報告的感知后悔數據,比較男性與女性的后悔程度,從而深入剖析感知后悔的性別差異對處置效應的影響。最后,我們通過一個田野實驗對研究結果的穩健性進行了檢驗。
本文可能的貢獻之處有三個。第一,本文厘清了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影響機理(3)值得注意的是,感知后悔在性別和處置效應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其它可能的中介變量(比如損失厭惡、認知失調和自我控制等)也可能作用于處置效應的性別差異(Shefrin and Statman,1985)。。雖然現有文獻探討了處置效應的性別差異(Barber et al.,2007;Da Costa et al.,2008;Cheng et al.,2013),但是這些研究對其內在影響機理的關注較少。Rau(2014)實驗研究發現,損失厭惡導致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基于李建標等(2019)的研究,本文則實驗檢驗了感知后悔對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作用,從而補充了Rau(2014)的研究(即豐富了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理論解釋),并進一步擴展了李建標等(2019)的研究(即從檢驗感知后悔與處置效應二者之間關系到檢驗投資者性別、感知后悔與處置效應三者之間關系)。第二,本研究以中國A股個人投資者為研究對象,發現中國A股個人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我們的研究結果與Rau(2014)以及Cheng et al.(2013)的研究結論相一致,與Barber et al.(2007)的研究結論不一致(4)具體分析請見總結與討論部分。。第三,本文補充了國內有關處置效應的實證研究,加深了對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認識。國內一些學者則利用投資者個人賬戶數據或證券市場公開交易數據,檢驗了我國個人投資者的股票交易行為和交易策略(史永東等,2009)、處置效應的產生條件以及處置效應中區分盈利和虧損的參考價格選擇(李學峰等,2011),本研究則實驗檢驗了處置效應的性別差異及其內在影響機理。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相關文獻和研究假設;第三部分為實驗設計,主要介紹了實驗基本原理、貝葉斯投資者的股票交易策略以及處置效應的測量方法;第四部分為實驗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穩健性檢驗,這部分我們以非學生被試為研究對象進行了一項田野實驗研究,進一步檢驗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的研究結論是否穩健;第六部分為結論與建議。
二、相關文獻與研究假設
處置效應是投資者進行股票交易的非理性偏差行為。迄今為止,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處置效應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國家、不同種類的資產和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如Odean(1998)、Grinblatt and Keloharju(2001)、Feng and Seasholes(2005)、Brown et al.(2006)分別發現了美國、芬蘭、中國和澳大利亞金融市場中的處置效應現象;Odean(1998)、Heath et al.(1999)、Genesove and Mayer(1997)、Locke and Mann(2005)分別研究了股票、股票期權、房地產和期貨資產中的處置效應現象;Odean(1998)、Shapira and Venezia(2001)分別研究了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現象。
早期研究主要對不同類型的投資者進行分類研究,初步發現了一些與處置效應相關的投資者特征。例如,與專業投資者相比,個體投資者的處置效應更高(Shapira and Venezia,2001);不成熟市場的投資者處置效應更高(Chui,2001)。始于Feng and Seasholes(2005)、Dhar and Zhu(2006),一些文獻嘗試從個體層面剖析影響處置效應的投資者特征。Feng and Seasholes(2005)發現隨著投資者股票交易經驗和股票操作老練度的提升,他們的處置效應會顯著降低,這表現為投資者會愿意處置虧損股票,而且處置盈利股票的比例也大幅減少。除了股票交易經驗,Dhar and Zhu(2006)還檢驗了個體投資者的收入和職業對處置效應的影響,他們發現高收入和從事專業性工作的投資者,處置效應更低。Calvet et al.(2009)發現富裕且持股多樣化的投資者處置盈利股票的意愿較弱,相反,他們更愿意賣出虧損的股票。Da Costa et al.(2013)實驗檢驗了股票交易經驗與處置效應之間的相關關系。與以上實證研究結論相一致,他們的實驗結果表明機器人被試不存在處置效應,無交易經驗的學生被試和有交易經驗的非學生被試均存在處置效應,并且有交易經驗的非學生被試處置效應更低。
(一)處置效應的性別差異
股票交易經驗和財富是投資者的外在特征,而個體投資者的性別是天生的。現有針對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文獻研究并沒有得到統一的研究結論。Rau(2014)以德國本科生被試為研究對象,實驗研究發現女性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具體地表現為男性與女性在處置盈利股票上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處置虧損股票。與Rau(2014)的研究結果相一致,Cheng et al.(2013)以中國臺灣個體投資者進行實證研究也發現,男性比女性更愿意處置虧損的股票,因此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
然而,Da Costa et al.(2008)以巴西本科生被試為研究對象,實驗研究發現處置效應并不存在性別差異。Barber et al.(2007)以中國臺灣個體投資者股票交易數據為研究樣本也發現雖然男性和女性均存在處置效應,但二者差異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基于以上文獻研究結果,提出如下兩個備擇假設:
假設1a:女性和男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不存在顯著差異。
假設1b: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投資者。
(二)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影響機理
性別是個體內部基本的生物因素之一。已有研究發現,情緒加工存在性別差異,這不僅體現在女性的情緒識別和記憶優勢,還表現在女性較差的負性情緒管理能力(5)情緒管理(Emotion Regulation)是指個體對情緒發生、體驗與表達施加影響的過程(Gross,1999)。。男性與女性在情緒體驗和情緒管理上存在的顯著差異,可能與其先天的腦—生理基礎有關。Chen et al.(2007)發現,在大腦單位容積內,女性灰質比更高,而男性白質比更高。灰質主要負責認知加工,女性的情緒加工優勢可能與其單位容積內的灰質比更高有關(Gur et al.,1999)。Gur et al.(2002)對男性和女性的前額葉和顳葉邊緣系統區域體積進行研究,發現女性具有更大的眶額皮層體積。眶額皮層是典型的情感聯結區域,與情緒的主觀體驗密切相關。McRae et al.(2008)研究了男性與女性負性情緒調節的神經機制差異。他們發現在負性情緒調節過程中,男性比女性杏仁核活動減少的更多,且卷入較少的前額葉區域活動。進一步,Mak et al.(2009)發現在控制負性情緒時,男性的左背外側前額葉、外側眶額皮層和右前扣帶回等區域有更強的活動,而女性僅僅在左內側眶額皮層——與情緒評價和體驗相關的腦區——有更多活動。這為女性較差的負性情緒管理能力提供了直接的神經機制證據。
認知神經科學和神經生理學的研究表明女性具有情緒加工優勢,并且女性的負性情緒管理能力較差。一些文獻依據情緒管理理論來解釋情緒體驗對個體決策的不同影響。例如,Seo and Barrett(2007)發現投資者提高識別、區分情感的能力以及增強對決策偏見的控制力,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Fenton-O’Creevy et al.(2011)定性研究了情緒管理策略對投資者股票交易決策的影響,結果顯示個體調節自身情緒狀態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其交易行為和投資績效不同。Hariharan et al.(2015)的實驗研究為個體投資者情緒管理、情緒體驗與股票交易決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他們發現情緒管理策略不僅降低了投資者的情緒體驗水平,還有利于投資者做出期望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交易決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如果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高于男性投資者,那么其影響機理可能是感知后悔。在股票交易決策過程中,女性的情緒加工優勢,可能導致女性投資者擁有更多的情緒體驗,而女性先天較差的情緒管理能力,使得她們難以控制情緒體驗對股票交易決策的不利影響,尤其在遭受資本損失時,女性會感知更高程度的后悔程度,從而做出非理性地交易行為,即過早賣出盈利的股票和過久持有虧損的股票。
假設2:如果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那么其內在影響機理是感知后悔。
三、實驗設計
(一)實驗原理
本文實驗設計基于Frydman and Rangel(2014)。實驗中,被試的任務是在看到股票A、股票B或者股票C的價格變動信息后,選擇是否交易股票。被試在做出股票交易決策前,需要報告自己的感知后悔程度。
整個實驗開始時,每個被試持有股票A、股票B和股票C各一股,并擁有50 ECUs(Experimental Currency Units,簡稱ECUs,代表實驗貨幣)的現金。每只股票的初始價格均為100 ECUs。實驗總共進行45期(6)為了控制截止期效應,我們告訴被試實驗進行n期。。每期,計算機從三只股票中隨機抽取一只,在被試的計算機屏幕上更新其價格。為了讓被試獲得每只股票的價格走勢信息,前9期他們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只會看到股票的價格變動情況。從第10期開始,被試看到某只股票的價格更新信息后,首先需要報告自己的后悔程度(“要是我不賣它就好了”或者“要是我不買它就好了”,1-7級量表),然后選擇是否交易股票(7)Lin et al.(2006)采用7級量表調查研究了后悔情緒對投資者股票交易決策的影響。我們借鑒Lin et al. (2006)和Li et al.(2018)對投資者后悔的測量方法,每期被試在做出股票交易前,讓他們報告對先前交易結果的感知后悔程度。。每期,如果被試持有股票,那么需要回答“要是我不買它就好了”的贊成度,然后選擇是否賣出;如果被試沒有持有股票,那么需要回答“要是我不賣它就好了”的贊成度,然后選擇是否買入。被試在計算機屏幕上會看到更新的是哪只股票、股票的最新價格、漲跌值、買入價格或賣出價格以及可用現金。
每期,僅有一只股票被隨機選中更新價格,沒有被選中的另外兩只股票,它們的價格在本期保持不變。被試每只股票最多持有一股,不允許賣空股票。為避免流動性限制,被試的現金不足時,可負債購買股票,負債額會從收益中扣除(8)充足的初始稟賦和最多持有一股的限制,使得被試在實驗最后幾乎不可能為負收益。。
每只股票的價格變動均由獨立的兩狀態(好狀態和壞狀態)馬爾可夫鏈決定。實驗開始時,每只股票的市場初始狀態隨機確定(0.5的可能為好狀態,0.5的可能為壞狀態)。假設T期,股票i的價格為Pi,T,市場狀態為Si,T,Si,T{好狀態,壞狀態}。T+1期,如果更新價格的不是股票i,那么股票i在T+1期的市場狀態Si,T+1=Si,T,股票價格Pi,T+1=Pi,T。如果T+1期更新價格的是股票i,那么股票i在T+1期的市場狀態Si,T+1=Si,T的概率為0.8,Si,T+1≠Si,T的概率為0.2。此時,如果Si,T+1為好狀態,那么T+1期股票i上漲的概率為0.6,下跌的概率為0.4;如果Si,T+1為壞狀態,那么T+1期股票i上漲的概率為0.4,下跌的概率為0.6。i股票價格的漲跌值服從{5 ECU,10 ECUs,15 ECUs}上的獨立均勻分布。
整個實驗過程中,被試均不知道每只股票的市場狀態,他們必須從股價的走勢來推測股票的好壞狀態。為了便于比較被試的交易行為和控制被試對未來股價的預期,與Weber and Camerer(1998)以及Frydman and Rangel(2014)的實驗設計相一致,我們預先設定每個股票的價格走勢。另外,為了排除股票價格走勢對被試買賣行為產生的潛在影響,我們使用2個系列的股票價格,主要區別是股票A的價格。圖1是實驗中被試觀測到的不同股票價格的走勢情況。價格系列1中三只股票為A1、B和C,價格系列2中三只股票為A2、B和C,期次均為45期。
Frydman and Rangel(2014)實驗設計的關鍵是股票的價格服從正自相關性,股票本期的價格上漲,那么它很可能是好狀態,如果是好狀態,那么它下期仍有80%機會是好狀態,因此股票價格繼續上漲的可能性大于下跌的可能性。這樣,如果被試是理性的,股票價格上漲時,最優的策略是持有,股票價格下跌時,最優的策略是賣出,這與處置效應的交易策略完全相反(9)然而,實驗中持有均值反轉信念的被試會非理性的認為股票價格上漲(下跌)到一定程度會逐漸下跌(上漲),他們也會處置上漲的股票,買入下跌的股票。采用與本文相同的實驗設計,Frydman and Camerer(2016)對比了顯示股票價格在未來期次最可能的漲跌情況和不顯示股票價格在未來期次最可能的漲跌情況設置中,被試的處置效應差異,結果發現顯示股票價格在未來期次最可能的漲跌情況可以部分減少被試的處置效應,但他們的交易行為仍然大幅偏離于最優決策,這表明均值反轉信念并不能完全解釋處置效應。在此基礎上,為了最大程度地排除被試的均值反轉信念,每期我們通過↑或者↓箭頭來提示被試股票價格在未來期次最可能的漲跌情況。。
45期期末,被試持有的股票將以其最新價格全部賣出。我們給予被試金錢激勵來誘導他們做出收益最大化的交易行為。實驗結束后,被試獲得的實驗幣總數為Y,則他們的最終收益是:Y/20元+10元(出場費)。被試的收益范圍28元到50元,平均收益31.23元。實驗通過Z-tree軟件在計算機上進行(Fischbacher,2007)。整個實驗大約持續60到70分鐘。
實驗在南開大學澤爾滕實驗室進行。132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參與了實驗(男性66名,女性66名;年齡范圍19到25歲,平均年齡21.66)。63名被試(男性27名,女性36名)參與價格系列1實驗,69名被試(男性39名,女性30名)參加價格序列2的實驗(10)不同價格系列和不同場次的實驗,被試的股票交易決策無顯著差異(所有p值均大于0.30)。因此,我們在后續分析中不再考慮價格系列對處置效應的影響。。
(二)處置效應的測量
每次當投資者面臨一個股票賣出機會時,他的決策可以分為四類:實現盈利(Realized Gains)、實現虧損(Realized Loses)、賬面盈利(Paper Gains)和賬面虧損(Paper Loses)。以股票購買價格為參照點,股票最新價格高于購買價格時,投資者賣出股票,為實現盈利,不賣出,為賬面盈利;股票最新價格低于購買價格時,若投資者賣出股票,為實現虧損,不賣出,為賬面虧損。統計每一個投資者賬戶中實現盈利、實現虧損、賬面盈利和賬面虧損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實現盈利率(Proportion of Gains Realized)和實現虧損率(Proportion of Loses Realized)。即實現盈利率=實現盈利/(實現盈利+賬面盈利);實現虧損率=實現虧損/(實現虧損+賬面虧損)。Odean(1998)通過計算股票的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之差來測量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即:處置效應=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
我們沿用Odean(1998)方法同時計算了調整處置效應。即,首先測量每個被試的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然后減去相應價格系列下貝葉斯投資者的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從而計算出調整的處置效應。之所以計算調整的處置效應,是因為:一是讓不同價格系列下的處置效應具有可比性,二是更清晰地比較每個被試的處置效應。在下文的數據分析中,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均為調整指標,即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均減掉了貝葉斯投資者的相應數據。
貝葉斯投資者的交易策略是,當本期更新的股票價格上漲時,持有股票,當本期更新的股票價格下跌時,賣出股票。根據貝葉斯投資者的交易策略,可以計算出貝葉斯投資者的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即:實驗中對于價格系列1和價格系列2,貝葉斯投資者的實現盈利率分別為0.235和0.200,實現虧損率均為1。如果投資者存在處置效應,調整后的處置效應值大于0。調整后的處置效應值越高,被試的處置效應越大。
四、實驗結果
(一)女性與男性的處置效應
表1是男性與女性被試股票交易決策的描述性統計。由表1可知,所有被試實現盈利的平均次數為3.221次,實現虧損的平均次數為1.543次,賬面盈利的平均次數為6.422次,賬面虧損的平均次數為8.245次。實現盈利率和實現虧損率的均值分別為0.220和-0.762。被試處置效應的范圍為[-0.027,1.800],均值為0.982,顯著高于0(t值為27.443)。4.5%(4男,2女)的被試,不存在處置效應;95.5%(62男,64女)的被試,存在處置效應。這說明95.5%的被試更愿意賣出盈利的股票,更不愿意賣出虧損的股票。

表1 女性與男性處置效應描述性統計
男性被試實現盈利和實現虧損股票的平均次數為3.152和1.686,與女性被試的3.282和1.410均沒有顯著差異(雙尾Mann-Whitney檢驗,z值分別為 0.571和1.183,p值分別為0.541和0.316)。女性被試賬面虧損的平均次數為9.243,顯著高于男性被試(7.243)(雙尾Mann-Whitney檢驗,z=2.402,p=0.017)。與此相反,女性被試賬面盈利的平均次數(4.591)顯著低于男性被試(8.254)(雙尾Mann-Whitney檢驗,z=4.283,p<0.01)。這就導致女性被試實現盈利率(0.329)顯著大于男性被試(0.115)(雙尾Mann-Whitney檢驗,z=4.864,p<0.01),實現虧損率(-0.814)顯著小于男性被試(-0.703)(雙尾Mann-Whitney檢驗,z=2.103,p=0.037),即女性被試的處置效應(1.132)顯著高于男性被試(0.822)(雙尾Mann-Whitney檢驗,z=4.785,p<0.01)。
圖2為男性和女性處置效應的累計分布圖。由圖2可知,77.273%(51名)男性被試的處置效應值小于1,而女性被試的這一比例僅為24.245%(16名)(雙尾Kolmogorov-Smirnov檢驗,p<0.01)。

圖2 女性與男性處置效應累計分布圖
進一步,依據處置效應的測量方法,被試的股票交易行為可以分為不同的決策類型。貝葉斯投資者的交易策略是當股票價格上漲時,持有股票,賬面盈利或賬面虧損是最優的決策;當股票價格下跌時,賣出股票,實現盈利或實現虧損股票是最優的決策。我們根據這一原則統計了男性和女性不同決策類型的最優和非最優交易數量。
圖3為不同決策類型下男性和女性股票交易決策的最優和非最優數量。男性與女性的非理性決策主要集中于實現盈利和賬面虧損,而理性決策主要體現在實現虧損和賬面盈利。女性在實現盈利和實現虧損中,非理性決策分別占比76.036%(165/217)和26.041%(25/96),均顯著高于男性(55.777%,116/208;11.111%,12/108)(所有的p值均小于0.01)。而男性與女性在賬面盈利中,非理性決策分別占比14.440%(80/544)和17.050%(52/305),在賬面虧損中,非理性的決策分別占比56.540%(268/474)和56.677%(348/614)。在賬面盈利和賬面虧損中,男性與女性非理性決策的比例不存在顯著差異(所有的p值均大于0.10)。

圖3 女性與男性股票交易決策分布圖
總之,女性被試實現盈利率顯著高于男性,實現虧損率顯著低于男性,導致女性被試的處置效應高于男性。具體地,男性與女性實現盈利和實現虧損的平均數量沒有差異,但是女性被試賬面虧損的平均數量顯著高于男性,而賬面盈利的平均數量顯著低于男性,即女性被試更多地持有虧損股票,更多地賣出盈利股票。假設1b得到驗證。假設1a沒有得到驗證。另外,我們發現男性與女性處置效應的差異,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較多地非理性持有虧損股票,而男性較多地理性持有盈利股票。雖然男性與女性實現盈利或實現虧損的決策數量沒有差異,但是男性投資者的賣出決策要顯著優于女性。
(二)男性與女性處置效應差異的影響機理
緊接著,我們分析了男性與女性處置效應差異的影響機理。首先,我們統計并對比了男性和女性被試報告的感知后悔均值。總體來說,女性投資者的感知后悔程度顯著高于男性(女性=3.572,男性=3.323,雙尾Mann-Whitney檢驗,z=1.713,p=0.089)。
表2為不同決策類型下男性和女性被試的感知后悔程度。由表2可知,在遭受資本損失且選擇繼續持有股票時,女性的后悔程度均顯著高于男性(女性=4.648,男性=4.372,差值為0.276,雙尾Mann-Whitney檢驗,p=0.027)。在面臨資本收益且選擇賣出股票時,女性的后悔程度均顯著小于男性(女性=2.016,男性=2.486,差值為-0.470,雙尾Mann-Whitney檢驗,p<0.01)。而其它的決策類型,男性與女性感知的后悔并沒有顯著差異(所有的p值均大于0.50)。

表2 女性與男性感知后悔描述性統計
表3為男性和女性感知后悔與處置效應的相關系數(Spearman’s rho)。由表3可知,女性投資者的感知后悔與實現虧損率顯著負相關(r=-0.393, p<0.01),與實現盈利率顯著正相關(r=0.334, p<0.01),并且與處置效應顯著正相關(r=0.553, p<0.01)。對于男性投資者來說,感知后悔和感知失望與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處置效應均不相關(所有的p值均大于0.20)。

表3 女性與男性感知后悔與處置效應的相關系數
為了驗證感知后悔對男性和女性處置效應影響的中介作用,我們進行了OLS回歸分析。表4是針對所有被試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的回歸分析(11)我們進一步進行了如下回歸分析。第一,我們剔除了第10期數據和前期沒有交易股票的子樣本數據,發現核心研究結論依然穩健。第二,我們以是否實現盈利,以及是否實現虧損的虛擬變量作為因變量,進行了Probit回歸分析,發現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具有正向作用、對實現虧損具有負向作用。第三,我們以前一期的感知后悔作為自變量,發現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和實現虧損的影響效應沒有發生變化。鑒于篇幅原因,這些回歸分析結果沒有在正文中列示,如需要請向作者索要。。表5是女性對感知后悔的回歸分析。感知后悔為實驗中投資者報告的后悔程度均值。女性為虛擬變量,取值1為女性,0為男性。女性×感知后悔為女性和感知后悔的交叉項。另外,我們控制了投資者的損失厭惡和交易經驗。損失厭惡采用投資者選擇安全選項的彩票數量來衡量(Rau,2015),取值范圍為0到10。交易經驗為虛擬變量,取值1代表有炒股經歷,否則為0(12)在回歸方程(1)、(2)和(3)中的股票交易經驗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股票交易經驗會減少投資者賣出盈利股票比例,這與現有的研究結論相一致(Feng and Seasholes,2005;Dhar and Zhu,2006)。另外,在回歸方程(4)、(5)和(6)中的損失厭惡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說明投資者越損失厭惡,他們越不愿意賣出持有的虧損股票,這與Rau(2014)的研究結論相一致。。
表4中,在回歸方程(1)、(4)和(7)中為女性對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的回歸分析。女性對實現盈利率和處置效應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96和0.927,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女性對實現虧損率的回歸系數為-0.706,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即:與男性投資者相比,女性投資者更不愿意賣出虧損的股票,更愿意賣出盈利的股票,因此處置效應更高。

表4 性別與感知后悔對股票交易決策的回歸分析
在回歸方程(2)、(5)和(8)中,我們加入感知后悔變量,發現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率和處置效應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02和0.274,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感知后悔對實現虧損率的回歸系數為-0.163,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具有顯著影響。更為重要地是,我們發現在回歸方程(2)、(5)和(8)中,當我們加入感知后悔變量后,女性對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的回歸系數分別由0.396變為0.214、-0.706變為-0.431、0.927變為0.421。
另外,在回歸方程(3)、(6)和(9)中,我們加入女性和感知后悔的交叉項,發現女性×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處置效應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43、0.017和0.108,均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與男性相比,女性的感知后悔對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和處置效應的影響更強。
表5回歸方程(1)中為女性對感知后悔的回歸分析,女性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06,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在回歸方程2中,我們加入交易經驗與風險態度控制變量,女性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12,在5%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與男性相比,女性的感知后悔程度更高。

表5 性別對感知后悔的回歸分析
圖4是根據表4和表5繪制的感知后悔在性別與處置效應之間中介作用的路徑圖。由圖可知,感知后悔在性別和處置效應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說,投資者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的影響機理在于感知后悔。假設2得到驗證。

圖4 感知后悔在性別與處置效應之間的中介作用
五、穩健性檢驗
我們的實驗室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感知后悔在女性投資者和處置效應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但是,一方面,實驗室實驗研究以學生為被試,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外部有效性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實驗中我們讓被試報告自己的感知后悔程度,然后做出股票交易決策,這可能會誘導被試的后悔情緒,從而觀測到男性與女性處置效應存在差異。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進行了一項田野實驗研究,以檢驗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的結果是否穩健。具體來說,我們招募了117名有股票交易經驗的非學生被試,其中男性投資者60名,女性投資者57名(13)為了控制投資者職業對處置效應的影響,我們招募的117名投資者均為非專業投資者。。被試通過問卷星在網上完成實驗。被試在完成實驗后獲得一份微信紅包,金額從10元到20元不等。
我們借鑒Aspara and Hoffmann(2015)的實驗設計,首先讓被試閱讀有關自己股票投資情況的說明,即“一年前,你購買了價值5000元人民幣的股票,即X股票3000元和Y股票2000元,現在兩只股票的價值變動情況如下:(1)股票X的價值由3000元下降到2600元;(2)股票Y的價值由2000元上漲到2600元。因此,現在你持有兩只股票的價值均為2600元,總價值為5200元。”閱讀完股票投資情況之后,被試需要分別評價自己現在賣出股票X和股票Y的意愿:“我愿意賣掉股票X”、“我愿意賣掉股票Y”。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進行度量,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股票X為虧損股票,股票Y為盈利股票(14)為了避免實驗者需求效應,我們增加了一些不相關任務,這些不相關任務包括讓被試完成如何在儲蓄、股票和債券之間進行投資組合分配,以及在完成投資組合分配后根據市場狀況計算個人投資收益等。另外,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證股票交易決策的真實性,我們告知被試股票X和股票Y為兩只真實的上市公司。。
實驗最后,讓被試報告自己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包含性別、年齡、家庭月收入和股票交易年限。家庭月收入為有序分類變量,1代表小于等于4000元,2代表4001元到15000元,3代表15001元到30000元,4代表30000元以上。股票交易年限為有序分類變量,1代表一年,2代表兩年到五年,3代表五年以上。被試的平均年齡為30.931歲,59%被試的股票交易經驗為兩年到五年,家庭月收入集中于15001元到30000元(占比48%)。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女性投資者和男性投資者在年齡、家庭月收入以及股票交易年限上均無顯著差異(所有的p值均大于0.35)。
圖5為女性與男性處置盈利與虧損股票意愿程度。女性投資者處置盈利股票意愿程度為6.033(SE=0.163),男性投資者處置盈利股票意愿程度為4.403(SE=0.215),二者差異顯著(雙尾Mann-Whitney檢驗,z=5.305,p<0.01)。女性投資者處置虧損股票意愿程度為1.267(SE=0.075),男性投資者處置盈利股票意愿程度為1.842(SE=0.122),二者差異顯著(雙尾Mann-Whitney檢驗,z=-3.918,p<0.01)。這表明女性投資者比男性投資者更愿意處置盈利股票,更不愿意處置虧損股票。

圖5 女性與男性處置盈利與虧損股票意愿程度(誤差線為±均值的標準誤)
表6是女性投資者對處置盈利股票和虧損股票意愿的回歸分析。女性投資者為虛擬變量,取值1為女性,0為男性。另外,我們控制了投資者的年齡、家庭月收入和股票交易年限。回歸方程(1)和(3)分別為單獨放入女性投資者的回歸分析,方程(2)和(4)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分析。表6回歸方程(1)和(2)中為女性投資者對實現盈利股票意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629和1.015,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即:與男性投資者相比,女性投資者賣出盈利股票的意愿更高。

表6 女性投資者對處置盈利股票和虧損股票意愿的回歸分析
回歸方程(3)和(4)中為女性投資者對實現虧損股票意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575和-0.555,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即:與男性投資者相比,女性投資者賣出虧損股票的意愿更低。因此,我們實驗室的研究結果依然穩健。假設1b得到驗證。
六、總結與討論
本文以處置效應為研究視角,實驗檢驗了女性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決策偏見特征及其內在影響機理,旨在回答女性的股票交易決策是否優于男性,她們是否是更好的股票交易者。主要研究結論為:1女性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決策并不優于男性,這主要表現為女性的處置效應顯著高于男性。在股票交易過程中,女性會較多的非理性持有虧損股票,而男性會較多的理性持有盈利股票。雖然男性與女性被試賣出盈利股票和虧損股票的數量沒有差異,但是男性被試的賣出決策要顯著優于女性。2女性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決策更容易受到后悔情緒的影響,偏離理性決策。女性在遭受資本損失且選擇繼續持有股票時,感知的后悔程度顯著高于男性。女性的后悔情緒與實現盈利率、實現虧損率、處置效應顯著相關,而男性的后悔情緒與股票交易決策不具有相關性。3投資者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的影響機理是感知后悔。
雖然Rau(2014)以及Cheng et al.(2013)發現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但是,Da Costa et al.(2008)和Barber et al.(2007)發現處置效應不存在性別差異。Rau(2014)以及Da Costa et al.(2008)對處置效應性別差異不一致的實驗結果,可能與德國和巴西學生被試所處地區的文化有關。另外,由于實證研究不能很好地控制其它變量的干擾(比如股票價格預期、市場環境、交易經驗以及風險態度等),因此,Cheng et al.(2013)以及Barber et al.(2007)雖然都以中國臺灣個體投資者為研究對象,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研究結論。
本文以中國A股個體投資者為研究對象,實驗研究了男性與女性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差異以及影響機理。我們的研究補充了有關股票交易決策偏見性別差異的行為金融學文獻。本文研究發現中國A股個體投資者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女性投資者會較多的非理性持有虧損股票,而男性投資者會較多的理性持有盈利股票,并且女性的股票賣出決策并不優于男性。究其原因在于女性在股票交易過程中感知的后悔程度更高。本文的實驗研究與Rau(2014)的實驗結果相一致,這表明德國和中國A股投資者處置效應均存在性別差異。本文的研究進一步補充了Rau(2014)的研究。Rau(2014)實驗研究發現損失厭惡導致處置效應存在性別差異。本文則實驗發現感知后悔也是產生處置效應性別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