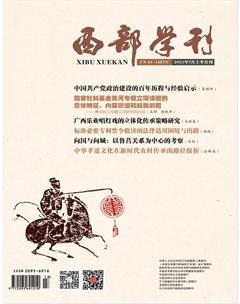小國安全戰略選擇的得與失
摘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數目眾多的小國經常是習慣性被忽略的對象。小國自身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令其形成了對安全的高度重視和與大國截然不同的戰略選擇。小國面臨的安全戰略選擇主要有結盟、集體安全、中立和兩面下注四種。其中,結盟的成本低廉,但易使小國被盟友拋棄甚至喪失主權;集體安全的優勢在于非排他性的安全保障機制,但其內部機制是否能夠充分發揮效力仍需依靠大國合作;獲得大國承認的中立地位能長期維護自身安全,但多數小國因自身地理因素和軍事實力的限制難以效仿;兩面下注能使小國在單極格局下有效地降低次強國的威脅,但需要穩定的單極格局作為依托。因此,小國無論選擇哪種策略,總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自助,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與霸權國或地區大國的良性互動才能保證自身安全。
關鍵詞:小國;安全戰略;戰略選擇;國際體系
中圖分類號:D73/7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3-0053-03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大國處在權力金字塔頂端,是最值得研究的對象。而小國則常常以調節大國關系的砝碼或是大國緩沖區的形象出現在國際關系研究視野中,是習慣性被忽略的對象。實際上,國際社會中占主體地位的反而是數量眾多的小國。對大國的研究偏好導致學界對小國的研究同樣使用分析大國外交政策的方法,而針對小國特點進行的研究和文獻較少。小國由于自身實力不足帶來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得其戰略選擇余地十分有限,更加依賴自身對安全戰略的選擇和對國際體系力量對比變化的研判。大多數情況下小國只能選擇追隨大國腳步,在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盡量尋求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小國如何選擇安全戰略才能最大限度保護自身安全?這些安全戰略在具體運用的過程中又有怎樣的優勢或限制?這些問題正是本文對小國安全戰略選擇得失的思考。
一、小國概念的界定
在討論戰略選擇之前首先要對小國的概念進行界定。當前學界尚未形成對小國的統一定義。經整理,界定小國概念的方法可以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1.主觀法。羅伯特·羅斯坦(ROBERT L. ROTHSTEIN)認為,“小國是由自身和別人的看法界定的,而不是根據小國本身所擁有或缺少的特性。”[1]羅伯特·考恩(ROBERT O. KEOHANE)也提出過類似觀點:“小國的領導人會意識到僅憑自身行動不會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2]主觀法強調觀念上的小國概念而并不加以其他要素的限制,是一種比較粗略的定性分析法。
2.客觀法。多數學者利用客觀因素、具體數據來對小國進行定義。一般來說,可以從領土面積、人口數量、軍事實力或是國民生產總值等數據進行衡量。這樣定量分析的好處是可以對小國進行明確界定,便于開展具體研究。
3.比較法。除上述兩種方法以外,一部分學者認為小國的概念是相對于大國來定義的。張亞中認為:“國際社會中大國和小國的差別應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上才有意義。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3]比較法以大國作為參照物,明確了小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坐標系。
二、小國面臨的安全戰略選擇
(一)結盟
結盟是小國為尋求大國安全庇護最常見的形式,是國家間以協議方式確定的對他國在特定情勢下的安全承諾。小國選擇對外結盟的直接影響因素有二:一是自身軍事實力弱小,不足以承擔戰爭或被入侵的風險;二是盡管一些小國的軍事實力處于較高水平,但由于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自身被次強國環繞,不得不尋求大國的安全庇護。
對小國而言,同大國結盟是一種成本較為低廉的安全戰略。一方面,小國可以將自身有限的資源和精力全部用于經濟發展而非國防和軍備,可以有效降低國內財政預算的壓力,防止因過度發展軍備導致國民生活水平下降。另一方面,與強國結盟是以一種明確方式向其他覬覦小國的鄰國發出的有效威懾信號。霸權穩定論認為,當次強國與霸權國實力相差較大時,次強國沒有挑戰霸權國的強烈意愿,因此同霸權國結盟能有效降低次強國對小國的安全威脅。
但結盟的弊端也體現在盟友選擇、主權讓渡、被牽連或被拋棄等方面。從盟友選擇來看,在單極格局下小國的選擇結盟對象較為簡單,僅需與權力結構金字塔頂端的國家結盟,便能在最大限度上保證自身安全。例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在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瓦解而美國獨大的單級結構下選擇加入北約,享受美國的安全庇護。但在兩極或多極化趨勢下,小國很難決定與誰結盟。一旦結盟戰略發生失誤,不僅無法保證自身生存,甚至會因大國權力競爭而落入被瓜分或成為附庸的下場。當然小國也可以選擇同一些與自身類似的小國結盟,但此類小國間盟約應對風險和威脅的能力均有限,當發生安全危機時最終仍需依靠大國出面調停。從主權讓渡的角度分析,自小國選擇結盟那一刻起,主權便不再完整。小國與大國巨大的實力差距導致大國會以安全作為與小國的談判籌碼。大國會利用小國對安全的根本需求在締約時附加諸多條件。小國往往需要接受大國在本土駐軍,甚至提供軍費等條件。此外,小國還面臨被牽連或拋棄的風險。被牽連指當大國向他國發起戰爭或他國對大國發起戰爭時,盟約的雙向性會強制將無意于參加的小國也拖入戰爭之中。被拋棄則多發生于大國實力下降、戰略收縮之時,一旦大國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性下降,或是自身實力受損,大國便不再愿意維持對小國的安全承諾。
(二)集體安全
集體安全是國際社會以集體力量威懾或制止任何潛在的侵略行為的安全保障機制,原則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4]。這一概念源于“一戰”后各國對均勢政策的反思。小國在制定集體安全政策時通常會選擇全球性的國際組織或是地區性安全組織。
小國選擇集體安全戰略的優勢有四:第一,集體安全具有非排他性。這意味著小國可以同時與多個國家締結了安全契約,無須像結盟一樣擔心被某一特定大國拋棄或是主權過度讓渡而淪為某國附庸的情況。第二,以集體強制力為后盾使締約國內部被有效的沖突管理機制所約束。軍事能力不足的小國在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時可以依托組織內部現有的機制調節兩國爭端,大大降低了訴諸戰爭的可能性。第三,集體安全的內向性使成員國內部沒有特定敵國或敵對集團[5]。與集團對峙不同,集體安全并不是為了防范特定的某一國家而成立,不存在權力爭奪的前提,因此小國不需要擔心被他國牽連。第四,集體安全往往建立在國際法的基礎之上,一旦小國卷入和其他成員國的爭端之中,可以采用調停、仲裁、斡旋等方式在國際法庭上調節爭端。
但在實際運用中,集體安全仍存在弊端。第一,締約國在意識形態上若存在根本性對立會導致締約國間無法采取一致行動,例如冷戰時期的美、蘇。第二,采取此戰略的部分國家缺少國際責任感,在侵略發生后不愿遵守條約采取行動進行反制,同樣會使安全機制失效。第三,成員國間對某一國是否為侵略者或是否已經采取了侵略行為等問題很難達成統一認知。因此新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稱:“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無論多么忠于國際法,都不能以集體安全的方法反對任何時候的任何侵略。”對小國而言,集體安全機制在正常運行時是保護自身安全的最佳選擇。但在國際關系的叢林法則中,集體安全僅僅是一幅大國描繪的美好愿景,實際卻難以達到其最初所承諾的安全目標。
(三)中立
中立的概念可以從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兩種角度定義。在國際法中,中立是指一國選擇不參加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以任何方式援助或支持任何交戰方,因此稱為戰時中立。從國際關系來看,中立一般指的是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就正式的國際制度而言,中立國的締約國要做到“不攻擊或威脅中立國;中立國領土受到攻擊時,應進行武裝干預”[6]。
中立戰略最顯著的優勢是能長期維護小國安全。歷史上有諸多因中立政策而成功保護自身安全的小國。能成為永久中立國的國家大多是在地緣政治上擁有重大意義的緩沖地區,例如瑞士、瑞典、土庫曼斯坦等國。這些國家的中立地位一般由兩種因素決定,即地區大國博弈態勢與自助。在地區大國博弈的過程中,如果不存在霸權國,大國之間往往會采取彼此制衡的政策,在維護自身權力的同時限制競爭對手的實力,即表現為承認一些小國或地區的中立地位,防止對手將小國劃入勢力范圍。當大國間就某小國達成均勢共識且大國間實力對比也未發生顛覆性的改變時,中立國家便應運而生。以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永久中立國瑞士為例,促成其永久中立國地位的因素有二:一是瑞士作為多山內陸國,阿爾卑斯山脈和汝拉山脈是瑞士的天險之地,不會被其他國家作為入侵的第一選擇。二是瑞士國內實行的是“武裝中立”政策,一直保持著全民皆兵、全民動員的民兵制度,并且保持較高的軍備水平[7]。因此在他國眼中,瑞士是一列站在山巔上待命的軍隊,不會主動參與戰爭,但也不能容忍其他國家的入侵。
試圖實施中立戰略的小國受到以下條件的制約:第一,并非所有小國都天然處于易守難攻的自然條件或是重要的地理位置。第二,即便位于重要地理位置,小國也不能完全依靠大國的實力均衡來維護安全。歷史上成功的永久中立國多為軍事上的“小強國”,高度發達的軍備仍是中立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三,小國實施中立政策的前提是在國際體系層面上存在大國均勢且達成了對于小國所處地理位置的中立共識。因此,中立策略在歷史上雖有成功,但大多是不可復制的案例,無法成為小國安全戰略的通用選擇。
(四)兩面下注
兩面下注則是由國際關系學者對金融學中對沖概念進行的理論遷移,是指一種近年來小國面對大國權力競爭,表現出一種既非制衡也非追隨的曖昧態度,試圖在回避風險的基礎上盡量為本國謀取利益的一種新型戰略。選擇兩面下注的小國大多不面臨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在戰略選擇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兩面下注的優勢在于:當國際體系處于穩定的單極格局時,小國與次強國進行更緊密的經濟接觸有助于發展本國經濟,還能順勢將自身的外貿體系嵌入次強國經濟體系之中。加強自身與次強國的經濟相互依賴也是穩定同次強國關系的一劑良藥。此外,小國會通過加入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方式來聯合其他小國同次強國建立緊密的經濟關系。這是因為小國對次強國的崛起目的并不明確,如果次強國在地區上擴大自身勢力,擠壓小國的生存空間,小國可以通過現有的經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次強國進行制衡。另外,在搭上次強國經濟發展便車的同時,小國也能享受到霸權國的安全庇護,并不擔心霸權國拋棄自己。因為霸權國不會坐視某一地區的次強國崛起并成為潛在的霸權競爭者[8]。對霸權國來說,限制次強國崛起成本最低的手段就是維持對小國的安全保護,防止次強國勢力擴張后小國對霸權國產生離心傾向。
兩面下注需要穩定的單極格局作為依托。當小國對次強國經濟依賴增加到一定程度,又恰好此時次強國的實力到達了挑戰霸權國實力的質變點,霸權國為遏制次強國便會以安全問題要挾小國,逼迫小國在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間進行選邊。此時小國就失去了從霸權國和次強國雙方得利的優勢,最終結果往往是戰略失效,小國不得不回到起點重新作出戰略選擇。
三、結論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性決定了體系中的安全是缺乏的,任何國家都需要通過自助來實現安全。小國在內部受到自身物質資源的限制,不能將有限的資源多數用于提升本國的軍事能力。而在外部又受到大國競爭、次強國擴張崛起等體系因素的約束,無法隨心所欲地選擇安全戰略。本文從結盟、集體安全、中立和兩面下注四種常見的小國安全戰略入手,分析了不同選擇下小國的得與失。小國作為國際體系的承受者和參與者清楚大國在國際體系內的主導作用,而大國也明確了解小國可能的安全需求以及小國能為大國提供的戰略價值[9]。因此小國無論選擇哪種安全策略,總是需要自身相對實力的提升,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霸權國或地區大國的良性互動才能保證自身安全。但需要注意的是,實際操作中一國維護自身安全的方式往往為多種戰略的融合或是交替使用,即使是施行永久中立政策的國家也要因國際體系變化而動。明確小國安全戰略選擇背后的邏輯和不同戰略的得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分析小國制定對外政策時的目標。總之,如何靈活地運用上述四種戰略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仍在考驗著小國的政治智慧。
參考文獻:
[1] EE BRAUN,ROBERT L.,ROTH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J].El Colegio De México Centr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1969(1).
[2] KEOHANE R. O.Lilliputians' Dilemma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2).
[3] 張亞中.小國崛起:轉折點上的關鍵抉擇[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9.
[4] 郭學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集體安全體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 王健.論國家自衛權[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5.
[6] 陳翔.析小國安全戰略抉擇及其效應[J].戰略決策研究,2017(1).
[7] 李小寧.瑞士軍刀和“軍國主義”[J].青年博覽,2012(24).
[8] 宋偉.實力轉變理論述評[J].現代國際關系,2016(10).
[9] 陳宇.不丹對印度的極不對稱安全困境:基于小國/弱國對大國/強國的“安全交換”解釋[J].南亞研究,2018(3).
作者簡介:劉稷軒(1997—),男,漢族,天津人,單位為南開大學,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