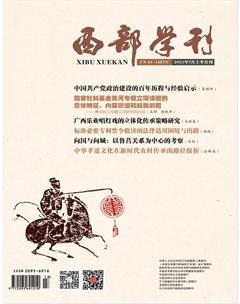淺談對(duì)中華法系的認(rèn)識(shí)
摘要:中華法系是我國在長達(dá)兩千多年封建歷史中形成的法律體系,其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影響深遠(yuǎn)。通過對(duì)《唐律疏議》法律條文的分析和整理,歸納出了中華法系的五個(gè)特征:(一)德主刑輔,禮法結(jié)合;(二)重視教化,寬仁慎刑;(三)家族本位,維護(hù)倫理;(四)貴賤有等,尊卑有序;(五)皇權(quán)至上,政法合一。在兩千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中,中華法系不僅推動(dòng)了古代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如日本、高句麗等法律制度的發(fā)展,而且對(duì)當(dāng)代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對(duì)推進(jìn)國家治理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也具有借鑒意義。
關(guān)鍵詞:《唐律疏議》;中華法系;古代法律
中圖分類號(hào):D92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2095-6916(2021)13-0069-04
在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huì)議上,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為全面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夯實(shí)法治基礎(chǔ)[1]。作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發(fā)展的重要體現(xiàn),中華法系歷經(jīng)兩千多年的發(fā)展積淀,自原始社會(huì)末期至近代,源遠(yuǎn)流長,獨(dú)樹一幟,對(duì)當(dāng)代法治中國建設(shè)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要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近平法治思想,推進(jìn)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對(duì)中華法系加以研究總結(jié),深入挖掘我國深厚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為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法治文化建設(shè)、推進(jìn)國家治理法治化提供有益借鑒。
一、中華法系的歷史概述
(一)中華法系的概念
中華法系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法學(xué)家穗積陳重《論法律五大族之說》一文。關(guān)于中華法系的概念,當(dāng)今法律史學(xué)界通常認(rèn)為,所謂中華法系,就是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huì)的法律制度以及在這種法律制度影響下各國所制定的封建制法律的總稱。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是以傳統(tǒng)中國法律為母法的東亞法系。它源遠(yuǎn)流長、歷史悠久卻從未中斷,具有其他法系所不具備的完整性與悠久性,是研究東方法律文明的典型范例。它不僅是中國法制文化深厚底蘊(yùn)的集中體現(xiàn),也被世界公認(rèn)為體現(xiàn)人類社會(huì)進(jìn)步和法治文明的瑰寶。
(二)中華法系的歷史嬗變
我國在夏商周時(shí)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以習(xí)慣法為基本形態(tài)的封建法雛形,但它并不向廣大民眾公開,法律和司法審判的神權(quán)色彩比較濃厚。在夏朝,得到發(fā)展的主要為刑事法律和軍事法律等部門法。商朝建立后,刑罰、民法制度以及司法體系有了一定的發(fā)展。商朝滅亡后西周建立,國家統(tǒng)治者創(chuàng)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對(duì)中國后世的法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公布成文法的運(yùn)動(dòng)悄然興起,如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國的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等[2]。這標(biāo)志著早期習(xí)慣法進(jìn)一步地向成文法轉(zhuǎn)變。在此期間,李悝制定的《法經(jīng)》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典體例,使封建法制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
秦朝時(shí)期,“以法為本”“專任刑罰”等法家思想大行其道,法律制度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秦朝的律令體例和法律內(nèi)容已經(jīng)相當(dāng)完備,為古代中國法制發(fā)展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兩漢時(shí)期,中國古代法制得到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前期主要是“漢承秦制”。西漢中期,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政策,董仲舒首倡“春秋決獄”的司法原則,開啟了法律儒家化的進(jìn)程,禮的精神逐漸融入法律,形成了中華法系獨(dú)具一格的特點(diǎn)。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shí)期,中國古代法制得到進(jìn)一步完善,“八議”“官當(dāng)”“重罪十條”等已經(jīng)成為成熟的制度。
隋唐時(shí)期,中國古代法制進(jìn)入了成熟時(shí)期和定型階段。唐律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中國封建法制的完備。作為唐律的杰出代表,《唐律疏議》總結(jié)了秦漢以來的立法經(jīng)驗(yàn)和司法實(shí)踐,并在此基礎(chǔ)之上,以儒家思想為指導(dǎo),構(gòu)建起技術(shù)成熟、體系完備的法律體系,達(dá)到了中國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全面體現(xiàn)著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風(fēng)格和基本特征。它不僅成為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而且超越國界,促進(jìn)了東亞、東南亞部分國家的法制發(fā)展,許多學(xué)者認(rèn)為,唐代的法律制度是中華法系完備和最終確立的標(biāo)志。
宋元明清時(shí)期,中國古代法制在唐朝以及五代法制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完善,立法更加成熟,先后出現(xiàn)了《宋刑統(tǒng)》《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著名法典。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發(fā)展,我國封建法制輾轉(zhuǎn)相承,到清朝時(shí)已達(dá)到高度完備,形成完整而系統(tǒng)的法律體系。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我國的封建社會(huì)開始解體,清政府在二十世紀(jì)初變法修律,進(jìn)行法制改革。中華法系隨著西方法制的大量引進(jìn),喪失了獨(dú)立存在的基礎(chǔ),逐漸走向解體。
結(jié)合上文的歸納和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在時(shí)間上,中華法系發(fā)源于夏,奠定于秦,成熟于隋唐,解體于清末。正如中國法制史學(xué)者喬偉教授所說:“中華法系基本上是與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相始終的。”[3]在空間上,中華法系以中國古代封建法律為中心,向外涵蓋包括日本、越南、朝鮮等東亞國家乃至東南亞等諸多地域,在世界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華法系的特點(diǎn)
在理論界,學(xué)者對(duì)中華法系特點(diǎn)的研究和論述不勝枚舉,且說法不一,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劉海年、楊一凡、張晉藩等著名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劉海年、楊一凡教授認(rèn)為,中華法系的主要特點(diǎn)有:在立法上,皇帝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司法上,行政與司法混為一體;在法的形式上,諸法合體,律令格式例并存;在法的內(nèi)容上,寓禮于法,禮法結(jié)合。張晉藩教授在《中華法系特點(diǎn)再議》一文中指出,中華法系的特點(diǎn)包括農(nóng)本主義的法律體系;皇權(quán)至上的法制模式;儒家學(xué)說的深刻影響;引禮入法,法與道德相互支撐;家族法具有重要地位;法理情三者的統(tǒng)一;多民族的法律意識(shí)與法律成果的融合;重教化慎刑罰的人文關(guān)懷等[4]。雖然這些學(xué)者觀點(diǎn)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cè)重,但在一些問題上還是存在共識(shí)的。在本文中,筆者以中華法系的杰出代表——《唐律疏議》為例,歸納了中華法系的特征。
(一)德主刑輔,禮法結(jié)合
在《唐律疏議》中,“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5]15較好地概括了中國古代封建國家治理中德與刑、禮與法的作用關(guān)系。在統(tǒng)治者看來,德禮為國家治理之核心和優(yōu)先手段,刑罰雖然可以禁頑止奸、懲惡除害,但由于其以剝奪生命、殘害身體等手段來實(shí)現(xiàn)其治理目標(biāo),因此只能厲行于一時(shí),否則不利于社會(huì)穩(wěn)定和發(fā)展。所以,以德為主、以刑輔之的法制思想和治國理念便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接受和認(rèn)同。正如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6]。這說明法律具有以刑懲惡的作用,也有著潛在的道德教化之功能。
德治與法治結(jié)合,禮教和刑罰并舉,不僅有利于促進(jìn)古代社會(huì)和諧,緩和社會(huì)矛盾,也有助于實(shí)現(xiàn)有效的國家治理。正是由于兩者交相為用,才使得傳統(tǒng)的法律體系和道德體系,經(jīng)過四千年之久而未發(fā)生斷裂[7]。
(二)重視教化,寬仁慎刑
一是援法而治,重惜民命。援法而治是中華法系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重民思想的產(chǎn)物。歷朝統(tǒng)治者出于維護(hù)統(tǒng)治秩序和推進(jìn)國家治理的目的,大多都堅(jiān)持以民為本的思想,推動(dòng)援法斷罪法律化,使中國古代法制表現(xiàn)出援法而治、重惜民命的特點(diǎn)。《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5]999“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麤細(xì)長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5]995這些條文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援法定罪的法制原則,既樹立了法的權(quán)威,同時(shí)也明確了司法官員的職責(zé),防止他們?yōu)E用私刑、擅作威福,體現(xiàn)了重惜民命的人本主義精神,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寬仁慎刑”的思想。
二是矜老恤幼,寬待婦殘。《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yīng)死者,上請”“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婦人年六十及廢疾,免流配”[5]166-172。之所以對(duì)這些特殊群體減免刑罰,一方面,由于此類群體的人身危險(xiǎn)性和對(duì)統(tǒng)治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大,實(shí)行恤刑對(duì)國家并無大害,另一方面,可以彰顯統(tǒng)治者的“仁愛”,體現(xiàn)其矜老恤幼、寬仁慎刑的本意。同時(shí),針對(duì)犯罪時(shí)間和事發(fā)時(shí)間不同的現(xiàn)實(shí)情況,《唐律疏議》還在正文中規(guī)定,假使有人犯罪時(shí)還沒到七十歲或者沒有發(fā)生疾病,但是到七十歲后或者患有病疾時(shí)才被發(fā)覺,都依照上述老、疾的有關(guān)法律規(guī)定處理。同理,如果有人幼小時(shí)犯罪,長大后被發(fā)覺,也是按照幼小犯罪的有關(guān)規(guī)定處理[5]174。這進(jìn)一步擴(kuò)大了恤刑的適用范圍,體現(xiàn)著鮮明的人文關(guān)懷。在唐以后,歷朝的統(tǒng)治者大多都延續(xù)了唐律中有關(guān)恤刑的法律規(guī)定,并不斷加以完善。中國傳統(tǒng)法制文化中矜老憐幼、為政以仁的思想得到傳承和發(fā)展,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cái)富。
三是存留養(yǎng)親,法外施仁。存留養(yǎng)親,即如果罪犯家里無其他男丁侍奉老人,那么該罪犯就可以獲批延緩或免予執(zhí)行原來判處的刑罰,回家侍奉年老親屬。這一原則在唐朝時(shí)得以定型和正式確立。在《唐律疏議》中,“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yīng)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quán)留養(yǎng)親,謂非會(huì)赦猶流者”[5]148-149等條文對(duì)存留養(yǎng)親做出了明確而全面的規(guī)定,假使罪犯觸及了不屬于“十惡”范圍內(nèi)的死罪,而且家中存在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親無子、孫侍養(yǎng)的情況,是否處以死刑,需上請皇帝裁定,聽候敕令處理。犯了流罪的,也可以權(quán)且留下來侍養(yǎng)尊親。這種制度的設(shè)立,說明立法者對(duì)維護(hù)封建倫理綱常的重視甚至要超過法律,以致法律上的公平有時(shí)還要讓步于孝道。同時(shí),這也使孝道逐漸納入法治軌道,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以仁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和對(duì)天道、國法與人情相融合的追求,對(duì)維護(hù)家庭關(guān)系穩(wěn)定,維護(hù)傳統(tǒng)倫理秩序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三)家族本位,維護(hù)倫理
家族本位是中華法系的一大特色,儒家經(jīng)典《孟子》也有“天下之本在于國,國之本在于家”[8]的論述,在中國古代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里,家庭作為社會(huì)的細(xì)胞,是承擔(dān)國家賦稅、徭役和兵役的基本單位,對(duì)維持社會(huì)穩(wěn)定、鞏固國家統(tǒng)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的法律中,有許多地方都體現(xiàn)了家族本位和維護(hù)倫理的特征。在唐朝,《唐律疏議》中《名例律》提出的“十惡”大罪里,便有“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名。統(tǒng)治者將倫常關(guān)系以法律的方式明確下來,并通過國家強(qiáng)制力對(duì)家族本位加以維護(hù)。根據(jù)這些法律條文,凡是違反家長意愿或者侵犯到家長人身的行為,如詛詈祖父母和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時(shí),子孫“別籍異財(cái)”,另立門戶等,都會(huì)觸犯十惡重罪。同時(shí),法律也賦予家長教令權(quán)、主婚權(quán)以及財(cái)產(chǎn)支配權(quán)等一系列的權(quán)力,并允許家長請求官府代為懲處不孝之子。
此外,唐朝法律在維持家族本位的同時(shí),以倫理為立法之根據(jù),對(duì)親屬相犯和親屬相隱等情況也做出了相應(yīng)規(guī)定。針對(duì)親屬間的侵犯和傷害行為,唐律根據(jù)尊卑長幼之序和服制之親疏遠(yuǎn)近,做出了特別規(guī)定。如《唐律疏議》的《斗訟律》中,便有“諸毆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遞加一等”“若尊長毆卑幼折傷者,緦麻減凡人一等”[5]760-761等規(guī)定。而且,若為卑幼殺傷尊長,則處罰重于常人,且關(guān)系越親,懲罰越重。反之,若為尊長殺傷卑幼,則處罰會(huì)輕于常人,且關(guān)系越近,懲罰越輕。而對(duì)于親屬相隱的情況,《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其事及撼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5]262-264由此觀之,統(tǒng)治者十分重視家族中的倫理道德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維護(hù)以封建家族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在不損害統(tǒng)治階級(jí)根本利益的情況下,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間可以互相隱瞞其罪行而不負(fù)刑事責(zé)任,體現(xiàn)了家族道德倫理與國家法律規(guī)范的統(tǒng)一。
在筆者看來,這些詳密的法律規(guī)定,一方面可以鼓勵(lì)人們維護(hù)家族利益和宗法倫理,以孝事其親,進(jìn)而通過孝與忠之間的互通性和一致性,將家庭倫理移植到政治范疇,讓臣民移孝作忠,從而構(gòu)建起一套“君父同倫”“忠孝一體”“家國同構(gòu)”的社會(huì)格局。另一方面在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huì)中,家長可以幫助官府傳達(dá)政令,催征賦役,管理族眾,督勸農(nóng)桑,這樣一來就能夠有效地降低治理成本,使社會(huì)井然有序。所以說,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倫理,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shí),它也是中華法系的基本構(gòu)成因素,在我國歷史上沿用了數(shù)千年,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四)貴賤有等,尊卑有序
“貴賤有等”“尊卑有序”是封建政體的基本原則,它涉及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生活等各個(gè)領(lǐng)域。
為了維護(hù)封建貴族官僚的特權(quán),歷朝法律都做出了相應(yīng)的規(guī)定。在《唐律疏議》中,立法者規(guī)定了議、請、減、贖、當(dāng)?shù)榷喾N制度,構(gòu)建了一套官貴刑罰特權(quán)體系。比如,《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應(yīng)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5]68這就是說,屬于“八議”范圍的人,若犯死罪,司法部門應(yīng)按條文記錄其所犯罪行及緣由,以及注明他在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勤、議賓和議貴這“八議”中應(yīng)屬哪一議,再向上奏報(bào)皇帝,由皇帝召集重臣于尚書省都堂討論,議定后,最終報(bào)請皇帝裁決。“請”即上請,根據(jù)《唐律疏議》的規(guī)定,應(yīng)請者包括皇太子妃的大功服以上親屬以及官爵在五品以上的官員,范圍比“八議”要大,若此類群體觸犯死罪,亦需請示皇帝,由其發(fā)落。“減”即例減之制,適用于七品以上官員以及官爵在五品以上的官員近親屬,若其犯了該判流刑以下各罪的,可照例減一等判處。“贖”是最低一等的特權(quán),適用于“應(yīng)議、請、減,及九品以上之官”[5]75以及官品得減者之近親屬,假使他們犯流刑以下的罪,皆可以財(cái)物贖罪。“當(dāng)”又稱“官當(dāng)”,也是唐朝官員的法定特權(quán),即以官品或爵位折抵徒、流兩種刑罰。若折抵后該官員仍余刑不盡,還可再以銅贖刑。因此,從此類條文可以看出,貴賤有分的官貴刑罰特權(quán)制度的體系化程度不斷提高,在唐朝尤為明顯。正如清人薛允升所說,“(唐律)優(yōu)禮臣下,可謂無微不至矣。”[9]
“貴賤有等”之禮不僅適用于官僚貴族,也適用于其他社會(huì)等級(jí)。在社會(huì)和家庭關(guān)系方面,普通的社會(huì)成員之間同樣存在著身份等級(jí)的尊卑、高下之分。比如,《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5]750反過來,“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傷,及詈者,流。”[5]625由此觀之,因良賤有別而同罪異罰,可以說是不言自明了。此外,《唐律疏議》中還有禁止良人與賤民之間通婚等的規(guī)定。
《唐律疏議》通過維護(hù)官員貴族的特權(quán)以及良人和賤民之間的不平等地位等方式,充分表明了“別貴賤、序尊卑”的禮制精神在唐朝已經(jīng)轉(zhuǎn)化成了法定的等級(jí)特權(quán)制度。所以說,貴賤有等、尊卑有序是以唐律為代表的中華法系一個(gè)鮮明特點(diǎn)。
(五)皇權(quán)至上,政法合一
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社會(huì),皇權(quán)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歷朝統(tǒng)治者無不采取包括立法等各種手段以維護(hù)和強(qiáng)化皇權(quán),其中就包括盛唐時(shí)期《唐律疏議》的編纂。在《唐律疏議》中,首篇《名例律》將“謀反”“謀叛”“謀大逆”“大不敬”等直接危害皇權(quán)的行為列入“十惡”重罪,并規(guī)定了很重的刑罰,且此類犯罪為常赦所不原,即使犯罪的人屬于八議的范圍,也不得減免刑罰。同時(shí),針對(duì)危害皇權(quán)的犯罪,《唐律疏議》還規(guī)定了人們強(qiáng)制告發(fā)的義務(wù)。《斗訟律》規(guī)定,如果知道有人有“謀反”“謀大逆”的行為,必須密告就近的官府,知情不告者,會(huì)被處以絞刑。知道有人有“謀叛”行為,知情不報(bào)的,會(huì)被判處流刑,發(fā)配二千里[5]785。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古代法律深受皇權(quán)至上觀念的支配,是實(shí)現(xiàn)君主專制的一種工具。
中華法系不僅受到皇權(quán)制約,還具有司法與行政合一的特點(diǎn)。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在我國古代,中央司法機(jī)關(guān)很少有獨(dú)立行使職權(quán)的機(jī)會(huì),大多受皇帝左右或受重臣牽制。而地方司法機(jī)關(guān)與行政機(jī)關(guān)直接結(jié)合,是行政機(jī)關(guān)的附庸[10]。因此,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司法權(quán)與行政權(quán)并無嚴(yán)格界限,司法權(quán)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從屬于行政權(quán),并不具有獨(dú)立地位。這一點(diǎn)在《唐律疏議》中也得到鮮明體現(xiàn)。比如,在中央層面上,《唐律疏議》規(guī)定了死刑復(fù)奏制度,在《斷獄律》中,“死罪囚,謂奏畫已訖,應(yīng)行刑者。皆三覆奏訖,然始下決。”“死罪囚,不待覆奏報(bào)下而決者,流二千里。”[5]1018死刑犯必須通過三次奏請才能決定最終是否處以死刑,否則主管官員會(huì)被判處流刑。所以說,掌握著國家最高行政權(quán)的皇帝,同時(shí)也是最高司法權(quán)的擁有者。在地方層面上,唐朝地方州、縣長官兼理司法事務(wù),其下還有專門負(fù)責(zé)民事和刑事訴訟的官員輔助長官審理案件,這也是包括唐朝等多個(gè)朝代地方司法的重要特點(diǎn)。
三、中華法系對(duì)周邊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
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源遠(yuǎn)流長,別具一格,為人類法治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在古代的封建社會(huì)時(shí)期,中國國力長期居于東亞甚至世界前列,逐漸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儒家文明圈。中國的法律制度自然而然地影響到周邊國家,其中以唐律為甚。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包括《唐律疏議》在內(nèi)的唐律超越國界,對(duì)亞洲諸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以日本為例,在日本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編撰《大寶律令》,共十七卷。根據(jù)日本許多學(xué)者所述,《大寶律令》在篇目和次序上大量參考唐律,特別是《永徽律》,它是日本制定的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典。此后千余年,日本法一本唐律的格局基本沒有改變。此外,還有朝鮮的《高麗律》、日本元正天皇時(shí)期的《養(yǎng)老律》、越南李太尊時(shí)期頒布的《刑書》等,也大都以唐律為藍(lán)本。從唐朝起,中國法典的先進(jìn)性、科學(xué)性逐漸受到相鄰國家的尊重與認(rèn)可,日本、高句麗、安南和琉球等都奉唐律為母法。
四、結(jié)語
中華法系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古代的,更是現(xiàn)代的。它作為中華民族智慧的結(jié)晶,雖然現(xiàn)在已經(jīng)解體,但它蘊(yùn)含的先進(jìn)思想以及留下來值得借鑒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如民為邦本、德法互補(bǔ)和慎重用刑等仍然在中國乃至世界法治文明的舞臺(tái)上煥發(fā)著絢麗的光彩。
當(dāng)前,我們正在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治體系。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tài)的法律文化和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構(gòu)成部分,同樣具有兩重性,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在建設(shè)法治中國的過程中,我們應(yīng)結(jié)合我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道德倫理及環(huán)境因素等國情,對(duì)中國古代法文化加以挖掘和總結(jié),批判吸收其精華與有益成分,傳承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使中華法系中固有的良法因素轉(zhuǎn)化到當(dāng)代法治中國建設(shè)上來。同時(shí),我們也應(yīng)科學(xué)、合理地借鑒世界各國的優(yōu)秀法律,并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加以吸收利用,進(jìn)而推動(dòng)依法治國邁向新的更高境界,推進(jìn)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
參考文獻(xiàn):
[1] 本報(bào)評(píng)論員.黨的領(lǐng)導(dǎo)是推進(jìn)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N].人民日報(bào),2020-11-21(1).
[2] 春秋左傳正義[M].杜預(yù),注.孔穎達(dá),疏.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1225.
[3] 張晉藩.中華法系研究的回顧與前瞻[C]//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律史學(xué)研究中心.中華法系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文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律史學(xué)研究院,2006:11.
[4] 張晉藩.中華法系研究新論[J].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2007(1).
[5] 曹漫之,王召棠,辛子牛.唐律疏議譯注[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6] 楊伯峻.論語譯注[M].簡體字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12.
[7] 張晉藩.中華法系特點(diǎn)再議[J].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05(8).
[8] 楊伯峻.孟子譯注: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0:167.
[9] 薛允升,懷效鋒,李鳴.唐明律合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4.
[10] 陳景良,張中秋.求索集——張晉藩先生與中國法制史學(xué)四十年[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353.
作者簡介:蔡浩威(2001—),男,漢族,廣東陽江人,單位為華南理工大學(xué),研究方向?yàn)榉▽W(xué)。
(責(zé)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