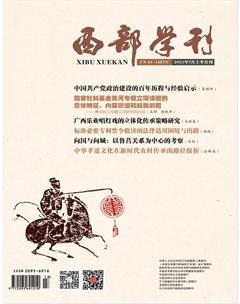仲裁價值研究
摘要:仲裁的價值不單是應然的追求,而是主體在國家法治框架中實現個人自由的現實理性選擇。從主體方面講,仲裁屬性集中在財產方面,是一種半司法、半民間的具有邊緣性質的制度,其存在的價值是國家權力介入的結果。從客體方面講,仲裁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的一種形式,其存在依據是當事人合意啟動的契約性精神。因此,仲裁歸屬價值當為財產性人格主體在國家司法權框架內以程序自治和契約自由解決糾紛的一種理性選擇。
關鍵詞:仲裁價值;財產性人格;國家司法權;程序自治
中圖分類號:D925.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3-0089-03
作為一種濫觴于古羅馬并一直延續到當今的糾紛解決方式,仲裁制度以其自身獨特的優勢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廣泛認可。仲裁制度的價值也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理解這樣一種國家權力邊緣的糾紛解決方式是憑借何種“正當性”或“有效性”而存在于歷史與現實之中,無疑有利于我們建構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體系。本文從制度的要素入手,從規范分析出發,對仲裁制度的價值進行靜態剖析。但是即使是完全的規范研究也必須借助于歷史的視角來論證現存事物的合理性,因為只有說明了現代仲裁制度的價值內核在歷史中同樣存在,才能表明這樣一種仲裁價值的真實性。
一、仲裁價值的規范分析角度
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仲裁價值隸屬于法律價值的大范疇。根據我國法理學新近研究成果,“法律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它所要揭示的關系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作為客體的法律與作為主體的人的理想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層面的關系是隱藏在法律與人的這種物與人關系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從規范的角度說明,仲裁制度的價值就是要在仲裁關系中說明仲裁客體對于仲裁主體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也就是揭示仲裁制度在法律主體視域中的理想圖景。學者歸納出的仲裁公正和仲裁效益等價值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指明了仲裁的價值追求,直接從客體對主體有用性的角度得出了結論,忽視了對仲裁主體和仲裁客體基于各自角度分析后的關系概括。所以,我們在“仲裁公正”“仲裁效益”等價值描述的語詞中看不到反映仲裁制度特有屬性的內涵分析,而且其有套用法律一般價值之嫌。仲裁制度的價值當然反映了一般法律的價值,可是它應當更有其自己的特殊性。正是這些特殊的因素使仲裁制度得以區別于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而在歷史和現實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仲裁主體和仲裁客體的相互作用使得仲裁制度表現出了其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仲裁主體和仲裁客體各自所具有的特性使得仲裁制度客觀上就具有了自身的價值。什么樣的主體與什么樣的客體就決定了客體可以對主體有何種有效性,主體和客體的性質范圍內在地決定了某種價值的內容。仲裁關系中的仲裁主體即是仲裁人,也就是可以參與到仲裁關系中的法律主體;何種自然人或組織體可以成為仲裁法律關系中的法律主體即成為決定仲裁主體特性的關鍵因素。仲裁關系中的客體即是仲裁法律制度這一糾紛解決的形式,仲裁主體可以運用此種機制的何種特性來解決沖突就反映了仲裁的基本價值。因此,仲裁制度的功能屬性是識別仲裁價值內涵的重要路徑。
二、仲裁主體的屬性對于仲裁價值的影響
隨著啟蒙運動所提倡的人權理念的盛行和自然法學對于平等主義的要求,自然人作為獨立主體的地位得到了公認。現代民法在賦予法律主體資格方面已經把倫理要求置于一種隱性的背景中了,而主要是采用了一種界定適格者并使其成為民事主體的方法,以符合社會發展要求。實現該路徑,主要是權利能力的引入和制度化。權利能力起初僅僅適用于生物人主體資格的賦予,“將權利能力制度化應當歸功于《德國民法典》。特別是其將權利能力的范圍擴大到了法人,通過高超的立法技術擬制出新型法律概念,將市場經濟主體也納入到法律規制范疇,真正意味著人類法治時代的到來。”[2]分析仲裁關系中主體的特性同樣需要注意這樣一種趨勢,因為正是主體資格的賦予與人自身特性的關系越來越疏遠,所以才有必要研究在某一種法律關系或某種法律制度場域中主體的哪種屬性處于主導地位。
我國《仲裁法》第二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第三條規定:“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可見,在我國納入仲裁關系中的主體基本上是財產關系中的人,而現在即使是在國際社會所達成一致規則和得到長足發展的也是商事領域的仲裁制度,那種解決社會沖突的廣義的仲裁已經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沒有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了。司法權的介入使得仲裁制度的合理化過程變成了一種仲裁機制的醇化過程,國家僅僅把仲裁主體的自治權限制在財產糾紛領域,以防涉及國家、社會秩序的人身利益被私人隨意裁決。
因此,可以說仲裁主體的屬性集中在財產方面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主體二元人格的存在,另一個是國家司法權對于私法自治的限制。一方面,歷史的發展使得主體的人格表現為財產性人格和人身性人格的兩個不同層次的分化衍變;另一方面,國家權力的強大又使得其可以把仲裁制度的使用范圍僅僅局限在財產糾紛領域,這樣便導致仲裁主體的財產屬性的出現。
自近代以來,財產性人格與人身性人格就以一種“似合而分”的形貌存在于大陸法系國家民法法理和法律規定中。自由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雖然對于人權和平等市民的形成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圍繞市場邏輯和財富流通的財產規則才是近代民法的重心所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這三大近代民法基本理念無一不是為了塑造一個財產中心主義的私法秩序格局,財產性人格得到了歷史發展的垂青。“作為契約自治的合理延伸,商事仲裁的意思自治不僅體現為民商事實體權利的支配,也體現為規則使用的選擇,更體現為裁判程序的約定性。這種對于意思自治的強化,悄然形成與國家司法權威并駕齊驅的態勢,使契約性與司法化的邏輯張力在商事裁判的領域繼續存在。”[3]此種契約性的財產屬性使得仲裁制度自身就內含了一種財產的因子,所以,主體的財產性人格自然會在仲裁制度中占據優勢地位。
三、仲裁制度本身的特性對于仲裁價值的影響
概念分析是制度分析的前提,沒有精準的概念界定,就無法充分認識特定法律制度的功能和價值。盡管對于仲裁的定義有所爭議,可是大家已經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仲裁又稱公斷,是指仲裁機構根據當事人之間書面達成的仲裁協議,取得對約定事項的管轄權,并據此對提交仲裁解決的爭議作出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裁決……仲裁實質上是由糾紛雙方當事人合意選擇糾紛解決途徑的表現。”[4]從這里可以看到仲裁中包括的諸要素,有以下三項對于仲裁價值影響至為重要。
(一)仲裁是一種糾紛解決方式
人類自從存在之日起,可用資源的相對不足和個人因地位、利益、欲望不同而產生的矛盾,引發了糾紛和爭議的綿延不斷。為了維護社會生產的進行和整體的利益,對于個人之間的糾紛必須予以正當地解決。秩序的要求促使人們在解決糾紛時不僅僅關注于一種實質上的公正結果,而且更努力在程序上一視同仁,以吸收社會的不滿情緒。因此,一種定型的、成熟的糾紛解決方式,其程序性特征必然十分明顯;諸如調解、仲裁甚至訴訟,它們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僅僅是為沖突的雙方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平臺,只是通過一套合理的程序進行及保障才促進其符合社會正義地緩和雙方的矛盾。仲裁作為一種規范的糾紛解決手段,其內在的程序要素對于理解仲裁本身的特性和價值有著基礎性作用。仲裁制度的自身完善不僅僅是其實質內容的發展,更主要的是仲裁體制和結構上的合理化發展。這種合理的形式構造一方面體現了任何糾紛解決中對于裁判者中立性的要求,即任何裁判者在處理糾紛過程中都必須嚴格依照該制度中的程序,不能有任何偏私,而且必須能夠讓一個中立的第三者不對其正當裁判產生任何依據的懷疑。這種形式上的要求促使仲裁制度與其他解決糾紛機制一樣,不僅使正義得以實現,而且力圖以一種“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正義。
(二)仲裁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的一種形式
現代社會中,“仲裁作為世界公認的糾紛解決方式之一,經歷了幾百年不斷的修正和完善,以其契約性和準司法性兼備的優勢在諸多糾紛解決機制中占據重要地位,是訴訟外土地性糾紛解決機制的一項重要內容,逐漸成為處理國家商業糾紛的重要救濟手段。自1697年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英國仲裁法》誕生之后,確立了國家貿易糾紛中的仲裁制度至今,世界各國大都制定了本國的仲裁法。”[5]不過,仲裁的價值特性必須在與訴訟價值的互補和比較中得以說明。仲裁及其他解決糾紛的形式不是作為替代訴訟的手段出現的,而是在彌補訴訟的不足中得以在現代社會中成長的。每一種ADR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存在空間和存在價值,都是面對當前利益主體多元、糾紛形式多樣和價值立場多維的合理應對機制。就仲裁而言,其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獨特性在于其自治屬性與準司法屬性的融合。本來作為商事糾紛解決手段的仲裁,是商人自治歷史發展的結晶和成果,其糾紛解決有效性經過了歷史的正當檢驗。而在近代民族國家肯定個體獨立地位和市民社會獨立空間后,被逐步納入國家機制的仲裁制度又邏輯地具有了國家主權的支撐,其裁決獲得了與訴訟結果相當的效力。這種集自治與強制于一體的特點,正是仲裁獲得現代糾紛解決機制地位的原因所在,也是當事人青睞和選擇仲裁的內在動機所在。
(三)仲裁是由當事人合意啟動的,其形式和實質都具有契約性
盡管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但一個仲裁關系從框架上看就是當事人之間及他們分別與仲裁庭的幾個契約的結合體,仲裁機制整體面貌的形成以及內部諸種要素的關系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運用契約工具的產物。如學者所言:“當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的基石,不僅仲裁程序的啟動源于當事人意思自治之合意,而且仲裁程序的每個步驟均浸潤著意思自治的光澤。”[6]從形式上講,仲裁程序的啟動必須由當事人雙方合意完成,同時仲裁庭人員的選擇也必須經由當事人雙方共同決定。程序的啟動和裁斷者的選定,充分表明了當事人在仲裁中的主體地位,而一個程序主體地位的樹立對于任何糾紛解決方式的發展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保證每一個利用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主體就是對這種糾紛解決存有某種正當預期和信賴的主體,而不是讓其被迫接受一種他不愿進入的解決糾紛的程序。從原則上講,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任何機構都不能隨意啟動這個程序,因此仲裁的合同屬性是價值層面的重要內容。從內容上講,仲裁庭適用的裁判規則也可以由當事人雙方選定。這表明解決糾紛的依據選擇權也是當事人合意一致的結果,而這些依據往往是主權國家或者國際組織制定的有國家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當事人的合意無形中獲得了等同于或者高于國家權力的特質。當然,程序的自主性也會反過來制約當事人本身,“仲裁協議的契約性質要求當事人‘約定必須遵守。當事人之間形成有效的仲裁協議,參與仲裁就不僅僅是當事人的權利,也是一種義務。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協議的約定進行仲裁,便具有違約性質,都構成對意思自治的損害。”
仲裁關系中的客體層面即仲裁制度的屬性對于認定仲裁價值的意義在于,它明確了仲裁所可以達到的價值極限,即仲裁制度只可以在這幾個其具有獨特優勢的方面發揮作用,我們不能促使其在其他方面滿足主體的需要。
四、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本文嘗試用一種歸納的方法概括出仲裁的價值。首先,主體是財產人格屬性占主導地位的主體,主體在仲裁關系中的存在是國家權力介入的結果。其次,仲裁制度作為人類的一種制度形式,是一種半司法、半民間的具有邊緣性質的制度,體現了社會多元對于糾紛解決多元的一種要求;仲裁制度在承擔國家司資源分配任務的同時又充分尊重了主體的自由意志,充分賦予主體以程序自主權和程序選擇權,這正是其特色所在。
仲裁主體與仲裁客體相互作用的仲裁關系里存在著一系列不可分割的因素,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私法人格和一個規范的法治國家運作,仲裁的功能便不可能得到實現。仲裁對于主體的價值說明實際上也在客觀上反映了仲裁制度的特征,而仲裁客體——仲裁制度的屬性又制約著可以利用仲裁的主體范圍。因此,在這種關系互動中,人們一般都用應然的“公正”“效率”“自治”來界定仲裁的價值。可是,應然的追求不能完全體現實然的價值,價值是客觀存在的,決不是主觀想象的。現實中的仲裁制度具備何種有用性應該是可以實證地研究出來的,在我們現實生活中解決糾紛的仲裁價值應該是具體的、清晰的,而不完全是抽象的一般法律價值的應用。
綜上所述,仲裁的價值可以概括為:財產性人格主體在國家司法權框架內以程序自治和契約自由解決糾紛的一種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 付子堂.法理學高階: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20.
[2] 彭中禮.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新論[J].甘肅社會科學,2019(4).
[3] 康寧.契約性與司法化——國際商事仲裁的生產邏輯及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啟示[J].政法論壇,2019(4).
[4] 江偉.民事訴訟法學: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5.
[5] 龍飛.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立法的域外比較與借鑒[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9(1).
[6] 杜煥芳,李賢森.國際商事仲裁當事人程序自治邊界沖突與平衡[J].法學評論,2020(2).
作者簡介:李飛(1983—),男,漢族,山西左云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法學理論專業2020年度博士研究生,山西省大同市云岡區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研究方向為刑事檢察、民事檢察。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