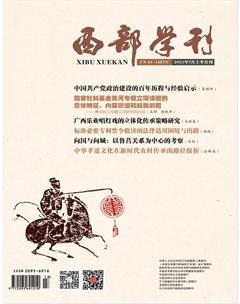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評析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相關問題予以專章規定。通過運用文獻分析法、邏輯分析法,對《社區矯正法》中構建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進行評析。研究發現,《社區矯正法》第七章確立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時代意義,各方主體義務承擔合理,執行底線明確,但在對“跨年齡階段”社區矯正對象的執行適用問題上尚有欠缺。
關鍵詞: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評析
中圖分類號:D9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3-0092-03
目前,我國仍在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道路上前行,具體體現在實踐中,我國處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時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對未成年人群體犯罪后依法從寬處理,對符合法定條件的未成年犯罪人適用非監禁刑,盡可能保護其受教育權等權益。雖然社區矯正早已由法律加以規定,但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卻并無明確規范支撐。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以下簡稱《社區矯正法》)正式通過,并于2020年7月1日起實施。《社區矯正法》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進行專章立法,正式確立了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順應了良法善治的要求。總的來看,《社區矯正法》廣泛吸取各方意見,是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制度建設需要和社會現實需要,受到公眾的廣泛理解,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一、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概述
(一)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含義
1.社區矯正的定義及性質
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相對,是對犯罪人實施的非監禁性矯正刑罰。我國學界對社區矯正的性質尚存較大爭議,立法也對此采取了“回避態勢”。但若不明確社區矯正的性質,后續討論便無立場。因其并非本文重點,故筆者在此直接引用學者司紹寒之觀點:社區矯正屬刑罰執行,其對象為具有人身危險性之罪犯[1]。
2.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中“未成年人”的界定
社區矯正屬刑事范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所規定。因此,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中“未成年人”之界定,應當遵循《刑法》之規定。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惡意年齡補足制度之規定,《刑法》所稱“未成年人”,是指已滿十二周歲而未滿十八周歲的中國公民。
因此,“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中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滿十二周歲、未滿十八周歲,因實施其應自行承擔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而受相關法律規制之人。
(二)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現實價值
刑法的謙抑性要求在合理限度內盡量少用或不用刑罰以獲取最大社會效益。在法定條件下更多使用較為溫和之手段促進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我悔改,符合謙抑性要求。未成年人處于成長關鍵期,是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塑造期,監禁刑對其帶來的影響不僅是“交叉感染”“監獄人格”,更會因教育、家庭關愛的缺失而造成不可逆之后果[2]。據此,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現實價值不言而喻。
二、《社區矯正法》“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特別規定”的時代意義
(一)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確立
《社區矯正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正式確立。就形式層面而言,由于長期以來我國未有法律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進行規定,因此,不能認為與成年人社區矯正具有較大差異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已經成為一項法律制度。在《刑法修正案(八)》引入社區矯正概念后,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和實施主體進行了規定。至此,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才得以正式確立。因此,若認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已經成為一項法律制度,至少要求在形式上存在由立法機關制定的相關法律對其進行專門規定。
就實質層面而言,由于我國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規定長期集中在部門規章與各地的地方政府規章之中,因此,長期以來我國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治理停留在政策式治理與運動式治理,而非制度治理。政策式治理具有相當的靈活性,但屬于事后反應式的治理模式,不利于對某一問題的統籌規劃,也難以實現提前防范;運動式治理是我國體制優勢的體現,但其側重于自上而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容易忽略某一問題所衍生的配套制度建設及相關問題解決,且易造成資源浪費[3]。政策式治理與運動式治理在制度治理的框架之中才能更好地發揮優勢。所謂的制度治理,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具有“統籌性”。因此,只有在具有統籌規劃意義的規范指導之下,各部門、各地綜合運用政策式治理與運動式治理模式,才可將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納入制度治理的范疇。
由此,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法》最為重大的時代意義,在于其從形式上與實質上分別滿足了對應要求,真正確立了我國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引領我國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進入制度治理新時代。
(二)良法善治理論的優秀實踐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了“良法”才有“善治”。基于對國家威嚴、法律權威與社會秩序的考慮,法律絕不可朝令夕改。那么,要使所立之法為“良法”,同時使“良法”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便要求在規范某一事項時,既要避免盲目立法,又要杜絕立法遲緩。我國并未在社區矯正試點之初便盲目照搬他國做法建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制度,也沒有等到立法缺失的種種弊端無可補救之時才消極立法,而是在長期試點實踐的基礎之上,結合體現我國特色的社區矯正的規律與時代特征,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制度建設需要、社會實際需要、公眾理解程度高的恰當時機所進行的、廣泛吸取各方意見的立法活動。這樣的立法符合良法善治理論所謂“良法”的要求,更能為“善治”提供制度保障。
三、《社區矯正法》視野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評價
(一)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整體評價
1.制度基礎扎實
《社區矯正法》第七章“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特別規定”正式確立了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至此,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法律依據由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部門規章及地方政府規章構成,制度的法律保障結構較為合理。同時,第七章中的相關規定并非空中樓閣,而是在充分認可基層的首創精神的基礎之上,將各地在實踐中積累的優秀方法予以總結、固定,并將其上升為法律制度,可以說制度基礎很扎實。
2.反映各方訴求
以動態的視角看《社區矯正法》的立法過程,其所奠定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是立法機關在廣泛征求立法建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意見的基礎之上確立的。
在《社區矯正法(征求意見稿)》中,對于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規定僅有一條共四款,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征求意見之初,立法機關并未察覺到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是亟需法律予以規范的。此后,《社區矯正法(草案)》經過三次審議,從一審稿中為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相關規定設立了專章共四條,到最終《社區矯正法》第七章共八條,這一變化充分說明立法機關傾聽各方聲音、反映各方訴求。
(二)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特別規定的具體評價
1.各方主體義務承擔合理,制度執行最低準則明確
法律本身是社會規范的一種,由于其受國家強制力的保障而區別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會規范。也正是基于法律所具有的極為嚴厲的國家強制性,而被認為是主體在進行行為活動時所應當遵守的最低標準。按照規則規定內容的不同,可以將法律規則分為授權性規則、義務性規則和權義復合性規則。由于《社區矯正法》的核心要義是規范社區矯正這一由相關有權機關所為的涉及“自由刑”的刑事執行制度,本質上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結合,因此,其內容多以權義復合性規則和義務性規則為主,授權性規則較少。
權義復合性規則兼具授予權力與設定義務兩種性質,通常表現為授予公權力的規則。《社區矯正法》第七章中包含了以公權機關為主體的權義復合性規定。社區矯正機構是我國社區矯正的主導機關,行使公權力,其享有對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矯正的權力,同時也負有在保證矯正質量的前提下依法完成矯正工作,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義務。其中,《社區矯正法》第五十二條以應為模式確定了社區矯正機構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執行過程中的最低標準,包括應當將成年人社區矯正與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區分進行、應當根據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具體情況采取針對性矯正措施、應當吸納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的人員參與矯正小組。這三點雖然在《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均有所體現,但其進步意義在于明確提出相關義務承擔主體為社區矯正機構,并以法律形式將其固定,有效破解了作為各地地方政府規章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執行規定的底線參差不一、社區矯正機構將矯正工作“全面外包”而不作為的亂象。
義務性規則在內容上規定人們的法律義務,具有強制性和利他性。《社區矯正法》第七章中包含以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監護人、相關社會團體為主體的義務性規定,其分別規定在第五十三條和第五十六條。此舉是在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特殊性之上所設立的“開創性”規定。所謂“開創性”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理解:其一,以社區矯正相關規定的延續性來看,將未成年矯正對象監護人的監護職責予以專門強調,且將相關社會團體明確納入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參與主體之中,是《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并未明確提及的。此規定是將各地長期實踐中暴露出的監護人怠于履行監護職責的實際問題及各社會團體參與未成年人社區矯正工作的優秀成果予以歸納、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有極強針對性的規定。其二,由于《社區矯正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以下簡稱《監獄法》)均屬于刑事執行法,二者關系彼此平行,均以涉及“自由刑”執行問題為調整對象,且均對未成年犯執行問題進行了專章立法,因此在規則內容的體現上存在一定相似之處,如均強調保障未成年人在執行過程中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然而,基于社區矯正非監禁刑的形式以及促使社區矯正對象順利回歸社會的目的,《社區矯正法》所規定的對于未成年人的執行制度應當體現出區別于《監獄法》相關規定的特殊性。將未成年被執行對象的監護人以及相關社會團體作為義務承擔主體納入刑事執行法律之中,充分體現了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的特殊性,是開創性的舉措。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法》第七章中法律規則的最大亮點,便是其對各方主體的義務承擔做出了既符合實際又富有“開創性”的規定,合理確定了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這一刑事執行制度的執行最低準則。
2.“跨年齡階段”社區矯正對象的執行適用規定有待完善
所謂“跨年齡階段”,是指《社區矯正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在矯正期間年滿十八周歲”的情形。依據《社區矯正法》規定,對該社區矯正對象仍然依據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相關規定執行。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有待完善。
根據《監獄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跨年齡階段的未成年犯,剩余刑期不滿兩年的,可以繼續適用對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執行的特別規定,即可以繼續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中執行。結合《社區矯正法》第五十八條來看,此類規定以期解決的問題是跨年齡階段未成年犯的刑事執行規定的適用問題。二者之間的區別在于,《社區矯正法》規定所有跨年齡階段的社區矯正對象均繼續適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相關規定,而《監獄法》的規定預留了調整跨年齡階段未成年犯適用何種年齡階段刑事執行規定的空間,且加入了剩余刑期不滿兩年的限制條件。相比之下,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法》對跨年齡階段社區矯正對象的規定存在一定局限性。從設立此規定的目的來看,保有對社區矯正對象執行模式的延續性是值得認同的,但之所以對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與成年人社區矯正進行區分,其根本在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上的特殊性,而非純粹年齡大小的問題。跨年齡階段的社區矯正對象通常是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中相對成熟的群體,也更符合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特點。若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在剩余刑期較長時便滿十八周歲,卻依舊“一刀切”地對其適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規定,這不僅會影響其矯正效果,也會影響其他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矯正效果。
綜合考慮之下,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法》第五十八條“跨年齡階段”社區矯正對象的執行適用規定還有待完善,可以考慮參照《監獄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改變目前“一刀切”的適用規定,加入社區矯正對象剩余刑期的限制條件,為跨年齡階段社區矯正對象究竟適用何種年齡階段的社區矯正執行規定預留一定的選擇空間。
四、結論
《社區矯正法》真正確立了我國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回顧其從萌芽到確立所經歷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權機關的積極探索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配合。誠然《社區矯正法》的相關規定仍有待完善,但正如不應沉痛打擊一個處于成長階段而正在為目標奮斗的孩子一樣,不能因為這項制度尚未成熟而否定各方為之發展而付出的努力。作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助其成長的個體,無論最終所能帶來的影響或大或小,都應在能力范圍內傾盡所能,與之一同成長。
隨著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現有制度必定會暴露出更多問題。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懼怕問題的心理與逃避問題的行為。筆者相信,會有更多有識之士為我國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法律制度建設添磚加瓦,不斷暴露出的問題也將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轉化為制度逐步完善的契機。
參考文獻:
[1] 司紹寒.試論《社區矯正法》的意義與不足[J].犯罪與改造研究.2020(8).
[2] 夏艷.未成年人犯罪非監禁刑適用的實證分析與展望——以S市A區人民法院2011—2015年審判實踐為樣本[J].青少年犯罪問題.2016(4).
[3] 李海青.從四個方面推進制度有效執行[N].學習時報.2020-03-16(5).
作者簡介:秦吳霄(1998—),男,漢族,北京人,單位為青海民族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刑事訴訟法。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