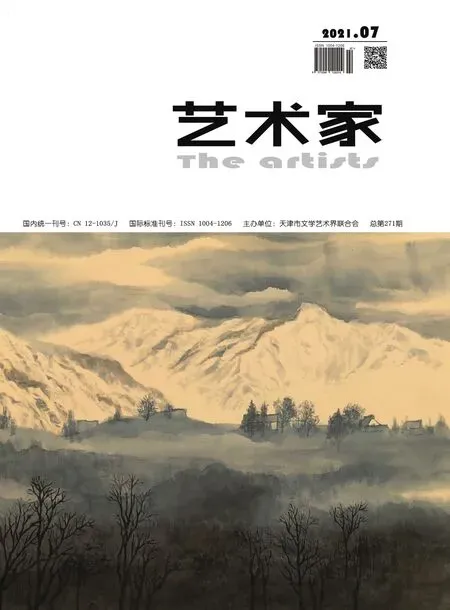與自然“對話”:藝術活動在“人類世”中的價值與痕跡
□路 意 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術學院
2019 年5 月21 日,據英國著名科學雜志《自然》報道,一組科學家投票選出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人類世”。但其實,早在1873年之前,人類就意識到了自身對環境的影響。從不確定的、完全隨意的時間位置開始,所謂“人類世”理論定義已經成為科學辯論的領域之一,其遠遠超出了地質學范圍,傳播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在認識到這個難以判斷但仍在進行的新時代之后,人們將“人類世”理解為通過生物學和地質學的角度重新考慮人類活動。該術語本身引起了環境正義的思想,提出了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創造了一個世界的問題。但是,正如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1)所觀察到的,“人類世”一詞有一個隱含的意義:“人類只是一種類型,人類本性可以歸納為造成這場危機的特征”[1]。
相較于現實,藝術活動常常更能反映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當前,我們不能淺薄地認為藝術只具有美學價值或是哲學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也發生著改變,當然不止在科學領域,在“人類世”的新階段中,藝術家們也許會成為農學家、思想學家,或許也會成為一名政治家,反之亦然。這種相互交融的情況也會增強藝術作品的豐富性,而大范圍的藝術活動,會使民眾也參與其中,所進行的研究也會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這也是藝術在當代社會中運行的意義與價值之一。藝術在“人類世”這個概念中爆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進化,我們不能否認通過石墨、青銅、帆布、石膏、橡皮泥創建的圖像的永恒有效性,但進化給予了藝術更多的發展軌跡與意義象征。雖然“人類世”并未有一個準確的開始年,但在其出現后至20世紀初,藝術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大波藝術運動浪潮涌現,對于“環境”藝術(大范圍意義)的理解和創作,人們也從階段性的藝術活動痕跡中了解了其發展和進化的過程。
一、存在于物品、廢物和回收品之間的當代藝術(復合作品藝術)
20 世紀,藝術最顯著的變化是藝術作品中不同元素的并置,其否認了以前所認為的材料和技術的同質性。由此,美學家雅克·蘭西埃(Jacques Rancière)談到了“異質的沖擊”這個概念,其強調生活就像藝術一樣,是由碎片組成的。
“我們可以用剪刀、膠水和許多材料,包括粉筆、麻布、紙和其他任何方式繪畫。”馬塞爾·揚科(Marcel Janco)這位達達主義藝術家如是說道,我們也從中找到了浪費價值。“現實生活就是垃圾”,任何物體隨即構成了新藝術的材料。年輕藝術家不再需要說:“我是畫家”“詩人”或“舞者”,他們都只是“藝術家”。所有的生活對他們都是開放的,他們將通過普通事物發現平凡感;他們不會嘗試變得與眾不同;他們會限制自己確定其真實含義;他們將一無所有地創造出異常的甚至虛無的東西。在這場運動中,評論家們會感到困惑,而觀者會對這天馬行空的想象和用材感到新奇與驚喜。這場運動至今仍未結束,藝術家們都不由分說地加入了這猶如“廢品回收”一般的狂熱運動中。
1961 年,美國紐約的瑪莎·杰克遜(Marthe Jackson)畫廊里,展出了一件由美國藝術家艾倫·卡普羅(Allan Kaprow)所創作的由數個輪胎組成的互動藝術裝置“圍場”(Yard)(見圖1)。卡普羅在畫廊的后院里放滿了舊輪胎,如此改造的空間就如同一個垃圾場,而不是美術館。流離失所的游客被邀請走路、坐下、躺在輪胎堆上、踩輪胎或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布置輪胎,然后放回原處。當然,游客們也可以隨意將輪胎扔向建筑物,使其掉落。同時,游客們還被邀請建造新的塔樓和墻壁,這樣,院子將不斷變化。

圖1 《圍場》(Yard)艾倫·卡普羅(Allan Kaprow)互動裝置 1961年 于瑪莎·杰克遜(Marthe Jackson)畫廊展出
這是藝術家源于對展覽空間的不合理使用的質疑而產生的作品,并成為卡普羅作品中的關鍵一環。隨著輪胎數量的不斷增加,展覽館幾乎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工業禪園,卡普羅證明了藝術家有將藝術與生活本身混淆的能力。當然,除了包羅萬象和充滿趣味的尺寸,在輪胎的再利用方面,卡普羅作品中還存在著諷刺意味:用于污染藝術世界的廢物,也是在環境終結時要清除的材料。
意大利藝術家,同時也是當代貧窮主義藝術的主角,米開朗基羅·奧利維羅·皮斯托萊托(Michelangelo Olivero Pistoletto)在1967 年創作的藝術復合品《破布的維納斯》(La Venere degli stracci)(見圖2)是概念藝術經典復興的著名作品之一。該作品中,由貝特爾·托瓦爾森(Bertel Thorvaldsen)雕刻的維納斯鑄模背對觀眾,并面對一堆廢棄的衣服,形成了新古典主義模型的度量和完善與破布的堆疊之間的特殊對比,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皮斯托萊托的維納斯模型是用混凝土制成的,是一種不起眼的材料,因此可以說代表了將“神圣”的表現體完美地融入一堆破舊衣服中。

圖2 《破布的維納斯》(La Venere degli stracci )復合裝置 1967年 創作者米開朗基羅·奧利維羅·皮斯托萊托(Michelangelo Olivero Pistoletto)
但是,《破布的維納斯》背后的概念顯然不限于簡單的理想對比。實際上,該作品涉及各種問題,首先是波普藝術模式中對消費主義社會的批評。破布,尤其是作品中所代表的數量,是消費主義和浪費的真實象征。而從當代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反思潛在的環境問題。當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與所謂快速時尚有關的問題,或者消費者和生產者傾向于使用高級貿易選擇來代替原生產品的趨勢。顯然,這涉及很多巨大且不必要的浪費,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我們生存的地球的健康。這也是這批藝術家們借由這些“垃圾”“浪費行為”“回收利用”的藝術運動,來警醒世人我們與環境的共存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潛在的危機。
二、“環境”藝術與社會活動
(一)土地藝術(Land Art)——景觀是藝術的素材
土地藝術(Land Art),是由格里·舒姆(Gerry Schum)在1969 年創造的一個術語,是“Landscape Art”的縮寫,它是反對繪畫和雕塑的藝術運動的一部分,主要收錄了一群美國和歐洲藝術家的作品。一些藝術家在1968 年左右開發了一條新的創作線,從極簡藝術的美學出發,使用常規的技術和材料替代土地的位置和尺寸。
而在1968 年,土地藝術得到了一代藝術家的回應,紐約Dwan 畫廊舉辦了名為“地球作品”的畫展。對于一些藝術家而言,“大地母親”既是媒介又是信息。參與者們共同提出了土方工程概念,即預期的戶外場所項目。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宣稱:“它與理性繪畫和雕塑的整個理念截然相反,這將導致對象不會受到追捧。”雖說這是一場簡短且小型的藝術運動,但為之后更加大型的環境藝術運動奠定了基礎,并且也涌現了一批年輕且憤世嫉俗的藝術創作家們,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留下了屬于自己的印記。
(二)塞拉藝術(Arte Sella)——一場意大利藝術事件
塞拉藝術(Arte Sella)是一場地處于意大利的藝術盛會,誕生于1986 年,在瓦爾迪塞拉(Val di Sella)(意大利特倫托省Borgo Valsugana 市)的草地和樹林中進行。
它由恩里科·法拉利(Enrico Ferrari)、伊曼紐爾(Emanuele Montibeller)和卡洛塔·斯特羅貝(Carlotta Strobele)于1986 年開始舉辦。在第一階段(1986—1996 年),該活動每兩年舉行一次,在“斯特羅貝利故居”(Casa Strobele)及其公園舉行;自1996 年以來,它沿著阿曼特拉(Mount Armentera)也在瓦爾迪塞拉(Val di Sella)的一條小路發展,并在約3 公里的路徑中放置了大約25 幅作品;1998 年之后,大部分展覽活動便移到鄉村建筑“哥斯達黎加小屋”(Malga Costa)舉行,該地區周圍有將近30 幅作品。
在這場盛大的藝術活動中,創作項目的目的不僅僅是要展覽合格的藝術品,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創造性的過程:作品的發展與日俱增,藝術家的設想和在其之上的再創作必須表達與自然的關系,在尊重這一原則的基礎上,從中汲取靈感和想象。這些作品通常是三維的,它們大多使用石頭、樹葉、樹枝或樹干這些自然物品;很少有人使用人造材料或顏料。游客可以在室外看到這些作品,同時欣賞該地方環境的奇特之處,如不同類型年歲的木材、巖石的存在、尺寸不一的樹木……它們被插入自然界的生命周期中,并且與自然融為一體,因此,這些作品注定要經歷或多或少的緩慢轉化和降解過程,直到最終消失。
三、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社會與自然
約瑟夫認為制作藝術是在思想領域為人類工作的一種手段,也是工作的最重要一環。其余的,類似于對象、設計、動作,這些都只能排在第二位。而藝術使他感興趣的唯一原因是其增加了與人對話的可能性。他也始終對生態問題持有高度的敏感。1973—1986年,他在博洛尼亞(意大利)的“天堂種植園”(Paradise plantation)從事農業工作,當然這不僅僅是工作,也是一項名叫“捍衛自然”的農業藝術實踐。“捍衛自然”這個詞語不僅僅代表一個簡單的稱號,還是一個具體的項目,一切都取決于希望在地球這個角落開展這項工作的人們的精力和熱情。他想證明的是,將藝術家分為畫家、雕刻家等的舊觀念現在已經過時。有些農民可以是藝術家,他們種著土地。“所以說如果一個人可以證明一個真實的東西,如果他可以發展出地球所需的重要產物,那么他就必須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創造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您必須接受他為藝術家。”當然,更重要的在于其與樹木共同工作期間的思考:我們的創造力在時間的流逝和發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們與自然物體及生態大環境的循環利用有何密切的關系?而在這個農業藝術實踐期間,約瑟夫也開展了其他的工作,最具啟發性的作品之一便是1982 年在德國卡塞爾(Kassel)腓特烈農場舉行的第七屆“Documenta”展覽中展出的《7000 橡樹》,他在博物館前放置了7000 塊玄武巖板。這些巖板可以被任何想要的人采用,而籌集來的資金會被用于購買和種植橡樹。該項目可以說是約瑟夫證明“自然保護”這個概念的最大項目。在這些充滿儀式感的石頭用盡之后,其便可能在玄武巖板旁邊種植7000 棵新橡樹,那時候整個卡塞爾(Kassel)便被7000 棵樹的森林所“入侵”。而借由這些藝術實踐活動,約瑟夫得以完善“社會雕塑”這個概念。

圖3 朱利亞諾·毛里(Giuliano Mauri)蔬菜大教堂(Cattedrale vegetale)2002年 塞拉藝術(Arte Sella)
當然這種社會與自然的互動藝術,也一直延續到了今天,藝術家門紛紛開始帶領民眾加入這場群體藝術的革命浪潮中,其中的一些藝術活動的開創也做到了對城市、社區環境的改善和美化,其中在意大利都靈的當代藝術實驗中心,“生活藝術公園”(Parco Arte Vivente)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一個成功案例。它結合了戶外展覽場和互動式博物館,可以作為聚會和實驗室的雙重體驗場所,可以作為藝術家作品的擺放區域,也可以作為民眾與藝術家的交流公園。這種結構組織化的藝術表現形態,可以說是當代藝術兼具實際意義和創造實驗性的重要展現方式。
結 語
為了進行交流,人們使用語言、手勢或進行書寫,或者在墻上畫一個標記,或者用打字機打出文字。簡而言之,人們會使用各種手段。而藝術活動便是與環境進行“對話”的最富有想象力的手段。隨著“人類世”這個新階段的到來,其所集成的新生態科學和批判性辯論為藝術實踐開辟了新的視野。在當代的環境藝術領域(當然不僅為環境藝術),藝術不單單體現出某種特定的美學或哲學價值,更是形成了一種復雜纏繞的價值關系網。在這種關系中,藝術價值也可以來自生物、技術、社會和政治成分的結合,與自然“交流”的藝術的豐富性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注釋:
(1)加拿大新聞記者、作家,激進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