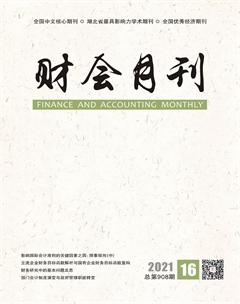合并商譽會影響商業信用供給和融資嗎
孫建強 哈文靜



【摘要】基于2008 ~ 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 實證檢驗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 研究發現: 企業的合并商譽越多, 其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越少, 且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融資的負向作用具有持續性。 考慮產權性質的影響后發現: 國有企業的合并商譽越多, 商業信用供給越多, 商業信用融資越少,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比民營企業更為顯著; 民營企業的合并商譽越多, 商業信用供給越少, 商業信用融資也越少, 與總體樣本回歸結果一致。 進一步討論合并商譽與凈商業信用的關系后發現, 合并商譽越多, 凈商業信用越少, 商業信用融資和商業信用供給同時減少且趨于接近, 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規模縮小。 總體而言, 在商譽的影響下, 商業信用的替代性融資作用不能有效發揮。
【關鍵詞】合并商譽;商業信用供給;商業信用融資;產權性質
【中圖分類號】 F275.1?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1)16-0076-9
一、引言
2006年版《企業會計準則》將商譽定義為合并方支付的對價與被合并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的差額, 將企業合并產生的商譽作為一項資產列示于資產負債表中。 近年來, 隨著資本市場并購浪潮的興起, 我國A股市場合并商譽總額以及由此引發的商譽減值總額均出現跨越式增長。 Wind數據庫的數據顯示, 2008年A股市場有84家公司披露商譽減值, 商譽賬面價值總額為551.17億元, 商譽減值總額約為23.16億元; 2018年A股市場有884家公司披露商譽減值, 商譽賬面價值總額為12263.92億元, 商譽減值總額為1664.13億元。 上市公司進行并購重組的出發點是獲取優質資源, 實現協同效應, 提高整體效率并降低單位成本, 以此增強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然而, 伴隨著企業并購的盈余管理和機會主義行為, 應有的并購協同效應往往難以得到發揮。
商業信用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融資途徑, 在企業供應鏈關系維護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現有對于商業信用的研究多是從融資性動機和經營性動機角度進行, 而企業合并作為一項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企業戰略層面的重大決策, 為研究商業信用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王秀麗[1] 的研究表明, 只有核心商譽才能發揮協同效應。 現行會計準則計量方式下的商譽不僅僅體現為核心商譽, 而是商譽整體, 其對企業產生的正面影響比較有限, 甚至更多地體現為負面影響。 從企業外部融資的角度來看, 商譽會導致企業產生融資約束[2-4] ; 從企業利益相關方認同的角度來看, 超額商譽會引發利益相關方(供應商、客戶、銀行等)對企業的負面評價[5] 。 合并后的企業面臨著融資約束, 其在面對負面評價時, 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會呈現怎樣的狀況以及商業信用的替代性融資作用是否得到發揮是本文研究的主題。
本文以2008 ~ 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中商譽賬面價值不為零的公司為樣本, 研究了合并商譽對供應鏈上商業信用使用規模的影響, 以及這種影響關系在不同產權性質企業中的差異, 為企業采取積極措施維護好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啟示。 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 首次在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之間建立聯系, 分別從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兩個角度討論合并商譽對其的影響; 豐富了合并商譽經濟后果的相關研究文獻, 同時為研究商業信用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二、文獻綜述
(一)合并商譽
葛家澍和杜興強[6] 將商譽定義為可以為企業帶來超額盈利的一切有利的要素和情形。 然而, 在現行會計準則計量方式下, 商譽是一個倒擠的“差額”, 其中相當一部分根本不能為企業帶來超額盈利能力[7] ; 商譽初始確認中的同伴效應也導致了商譽的高估[8] 。 目前, 關于商譽超額盈利能力也即并購協同效應是否得以發揮的研究, 多是從考察合并商譽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角度進行的[9-12] , 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商譽對企業績效的具體影響的結論也不一致。 朱榮和溫偉榮[13] 研究發現, 高業績承諾成為并購重組中推高估值、炒作股價的工具。 還有學者發現, 高溢價并購形成的巨額商譽會引發股價崩盤風險[14] 和商譽減值風險[15] 。 商譽已成為企業承擔較高水平風險的信號[16] , 而且有高管變更的公司, 其商譽減值程度往往更大[17] 。 還有學者發現, 商譽減值的盈余管理動機加大了商譽存在的風險[18] , 影響著債權人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3] 以及債務融資成本[4] 的權衡。
(二)商業信用
商業信用是企業在商品交易中自發形成的借貸關系。 根據商業信用在供應鏈上方向的不同, 將其分為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
現有關于商業信用供給的研究多是基于經營性動機理論。 學者們研究發現, 客戶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19] 、產品獨特性[20] 、產品市場競爭優勢[21] 、多元化經營以及獲得的銀行信貸[22] 、行業競爭程度[23] 、供應商集中度[24] 及其財務狀況[25] 等都會影響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 而且商業信用供給存在最優值, 客戶關系型交易與商業信用供給的倒U型關系[26] 、商業信用供給與公司業績[27] 的倒U型關系驗證了這一結論。
現有關于商業信用融資的研究多是基于替代性融資理論。 學者們研究發現, 供應商關系與社會信任[28] 、財務重述[29] 、財務戰略[30] 、公司戰略[31] 、社會資本[32] 等都會影響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 對于商業信用的替代性融資作用是否得以發揮, 曹云祥和宮旭紅[33] 、王貞潔和王竹泉[34] 、趙勝民和張博超[35] 的研究均表明, 商業信用對銀行信貸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
在現行會計準則下, 外購商譽已成為容納各種原因導致的“計價差額”的“容器”, 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根本不能為企業帶來超額盈利能力[7] 。 合并報表中的商譽在初始確認時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高估, 而僅有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核心商譽能夠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影響[1] , 并且股份支付方式的使用會導致商譽價值虛高[36] 。 鄭海英等[9] 的研究表明, 當期確認的合并商譽提升了短期業績, 但降低了長期業績。 而當期確認的合并商譽對短期績效的積極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正向盈余管理實現的, 企業真實績效并未得到實質性改善, 合并商譽賬面價值通過影響融資約束而對企業績效產生了消極作用[12] 。 杜春明等[3] 研究發現, 商譽信息通過影響債權人信貸決策進而影響企業債務期限結構, 商譽減值信息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 發揮了其在企業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徐經長等[4] 發現, 商譽減值金額對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產生了顯著正向影響; 黃蔚和湯湘希[2] 發現, 合并商譽與企業的融資約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以上研究表明: 商譽自產生之時就存在被高估的問題, 其代表的超額盈利能力并不能總是得到有效發揮, 對于企業經營業績也存在“虛假改善”作用; 融資約束在合并商譽賬面價值對企業績效的負面影響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 加之商譽信息為債務期限結構以及債務融資成本帶來的消極影響, 有合并商譽的企業會面臨一定程度的融資約束。 在企業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的渠道受限時, 企業有動機通過減少對下游客戶的商業信用供給來維持自身流動性需求。 據此, 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H1: 在其他條件一定時,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負相關。
(二)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
商業信用配給是上下游企業博弈的結果, 下游企業能夠獲得多少商業信用, 取決于上游企業愿意提供多少商業信用。 在當今資本市場高商譽并購、巨額商譽減值事件頻發的環境下, 超額商譽已成為企業經營的負擔。 超額商譽未能給企業帶來應有的并購協同效應, 反而對企業的成長性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同時耗費了企業寶貴的資源, 還會引發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經營的負面評價[5] 。 周澤將等[16] 認為, 合并商譽已成為企業承擔較高水平風險的重要信號, 公司擁有的商譽資產越多, 其承擔的風險水平相應越高。 朱榮和溫偉榮[13] 研究發現, 高業績承諾助長了高估值, 導致高商譽確認, 從而增加了巨額商譽減值的風險, 并購之后的巨額商譽減值和業績下滑成為當期財務業績虛高的代價。
考慮到宏觀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下行周期中, 商業信用融資約束會隨著銀行信貸的收縮而收緊, 商業信用對銀行信貸的替代效應順周期下降, 市場整體流動性風險上升[37] 。 此外, 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較高時, 企業獲取商業信用的難度較大, 獲得的商業信用規模總體上有縮小的趨勢[38] 。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 宏觀環境變化會影響商業信用融資規模, 超額商譽削弱了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 成為高風險水平的信號, 還會引發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的負面評價, 上游供應商因此而減少商業信用的供給。 據此, 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H2: 在其他條件一定時,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負相關。
(三)不同產權性質下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供給與融資的影響
在我國特殊的市場制度環境下, 產權性質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決策行為。 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有著更為嚴苛的考核標準, 同時也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 就此而言, 在同民營企業的競爭中其可能處于劣勢地位。 企業社會責任的信任觀點認為, 企業社會責任和貿易信貸提供正相關,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信任增強手段, 可以補充貿易信貸的不完全合同性質[39] 。 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受到政策扶持, 相較于民營企業, 其融資途徑更廣, 加之我國國有企業和商業銀行之間“國有同源性”的存在, 在同樣的市場環境中, 相比民營企業, 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小, 融資成本較低且更容易獲得外部融資, 因而國有企業的商業信用所發揮的替代性融資作用也較小[40] 。
根據商業信用的經營性動機理論, 商業信用可以作為保證產品質量的隱性擔保, 以及吸引客戶和刺激交易的營銷工具和競爭手段; 寬松的商業信用政策可以促進銷售并改善企業與客戶之間的關系[19,41] 。 同時, 商業信用不僅有助于客戶進行庫存融資、降低信息不對稱性和交易成本, 而且能夠為賣方提供一種更靈活的定價方法, 以及作為一種融資工具。 具有借貸能力的供應商通過將收益轉移給客戶, 改善資金管理, 使商業信用成為重要的戰略和競爭工具[42,43] 。 黃蔚和湯湘希[2] 、杜春明等[3] 、徐經長等[4] 的研究均發現, 在合并商譽的影響下, 相比民營企業, 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小。 所以, 國有企業更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向客戶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 以鞏固和維持自己的市場地位和市場份額; 同時, 更少地占用供應商資金, 通過減少商業信用融資, 維護其在供應鏈中的地位, 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 樹立負責任公司的良好形象。 據此, 提出本文的第三、第四個假設:
H3: 在國有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正相關; 在民營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負相關。
H4: 與民營企業相比,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在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2006年版《企業會計準則》將商譽單獨作為一項資產列示于財務報表中, 考慮到會計政策變更年度的商譽信息噪音較大, 本文選取2008 ~ 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中商譽賬面價值不為零的公司為研究樣本。 本文的數據篩選過程如下: 首先, 剔除ST、?ST類公司; 其次, 剔除金融類公司; 最后, 剔除數據缺失的觀測值。 為消除極端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 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上進行了縮尾處理。 本文的實證研究所涉及的相關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
(二)變量設置
1.商業信用(TC)。 本文借鑒陳勝藍和劉曉玲[44] 、Mateut[45] 的做法, 用應收賬款、應收票據以及預付賬款的總和除以期末總資產來表示商業信用供給(TCs); 借鑒陸正飛和楊德明[46] 、劉歡等[47] 的做法, 采用應付賬款、應付票據以及預收賬款的總和除以期末總資產表示商業信用融資(TCd); 用商業信用融資(TCd)減去商業信用供給(TCs)表示凈商業信用(NTC)。
2. 合并商譽(GW)。 本文借鑒黃蔚和湯湘希[2] 的做法, 采用年末資產負債表的商譽凈額除以年末總資產即標準化后的商譽進行度量。
3. 控制變量。 參照王竹泉和孫蘭蘭[27] 、魏志華和朱彩云[5] 、黃蔚和湯湘希[2] 的研究, 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股權集中度(Large1)、標準化無形資產(Intass)、市場份額(Mshare)、行業競爭程度(Competation)、產權性質(State)等變量。 此外, 本文還引入了行業、年度虛擬變量以控制行業和年度。
本文實證檢驗中所涉及的主要變量及其含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計
本文分別從商業信用供給和需求的角度研究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的影響, 均適用如下模型:
TC=β0+β1GW+β2Size+β3ROA+β4LEV+
β5Large1+β6Intass+β7Mshare+β8Competation+
β9State+β10Industry+β11Year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關鍵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商業信用供給(TCs)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184和0.166, 均大于商業信用融資(TCd)的均值(0.173)和中位數(0.143), 呈現出凈商業信用(NTC)總體趨向于負值的狀況。 解釋變量商譽(GW)的均值為0.049, 中位數為0.008, 數據整體呈現右偏態勢。 企業規模(Size)的均值(22.21)和中位數(22.04)較為接近, 最小值為19.24, 最大值為25.97。 樣本企業資產收益率(ROA)的均值為4.3%, 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為42.7%, 市場份額(Mshare)的均值為8%,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Large1)的均值為34.6%, 無形資產與總資產比值(Intass)的均值為4.8%。 此外, 樣本中有35.8%的企業所屬行業的行業競爭程度較高, 國有企業占比為35.6%。
(二)相關性檢驗
表3列示了關鍵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和Spearman相關系數。 由表3可以看出, 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較小, 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基本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 此外, 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VIF最大值為2.49, 小于10, 所以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解釋變量商譽(GW)與被解釋變量商業信用融資(TCd)的Pearson相關系數和Spearman相關系數均為負, 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 本文提出的H2得到初步驗證。
(三)多元回歸分析
1. 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供給的影響。 表4列示了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的回歸結果, 其中第(1) ~ (3)列分別為將商業信用供給當期數據(TCs)、滯后一期數據(F.TCs)以及滯后兩期數據(F2.TCs)代入模型的回歸結果。 在使用當期數據回歸時, 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044,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合并商譽越多, 企業對外提供的商業信用越少。 這一結果表明, 隨著合并商譽的增加, 企業傾向于減少商業信用供給, 以緩解自身面臨的融資約束, 儲備更多資金來維持自身的流動性需求。 由此, 本文提出的H1得到驗證。
此外, 上述關系在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滯后兩期時均不顯著, 說明合并商譽對企業商業信用供給的影響不具有持續性。
2. 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 表5列示了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回歸結果, 其中第(1) ~ (3)列分別為將商業信用融資當期數據(TCd)、滯后一期數據(F.TCd)以及滯后兩期數據(F2.TCd)代入模型的回歸結果。 合并商譽(GW)與各期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25、-0.108、
-0.115, 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合并商譽越多, 企業獲得的商業信用融資越少。 這一結果表明, 隨著合并商譽的增加, 上游供應商傾向于減少商業信用供給, 企業可以獲得的商業信用融資會相應減少, 并且這種關系具有持續性。 由此, 本文提出的H2得到驗證。
與H1的驗證過程相比, 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供給的影響不具有持續性, 而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具有持續性, 說明企業對于商業信用的使用也受到一定約束, 在商業信用融資持續減少的情況下, 商業信用供給并不會保持同方向變動, 企業對商業信用的占用(凈商業信用)呈現出減少的趨勢。
3. 產權性質的影響。 表6列示了不同產權性質下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和融資的回歸結果。 表6第(1)列顯示, 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135,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在國有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顯著正相關。 國有企業中合并商譽越多, 其向下游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越多。 第(2)列顯示, 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066,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在民營企業中, 合并商譽越多, 企業的商業信用供給越少。 第(1)列與第(2)列的組間差異在1%的水平上顯著。 這說明, 產權性質這一變量對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之間關系的影響具有顯著性。 在企業總體融資需求穩定的情況下, 相比于民營企業, 國有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較小, 且出于鞏固市場地位和刺激產品需求的目的, 其有能力對外提供更多商業信用; 而民營企業在面臨嚴峻融資約束的情況下, 會減少商業信用供給以保證自身的流動性需求。 由此, 本文提出的H3得到驗證。
表6第(3)列顯示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230, 第(4)列顯示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102, 兩者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 而且產權性質分組的組間差異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 這說明產權性質這一變量對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之間關系的影響具有顯著性。 從回歸系數來看, 國有企業合并商譽的系數大于民營企業合并商譽的系數, 表明在國有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更為顯著, 若商譽增加, 則國有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融資減少, 占用上游企業的資金減少。 由此, 本文提出的H4得到驗證。
(四)進一步討論
凈商業信用可用于衡量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凈融資水平。 本文的凈商業信用(NTC)采用上文的商業信用融資(TCd)減去商業信用供給(TCs)所得的差額進行計量。 表4和表5列示的結果分別驗證了本文所提出的H1和H2, 即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均顯著負相關。 在合并商譽的影響下, 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的變化將會導致凈商業信用如何變化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于是, 本文將凈商業信用(NTC)作為被解釋變量, 仍使用上文中選擇的樣本與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結果如表7 所示。
根據表7列示的回歸結果, 第(1)列中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080,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合并商譽越大, 凈商業信用越小, 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凈融資規模越小。 這表明在合并商譽的影響下, 企業的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都會減少, 但相比商業信用供給, 商業信用融資減少的幅度更大。 這也與上文關于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的檢驗結果一致。
由于凈商業信用(NTC)取值有正有負, 可能出現相互抵消的現象, 所以本文進一步將總樣本分為凈商業信用為正和凈商業信用為負兩組分別進行回歸。 當NTC>0時, 表示為凈商業信用融資(NTCd); 當NTC<0時, 取其絕對值表示為凈商業信用供給(NTCs)。 表7第(2)列顯示, 當凈商業信用為正值時, 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151,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表明合并商譽越大, 凈商業信用融資越小, 這與第(1)列的結論一致; 第(3)列顯示, 當凈商業信用為負值時, 合并商譽(GW)的系數為-0.025, 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 表明合并商譽越大, 凈商業信用供給越小。 以上分組回歸結果表明, 合并商譽越大, 商業信用供給(TCs)與商業信用融資(TCd)越接近, 兩者之間的差額越小, 此時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整體規模減小, 商業信用在供應鏈中可以發揮的作用降低。 總體而言, 在合并商譽的影響下, 商業信用的替代性融資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五)穩健性檢驗
1. 替換被解釋變量。 借鑒馬亞明和張潔瓊[37] 的做法, 用應收賬款與應收票據合計數除以總資產表示商業信用供給(TCs2), 用應付賬款與應付票據合計數除以總資產表示商業信用融資(TCd2), 回歸結果如表8第(1)、(2)列所示, 可見回歸結果依然保持穩健。
2. 增加關鍵變量。 成長性是影響和衡量企業特征的關鍵變量之一, 借鑒徐經長等[4] 、方紅星和楚有為[31] 等的做法, 使用營業收入增長率作為衡量企業成長性(Growth)的替代指標。 將企業成長性(Growth)這一變量引入回歸模型中再次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8第(3)、(4)列所示。 企業成長性變量本身在模型中具有顯著性, 可作為影響被解釋變量的指標, 且解釋變量(GW)的符號和顯著性與前文一致, 結果保持穩健。
3. 內生性問題的處理。 由于本文選擇商譽不為零的企業為樣本進行回歸, 有的商譽數據可能對本文研究的問題產生系統性偏差, 因而存在樣本自選擇問題。 為此, 本文基于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PSM)對合并商譽與企業商業信用之間的關系進行穩健性檢驗。 將商譽大于零的樣本歸為“處理組”, 共9503個樣本, 然后選擇企業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Large1)、標準化無形資產(Intass)和市場份額(Mshare)計算傾向評分(PS), 分別使用最近鄰匹配和核匹配構建處理組和控制組。 傾向性得分匹配結果如表9所示, 匹配后的平均處理效應顯著, 表明控制合并商譽的樣本自選擇問題后, 合并商譽對企業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依然具有顯著的影響, H1和H2進一步得到驗證, 說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分別從商業信用供給和融資角度討論合并商譽對商業信用的影響,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均表現為負相關關系, 且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具有持續性, 即合并商譽增加, 當期企業供給的商業信用會減少, 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會持續減少。 將樣本進行分組后, 考察不同產權性質對上述關系的影響, 發現: 在國有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正相關, 與商業信用融資負相關; 在民營企業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供給負相關, 與商業信用融資也負相關; 而且相比民營企業, 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在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 進一步檢驗合并商譽與凈商業信用的關系, 發現合并商譽與凈商業信用顯著負相關。 區分凈商業信用正負號后, 發現合并商譽與凈商業信用融資、凈商業信用供給均呈負相關關系, 即合并商譽越大, 凈商業信用融資和凈商業信用供給越小, 商業信用融資與商業信用供給同時減小且趨于接近, 總體呈現出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規模減小的狀況。 總體而言, 在合并商譽的影響下, 商業信用的替代性融資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本文使用替換被解釋變量、增加關鍵變量以及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PSM)對上述結論進行了檢驗, 檢驗結果表明研究結論依然穩健。
(二)啟示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 研究了合并商譽對企業商業信用的影響, 分別從商業信用供給和商業信用融資兩個角度進行討論, 而現有文獻對于商業信用的探討多是僅考慮其中一個角度; 同時, 在合并商譽與商業信用之間建立聯系, 豐富了商譽經濟后果的相關研究文獻, 也為研究商業信用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 企業應適當實施并購戰略并合理控制商譽的規模, 企業合并絕不僅僅體現為一項商譽資產, 也不只會影響企業自身的經營決策, 還會影響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的評價, 而供應商和客戶就是重要的利益相關方。 本研究發現, 合并商譽增加, 則企業使用商業信用的規模減小, 商業信用供給、商業信用融資、凈商業信用都會減少, 從而導致企業在供應鏈中的地位及其與客戶、供應商之間的關系都會發生一定的變化。 企業應謹慎實施并購戰略, 并且要維護好與供應商、客戶等利益相關方之間的關系, 從而保證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王秀麗.并購商譽、超額收益與市場反應——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證據[ J].新疆財經,2013(5):22 ~ 29.
[2] 黃蔚,湯湘希.合并商譽會增加企業的融資約束嗎?[ J].證券市場導報,2018(12):32 ~ 40+46.
[3] 杜春明,張先治,常利民.商譽信息會影響企業債務期限結構嗎?——基于債權人的視角[ J].證券市場導報,2019(2):45 ~ 54.
[4] 徐經長,張東旭,劉歡歡.并購商譽信息會影響債務資本成本嗎?[ 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7(3):109 ~ 118.
[5] 魏志華,朱彩云.超額商譽是否成為企業經營負擔——基于產品市場競爭能力視角的解釋[ J].中國工業經濟,2019(11):174 ~ 192.
[6] 葛家澍,杜興強.中級財務會計學(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 ~ 609.
[7] 杜興強,杜穎潔,周澤將.商譽的內涵及其確認問題探討[ J].會計研究,2011(1):11 ~ 16+95.
[8] Liping Xu, Yueqin Guan, Zhihong Fu, Yu Xin. Peer effect in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goodwill[ J].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20(1):57 ~ 77.
[9] 鄭海英,劉正陽,馮衛東.并購商譽能提升公司業績嗎?——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會計研究,2014(3):11 ~ 17+95.
[10] Li Xiao, Yiwei Liu. The impact of the merger goodwill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J].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2016(4):749 ~ 758.
[11] 馮科,楊威.并購商譽能提升公司價值嗎?——基于會計業績和市場業績雙重視角的經驗證據[ 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20 ~ 32.
[12] 黃蔚,湯湘希.合并商譽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基于盈余管理和融資約束中介效應的分析[ 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9(12):93 ~ 106.
[13] 朱榮,溫偉榮.高業績承諾下我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估值風險研究[ J].中國資產評估,2019(9):31 ~ 40.
[14] 鄧鳴茂,梅春.高溢價并購的達摩克斯之劍:商譽與股價崩盤風險[ 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9(6):56 ~ 69.
[15] 田新民,陸亞晨.中國上市公司商譽減值風險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12):114 ~ 127.
[16] 周澤將,胡劉芬,馬靜,張東旭.商譽與企業風險承擔[ J].會計研究,2019(7):21 ~ 26.
[17] Zhiqiang Li. Impact of executive changes on goodwill impairment[ J].Modern Economy,2020(2):561 ~ 569.
[18] 盧煜,曲曉輝.商譽減值的盈余管理動機——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7):87 ~ 99.
[19] Daniela Fabbri, Leora F. Klapper. Bargaining power and trade credit[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6(41):66 ~ 80.
[20] 肖作平,劉辰嫣.上下游企業議價能力、產品獨特性與企業商業信用——來自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證券市場導報,2017(9):33 ~ 41.
[21] 吳育輝,黃飄飄,陳維,吳世農.產品市場競爭優勢、資本結構與商業信用支持——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J].管理科學學報,2017(5):51 ~ 65.
[22] 吳昊旻,王杰,買生.多元化經營、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提供——兼論融資約束與經濟周期的影響[ J].管理評論,2017(10): 223 ~ 233.
[23] 張會麗,王開顏.行業競爭影響企業商業信用提供嗎?——來自中國A股資本市場的經驗證據[ 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2):64 ~ 73.
[24] 李振東,馬超.供應商集中度與企業外部融資約束[ J].經濟問題,2019(8):27 ~ 35.
[25] Sijing Deng,Ke Fu, Jiayan Xu, Kaijie Zhu. The supply chain effects of trade credit under uncertain demands[ J].Omega, 2019(8):N/A.
[26] 章鐵生,李媛媛.客戶關系型交易、產品獨特性與商業信用供給[ J].會計與經濟研究,2019(1):86 ~ 102.
[27] 王竹泉,孫蘭蘭.市場勢力、創新能力與最優商業信用供給[ 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10):36 ~ 46.
[28] 孫蘭蘭,翟士運,王竹泉.供應商關系、社會信任與商業信用融資效應[ J].軟科學,2017(2):71 ~ 74.
[29] 錢愛民,朱大鵬.財務重述影響供應商向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嗎——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7(4):62 ~ 69.
[30] 朱杰.財務戰略影響公司商業信用融資能力嗎?[ 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8(6):71 ~ 82.
[31] 方紅星,楚有為.公司戰略與商業信用融資[ J].南開管理評論,2019(5):142 ~ 154.
[32] Mostafa Monzur Hasan,Ahsan Habib. Social capital and trade credit[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9(61): 158 ~ 174.
[33] 曹云祥,宮旭紅.商業信用能否緩解企業信貸約束——基于企業產權異質性的實證分析[ 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 2015(6):82 ~ 92.
[34] 王貞潔,王竹泉.基于供應商關系的營運資金管理——“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 J].南開管理評論,2017(2):32 ~ 44.
[35] 趙勝民,張博超.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能相互替代嗎——基于2000-2018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的實證分析[ J].上海金融, 2019(1):16 ~ 23.
[36] 謝紀剛,張秋生.股份支付、交易制度與商譽高估——基于中小板公司并購的數據分析[ J].會計研究,2013(12):47 ~ 52+97.
[37] 馬亞明,張潔瓊.商業信用:替代性融資,還是流動性危機的信號?[ J].商業研究,2019(6):103 ~ 112.
[38] 王化成,劉歡,高升好.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產權性質與商業信用[ 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6(5):34 ~ 45.
[39] Adrian(Waikong) Cheung, Wee Ching Pok.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ision of trade credit[ 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9(3):N/A.
[40] 葛結根.并購對目標上市公司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 J].會計研究,2017(8):68 ~ 73+95.
[41] Travis Box, Ryan Davis, Matthew Hill, Chris Lawrey.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aggressive trade credit policies[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8(89):192 ~ 208.
[42] Salima Paul, Rebecca Boden. The secret life of UK trade credit supply:Setting a new research agenda[ J].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08(3):272 ~ 281.
[43] Jaideep Shenoy, Ryan Williams. Trade credit and the joint effects of supplier and customer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5(29):68 ~ 80.
[44] 陳勝藍,劉曉玲.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公司商業信用供給[ J].金融研究,2018(5):172 ~ 190.
[45] Mateut S.. Reverse trade credit or default risk?Explaining the use of prepayments by firms[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4(29):303 ~ 326.
[46] 陸正飛,楊德明.商業信用:替代性融資,還是買方市場?[ J].管理世界,2011(4):6 ~ 14+45.
[47] 劉歡,鄧路,廖明情.公司的市場地位會影響商業信用規模嗎?[ 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5(12):3119 ~ 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