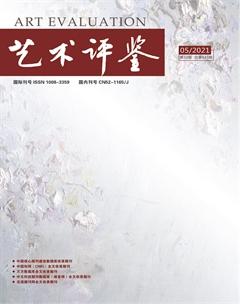杜塞爾多夫?qū)W派與貝歇夫婦的類型學攝影
辛智晟
摘要:類型學攝影是由貝歇夫婦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攝影類分化,其指示了一種全新的多學科跨媒介的客觀研究方法,為當代攝影的觀念化提供了一種嚴謹?shù)霓D(zhuǎn)化方法,其主要使用大畫幅相機拍攝工業(yè)時代的建筑,并采用田野調(diào)查的方法手段加上科學實驗式的客觀態(tài)度進行攝影拍攝與制作。貝歇夫婦創(chuàng)立的杜塞爾多夫?qū)W派為當代攝影提供了一種觀念化表達的通道與方法,改變了傳統(tǒng)“紀實”的定義。
關鍵詞:貝歇夫婦 ?當代攝影 ?觀念攝影 ?杜塞爾多夫?qū)W派 ?當代藝術
中圖分類號:J0-05
在傳統(tǒng)攝影盛行的時代,“決定性瞬間”等以隨機化、無干涉的外部環(huán)境為主要特征的黑白紀實攝影系統(tǒng),以快速捕捉的方法論影響著當代攝影,而貝歇夫婦選擇與主流背道而馳的客觀與冷靜的大畫幅攝影方式,跳出攝影本身系統(tǒng),使用人類學等多學科調(diào)查思維思考全新的攝影,作為單一藝術媒介的邊界,并將具有當代藝術特征的觀念性置入攝影語境之中,使其成為了當代觀念攝影的開端。
一、杜塞爾多夫?qū)W派以及類型學攝影的產(chǎn)生
(一)貝歇夫婦生平
伯恩德·貝歇于1931年出生于德國錫根市,他于1953至1956年在斯圖加特國立美術館學習繪畫,這段繪畫經(jīng)歷給貝歇帶來了“新客觀主義的影響”,緊接著在1957年他在杜塞爾多夫?qū)W院學習印刷,并開始拍攝一些繪畫素材,并在同年進入杜塞爾多夫的一家廣告公司擔任自由攝影師,專注于產(chǎn)品攝影,并與希拉·貝歇相識。1934年希拉·貝歇出生于波茨坦,并在1951年至1954年完成了攝影學徒的計劃,并于1958年在杜塞爾多夫?qū)W院作為攝影教授,同時在杜塞爾多夫的廣告公司遇見伯恩德。兩人于1959年首次合作拍攝正在消失的德國工業(yè)建筑,他們經(jīng)常一起帶著一臺8x10大畫幅相機出門,第一次拍攝的地點是伯恩德家人原工作的鋼鐵與采礦行業(yè)的魯爾河谷,伯恩德原來的成長環(huán)境為之后作品的選材帶來了顯著的影響。在1961年兩人成為夫妻,1976年,伯恩德開始在杜塞爾多夫?qū)W院教授攝影。
(二)貝歇夫婦的類型學初探
在1959年兩人開始在魯爾河谷合作拍攝,他們起初被工業(yè)化建筑的外形與設計吸引,但在大量拍攝后,貝歇夫婦意識到某種結(jié)構與形式的規(guī)律,他們開始有意識的拍攝包括:谷倉、水塔、卸煤機、冷卻塔、燃料罐、倉庫等建筑,并開始排除任何可能影響整體中心形式主題的細節(jié),同時設置了視點的比較,通過這些比較,我們可以清晰的識別影像中的基本圖案與形式,同時在展示上,貝歇夫婦將具有共同特性的影像以9、12、15等為單位進行方陣排列,強調(diào)相同建筑與物體在不同地理環(huán)境以及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外表差異,并以分組的方式將這類差異化進行了最大程度的體現(xiàn),最終,在拍攝形式上對“類型”的視覺特征進行完全統(tǒng)一,使其對照于田野調(diào)查存檔影像形成一種參照感。
(三)類型學的時代與藝術美學背景
類型學攝影并非空穴來風或是一蹴而就,其背后是藝術環(huán)境以及攝影前驅(qū)互相作用的結(jié)果。首先在時代背景中,在戰(zhàn)爭技術后攝影藝術家們意識到攝影作為藝術媒介所具有的公共藝術以及傳達屬性,認為攝影也應具有一些社會關切與思想表達的意識。在20世紀伊始,德國攝影師奧古斯特·桑德斯、倫格·帕奇等人是最早運用類型學方法拍攝的攝影師,而貝歇夫婦正是深受到奧古斯特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奧古斯特的“德國人”系列影響而進入了類型學攝影的方向。而在60年代同時期,觀念藝術正在藝術界廣泛傳播,這一種全新的藝術范式加強了當時藝術家們的表達思想,使一種嚴謹?shù)谋矸ǚ椒ㄅc一套觀念藝術的理論傳播開來。
而在當代攝影史上,盡管主流攝影仍屬以決定性瞬間為代表的以黑白作為色彩媒介的傳統(tǒng)攝影,世界攝影界都在強調(diào)攝影拍攝所需要具有的主觀審美性、形式的規(guī)律性,但當代攝影史上做出重大改變的攝影師正在開始創(chuàng)作,如那時正在安迪·沃霍爾藝術工廠工作的史蒂芬·肖爾,景觀的定義也正在被改變,攝影藝術同時正受到例如美國大都會博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等藝術機構的承認。
(四)杜塞爾多夫?qū)W派的出現(xiàn)
在1976年,伯恩德·貝歇正式在德國杜塞爾多夫?qū)W派開創(chuàng)攝影專業(yè)并任教,直至其任教結(jié)束的1996年間,貝歇教授了以坎迪達·霍夫、托馬斯·魯夫、托馬斯·施特魯斯以及安德烈亞·古斯基為代表的攝影藝術家,其中古斯基的作品《萊茵河二號》成為了史上拍賣價格最高的藝術作品,其他幾位藝術家也繼承發(fā)揚了貝歇夫婦的類型學攝影,并繼續(xù)向前推進了其觀念性的抽象化以及客觀化。貝歇在學院主要教授類型學攝影的基本方法,從選題開始,貝歇認為類型學攝影首先需要選擇一個社會議題或社會話題進行討論研究,并確定一個拍攝方向,之后采用客觀調(diào)查的科學實驗方法進行拍攝,在拍攝了大量作品后即會在形成類型學的基礎上展示其觀念的傳導性,并形成一種客觀嚴謹?shù)恼J知對比,而在形成對比后作品的觀念性討論則進入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狀態(tài),這時就可以開始考慮作品的展覽方式以及排布問題,貝歇認為“我們的作品中不存在個別的物體和因素,如單個的水塔住又在某個水塔系列作品里才有意義”。
而隨著貝歇夫婦在1972年受到國際認知與認同后,其代表性的類型學作品以及展陳方式形成了類型學的視覺風格,并正式形成了類型學攝影的學術攝影風格,同時其學生在貝歇任教的杜塞爾多夫?qū)W院畢業(yè)后也在原基礎上繼續(xù)推進了類型學攝影的邊界,有的采用了類型學攝影冷靜客觀的觀察風格,有的繼承了類型學攝影的科學實驗方法,并最終形成了各自的風格,且由于他們都師承貝歇夫婦,且畢業(yè)于杜塞爾多夫?qū)W院,所以最終被整體稱之為“杜塞爾多夫?qū)W派”,并作為當代攝影的重要學派存在于世界藝術界。
二、類型學攝影以及杜塞爾多夫?qū)W派的藝術表征
我們必須從類型學本身之意義出發(fā)研究分析貝歇夫婦與其門徒一派開創(chuàng)的類型學攝影以及杜塞爾多夫?qū)W派的藝術表征。
類型,本身是指一種分類方法與手段,是以某種特殊物化屬性進行分類與識別的,同時能夠在目標研究對象中建立借由這類屬性建立某種聯(lián)系與關系以進行對比以及對照的研究行為。琳妮·沃倫在其著作《20世紀攝影百科全書中》寫到類型學攝影應屬于分類學在攝影中的分化,且產(chǎn)生的相應流派應被稱為“新客觀主義”,但不管是類型學本身定義或是產(chǎn)生并分化所得出的結(jié)果,其都應證了類型學攝影是一種繼承類型學理性、客觀以及冷靜態(tài)度的以攝影為媒介,通過分類建立聯(lián)系,對比以分析研究對象的跨媒介、跨學科的攝影方法學。
(一)客觀且冷靜的藝術表征
通過了解類型學與類型學攝影的基本定義與理論來源,客觀與冷靜不可避免的成為了類型學攝影以及杜塞爾多夫?qū)W派所具有的強烈藝術表征之一。縱觀杜塞爾多夫?qū)W派自70年代開始發(fā)展的藝術作品,一種克制的秩序以及精心思考的感受在畫面中顯現(xiàn),如貝歇夫婦的代表工業(yè)建筑系列,其為了減少光比的改變與整體畫面不需要雜音的出現(xiàn),盡量選擇陰天的白光環(huán)境拍攝,并使用大畫幅相機矯正透視與視差,同時控制景深以達到完全的一致,同時控制主體在畫面中的整體比例與位置,以同時呈現(xiàn)一種堅實簡約的雕塑感受以及一種來源于現(xiàn)實但脫離于現(xiàn)實的抽離感。
(二)大畫幅下的夢境感受
通過大畫幅拍攝意味著長時間的調(diào)整與準備工作,更加縝密的細節(jié)調(diào)教、更可控制的畫面產(chǎn)出,同時大于普通135膠片數(shù)倍的8x10膠片能帶來更多的畫面細節(jié)與信息。而從拍攝進入到實際展陳中,大畫幅的拍攝進一步顯示了其繁瑣操作背后所帶來的益處,尺幅超越常人身高的巨幅作品帶來了異常清晰的細節(jié),并帶來了巨大的視覺沖擊力,瞬間觀眾開始注意到地面上不起眼的某樣物品原來存在如此多的細節(jié),主體物中大量的時間痕跡開始進入觀眾視野,大畫幅帶來的大量視覺信息改變了觀眾觀看的習慣,突破了人類視覺的正常模式,將其帶離到一種巨細無遺的疏離夢境中。
(三)強烈觀念性的置入
如前文所說,類型學攝影本質(zhì)是一種研究客觀課題的攝影方法學,而在研究中必須要放置的研究者的思想或思考,也就是藝術家對議題在畫面中表達的暗示安排與思考,而在杜塞爾多夫?qū)W派中,代表性觀念置入的有托馬斯·魯夫于1989年創(chuàng)作的《人像》系列,還有創(chuàng)作攝影藝術史上最高拍賣價格作品《萊茵河二號》的藝術家安德烈亞·古斯基,其分別從類型學攝影的本身方法入手,進一步拓寬了其邊界,從自表現(xiàn)形式入手拓寬了其表達界限。
首先是魯夫的《人像》系列,其畫面主要由魯夫身邊認識的人組成,在那時魯夫意識到他正生活在20世紀末期,一個監(jiān)控無處不在的西方世界。那時德國發(fā)生了恐怖事件,很多政客被暗殺,社會氛圍十分緊張,經(jīng)常會被要求出示護照。而魯夫正是以護照照片為類型學的視覺分類范式,他要求被攝者不表現(xiàn)出任何情感的看著鏡頭,并將被攝者可呈現(xiàn)出的暗示個人個性與能夠指向任何個人情況的特征去掉,但同時保留了不同的衣物,制造出一套似護照登記照且所有人的視覺指向性極其相似并類似同一人的影像。魯夫認為機場登記照本身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功能性影像材料,警察對其查看以獲取一些當事人的面部信息以及一些對當事人的指向性暗示推測信息,但魯夫?qū)⑦@種能夠表達個體信息以及意指的視覺元素從這類固定的視覺感受中抽離開來,并將被攝對象盡量成為同一類型的人像,同時又都處于登記照人像的視覺分類中,即這組影像呈現(xiàn)了一種類型上的一致,同時在內(nèi)核中又完全不處于同一類型的視覺矛盾效果。
其次是古斯基的《萊茵河二號》,其原本是存在《萊茵河一號》或其他系列作品的,但古斯基只從系列作品中選取了第二號作品,這是其對類型學攝影的第一步推進,不再選用完整的作品,而是使用數(shù)字處理后期技術,進而引向單一作品的出現(xiàn)。此外,觀念性的表達在萊茵河二號中也由數(shù)字后期處理技術達成,古斯基首先采用的是類型學攝影中冷靜與客觀的視覺形式,但本幅作品呈現(xiàn)的萊茵河是現(xiàn)實中不存在的,數(shù)字后期合成的萊茵河二號,這本身就打破了冷靜客觀形勢下給人帶來的事實證據(jù)之感,事實上萊茵河的景象是充滿了各類人類足跡,如河對岸的工業(yè)建筑被古斯基使用技術手段去除,草坪上的大量人類痕跡也被去除,古斯基使用類型學所提供的客觀之感作為形式,首先說服了觀眾其景象的真實性,同時在景象中作假,制造了自己認為的在此地未曾有人類出現(xiàn)時的景象,將這種信以為真的假象向觀眾提出疑問,也同樣制造了一個內(nèi)容與形式上的視覺矛盾與轉(zhuǎn)折,使“假象”形成了“真實”。
三、杜塞爾多夫?qū)W派以及類型學攝影對當代攝影產(chǎn)生的影響
貝歇夫婦以及其開創(chuàng)的類型學攝影在其發(fā)展初期就受到了大量的國際關注與評論。在1975年與美國喬治·伊斯曼故居舉辦的標志當代攝影流派“新地形”形成的“新地形學:人為改造的地理影像”展覽中,貝歇夫婦被作為唯一在美國之外的外國攝影師參加了這場展覽,同時參加這場展覽的還有當代攝影新彩色運動中重要的攝影師斯蒂芬·肖爾以及羅伯特·亞當斯等當時的年輕攝影藝術家,并成為了包括新地形攝影的新客觀主義攝影的一部分,貝歇夫婦所開創(chuàng)的類型學攝影在那時就已經(jīng)開始對當代攝影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而貝歇夫婦創(chuàng)立的杜塞爾多夫?qū)W派對當代藝術攝影市場也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其幾大門徒之一的古斯基刷新了藝術拍賣市場對于攝影藝術作品的價格,一舉成為歷史上價格最貴的照片,照片尺幅的增加隨之帶來的是價格的增長,為攝影藝術市場注入了全新的收藏活力。
隨著杜塞爾多夫?qū)W派的逐漸成熟,其對下一代攝影藝術家也帶去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英國藝術家納達夫·坎德在2006年5次進入中國拍攝《長江》系列,其呈現(xiàn)了中國飛速發(fā)展下長江沿岸的生活景觀與工業(yè)景觀;加拿大藝術家愛德華·波丁斯基在中國拍攝的三峽系列;杜塞爾多夫?qū)W派客觀與冷靜敘述的事實性在他們的作品中一覽無遺,有力表現(xiàn)了經(jīng)濟全球化以來中國的發(fā)展景觀。
四、結(jié)語
貝歇夫婦自1959年開始建立的類型學攝影以及其教授的門徒們所組成的杜塞爾多夫?qū)W派深刻影響了以觀念性為主要特征的當代攝影,其將一種慢節(jié)奏同時在內(nèi)容與形式深刻表達的攝影范式提供給當代攝影師們。“攝影家們更注意的首先是在照片中表現(xiàn)自己的觀念。他們往往強調(diào)拍攝中的觀念主導,常常以一種統(tǒng)一的風格來處理主題、強調(diào)對主題的理性把握,而不是像以前的攝影師那樣只是依賴于拍攝過程中的偶然性邂逅”。由顧錚在《國外后現(xiàn)代攝影》一書中陳述的關于當代攝影的觀念性方法學很好地解釋了杜塞爾多夫?qū)W派給當代攝影帶來的改變,即是由被動依賴轉(zhuǎn)換成為有計劃、有方法的研究與表達,同時借由各類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創(chuàng)作與拍攝。
所以深刻研究貝歇夫婦以及其創(chuàng)立的杜塞爾多夫?qū)W派,真正帶給當代攝影的是對于攝影媒介所獨特具有的本真性以及證據(jù)性的全新答案,是對“紀實”二字的另一種解釋。冷靜客觀的大畫幅攝影背后不僅代表著拍攝者熟練高超的相機操作技巧,更代表著觀念、信息的集成傳達與思想、哲學的暗示與意指。
參考文獻:
[1]繆曉春.貝歇訪談[J].中國攝影,2001(02):48-52.
[2]陳建中.由“類型學攝影”到“景觀攝影”[J].中國攝影家,2010(04):10-11.
[3]劉憲標,王振冠.杜塞爾多夫攝影學派研究[J].歌海,2019(05):117-119.
[4]顧錚.國外后現(xiàn)代攝影[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