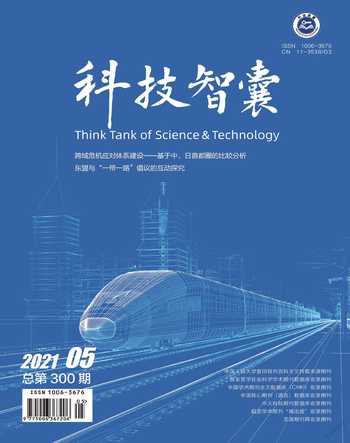人工智能環境下傳播格局的重構
李丹 裴碩
摘? 要:隨著VR/AR、5G等技術的逐漸普及,各類終端媒介走向深度融合,萬物互聯、人機共存成為未來發展趨勢,整個社會呈現出智能化傾向。文章在媒介環境學視域下,分別從感知環境與符號環境兩個層面來理解人工智能,探究當前人與技術的共存關系、媒介與社會文化的共生關系、媒介與思想意識的共長關系。在這一新的媒介環境下,原有的傳播格局被逐漸消解,新的傳播格局正在形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引發傳播形態的交互,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更為復雜;二是信息系統的深度融合,導致了傳播內容的轉變;三是這一新格局倒逼媒介管理者對自身角色做出改變,并完善傳媒管理體系。
關鍵詞:人工智能;傳播格局;媒介環境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5.08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tern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Li Dan1? Pei Shuo2
(1.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100024;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imary Education,Beijing,100048)
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VR/AR,5G,and other technologies,various terminal media are gradually being deeply integrated,the inter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and human-machine coexistence have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the whole society presents an intelligent ten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this article understan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wo levels of 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and symbolic environment respectively explores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the symbiosis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culture,and the co-grow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ideology. In this new media environment,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been dissolved,and a new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taken shape or is taking shape,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leads to the interaction of communication forms,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is more complex. Second,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Finally,this new pattern forces media managers to change their roles and improve the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mmunication pattern;The media environment
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隨著5G、人工智能、VR/AR等媒體融合技術的發展,社會開啟了智能化媒體的新時代。智能化媒體的特征主要體現為萬物皆媒、人機共生、自我進化[1],其中尤以人工智能為主要代表。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原有的以大眾傳播為主導的傳播格局受到挑戰,新的傳播格局正在形成。
一、人工智能的媒介環境學分析
將媒介當作環境來研究是媒介環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一“環境”包含符號環境、感知環境及社會環境三個層面。媒介環境學強調,人是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其研究重點是人與傳播媒介的關系。[2]1968年,波斯曼在公開介紹這一學科范式時指出,媒介是復雜的訊息系統,而媒介環境學則試圖去揭示其隱含的、固有的結構,以及它們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響。麥克盧漢也指出,當社會的主導媒介發生變化時,其對應的符號系統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且這一變化又會致使人的感官發生變化。因此,將人工智能這一新時代媒介當作一種環境來研究,意味著至少可以在兩個層面來理解它。
(一)作為感知環境的人工智能
正如麥克盧漢指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每一種媒介都對應著一套感官特征。例如,以閱讀為主的印刷媒介是對視覺的延伸,需要用耳朵收聽的廣播媒介是對聽覺的延伸,看電視則是視覺與聽覺延伸的結合。這種透過媒介過濾的感知環境即李普曼所說的“擬態環境”,在感官形貌發生變化的環境中,人們接收感覺資料的方式也發生了轉變,進而迫使人們重新理解和建構周圍的世界。人工智能帶領人類進入一個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感知環境,它延伸與擴展的不僅是某一感官或某幾個感官的組合,而是人的智識。通過對人的意識及思維過程的模擬,人工智能與人共生共存,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接收感覺資料時,人們不會因一種感官的加強而導致其他感官的削弱,人們整體的感知系統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一種全身心地浸入式體驗和參與。在這一仿真環境下,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發生交互,且二者的邊界趨于模糊,這使得人們在理解世界時更易將虛擬世界當成需要付諸行動的真實世界,隨之改變的是人類的行為習慣與思維模式。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類的大腦首先獲得了解放。在人與機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人類得以更為深入地了解自己。例如,人們可以運用自己最為熟悉的語言進行人機交互,而無須學習復雜的編程系統,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生存,同時,機器也可以識別和理解人類的情感,使其在需要表達或發泄情緒時獲得“同伴”。人工智能環境下人與機器共同創設的人機共生共存,是對人的感官功能的解放,這也倒逼人類更謹慎地判斷人與技術的關系。
(二)作為符號環境的人工智能
從符號層面來看,我們將人工智能設想為一種符號環境,且是由一套獨特的代碼及語法有序組成的符號環境。例如,為了能順暢地閱讀,我們需要掌握書面語的詞匯與相關語法;為了能流利地看電影,我們需要對其構成元素有一定的了解。而在智媒時代,為了能夠和諧地與機器共處,我們需要學習相關的數字代碼,以了解其運作機制。當我們與媒介相互作用時,我們也融入媒介所構建的環境中,因這一環境正是媒介本身,這一點在人工智能的運用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我們通過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真切地感知周圍的物質世界;另一方面,我們又從其顯示的智能化符號世界內部來思考和表征物質世界,而這一世界也成為我們所認為或了解的世界。因此,在萬物皆媒的環境下,世界“感知起來”就像是一個又一個的終端,且我們就身處其中。具體來說,智能媒體所攜帶的符號結構,給我們的認知、意識及心靈活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我們描寫經驗的方式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固定的、無法修改的,而是可不斷修改甚至擴充的。此外,更加依賴技術和系統的研判和決策,也會導致人類的認知能力與主動思考能力的下降,這警示我們在通過人工智能界定或建構描寫經驗的方式時,要對其符號結構持審慎的態度,不應忘記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
感知環境與符號環境是人工智能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兩個方面,人們在交流與獲取信息時,并不會有意識地區分這兩個方面。但感知與符號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且人工智能這一全媒化的終端技術在這兩方面都有了較之以往更為深遠的轉變,所以筆者將人工智能分別當作兩種環境來論述,以便我們能更為細致、全面地了解人工智能。此外,除從上述兩個層面對人工智能進行理解外,還可以從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層面來對其進行研究,不同的媒介形式提供不同的傳播結構,并影響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由此,在微觀環境與宏觀環境的共同作用下,舊的傳播格局被消解,新格局得以重構。
二、人工智能環境下傳播格局的重構
人工智能環境下傳播格局的重構體現在各傳播要素的改變及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以下將從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出發,通過探討人與媒介之間關系的轉變理解傳播格局在新媒介環境下的重構。
(一)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引發傳播形態的融合
隨著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更為智能、融合的數字化終端技術被應用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當前各類社交媒體的泛濫,使得傳播的主體不再局限于大眾傳播時代的傳媒機構及其把關者,低門檻、自組織、去中心化、無管理主體的技術特性使更多以往邊緣的、沉默的群體成為傳播主體。尤其是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及各類網絡直播技術的平民化、大眾化,使得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制作者、傳播者。有人將傳播主體劃分為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產內容)、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和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職業生產內容)三類,也即傳統媒體、社會化媒體、自媒體、營銷組織、興趣小組、個人等各種主體共同雜糅地參與互聯網的信息傳播活動,共同構成社會傳播主體。[3]傳播主體的多元化構成了傳播格局演變的根本誘因,由此導致了各類傳播形態的博弈與相互融合。在互聯網傳播中,大眾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及人際傳播都被納入其中,這消解了此前大眾傳播“一家獨大”的局面,各類傳播方式此消彼長間也在重構著傳播的格局。例如,傳統媒體在發布新聞報道時更傾向于使用網絡流行熱詞,即大眾傳播與群體傳播在博弈的同時也在合作,以期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各平臺企業當前的直播帶貨事業發展得如火如荼,這是組織傳播在借群體傳播迅速、自發的聚合行為來獲得更高的盈利;謠言傳播的速度極快,公眾輿論往往會迅速發酵等都是人際傳播與其他3種傳播形態相互作用的結果。
技術賦權于民帶來了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并由此導致了4種傳播形態之間的競合,在這一集聚、交融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復雜。傳統的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人際關系逐漸淡化,以趣緣或業緣等為主要紐帶的弱關系、淺關系、隱關系等逐漸增強。這些關系對個體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產生影響,反過來又加速了舊有的傳播格局的消解,促進新格局的形成。
(二)信息系統的進一步融合導致傳播內容的轉變
在一個信息系統中,各類媒介因共同存在于其相互連接的網絡中而形成所謂的媒介矩陣。對外,它們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對內,它們之間高度相關、聯系密切。梅羅維茨在論述場景與行為的關系中認為,電子媒介所營造的開放場景,融合了印刷媒介時期互相隔離的信息系統,由此改變了社會信息獲取的模式,并重塑了社會行為。在智媒時代,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的加入,拓展了這種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加場景化、個性化。如果說電視、收音機、廣播等電子媒介是對印刷媒介時期因物理場景的分隔而導致信息系統分隔的一種跨地域、跨場景融合,那么,物聯網、VR/AR、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營造的則是一種跨思維、跨意識的融合,較之早期的融合更為深入。此外,早期信息系統的融合使場景不再具有決定性作用,而這種去場景化后新的媒介環境則又成為場景本身。因此,場景化和個性化成為人工智能環境的主要特征。
新媒介帶來的信息系統結構變化,不僅直接改變了人們的行為習慣,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為復雜,也對媒介傳播的內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原有各種不同類型內容的同化
將相對類似的材料暴露給所有群體是所有電子媒介的共同傾向,而社交媒體的泛連接性又易于將各種類型的信息在人們中間快速傳遞,這導致了媒介所設置的內容遵從一種既混合又富個性化的結構設置。由于群體間差異越來越小,所以做完全不同的主題節目不再具有意義。與此同時,個體的主體性越來越強,更多的類型群體逐步在這種融合性信息系統的包圍下形成了區別于其他群體的小社群,形成新的區隔,并由此形成了以用戶流量和用戶黏性為主要目標的兩種節目風格,而二者兼顧成為媒介主要的努力方向。
2.新的角色行為被描述為傳播內容
信息系統的融合模糊了場景的前區與后區、公開與私下的界限,迫使角色調整其行為習慣,連接的廣度、傳播速度的即刻性,使得這種變化被呈現出來。例如,公務人員在公共場合的發言、公眾人物在表演時的細節等都成為話題,在人際交互中被傳播、解讀。
3.舊有媒介以智能化媒介作為標準來決定“恰當的”內容
當前,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作為主要趨勢的一個標志是,傳統的大眾化媒介常常與其所提供的信息種類與形式形成競爭關系。傳統的印刷與大眾電子媒介的使用在潮流趨勢中維持或創造“個性”。例如,網絡語言在書面語及視頻化媒介中的應用,體現出舊媒介在描述事件時模擬人們可能在社交媒介等其他智能化媒介中所體驗到的方式。這些媒介訊息的變化共同展現了信息系統結構與其內容之間的一種環形關系,信息系統的變化必定帶來傳播內容的變化。
(三)傳播格局重構倒逼媒介管理者轉變角色,完善傳媒管理體系
任何改革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給人類及其社會帶來新的問題。在新的傳播格局形成的過程中,由于信息系統的深度整合,權威與普通之間的界限不復存在,原有的神秘光環消失,信息發布者成為與民眾一樣的普通人,相應的“信任”問題便隨之而來。此外,泛濫的信息引發了諸如商業平臺的無序競爭、謠言的大范圍傳播、個人隱私被侵犯等媒介亂象,甚至新一輪的民粹主義、群體狂歡、群體孤獨、社會沖突等都導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這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媒介跨越時空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現代性中結構和行動的二元對立,令制度的作用凸顯出來。[4]因此,當公眾因手握技術而接觸到更多以往被隔絕的內容時,也就相應獲得了要求政府對各種事件進行回應和反饋的權利,而相關制度的改進也成為問題破解中最受關注的一環。在公眾訴求的倒逼下,管理者首先需要調整自身角色、轉變個人思想,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在新的傳播環境下,管理者應通過接觸和學習各類新媒介技術,關注普通大眾日常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經常與公眾互動和交流,增加個人親和力,改善自身形象。
轉變個人形象關鍵的一步是根據對當前環境的全方位認知,做出科學決策,以穩定人心。例如,當前人們對智能化技術是否會取代人的主導地位多有困惑和疑慮,相關技術部門應積極開展技術知識普及,祛除強加于技術之上的“魔力”,使之更好地與人類相處。
加強媒介管理法治化體系的建設,針對不同的傳播主體,細化相關的法律法規。例如,在尊重、保護一般自媒體用戶表達自由的同時,規范其言論自由;對以內容提供為主的自媒體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實時監管,并根據其所提供內容的不同形態,出臺更為精準的網絡著作權法,對原創內容及著作權進行保護;使作為內容和服務提供者的自媒體運營商,明確各自的職責和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打擊各商家之間的惡性競爭,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此外,針對當前網絡環境中充斥的負面情緒,建立心理疏導機制,幫助網民進行情緒管理。例如,設立專業化、權威性的心理咨詢機構,正確全面地認識情緒,有效合理地疏導情緒,尊重不同意見,減少社會的負能量,以降低社會風險,減少謠言的產生和傳播,促進理性的回歸。
三、余論與反思
當前,智能化的發展及應用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便捷和益處,其中最為突出的人工智能更是通過對人腦的模擬改變了人類經驗世界的結構。然而,從長遠發展來看,人工智能以及更多的智能化媒介技術還不能算是一項完善的技術,它們仍處于發展階段,因而對其的認識與研究也有諸多局限。但無論如何,“一機一世界,一端一如來”已經構成了當前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并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共同影響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隨著信息系統的進一步整合,從傳播主體到傳播內容,從人際交往到社會關系,傳播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更多的傳播主體從邊緣走向中心、由“沉默的共同體”到“眾聲喧嘩”,人與人的關系隨之也變得更為復雜。傳播模式的轉變也導致了傳播內容的改變與創新,更多適應新信息系統的內容應運而生,并與之共同構建了新的傳播形態。新的傳播格局在形成的過程中也帶來了諸多問題,進而凸顯了管理者及制度的作用,應積極針對不同類型的傳播主體,制定相應的媒介管理政策,完善傳媒管理體系。
一直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對倫理問題的探討,在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在享受其便捷的同時仍需對其進行理性的反思。諸多學者都懷著人文主義式的關懷對此進行過探討,媒介環境學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芒福德在技術的膨脹中看到了人們所受的非理性驅動,他認為由于受到資本和利潤的驅使,技術發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在將人推向異化邊緣的同時也使人性時刻面臨著喪失的危險。芒福德提倡理性地思考,在其呼吁振興有機論的意識形態里,潛藏著這樣一種倫理:生命優先,生命的驅動力優先,也就是生存、繁衍和樂趣的優先。[2]因此,在與技術共生共存的進程中,要正確、辯證地看待技術對人的作用,在享有其成就的同時,也要時刻警惕其對人的控制和奴役。
參考文獻:
[1]? 彭蘭.智媒化:未來媒體浪潮——新媒體發展趨勢報告(2016)[J].國際新聞界,2016,38(11):6-24.
[2]? 林文剛.媒介環境學 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M].何道寬,譯.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3]? 隋巖.群體傳播時代:信息生產方式的變革與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18(11):114-134,204-205.
[4]? 毛湛文.理解媒介融合的元理論:視野與路徑——評延森的《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一書[J].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17(01):2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