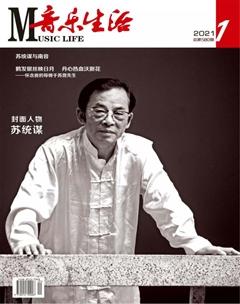論舒伯特藝術歌曲的特色
牛文潔 狄其安
舒伯特,奧地利作曲家,浪漫主義早期重要音樂家之一,德國近代藝術歌曲的創始人,被稱為“藝術歌曲之王”。他改革了藝術歌曲中聲樂獨唱加和弦伴奏的簡單形式,為鋼琴部分賦予了獨奏意義的價值,通過細膩豐富的音樂語匯,將音樂與詩歌結合在一起,使二者相得益彰,具有劃時代的影響力。他的藝術歌曲《冬之旅》是以繆勒的同名詩作為藍本創作的,本文以其中第二首作品《風信旗》為例,從旋律寫作的特色以及鋼琴與聲樂交融這兩個方面分析舒伯特藝術歌曲的特色。
藝術歌曲是一種獨唱形式與鋼琴演奏相結合的音樂體裁。舒伯特逝世于1828年,藝術歌曲《冬之旅》是他在1827年創作的,當時的舒伯特已近人生暮年,整部套曲講述的是一位失戀者在冬日旅行中的故事,充斥著流浪、消亡的色彩。其中第二首《風信旗》以第一人稱的角度,描繪了主人公在旅途中遇到“風信旗”這個信物后,昔日的快樂回憶與如今的苦悶情感同時涌上心頭的場景,歌曲短小精悍,節奏明快流暢。
一、旋律寫作的特色
(一)旋律寫作的線條感
《風信旗》是一首帶有變奏性質的二段式通體歌,節拍穩定,從頭至尾都是6/8拍,旋律寫作多使用音階模進式的進行,時而上行,時而下行,富有線條感。奧地利音樂理論家愛德華·漢斯立克說:“我們見到一些弧形曲線,有時輕悠下降,有時陡然上升,時而遇合,時而分離,這些大大小小的弧線相互呼應,好像不能融合,但又構造均勻,處處遇到相對或相輔的形態,是各種細小的集合,又是一個整體。”[1]漢斯立克在這段文字中所說的“曲線”就是指旋律中音符組成的線條。
譜例1
“譜例1”是《風信旗》的引子,是鋼琴的獨奏,全曲開始處標有“Ziemlich geschwind”記號,要求鋼琴進入時要像一陣疾風一樣迅捷。引子部分的鋼琴在織體上是簡潔的八度音程,這似乎是一段單旋律,但是卻內含了和聲的進行。左右手兩個聲部來回的音階模進式琶音十分流暢,一往無前,仿佛停不下來一般飄忽不定,描繪出了歌詞中“風兒恣意擺弄它的方向”的景象。第3小節旋律下行模進,愈發低沉,第4、5小節的鋼琴顫音密集而綿長,好似一聲聲嘆息,表現出流浪者內心的戰栗與掙扎。
(二)旋律中的調性變化
全曲僅僅51個小節,調性轉換卻十分頻繁,有時一個樂句一次轉調,甚至一個小節一次離調,其中包括了自然大調、和聲大調以及和聲小調,因此在旋律色彩明暗度上的變化明顯,這也體現了舒伯特在調性運用上的大膽與先鋒性。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音樂既不是由個別孤立的音程,也不是由一系列純然抽象的聲音或互不相關的不同的聲音來形成的,而是各種聲音的一種具體的齊鳴,沖突與和解,這些聲音因此就勢必形成一種發展過程和一種互相轉變的過程。”[2]黑格爾在這段文字中所說的“沖突與和解”、“互相轉變”即為調性轉換。
譜例2
“譜例2”是《風信旗》的一個片段,其中第1小節是鋼琴演奏,調性為a和聲小調;第2小節至第3小節調性為C和聲大調;第3小節的第4拍是C和聲大調與e和聲小調的共同和弦,第4小節調性轉到了e和聲小調上。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在短短的五個小節的旋律中舒伯特也使用轉調的手法改變音樂的色彩,盡管轉換的幾個調性為近關系調,但是大調與小調明亮與暗淡的變化是存在的。
二、鋼琴與聲樂交融
(一)鋼琴與聲樂同時創作
“人聲歌唱常常突出人物,描繪詩歌所包含的內容和感情;鋼琴伴奏則起到提示場景,傳達詩歌意境的作用。”[3]與其他歌曲寫作以聲樂為主、鋼琴伴奏為輔的手法不同,在舒伯特的藝術歌曲中,鋼琴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不再只是聲樂的簡單襯托,二者的寫作沒有主次之分,而是同時構思,并駕齊驅,共同闡釋歌曲的內涵,這種獨特的創作思路在《風信旗》中也有所體現。
譜例3(a)
譜例3(b)
“譜例3”有(a)、(b)兩個例子,其中(a)是樂曲的引子,由鋼琴獨奏,(b)則是第二樂段中的一個片段,這里可以說明舒伯特在創作引子時已經考慮到了這個旋律在后面要用,因此并沒有先寫鋼琴或先寫聲樂之分,而是將兩個聲部同時進行創作,體現了鋼琴與聲樂是不能分離的,它們融為一體,具有嚴密的邏輯性。此外,(b)譜例的片段運用了對比復調的寫作手法,運用鋼琴的顫音描繪冬日里的寒風凜冽,以及風信旗來回快速擺動的場景,減七和弦制造了彷徨、壓抑的效果,與聲樂唱詞中“風兒在屋頂恣意擺弄著心”的意境相吻合。
(二)混合音色
如“譜例4”所示,聲樂進入后,鋼琴聲部使用八度襯托,與聲樂完全重合,同音卻不同質感,起到了“混合音色”的效果,二者以不同的音高、不同的音色共同完成音樂所要表現的內容與情感。
譜例4
鋼琴聲部采用這樣的八度進行并不是簡單地伴隨聲樂旋律,而是通過混合的音色在縱向上增加立體感,加強聲樂的顆粒性,使得音響效果更加純粹,放大了旋律本身的優點,將旋律的起伏、張力表達了出來,同時對演唱者也有提示作用,有助于推動旋律的發展。
譜例5
“譜例5”是《風信旗》第二樂段的開始,它和第一樂段聲樂進入的地方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也依舊是鋼琴和聲樂混合音色,但此處與第一樂段不同的是,鋼琴聲部低了八度且力度變弱,之后的四個唱句之間強弱對比明顯,伴隨著大小調的交替,體現的是動蕩不安的、有些失控的情緒。
全曲最后一個唱句在“laut”的基礎上持續做漸強,聲樂唱出“我為什么要痛苦?很快她就是個有錢的新娘”的歌詞,鋼琴在正拍上伴以強有力的柱式和弦,兩個聲部融合一體,交相輝映,將徹底夢碎的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
在這首《風信旗》中,主人公看到了昔日愛人屋頂上被狂風吹動的風信旗,這一物象一方面明指為了金錢而奔向有錢人的負心女人,另一方面又暗指自己隨風飄蕩的流浪宿命。旋律奔流不止,仿佛難以自抑的情緒,調性明暗變化,象征著心態的糾結與轉變。這首作品放在當時的年代,是一種打破古典秩序的、理性的嘗試,是典型的浪漫主義自我中心的宣泄。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說:“浪漫主義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對生活豐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蒼白的,是熱病、是疾病、是墮落、是世紀病、是美麗的無情女子、是死亡之舞,其實就是死亡本身。”[4]
舒伯特的一生是在奧地利反動封建勢力復辟的年代里度過的,因此在他的創作里反映的個人生活和命運問題,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冬之旅》就像是舒伯特的一部自傳,他通過創作來反映當時市民階層的生活,心中對于美好的向往以及希望落空后的悲傷。美妙旋律的背后也蘊含著深切的傷感之意,這種情感與他不幸的人生際遇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為此,他的音樂才會深深觸動我們的內心。
注釋:
[1]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
[2]愛德華·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楊業治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頁。
[3]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上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67頁。
[4]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
參考文獻:
[1]張洪島:《歐洲音樂史》,上海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版。
[2]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16年版。
[37]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4]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
[5]沈旋、谷文嫻、陶辛:《西方音樂史簡編》,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頁。
牛文潔 上海大學音樂學院研究生
狄其安 上海大學音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