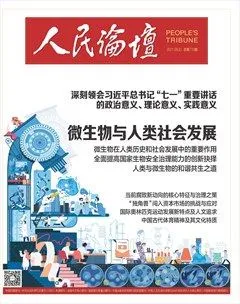當前腐敗新動向的核心特征與治理之策
李輝
【關鍵詞】新型腐敗 權力監督 反腐敗
【中圖分類號】D262.6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1月22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對我國反腐敗面臨的形勢作出重要判斷:“黨的十八大以來,盡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必須清醒看到,腐敗這個黨執政的最大風險仍然存在,存量還未清底,增量仍有發生。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威脅黨和國家政治安全。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交織,貪腐行為更加隱蔽復雜。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交織,‘四風成為腐敗滋長的溫床。”
在三個“交織”中,“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交織”引起了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新型腐敗”,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輸入“新型腐敗”可以得到2570萬個結果,在“知乎”上有專門的帖子討論“哪些行為是新型腐敗?”可以說,這個全新的提法引發了一系列值得追問和探討的問題:到底什么是新型腐敗?新型腐敗的出現和發展對于中國目前的反腐敗斗爭意味著什么?新型腐敗產生的根源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新型腐敗?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首先對新型腐敗的特征和類型做一些粗略的分析和介紹。其次,與許多學者提出的治理新型腐敗要使用新的策略和新的技術手段的觀點①不同,本文強調,新型腐敗是一個動態概念,不同時代有不同表現,今天的新型腐敗從手法和形式上來說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高明”,新型腐敗的發生究其根源依然是權力監督的有效性不足,解決新型腐敗的根本之策還是需要持續不斷地完善黨和國家權力監督體系,提升公權力監督的能級。
隱蔽性與復雜性:新型腐敗的核心特征
要治理“新型腐敗”,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是:什么是“新型腐敗”?我們是否可以給新型腐敗下一個完整準確的定義?是否可以用標準化的指標來區分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筆者認為,這恐怕是不行的。原因有以下三點:首先,新型腐敗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新型”二字,但很顯然新型是一個非常模糊且寬泛的表述,僅憑這兩個字是無法給出確定定義的。其次,在總書記的講話中,新型腐敗是針對傳統腐敗而提出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傳統腐敗呢,目前我們對其也沒有清晰的認識,如果無法確定什么是傳統腐敗,那么確定新型腐敗也無從下手。最后是時間問題,如何對“新—舊”做時間上的切割,今天的傳統腐敗,可能是過去的新型腐敗,今天的新型腐敗,假以時日又會轉化成傳統腐敗。基于以上三點原因,筆者認為尋求對新型腐敗的準確、可操作化的定義并不明智,也不是研究和分析新型腐敗的正確思路。
那么我們應該從何處入手來探討“新型腐敗”呢?筆者認為答案依然在總書記的講話中,也就是這句話的后半句——“貪腐行為更加隱蔽復雜”。這句話其實已經指明了新型腐敗的最核心特點——隱蔽復雜,因此,隱蔽性和復雜性才是新型腐敗的核心屬性。同時,通過對新型腐敗的現實案例分析,我們發現,復雜性從屬于隱蔽性,新型腐敗的發生機制之所以變得更加復雜,是為了讓其變得更加隱蔽,更加難以發現和覺察。
循著這個思路,我們首先可以先澄清一些關于新型腐敗的錯誤認識。比如把新型腐敗看作是一些新領域的腐敗,認為“學術腐敗、教育腐敗、藝術腐敗、公益腐敗”等是新型腐敗,其實這些現象能否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構成腐敗都是存疑的,更不用說構成新型腐敗了。再比如把一些腐敗行為中的新現象當作新型腐敗,包括“信息腐敗”“清水衙門腐敗”和“文雅腐敗”等②。其次,我們可以進一步框定新型腐敗的范疇,即只有那些相較于傳統腐敗更加具有隱蔽性的腐敗行為,才可以被稱為新型腐敗。
從新型賄賂到新型腐敗
實際上,隨著反腐敗的深入,腐敗的形式和手法一直在不斷演變。早在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針對當前中國賄賂案件中出現的十一種新情況進行了解釋和進一步界定。其中九種賄賂的新形式可以被稱為“新型賄賂”,包括:
1.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2.以收受干股的形式收受賄賂;3.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4.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5.以賭博形式收受賄賂;6.以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的方式收受賄賂;7.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 8.收受賄賂物品但并不辦理權屬變更;9.在職為請托人謀利,離職后收受財物。
這九種新形式的賄賂大部分都符合我們前述提出的隱蔽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因此與我們對于新型腐敗的界定相吻合。其中比較典型的形式包括:
以正當市場交易為表現形態的賄賂。比如在一些高價值商品的交易過程中,廠商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給官員,以達到利益交換的目的。這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購買房產,近些年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房價一路突飛猛進,中心城區的房子動輒就要上千萬,開發商只要在市場價的基礎上稍微打一點折扣,就可以輸送幾十萬至上百萬的利益給官員。這樣的例子近些年簡直不勝枚舉,比如北京市委原副書記、組織部原部長呂錫文從扶持企業所開發的高檔小區中以低價購買了共計五套住房,與市場差價達2000余萬元。
以收受股權代替賄金的干股型受賄。在“干股”型的受賄中,官員并不需要實際出資就可以獲得股份,所有的賄金都是以“分紅”的名義輸送的,相對于直接送現金的傳統賄賂,干股型的賄賂看似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與循環經濟處原處長李鐳,號稱從未向企業索賄,堅持拒收企業贈予的現金、購物卡等,但實際上李鐳利用職權幫助某科技公司、某環保公司向深圳市發改委成功申報政府扶持資金和政府投資項目……事后,他從某科技公司以1.5元每股的價格購入50萬股原始股,從某環保公司收受干股50萬股。據核算,李鐳從這兩筆股權交易中獲利高達550萬元。甚至在有的干股受賄案件中,行賄人還幫受賄人代持干股,表面上看起來受賄人根本沒有拿到任何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