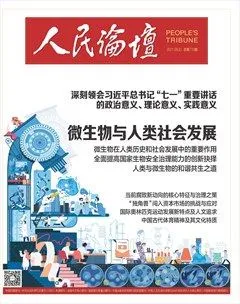法律帝國主義的本質、表現及因應對策
魏磊杰
【關鍵詞】法律帝國主義 霸權 長臂管轄
【中圖分類號】DF11 【文獻標識碼】A
傳統法律帝國主義的表現及其轉型
作為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帝國主義,伴隨冷戰的結束,日漸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特征:其一,早期的帝國主義為確保對其有利的非對稱性交換模式而主要踐行阿銳基意義上的“權力的領土邏輯”,而當下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則更側重“權力的資本邏輯”。為完成重建資本的循環過程,資本主義的運轉必須不斷地溢出原有的市場軌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當有形的領土空間支配無法滿足時,撕裂民族國家的邊界向外伸張的無形的權力支配必將成為應然模式。其二,不同于過去一切帝國那樣建立在金字塔式直接控制基礎之上,美國的霸權是新型的,其全球力量明顯是通過一個由美國設計的,必然反映其國內經驗的全球體系來發揮近乎無所不在的作用。在殖民時代,國際霸權的斗爭主要以公開使用的政治暴力為之,但在經濟帝國主宰的全球化時代,政治暴力卻轉變成了法律暴力:更多地采用法律規則、投資貿易、金融體系、知識產權、人權、法治和文化意識形態滲透等來征服與擴大全球市場。如果說帝國主義本質在于謀求資本的無限擴張,那么法律帝國主義就是將法律作為一種全球治理工具來謀求相同目的的操作形式:在全球治理結構中確立一種服膺于強權者利益的法治模型,造就一種“沒有殖民的殖民形式”,將壓迫性的新殖民主義掠奪行為正當化和合法化。
這一階段的法律帝國主義主要表現為一種無需霸權的法律支配形式,即法律體系在根本上近乎是在無需同意的基礎上施加政治力與經濟力的一種強制性工具。一方面,通過武力進行法律輸出,如美國對其占領下的伊拉克、阿富汗實施法律強加。美國占領伊拉克根本目的在于操控伊拉克的石油。其主要手段是通過巴格達親美傀儡政府強制推行的石油私有化計劃。這主要表現在盟軍臨時主管保羅·布雷默頒布的第39號法令中,該法令允許伊拉克200多家國有企業私有化,允許外資對伊拉克商業100%的持有資格,允許外國公司享受“國民待遇”,允許對所有利潤無限制地免稅匯款,以及允許40年的所有權許可。美國占領軍頒行的這些私有化法令最終導致了當前伊拉克《石油天然氣法》的通過。2007年2月,伊拉克內閣批準了一項石油法草案,將伊拉克石油天然氣管理權力從中央移到地方,這實質上就是對大規模私有化的肯認。在非法占領軍的幫助下,這些法律名正言順地成為將伊拉克石油財富轉移到美國跨國公司手中的有利工具。
另一方面,通過“協商”強制推行法律,如強權國家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南方世界國家施壓。國際信貸,無論是以發展為目的還是以償債為目的,在今天皆伴隨著嚴苛的援助條件。事實上,所謂結構重組方案就是一種協議,它使得受援國以放棄經濟和法律主權為代價獲得融資,而一旦移交此等權力給國際信貸機構,就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必須沿著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路線重新架構。由此,通過結構重組方案,在弱勢國家便順理成章地發展出一套“市場友好型的法律系統”:法律應為市場行為者創造激勵,其正當性必須建立在以確保市場自由吸引外資能力為標準的經濟效益而非社會公平基礎之上。在權力不均衡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就像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一樣,法律本應通過為弱勢主體提供市場管控、提升公共福利等反市場替代方案來維持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平衡,維護社會的公平與穩定。然而,實際上在廣大南方世界國家,法律卻造就了一種截然相反的結果:法律不再被認為是控制和約束市場的工具,相反,市場轉而控制和約束法律。通過這一戰略,國際金融機構在消解受援國經濟與法律主權概念的同時,重新建立了凌駕于地方政治之上服從并服務于新自由主義霸權體系的新的“主權”。
如果說這種形式的法律帝國主義針對的主要對象是深處世界體系外圍和半外圍的民族國家,進入新世紀后,法律帝國主義日趨呈現出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國家將本國法律向世界范圍大幅擴張的態勢,而且針對的對象也從相對弱勢的南方世界國家轉向了被視為潛在競爭對手的大國(尤其是中國)。究其原因,大體有二:其一,2016年以來,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為代表,西方傳統大國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保守主義乃至孤立主義傾向。美國的大量“退群”之舉,實質侵蝕了其原先主要依托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來推行法律帝國主義的現實基礎。同時,中國發起設立的亞投行、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決策及治理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在現有多邊安排下的國際公共產品的短缺,為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選項。
其二,只有在單極世界里,因不存在大國競爭,作為唯一一極的美國可以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從理想主義出發推行對外政策,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中國尋求民族復興的和平崛起之路,在美國看來挑戰了其世界霸主地位,這是其不可接受的。如此一來,美國就主要關心如何遏制中國,防止中國崛起。當今,美國的法律帝國主義明顯是在配合其針對中國展開的遏制戰略而同時進行的法律戰,實質都是將美國國內法和司法權凌駕于國際法與國際社會之上,通過建構全球法律“帝國”秩序來阻遏中國的崛起,維護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全球霸權。
支撐法律帝國主義的基礎性條件
在為皮耶魯齊的《美國陷阱》一書撰寫的書評中,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美國司法部可以調查一起法國公司與印度尼西亞的商業交易?為什么美國法院對美國領土之外的經濟活動擁有司法管轄權?為什么美國可以將自己的國內法凌駕于國際社會之上,從而對其他主權國家或其他國家的公民進行司法調查和司法審判?”顯然,當前法律帝國主義版本的基礎結構直接來自美國,它不僅將美國的實體法標準而且將其程序和法律文化標準強加于人。那么,支撐法律帝國主義的基礎性條件究竟何在?既有的研究更多地將其歸因于美國強悍的軟硬實力上,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本文擬從美國司法體制的內在機理來細化對這一問題的探討。
首先,美國法院將自己認定為全球仲裁者,聲稱自己是國際領域的國內法官,這導源于美國法治及其反應性哲學的全球化。這種反應性哲學又深植于從建國之初便在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中持續存在的賦予美國人民拓展疆域的“昭昭天命”觀以及作為上帝選定之子民引領人類的使命感。在此種動機的驅使下,傳統上,美國法院不愿放棄管轄權并將其假手于外國法院,它們往往篤信:美國法院才是唯一“真正法治”的踐行者,其可以作為政治斗爭和革命實踐的另一替代品,從而建設一個與眾不同的美麗新世界。當然,“長臂管轄”之所以發揮實質效用,是由美國所控制的美元交易、互聯網及其背后強大的經濟實力所支撐的。如今的美國,正是以其對全球經濟體系的掌控為依托,通過一系列法律將“經濟制裁”變成了一種類似于中世紀教皇開除教籍的法律權力。而在一個基督教的世界中,如果被剝奪了基督教的教籍就意味著剝奪了靈魂進入天堂的權利。“長臂管轄”在很大程度上為被告所“自愿”接受,原因即如此(因為許多被告都在美國擁有重要資產);歐盟出臺的“阻斷法令”在現實中難以奏效,原因更是如此。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重啟對伊制裁后,雖然歐盟重啟了“阻斷法令”,但面對美國的脅迫,包括道達爾、雷諾、西門子等百余家歐洲企業最終還是中止了在伊朗的投資和貿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