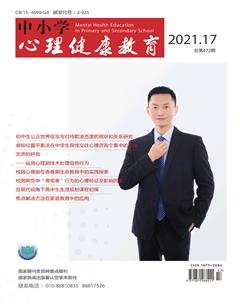班級環境和學習自我效能感對高中生學業情緒的影響
徐先彩


〔摘要〕為探討高中生的班級環境和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業情緒的影響,采用學業情緒量表、班級環境問卷和學習自我效能感問卷,對江西省鷹潭市第一中學的492名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高中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班級環境與學業情緒均存在顯著的相關,學習自我效能感能正向預測積極學業情緒,負向預測消極學業情緒;班級環境中的師生關系對高興、平靜、厭倦、無助等學業情緒維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學習負擔能正向預測厭倦和無助這兩種學業情緒維度,同學關系是學業情緒中放松這一維度的重要預測變量,競爭是自豪、焦慮兩個維度的重要預測變量。
〔關鍵詞〕班級環境;學習自我效能感;學業情緒;高中生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21)17-0009-05
一、問題提出
學業情緒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體驗到的與學業相關的各種情緒[1]。它不僅可以影響和調節學生的認知加工過程,還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以及學習策略的使用[2]。
學業情緒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佩克倫(Pekrun)[3]提出控制—價值評估模型來探索學生學業情緒的影響因素。該理論指出,一方面,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控制和價值的評估對學業情緒有直接影響,控制評估是學生對自己能否完成學習任務、掌握學習材料的評估,其相關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歸因方式、成就預期等。其中,自我效能感對學業情緒的預測作用最強,有學者指出,它可以影響個體對任務難度的選擇、遇到困難時的堅持性和信息加工的策略等[4]。價值評估則是學生對學習任務重要性和有用性的評估,學生只有對學習任務感興趣并且認為所學的東西是很有價值時,才會產生積極的情緒。另一方面,外界環境因素如教師的反饋、班級競爭與合作氣氛、同伴的支持以及互動,也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情緒。有研究發現,隨著班級社會心理環境變差,學生的積極學業情緒會逐漸減少,消極情緒逐漸增加[5]。
這些研究表明,學業情緒是個體內在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班級社會心理環境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影響因素,學習自我效能感則作為內部認知因素對學業情緒起到重要作用。高中階段學業壓力巨大,很多學校的學生平均每天在班級里學習生活的時間會超過十小時,學生知覺到的班級環境的不同維度,如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秩序紀律、競爭和學習負擔對其學業情緒會產生哪些影響?學生在不同時期(如高一剛入學、高二文理分科后、高三高考前)對班級環境的知覺有什么差異?高中生正處于自我意識快速發展的階段,其學習自我效能感會怎樣發展?班級環境和學習自我效能感是怎樣共同作用于高中生的學業情緒的?本研究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究。
二、對象與方法
(一)被試
本研究采取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江西省鷹潭市第一中學高一至高三的學生為被試,共發放問卷550份,回收有效問卷492份。其中,高一男生97人,高一女生96人;高二男生82人,高二女生87人;高三男生61人,高三女生69人。
(二)研究工具
1.學業情緒量表
采用高中生學業情緒量表,此量表根據董妍、俞國良[6]編制的青少年學業情緒問卷修訂而成,包括積極高喚醒學業情緒、積極低喚醒學業情緒、消極高喚醒學業情緒、消極低喚醒學業情緒四個分問卷。各分問卷的Cronbach'α系數分別為0.82、0.85、0.83、0.84,分半信度分別為0.81、0.80、0.83、0.82。
2.班級環境的測量
采用江光榮[7]編制的“我的班級”問卷進行班級環境的測量。問卷包含五個維度,即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秩序和紀律、競爭與學習負擔,共38個項目。量表各維度的Cronbach'α系數在 0.60~0.87之間。
3.學習自我效能感問卷
采用曾興華[8]編制的高中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問卷。此問卷由華中師范大學梁宇頌編制的大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問卷修訂而成。問卷有學習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學習行為自我效能感兩個維度,能解釋項目總體變異的46.484%,兩個維度的Cronbach'α系數分別為 0.825 和 0.858,總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891。
(三)施測過程與數據處理
采用集體施測方式,以紙筆方式進行,時間為20分鐘。問卷收回后,用SPSS 17.0錄入與分析數據。
三、研究結果
(一)高中生學業情緒、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班級環境的特點
以班級環境的五個分量表、學習自我效能感、學業情緒各維度為因變量,以性別為自變量,做獨立樣本t檢驗,以比較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這些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在高興、放松、焦慮和無助這些情緒體驗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生的高興、焦慮和無助得分顯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則體驗到更多的放松情緒。在自豪、放松和厭倦這些情緒體驗上,男女生之間差異不顯著。男女生在師生關系和同學關系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女生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在秩序和紀律、競爭、學習負擔及學習自我效能感上差異不顯著。
以年級為自變量,以班級環境的五個分量表、學習自我效能感、學業情緒各維度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研究結果發現,三個年級學生在自豪、平靜、放松和無助上得分差異不顯著,高三年級學生的高興、焦慮體驗顯著高于高二年級,高二年級的厭倦體驗顯著高于高一年級。不同年級在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秩序與紀律、競爭、學習負擔上差異顯著。高三年級學生在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秩序和紀律、競爭上的得分都顯著高于高一和高二年級學生,高一高二兩個年級之間差異不顯著。在學習負擔這一維度,高一年級顯著高于高二年級,高三年級顯著高于高二年級,高一年級與高三年級之間差異不顯著。三個年級學生的學習能力效能和學習行為效能差異均不顯著。
(二)高中生班級環境、學習自我效能感與學業情緒相關分析
高中生的學業情緒各因子與班級環境各維度及學習效能感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3。從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師生關系與高興、平靜呈顯著正相關,與厭倦和無助呈顯著負相關,與自豪、放松和焦慮相關不顯著;同學關系與平靜和放松呈顯著正相關,與厭倦和無助呈顯著負相關,與高興、自豪和焦慮相關不顯著;秩序和紀律與平靜呈顯著正相關,與厭倦和無助呈顯著負相關,與高興、自豪、放松和焦慮相關不顯著;競爭與高興、自豪、焦慮呈顯著正相關,與平靜、放松、厭倦和無助相關不顯著;學習負擔與高興、焦慮和無助呈顯著正相關,與自豪、平靜、放松和厭倦相關不顯著。學習能力效能與高興、自豪、平靜、放松呈顯著正相關,與焦慮、厭倦、無助呈顯著負相關;學習行為效能與高興、自豪、平靜、放松呈顯著正相關,與厭倦、無助呈顯著負相關,與焦慮相關不顯著。
(三)班級環境、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習情緒的回歸分析
以學習情緒各因子為因變量,以班級環境中和學習自我效能感上與學業情緒各因子相關顯著的具體維度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更深入了解高中生知覺的班級環境及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業情緒的具體影響。結果發現,進入高興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7.1%)、師生關系(預測率為3.9%)和學習負擔(預測率為1.2%);進入自豪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5.6%)和競爭(預測率為2.1%);進入平靜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15.8%)、學習行為效能(預測率是2.8%)和師生關系(預測率為1.2%);進入放松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26.6%)和同學關系(預測率為1.3%);進入焦慮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5.5%)、競爭(預測率為4.1%)和學習負擔(預測率為1.1%);進入厭倦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11.8%)、師生關系(預測率為3.8%)和學習行為效能(預測率是0.9%);進入無助回歸模型的是學習能力效能(預測率是30.7%)、師生關系(預測率為0.7%)和學習負擔(預測率為0.6%)。
四、討論
(一)高中生學業情緒、班級環境和學習自我效能感的發展特點
本研究發現,女生更多地體驗到高興情緒,這可能與他們采用的情緒表達方式有關。隨著性別角色社會化的發展,高中男生越來越認同“男兒有淚不輕彈”,認為男生要強大而克制,女生則可以不需隱忍地表達開心或悲傷[9]。有研究也發現,男性會更多地使用表達抑制,而女生則會有更多的積極情緒表達[10]。女生的焦慮和無助要明顯高于男生,這可能與女生情緒情感豐富而細膩、情緒體驗深刻有關。初中升入高中后,學習難度增大,尤其是在數理化等學科上,女生的學習成績優勢逐漸消失,在學習中投入很高但成績進步不明顯,往往會讓她們更加焦慮和無助。男生的放松顯著高于女生,這可能與思維發展特點與情緒調節方式有關,高中階段男生邏輯思維發展更快,學習相對輕松,同時,男生參加課余活動如社團、打球等的比率明顯高于女生。因此遇到消極情緒后,男生有更多的放松途徑。
高三年級學生的焦慮體驗顯著高于高二年級。高三是整個高中學習生涯中強度最高、學習壓力最大的時期,學生、家長、教師對學業成績也最為重視。隨著高考的臨近,學習會變得更緊張,學習壓力也更大,學生的焦慮水平也更高。高一年級學生剛入學,剛開始一段全新的學習歷程,所接觸的學習環境和教學資源都是新鮮的,他們會產生新鮮和好奇感。到了高二,隨著學習瓶頸期的到來,學生的厭倦情緒會增多。由于高考是對學生非常重要的考試,到了高三,學生的學習動力較之前有顯著的增加,所以學生此時的厭倦會有一定程度的減弱,這可能是高二年級的厭倦顯著高于高一年級、高三年級學生的高興情緒體驗顯著高于高二年級學生的原因。這也提示我們,應該看到對學習的不滿足和適當的焦慮水平對學生學業發展的積極意義。
班級環境方面,性別在師生關系和同學關系這兩個維度上有顯著差異,男生得分顯著低于女生,這可能是因為在青春期后,男女生在人際互動中存在較大差異。已有研究表明,男生在青春期人際互動中,信任與支持、陪伴與娛樂、肯定價值、親密袒露與交流均顯著低于女生[11]。一般來說, 女生更喜歡親密袒露與交流,更愿意跟老師溝通和交流,所以師生關系更好,同伴關系更親密。
年級在班級環境的五個維度上都差異顯著,高一年級和高三年級學生感知的學習負擔都顯著高于高二年級,高三年級學生在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秩序和紀律、競爭上的得分都顯著高于高一和高二年級學生。該結果的出現,可能與學生的認知發展和客觀要求有關。隨著認知逐漸成熟,同學之間能夠相互體諒、包容,再加上長時間的相處,師生之間、同學之間更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人際互動逐漸變得融洽。在高三階段,學生面臨高考的壓力,會更加遵守秩序和紀律,加倍努力學習。很多學生為了取得好成績,增加做題量,學校的考試次數也會增多,所以該階段學生感知到課業負擔更重,競爭也更激烈。與初中階段的學習相比,高中學習科目更多、難度更大,所以高一學生會感知到很重的學習負擔,而高二學生度過了高一的適應期,尚無高考的壓力,課業負擔感知最輕。
在學習自我效能感方面,性別和年級在自我效能感上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可能隨著自我意識的不斷發展,高中生對自我的認識趨向成熟穩定,不會像初中生波動那么大,由此他們在學習自我效能感上沒有顯著差異。
(二)班級環境、學業自我效能感對高中生學業情緒的影響
從班級環境與學業情緒、學習自我效能感的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來看,班級環境中的師生關系與高興、平靜、厭倦、無助都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并對高興、平靜、厭倦、無助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意味著學生和教師之間交流順暢,彼此之間保持著良性互動關系。高中階段,學生依然非常在意教師對自己的評價,當學生能感受到來自教師的關心和支持時,學生就能獲得更多愉快的學習經歷和心理滿足感;反之,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沖突性事件則會增加學生的消極體驗[12]。已有研究也發現,高中學生的師生關系是預測他們學習投入程度的重要變量,師生關系越好,學生的學習投入程度越高,積極的學業情緒體驗也越多[13]。另外,教師作為學校及班級環境中影響學生成長的“重要他人”,其領導風格也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教師通過對學生的目標激勵、個性化關懷,給予學生充分的信任與期望等,影響學生的自我認知和評價,從而改善學生的學習及行為表現[14]。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要積極支持和信任每一位學生,并在生活上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提高學生的歸屬感、安全感和效能感。
同時,同學關系是學業情緒中放松這一因子的重要預測變量。高質量的友誼能讓學生從同學處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幫助,親密的朋友關系也能夠給予個人歸屬感和安全感,朋友的傾聽和陪伴能夠緩沖他們的心理壓力[15]。這充分說明,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學生積極學業情緒體驗的必要條件。競爭是自豪、焦慮的重要預測變量,班級競爭氣氛越濃,學生感受到的學業壓力就會越大,會越焦慮,與此同時,學業成就帶來的自豪感和學習效能感也會越強。也就是說,競爭是把“雙刃劍”,良性競爭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使其提高學習效能,而惡性競爭則會增加學生的壓力,破壞同伴友誼。所以教育工作者要引導學生在班級里形成良好的競爭氛圍。
學習負擔能正向預測厭倦和無助這兩種情緒,學習負擔越重,越容易引發學生的倦怠感和無助感。如果學習負擔過重,學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是總是完成不了學習任務,容易引發學生的習得性無助感,導致他們失去學習興趣。由此可見,“減負”確實是非常必要的。
同時我們也發現,學習自我效能感(尤其是學習能力效能)能正向預測積極學業情緒,負向預測消極學業情緒,這說明學習自我效能感是學業情緒的重要影響因素。許多研究者一致認為,直接的成功經驗和積極的鼓勵評價對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作用是最大的[16]。因此教師要根據學生能力水平設置學習目標和任務難度,以提高他們的成功體驗,并給予他們更多的鼓勵和正向評價,提高他們的學習能力效能感。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20年度普通類重點課題“高中生學業情緒的影響因素及干預研究——基于控制—價值理論”(編號:20PTZD026)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Pekrun R,Gortz T,Titz W,et al.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2002,37(2):91-105.
[2]Efklides A,Petkaki C. Effects of mood on students'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05(15):415-431.
[3]Pekrun R.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assumptions,corollaries,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06(18):315-341.
[4]趙淑媛.基于控制—價值理論的大學生學業情緒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3.
[5]李丁丁.初中生學業情緒、班級社會心理環境與學業求助行為的影響[D]. 沈陽:沈陽師范大學,2012.
[6]董妍,俞國良.青少年學業情緒問卷的編制及應用[J].心理學報,2007(5):852-860.
[7]江光榮.中小學班級環境:結構與測量[J].心理科學,2004,27(4):839-843.
[8]曾興華.高中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及其與應對方式、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08.
[9]Chaplin T M,Aldao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expression in children:A meta-analytic review[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3,139(4):735-765.
[10]姜媛,白學軍,沈德立.中小學生情緒調節策略的發展特點[J]. 心理科學,2008,31(6):1308-1312.
[11]金燦燦,鄒泓.中學生班級環境、友誼質量對社會適應影響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J]. 中國特殊教育,2012(8):60-65.
[12]王靜.中學生師生關系、學業情緒與學業成績的關系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6.
[13]范金剛.高中生的學習投入與班級心理氣氛的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0,18(9):1115-1117.
[14]袁平平.高中生成就動機與學習投入的關系:教師變革型領導、樂觀的作用[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20.
[15]金燦燦,鄒泓,李曉巍.青少年的社會適應:保護性和危險性因素及其累積效應[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1) :12- 20.
[16]謝思敏.高中生班級環境、社會比較與學業自我效能感的關系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20.
(作者單位:江西省鷹潭市第一中學,鷹潭,335000)
編輯/張國憲 終校/劉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