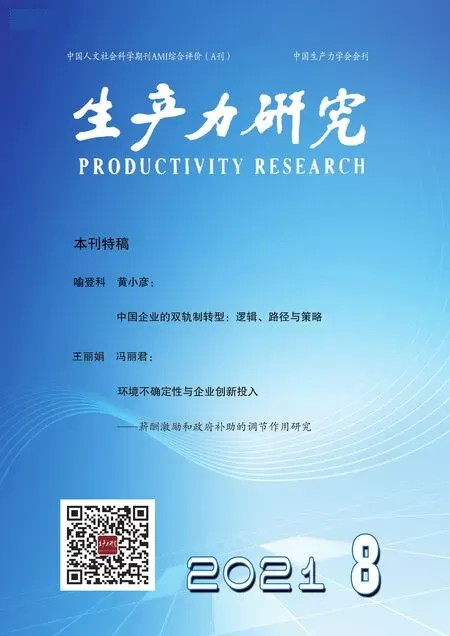浙江省產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生態足跡的影響研究
鄭瑤琪
(寧波大學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一、引言
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稀缺品”一旦被過度開發乃至枯竭將會對人類社會產生毀滅性的影響已成為全球共識。從可持續發展角度而言,人類社會為發展經濟而從生態環境中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速度不能超過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為保障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方式應轉變為高效集約型。而如何量化人類經濟活動和自然資源之間的復雜關系,判斷其是否沿著可持續方向發展成為優化經濟發展路徑的基礎性工作。1992 年,生態經濟學家William Rees 基于人類的一切活動和消費均可換算為土地面積占用和人類活動一旦超過土地總面積將損害生態質量,提出生態足跡概念,Wackernagel 則進一步將其完善成為測量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法。生態足跡模型被國內外學者在多領域廣泛運用,并在該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
浙江省作為國內經濟發展程度差異最小的省份,經濟社會發展迅速,但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能源枯竭等問題也不容忽視。在此背景下,走經濟生態化和生態經濟化道路是浙江省協調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均衡可持續的重要發展戰略。產業結構是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表現形式,優化產業結構是轉變不文明不生態的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發展綠色可持續的必然途徑。本文將對浙江省2006—2017年的生態足跡進行測量,并進一步將總生態足跡細分為三次產業分別占用的生態足跡,測算三次產業各自的生態足跡動態變化,并以此分析浙江省產業結構變動對三次產業生態足跡產生的不同影響,在判斷其經濟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提出優化產業結構的可行性建議。
二、文獻回顧
圍繞本文的研究目標,這一部分將從生態足跡的研究尺度、研究方法、研究領域以及生態足跡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相關研究三個方面對過往文獻進行回顧評述:
(一)研究尺度
全球尺度:Wackernagel 等(1997)[1]首先以世界52 個國家和地區為研究對象,建立生態足跡模型對1997 年的生態足跡占用進行測算。WWF 自1998 年開始在《地球生命力報告》中發布全球生態足跡狀況。國家和區域尺度:Lenzen 和Murray(2001)[2]利用澳大利亞土地的使用面積以及排放物測算其生態足跡為13.6ha/cap;徐中民等(2003)[3]指出中國1999年人均生態足跡為1.326hm2,遠超生態承載力;李金平和王志石(2003)[4]指出2001 年澳門生態足跡是其生態承載力的272 倍,生態系統倍受高壓挑戰。國內關于國家和區域尺度上的生態足跡測算已經從單一年份發展為對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研究的區域既涵蓋發達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也涉及欠發達地區,如甘肅、新疆等地。
(二)研究方法
顧曉薇等(2005)[5]指出傳統“全球公頃”測算方式的不足,并提出以“國家公頃”作為計量單位,測算沈陽的生態足跡;張恒義等(2009)[6]又在“全球公頃”和“國家公頃”的測算基礎上,提出以“省公頃”作為計量單位;熊德國等(2003)[7]則提出將生態足跡區分為消費性和生產性兩類,并據此建立更真實衡量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從創新概念、改進生態足跡賬戶和改進測算方法等角度對生態足跡研究方法的改進較多。
(三)研究領域
生態足跡被廣泛運用在經濟社會的多領域中,Colin Hunter 等率先提出的“旅游生態足跡”更是被應用于世界各地的旅游生態足跡測算,Gossling 等(2002)[8]為塞舌爾為例,構建和完善對旅游地生態足跡的計算模式。國內學者也逐漸將生態足跡模型運用到多個領域,如章錦河等(2005)[9]對中國部分旅游勝地九寨溝的旅游生態足跡進行測算和分析;亦有針對水生態足跡的測算和分析,如黃林楠等(2008)、馬晶等(2013);與此同時,各行業和多領域都逐漸開始運用生態足跡模型進行相關分析。
(四)生態足跡和產業結構關系研究
傅春等(2011)[10]利用生態足跡模型計算1989—2008 年間環鄱陽湖區的生態足跡及承載狀況,結果證實三次產業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均為正相關,而第一產業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力度最大;許晴(2013)[11]以吉林省為例,證實產業結構的經濟效益增長會導致生態足跡的增加,且對生態足跡的影響程度以此為二、三、一產業;樊高源等(2015)[12]利用生態足跡和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產業結構對生態足跡的影響,證實烏魯木齊生態赤字現象非常嚴重,其對生態足跡的影響程度依次為三、一、二。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生態足跡模型的研究較為豐富,主要集中于利用傳統生態足跡模型或改進方法的生態足跡模型對不同尺度、不同領域進行測算,而與產業相關的生態足跡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產業,如旅游業、交通運輸業等,卻極少有針對產業整體的生態足跡的測算,也尚未建立一套專門基于產業部門對生態足跡進行劃分和測算的標準。此外,對生態足跡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也相對較少,在生態足跡指標確定中,大多數研究采用與國際生態足跡研究結果具有較強可比性的傳統生態足跡模型;在衡量產業結構變動的指標中,大多數研究采用產業產值占GDP 的比重。基于此,本文將對生態足跡和產業結構的測算作出調整,使結果更為準確地反映產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生態足跡的影響,并由此提出產業結構改善的可行性建議。
三、產業生態足跡測算
(一)生態足跡模型
傳統生態足跡(EF)計算模型:

其中,ef為人均生態足跡;N 為人口數;i為6 類生產性土地面積,即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地、建筑地;ri為調整6 類生產性土地同等生產力的均衡因子;cj為j種生物資源、化石能源的人均消費量;pj為j種生物資源、化石能源的全球生產力水平。
針對本文的研究目的,基于傳統生態足跡模型中的不足,現作出以下改進:
1.采用生物資源的人均產量代替人均消費量。
傳統生態足跡模型采用某地生物資源消費量進行測算,或利用貿易往來對某地生物資源產量進行調整。但生物資源不同于只有在消費時才占用生態足跡的化石能源,其在生產時已然占用了某地的生產性土地,并產生生態足跡。若利用消費量或區間貿易進行調整,則會導致本地區生態足跡隨著貿易轉移入其他地區,從而使得本地區的實際生態足跡存在偏差。因此采用生物資源的人均產量能夠更為準確的測算本地區真正產生的生態足跡。
2.采用“國家公頃”代替“全球公頃”作為計量單位。大多數研究為保證生態足跡測算結果的可比性,則借鑒Wackernagel 等(1997)采用的聯合國糧農組織1993 年有關生物資料的世界平均產量數據。但各國生物資源的平均產量存在較大差異,使用“全球公頃”難以準確反映一國內各省市實際產生的生態足跡,而1993 年距今較遠,其數據已不具有代表性,因此計量單位的調整將采用“國家公頃”[5]。此外,本文的研究重點在于觀察2006—2017 年間浙江省產業結構變動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因此將以2006 年為基年計算各類生物資源的國家平均生產力,能更準確反映浙江省生態足跡在時間序列上的動態變化趨勢及其變化程度。
3.采用“凈生態系統生產量”代替“全球平均能源足跡”。在Wackernagel 的假設中,化石能源燃燒的溫室氣體將由林地吸收。而根據謝鴻宇等(2008)[13]對碳循環的分析,化石能源燃燒的溫室氣體是由林地和草地共同吸收。因此本文將借鑒該研究結論,測算更為準確的基于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化石能源生態足跡,即:某地化石能源生態足跡=某種化石能源消費量×(1 噸溫室氣體排放的林地吸收量+1 噸溫室氣體排放的草地吸收量)。
4.采用水力發電量代替電力消費量。在電力核算上,大多數文獻直接利用某一地區的電力消費計算建筑地的生態足跡,與生物資源消費量核算相同,電力消費量也無法準確地衡量某地實際占用的建筑地生態足跡。此外,根據發電的方式不同,生態足跡的核算也應有所區別,浙江省的發電方式包括火電、水電和核電,考慮到核電量較少,因此主要區分火電和水電的不同測算方式。火電主要是利用可燃物燃燒時的熱能進行發電,其中可燃物主要是煤炭,而在化石能源的生態足跡測算中已然將煤炭消費量納入,為避免部分煤炭消費的重復計算,在建筑地生態足跡核算時不應將火電納入。而水電所占用的生態足跡主要來自于建立水電站蓄水淹沒的耕地,因此水電生態足跡也借鑒謝鴻宇等(2008)[13]的研究,即某地水電占用的生態足跡=水力發電量×1k Wh 水電淹沒的耕地面積。
綜上所述,調整后的生態足跡模型可分為生物資源和化石能源兩類生態足跡賬戶進行核算,具體模型如下:


式(1)為生物資源生產所占用的生態足跡(hm2)。其中ri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4 類生產性土地的均衡因子;Lj為某地j種生物資源的人均產量(kg/人);Kj為j種生物資源國家平均生產能力(kg/hm2);式(2)為化石能源消耗所占用的生態足跡(hm2)。其中r5和r6為化石地和建筑地的均衡因子;Lt為某地t種化石能源的人均消費量(t);Ht為t種化石能源燃燒的熱量(TJ/103t);Qt為t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數(tC/TJ);Perf和Perg為林地和草地吸收碳的份額,分別為82.72%和17.28%;Sf和Sg分別為全球林地和草地平均碳吸收能力(t/hm2);Lw為某地人均水力發電量(KWh/人,1J=2.778×10-7KWh);Aw為全國水電站淹沒的耕地面積(hm2);Kw為全國平均水力發電量(KWh/hm2);式(3)為總生態足跡。
(二)生態足跡測算
數據來源及使用說明。浙江省各類生物資源的人均產量、人口總數來自浙江統計局,其中木材和竹材產量來自《2007—2018 中國林業統計年鑒》;化石能源消費量來自《2007—2018 浙江省統計年鑒》;水力發電量來自《2007—2018 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國家公頃”計算中所需的各類土地面積和生物資源產量均來自《2017 中國統計年鑒》,部分農產品和林產品全國生產力數據缺失,采用同年FAO 數據庫的數據進行填充。
1.生物資源賬戶。根據農產品、動物產品、林產品的生產屬性,對其所占用的生產性土地進行劃分。動物產品占用的生產性土地借鑒謝鴻宇等(2008)[14]劃分方法,除水產品以外的動物產品可基于生產方式的不同分為飼養和放牧兩類,飼養型動物產品占用耕地,放牧型動物產品占用草地。浙江省生物資源賬戶如表1 所示。

表1 浙江省生物資源賬戶
2.化石能源賬戶。浙江省化石能源賬戶如表2所示。

表2 浙江省化石能源賬戶
3.均衡因子。均衡因子作為調整6 類生產性土地同等生產力的參數值,應與“國家公頃”為計量單位的平均生產力水平相一致,此處均衡因子借鑒劉某承和李文華(2009)[15]基于凈初級生產力所得的結果,再次考慮到化石能源燃燒后的溫室氣體將會被林地和草地共同吸收,因此化石地的均衡因子有兩類,分別采用林地和草地的均衡因子,如表3 所示。

表3 基于“國家公頃”的均衡因子
4.生態足跡。經過上述模型和數據的測算,浙江省經均衡因子調整后的人均生態足跡如表4 所示。

表4 2006—2017 年浙江省均衡人均生態足跡
(三)產業生態足跡測算及分析
人類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生物資源和化石能源,進而產生生態足跡。三次產業作為國民經濟部門結構的表現形式,每一產業都會由其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而產生相應的生態足跡,即為產業生態足跡。因此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量可作為三次產業生態足跡的劃分標準。
第一產業生態足跡。一產主要為農林牧漁業及基礎水利業。農林牧漁業在生產過程中表現為對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化石地4 類土地的占用,其中對化石地的占用可根據農其能源消費量占總消費量的比重進行分配;基礎水利業在生產過程中表現為對建筑用地的占用,因此可根據水利設施用地占總建筑用地的比重進行測速啊。
第二產業生態足跡。二產以工業和建筑業為主。工業生產主要是對化石地的占用,因此可根據工業的能源消費量占總消費量的比重進行測算;建筑業則表現為對化石地和建筑地2 類生產性土地的占用,因此可根據其能源消費量占比和建筑用地占比進行測算。
第三產業生態足跡。三產包含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等。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可表現為對化石地和建筑地的占用,因此可根據其能源消費量的占比以及交通運輸用的占比進行測算;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及其他第三產業均可根據其能源消費量的占比進行測算。
此外,由于浙江省土地利用類型變更較少,對總建筑用地的占用比例根據2016 年浙江國土資源公報中的土地占用面積進行計算,分別為:10.6%、78%、11.4%。具體測算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2006—2017 年浙江省人均產業生態足跡
從總量來看,2006—2017 年浙江省人均產業生態足跡大小依次為一、二、三產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仍然是占用浙江省生產性土地最多的產業,需要消耗巨大的生物資源和化石能源維持人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求。此外第二產業人均生態足跡略低于第一產業,表明浙江省正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而第三產業的人均生態足跡遠小于第一、二產業,可見第三產業相較于其他兩個產業對生物資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耗極少;從年增長率來看,2006—2017 年間浙江省人均產業生態足跡年增長率速度依次為三、二、一產業,與產業生態足跡總量正相反。其中第一產業生態足跡已經呈現負增長,為-0.31%;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則為緩慢的正增長態勢,為1.13%;而第三產業生態足跡增長速度遠超第二產業,為4.98%。可知,浙江省產業結構正處于向合理化和高級化轉型的快速發展階段。
四、產業結構度量
從動態演進的角度來看,產業結構變動表現為雙重維度的優化,即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產業間協調發展和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程度;產業結構高級化則是隨著經濟增長,產業結果依次以第一、二、三產為主導產業。本文將分別從這兩個維度對浙江省產業結構變動進行度量。
(一)浙江省產業結構合理化度量
產業結構合理化可看作是對生產要素在產業間投入產出效率水平的衡量。目前多數研究采用結構偏離度對其量化,產業結構的合理程度與偏離程度負相關。但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產業對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為修正這一誤差,本文借鑒干春暉等(2011)[16]修正的泰爾指數,即:

(4)式中,R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泰爾指數;Yi為第i產業的生產總值;Y為三次產業的生產總值;Li為第i產業的就業人數,L為三次產業的總就業人數。若TL=0,則該時期產業結構處于合理的均衡狀態;若TL≠0,則該時期的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狀態。泰爾指數與產業結構偏離均衡的程度為正相關。具體度量結果如表6 所示。
由表6 可知:(1)2002—2017 年浙江省的泰爾指數均不為0,可見浙江省產業結構一直處于偏離均衡的狀態,即產業結構仍未達到合理狀態;(2)從2002—2017 年泰爾指數大小的變化趨勢來看,浙江省產業結構偏離均衡的程度總體下降,可見浙江省產業結構逐漸趨于合理化發展;(3)自2011 年起,泰爾指數總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且下降速度減緩,這是由于處于經濟優化升級階段的浙江省更加注重產業發展的質量。

表6 浙江省產業結構泰爾指數
(二)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度量
產業結構高級化可表現為產業結構中主導產業的變遷。本文借鑒付凌暉(2010)[17]基于Moore 系數法構建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度量指標,具體計算如下:首先,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量化值定義為H,并根據三產產值占GDP 的比重構建三維向量,即X0=(x1,0,x2,0,x3,0)。
其次,分別計算X0與產業結構由低向高升級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夾角θ1,θ2,θ3,即:

最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量化值計算公式為:

H值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正相關。具體度量結果如表7 所示。
由表7 可知2002—2017 年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基本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可見浙江省的三次產業逐漸向高端生產制造方向調整。

表7 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量化值
五、浙江省產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生態足跡的影響分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利用2006—2017 年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H)、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R)分別檢驗其對浙江省第一產業(F)、第二產業(S)、第三產業(T)生態足跡的影響。
(一)單位根檢驗及最優滯后階數確定
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的檢驗結果的準確性要求誤差向量需滿足白噪聲序列向量,因此本文使用Stata 15.0 軟件對浙江省產業結構指數和三產生態足跡進行單位根檢驗。經檢驗,H、R 及其一階差分均不平穩,其二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F 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S 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T 的一階差分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因此,采用序列△2H、△2R、F、S、△T 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
最優滯后階數。最優滯后階數的選取原則上應同時考慮FPE、AIC、HQIC、SBIC 準則所給定的滯后階數,選取一致性較大的階數,但由于本文所設計的數據較為龐雜,較早年份的原始數據缺失,變量的時間序列較短,因此在選擇中還需避免損失過多自由度。經檢驗,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分別對三次產業的最優滯后階數選擇為:H-F 為1 階、H-S為3 階、H-T 為3 階、R-F 為3 階、R-S 為3 階、R-T為3 階。
(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主要用于分析向量自回歸模型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對其他變量的影響,即模型對自身某一變量擾動的一個沖擊所作出的動態反映。圖1、圖2、圖3 中從左往右依次為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對三次產業生態足跡的影響。

圖1 第一產業生態足跡對產業結構變動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

圖2 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對產業結構變動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

圖3 第三產業生態足跡對產業結構變動新息沖擊的脈沖響應
圖1 中,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使得第一產業生態足跡在初期為正向響應的最高值,隨后逐漸變為負向響應,但趨于穩定且收斂到零。可見產業結構高級化可以在短期減少第一產業生態足跡,但影響效果較弱;來自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使得第一產業在生態足跡在初期為正向響應的最高值,隨后響應在第1 期迅速減弱至零,在第3 期時達到負向響應的最高值,隨后響應在第4 期快速上升為零,又在第6 期快速達到正向響應的一個小高峰,在第7 期又收斂為零。由此可見,第一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合理化沖擊的響應呈現周期性變化的特點,具有密切的聯系。短期內產業結構合理化會促使第一產業生態足跡的明顯減少,但長期會呈現周期性變化的特點。
由此可見,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能減少第一產業對生產性土地的占用,符合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內涵,但隨著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所能減少的額度逐漸下降,因此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第一產業生態足跡的減少程度也逐漸減弱;此外,浙江省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為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的衡量指標,常常受限與于技術水平的進步。產業投入產出效率提高在短期能減少第一產業的生態足跡,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其生態足跡又會增加,但增加幅度小于初期,因此就整體而言,產業結構合理化能夠減少第一產業生態足跡。
圖2 中,一方面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分別承受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趨勢較為相似,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在初期為正向響應的最高值,隨后響應在第1 期迅速減弱至零,在第3 期時達到負向響應的最高值,隨后響應在第4 期快速上升為零,又在第6 期快速達到正向響應的一次小高峰,在第7 期又收斂為零。另一方面二者又存在不同,即第二產業生態足跡承受產業結構高級化沖擊的響應程度要強于承受產業結構合理化沖擊。
由此可知,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變動趨勢呈現周期性減少的特點,其周期性減少的特點主要是產業結構的優化所減少的生態足跡受經濟增長、產業規模擴張、人口增加、需求上升等因素再次上升所導致的。與已經發展成熟逐漸比重降低的第一產業不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貢獻比重極為相近,可見浙江省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動的轉折時期,整個產業經濟體的結構變動仍然不穩定,因此周期變動中也存在調整平臺期。此外,雖然技術進步、清潔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已經逐步投入市場并開始應用,但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耗為主的工業仍然浙江省產業經濟的支柱,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其生態足跡又會增加。但就整體變動而言,兩圖中第6 期的小高峰均已經低于初期的最高值,因此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發展還是能夠減少第二產業生態足跡的占用。
由圖3 可見,第三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趨勢與第二產業生態足跡的響應趨勢較為相似,但由縱軸顯示的響應程度來看,第二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變動的程度要強于第三產業。
由此可知,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變動對第三產業生態足跡的影響趨勢也呈現明顯的周期性特點。第三產業與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要素的第一產業和以化石能源消耗為支撐的第二產業不同,第三產業相對一、二產業而言是“輕足跡”產業,因此第三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程度天然要弱于第二產業受變動的影響程度。此外,第三產業生態足跡受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變動的影響趨勢有細微差別,前呈現穩定的周期性變動趨勢,但第6 期正向響應的高峰略高于初期,這是因為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動最終是以第三產業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雖然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生產性土地較少,但近年來浙江省第三產業正處于由低端服務業向高端化調整發展,因此在總體變動趨勢上所占用的生態足跡還是未能減少。后者則呈現周期性減少的變動趨勢,第6 期正向影響的高峰略低于初期,可見產業結構合理化,即產業投入產出效率的提高能在長期作用下推動第三產業生態足跡的減少。
六、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研究有如下結論:(1)浙江省人均總生態足跡呈現不斷上升趨勢。其原因是隨著省內經濟發展、產業擴張、人口集聚和需求上升等因素,對生物資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耗量也隨之增加。此外,各生產性土地對總生態足跡的貢獻順序依次為化石地、水域、林地、耕地、草地、建筑地。其中耕地、草地、林地的年增長率均為負值,而水域、化石地、建筑地的年增長率則依次增加,化石地和建筑地作為二、三產業占用的主要生產性土地,可見浙江省的二、三產業正在蓬勃發展,而水域的生態足跡的增長也符合浙江發展海洋強省的戰略方針。(2)浙江省三次產業生態足跡大小依次為一、二、三,但其增長速度依次為三、二、一。足可見浙江省第三產業正在以超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的速度發展,但由于第三產業是“輕足跡”和“低重量”的產業,其生態足跡仍然遠低于一、二產業。(3)在長期變動趨勢中,浙江省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程度加深有利于三次產業生態足跡的減少。就第一產業而言,產業結構高級化會減少其生態足跡,但影響程度會逐漸減弱,而產業結構合理化能在整體上促進其生態足跡的減少;就第二產業而言,在長期變動趨勢下,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均有利于其生態足跡的減少;就第三產業而言,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呈現穩定的周期性變動,在整體上尚未能減少其生態足跡,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則能在長期作用下促進其生態足跡的減少。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考慮到浙江省的地理優勢和對水域的生態占用,浙江省在依托優勢大力發展海洋產業的同時,應時刻關注是否存在過度捕撈、過度開發的現象,加強對海域使用的科學管理,合理規劃休漁期,避免出現涸澤而漁和嚴重污染的現象;(2)穩步推進產業高級化進程。浙江省目前正處于由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向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的轉型關鍵時期,一方面,要持續推進主導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在主導產業轉移時,要避免“產業空心化”現象的出現。因此,浙江省應穩步推進產業高級化進程,尤其在城鎮化過程中,要避免城鎮產業轉型和轉移過急過躁,從而產生經濟萎縮,失業率增高等嚴重后果;(3)加速推動產業合理化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浙江發展的應有之義,一方面,要遏制隨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出現的環境退化,即產業生態化;另一方面,要將美好的生態環境通過產業發展形式轉化成居民的經濟收入,即生態產業化。因此,浙江省在調整產業結構時,既要重視產業結構的生態化發展,譬如政府應強對加強新能源技術項目開發的財政支持,利用稅收和行政手段大力扶植新能源企業的發展并積極督促重能企業的“瘦身”,鼓勵其對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加快建立綠色監督考核制度,根據各產業能耗需求明確企業節能減排的目標,完善目標考核的獎懲制度;又要積極推動生態環境產業化發展,譬如依托省內具有生態優勢的城市,如麗水、衢州,大力開發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業,亦可將二者結合,形成頗具特色的旅游農業、休閑農業等。
——張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