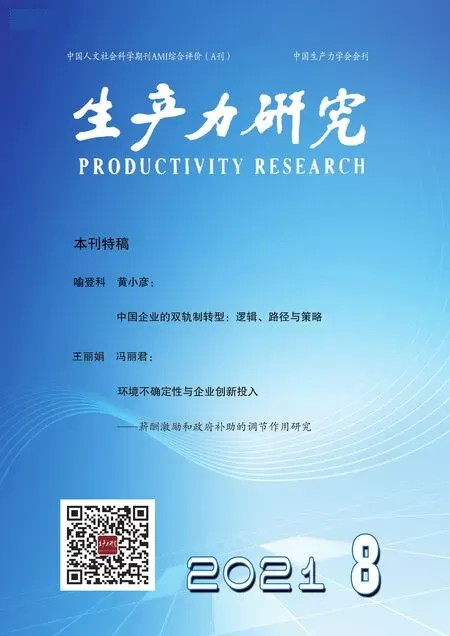稅收政策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影響研究
弋 戈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發(fā)展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若是從經濟結構來看,我國仍然面臨著產業(yè)結構失衡、需求結構失調以及分配結構扭曲的缺陷。進入新時代以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為主的多元產業(yè)格局失去了優(yōu)勢,在促進經濟增長上明顯動力不足,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領導人與社會學者開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希望通過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來調整企業(yè)甚至產業(yè)的發(fā)展模式,從而達到改善需求與分配的目的。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經濟繼續(xù)保持健康高速的發(fā)展,而改革少不了政府的牽頭,也少不了相關產業(yè)政策的支持、規(guī)范與指引。因此,在經濟和政策的形勢下,研究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與政府政策的互動關系和內在規(guī)律顯得十分必要。就現在而言,站在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和歷史背景下,低廉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的喪失,第二產業(y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第三產業(yè)發(fā)展受阻,因此,產業(yè)結構依靠其自身力量已經無法順利實現升級與轉換,要想實現經濟的健康增長,對適當且及時的產業(yè)政策和稅收政策的需求就變得十分迫切。對于如何有效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這一問題,近年來,一些研究表明,財政政策中特別是稅收政策的調整,會對資源在產業(yè)之間流動產生作用,進而會影響到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調整。那么,到底怎樣的稅收和稅種結構有利于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 本文擬在以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1)將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納入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分析框架。(2)本文將用協整模型實證檢驗稅負和稅制結構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作用機制。
二、文獻述評與稅收的作用機制
我國以往研究已經從多個視角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闡釋。例如:陳文潔(2020)[1]指出,當前,我國的投資性支出,特別是高新技術研發(fā)和新興企業(yè)的投資嚴重不足,而我國的居民消費,特別是對服務業(yè)和高技術含量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大,由此導致了經濟增長的內部缺陷,即內生性不足。鄒璇和余蘋(2018)[2]著眼于行業(yè)視角與區(qū)域視角,探究了稅收政策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作用,認為需要針對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才能最大化地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孫正(2016)[3]以“營改增”為出發(fā)點,研究了流轉稅改革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促進作用。任愛華和劉歡(2017)[4]通過對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分析發(fā)現,財政政策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存在著非線性的效應,基于以上結論將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進行劃分,發(fā)現在不同的經濟時期,不同的稅收手段對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存在著不同的效應。趙天宇(2018)[5]以河南省作為研究對象,加入創(chuàng)新這一外生因素,檢驗了創(chuàng)新性不同的企業(yè)稅種結構調整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作用,提出了優(yōu)化稅收結構,使得稅收結構與產業(yè)結構相匹配才能最高效地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馮瑜(2011)[6]指出,在稅收制度上,投資優(yōu)惠要向新興產業(yè)以及技術改進與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傾斜,用先進技術和高新技術來改進和提升傳統(tǒng)產業(yè),進而推動我國產業(yè)結構的升級。羅點點(2017)[7]通過分析全球發(fā)展現狀以及我國產業(yè)結構內部組織架構存在的問題,認為我國目前第二產業(yè)效率低下,第三產業(yè)發(fā)展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企業(yè)研發(fā)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詹結祥和覃子龍(2009)[8]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產出結構與需求結構達到互相適應,產業(yè)之間及產業(yè)內部的比例達到相對協調時,一個國家的產業(yè)結構才會處于一種合理的狀態(tài)。孫雁冰(2018)[9]通過工具變量法研究了稅制結構、稅制改革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作用,研究結論認為增值稅改革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作用不大。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變量選擇與測算
本文選取了2001—2011 年第二產業(yè)、第三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水平數據,由于國家在2013 年全面實行營改增,因此分別選取第二產業(yè)、第三產業(yè)的營業(yè)稅和增值稅稅收負擔水平數據,以及第二產業(yè)、第三產業(yè)企業(yè)所得稅稅收水平數據,接著計算出上述數據在年度的總稅收中所占的比重,以前兩者所得比重作為不同產業(yè)的稅收負擔水平這一變量指標,以后兩者所得比重作為不同稅種的稅收負擔這一指標變量,分別記作STB、TTB、VBTB和CITB。通過《中國稅務年鑒》即可獲得上述相關的數據,但是第一產業(yè)的相關數據存在缺失,因此未將第一產業(yè)納入模型之中。對于被解釋變量產業(yè)結構系數這一指標,以張丹丹對我國2001—2011 年相關數據進行測算所得到的我國的產業(yè)結構系數來作為被解釋變量,記作CIS。考慮到2001—2011 年國內通貨膨脹的擴張對貨幣價值的影響,使用國家公布的2001—2011 年的CPI 來對上述數據進行剔除通貨膨脹的處理,接著,再對上述的處理結果取了自然對數。最后,將得到的變量表示為:LNSTB、LNTTB、LNVBTB、LNCITB和LNCIS。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不同產業(yè)稅收占比和不同稅種的總產業(yè)占比來構建我國不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同兩個產業(yè)總年度稅收負擔水平的比值與產業(yè)結構系數的協整估計模型;建立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與產業(yè)結構系數的協整估計模型,來檢驗我國不同產業(yè)的稅收負擔以及不同稅種的稅收負擔對我國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yt=[LNCISt,LNSTBt,LNTTBt]或者[LNCISt,LNVBTBt,LNCITBt],其中的5個變量LNCISt、LNSTBt、LNTTBt、LNVBTBt、LNCITBt分別為產業(yè)結構系數、第二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第三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a0,a1,a2,···,表示系數矩陣,N為樣本容量,εt表示擾動向量。
四、估計結果分析
(一)數據的平穩(wěn)性檢驗
單位根檢驗的輸出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5 個變量的平穩(wěn)性檢驗結果
非平穩(wěn)的數據容易使得進行檢驗得到的回歸屬于偽回歸,也就是說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明明沒有關系卻得到了一個存在某種關系的結果,因此需要先進行平穩(wěn)性檢驗。出現從表1 所得到的結果可以明顯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被解釋變量LNCIS和解釋變量LNSTB、LNTTB、LNVBTB、LNCITB均未通過平穩(wěn)性檢驗,即以上5 個變量都是非平穩(wěn)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再進行檢驗,輸出的t 統(tǒng)計量的值都小于5%的臨界值水平,意味著被解釋變量LNCIS和解釋變量LNSTB、LNTTB、LNVBTB、LNCITB經過一階差分后的變量DLNSTB、DLNTTB、DLNVBTB、DLNCITB、DLNCIS都是平穩(wěn)序列。
(二)模型的協整檢驗
在第一步數據的平穩(wěn)性檢驗中可知,本文可以通過采用協整檢驗模型來對文中的兩對系統(tǒng)5 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從而得到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將第二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第三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和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一個三元變量矩陣系統(tǒng),同理,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與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另外一個三元變量矩陣系統(tǒng),分別代入數據對兩個系統(tǒng)進行檢驗,所得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模型的協整檢驗結果
從表2 的協整檢驗結果中來分析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的系數以及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在5%臨界值的系數,不難看出,在5%的臨界值水平下,不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同兩個產業(yè)總年度稅收負擔水平的比值以及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的一個三元變量之間,在原假設方程數目為0 或1 時拒絕原假設,而在假設方程數為2 時接受原假設,因此以上3 個變量之間存在著2 個協整關系,同時,在5%的臨界值水平下,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與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的一個三元變量之間,在原假設方程數目為0 時拒絕原假設,而在假設方程數為1 或者2 時接受原假設,因此以上3 個變量之間存在著1 個或者2 個協整關系。基于以上檢驗結果的分析可以確定以上兩個三元矩陣系統(tǒng)之間都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
(三)實證結果分析
在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檢驗分析基礎上,由于數據滿足協整檢驗的要求而且確實存在著協整關系,因此將所得的一系列時間變量序列數據帶入上文所述的兩個三元變量系統(tǒng)中來建立協整模型,分別建立模型1 和模型2。所得到的模型輸出結果如下:
模型1 最終所得結果整理如下:

模型2 最終所得結果整理如下:

通過對協整方程最終所得結果整理后的矩陣進行分析,從不同產業(yè)的稅收負擔對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影響來看,由所得的系數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第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的系數為大于零的正數,體現了該變量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從系數大小來看,這一變量的系數較大為2.307 1,說明這一變量不但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而且所產生的影響較為劇烈。再看第三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可以看出這一變量的系數仍然是一個大于零的正數,也體現了該變量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從系數大小來看,這一變量的系數較大為3.070 2,說明這一變量不但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而且所產生的影響較為劇烈,并且第三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比第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對產業(yè)結構的沖擊更為嚴重。這充分說明不同產業(yè)的稅負水平會影響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
從不同稅種的稅收負擔對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影響來看。由所得的系數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第二產業(yè)年度增值稅和營業(yè)稅的稅收負擔、第三產業(yè)年度增值稅和營業(yè)稅的稅收負擔的累計之和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的系數為大于零的正數,體現了該變量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從系數大小來看,這一變量的系數較大為1.340 6,說明這一變量不但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正向的影響,而且所產生的影響較為劇烈。再看第二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第三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累計之和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可以看出這一變量的系數仍然是一個小于零的負數,體現了該變量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反向的影響,從系數大小來看,這一變量的系數較小為-0.883 2,說明這一變量雖然會對產業(yè)結構系數產生反向的影響,但是所產生的影響有限,沖擊并不劇烈。這充分說明不同稅種的稅收負擔會影響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通過以上的數據輸出結果,可以確定由不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同兩個產業(yè)總年度稅收負擔水平的比值以及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的一個三元變量之間以及由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與產業(yè)結構系數組成的一個三元變量之間確實存在著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分析LNCIS、LNSTB、LNTTB、LNVBTB、LNCITB之間是否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上述兩個協整模型的基礎上,對LNCIS、LNSTB、LNTTB、LNVBTB、LNCITB5 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模型中存在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從表3 中可以看出,所得結果均拒絕原假設,意味著產業(yè)結構系數與第二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之間存在著格蘭杰因果關系,產業(yè)結構系數與第三產業(yè)的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這一變量之間存在著格蘭杰因果關系,產業(yè)結構系數與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這一變量之間存在著格蘭杰因果關系,產業(yè)結構系數與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這一變量之間存在著格蘭杰因果關系。由此可見,不同產業(yè)的稅負水平波動以及不同稅種的稅收負擔波動均是造成產業(yè)結構系數波動的原因。
(五)脈沖響應分析
根據檢驗結果,確定所構建的模型都是穩(wěn)定的,因此可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脈沖響應情況如圖1所示。
圖1 中(a)、(b)、(c)和(d)分別表示從不同層面給予一個沖擊后,產業(yè)結構系數的反映情況,依次分別體現了產業(yè)結構系數對第二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的脈沖響應情況、產業(yè)結構系數對第三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在年度總稅收中所占比重的脈沖響應情況,產業(yè)結構系數對兩個產業(yè)中2013 年后增值稅額或2013 年之前的營業(yè)稅額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的脈沖響應情況,產業(yè)結構系數對兩個產業(yè)的年度企業(yè)所得稅的之和與年度總稅收的比值的脈沖響應情況。從圖1 可以看出,不同產業(yè)年度稅收負擔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影響在當期并不明顯,在第2 期時,影響達到最大,之后逐步減弱,并且在第5 期之后變得平穩(wěn)。而不同稅種對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影響在當期都不明顯,但在隨后的1 期都開始產生正向的影響,在第2 期時,影響達到最大,之后逐步減弱,并且在第5 期之后變得平穩(wěn)。通過脈沖響應的圖示可以看出,短期內,改變稅收負擔和稅種均會對產業(yè)結構產生正向影響,但從稅收沖擊的長期效應來看,兩者對產業(yè)結構變動產生的影響會越來越小。

圖1 脈沖響應
五、結論及啟示
進入新時代以來,國際競爭愈發(fā)激烈,以前我國所存在的低廉勞動力優(yōu)勢逐漸減弱并且消失,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改革的呼聲愈發(fā)強烈,同時,我國產業(yè)發(fā)展不平衡,第三產業(yè)發(fā)展不足,而政策措施卻不利于產業(yè)自我的優(yōu)化升級,這必然會給我國整個產業(yè)結構帶來沖擊,因此,能否順利實現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調整將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在新時代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且健康的增長。在這一目的下,少不了政府的政策推動作用,即政府應當制定與產業(yè)結構布局相匹配的產業(yè)政策,調整財政稅收政策,使得政策向著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方面傾斜。
通過上述協整模型的輸出結果以及對相關結果所進行的分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現階段的稅收政策進行調整由此來達到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的作用:
第一,調整稅制結構,把營業(yè)稅改增值稅作為契機,通過稅率和一定的獎勵機制來引導資源到產業(yè)的流向,使得更多的優(yōu)質資源流入第三產業(yè),從而達到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目的。
第二,調整不同產業(yè)的稅收負擔,實現各產業(yè)稅負公平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二產業(yè)在政策環(huán)境優(yōu)勢以及外商投資的大背景下,發(fā)展迅速,各種稅收政策和外部資源都傾向了第二產業(yè),在短期中,促進了第二產業(yè)的發(fā)展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但伴隨著第二產業(yè)發(fā)展到達瓶頸,對第三產業(yè)發(fā)展的需求愈發(fā)旺盛,使得產業(yè)發(fā)展與政策、資源投入不匹配,因此,適度調整不同稅收負擔水平,從而達到各產業(yè)公平稅負的目的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第三,建立淘汰制度與扶持制度,通過淘汰制度來應對產能嚴重過剩的現象。對于產能過剩的企業(yè)、資金嚴重不足的企業(yè),要嚴格控制財政的支持。對于研發(fā)創(chuàng)新、技術革新的企業(yè),通過扶持制度來支持和培育企業(yè)的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以及新興產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