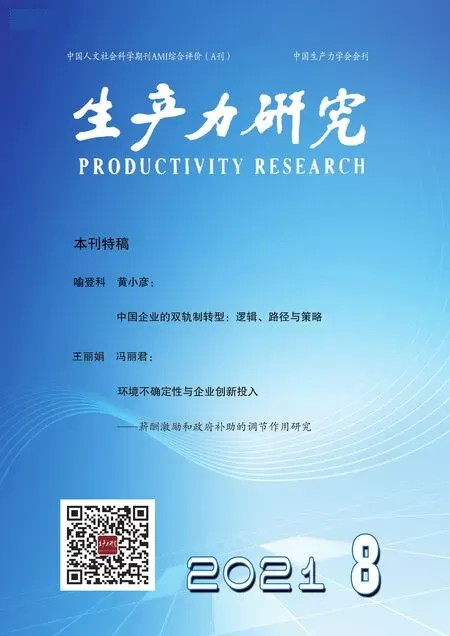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溢出效應研究
——基于PVAR 模型的實證分析
陸佳穎,郭建偉
(江南大學 商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一國經濟政策的變化不僅會影響本國的宏觀經濟,還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因此,研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一直以來都是宏觀金融領域的熱點話題。然而,現有國內外研究主要以美歐等發達國家作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主體,而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關注較少。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2000—2019年,中國GDP 從12 113.69 億美元上升到143 429.03億美元,占世界的份額從3.60%上升到16.35%,進出口金額從4 742.97 億美元上升到45 778.91 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貿易大國。2016 年10 月,人民幣加入SDR,人民幣國際化邁上一個新臺階。因而,中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開始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2013 年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合作交流已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存在溢出效應嗎?如果存在,其程度如何?這是本文探討的出發點。
二、文獻綜述
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其貨幣政策對他國的影響毋庸置疑。國內外學者對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進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認為美國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溢出影響。劉克崮和翟晨曦(2011)[1]認為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促使我國物價水平大幅上升,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現象嚴重。齊曉楠等(2013)[2]的研究表明,長期而言,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人民幣升值,且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構成負向沖擊。Cho 和Rhee(2014)[3]的研究則發現,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國內收益率和信用違約掉期溢價,顯著推動國際資本流向亞洲國家。馬理和余慧娟(2016)[4]運用PVAR 模型研究發現,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具有較強的正向溢出效應。Xu 和La(2017)[5]的研究發現,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顯著促進了亞洲的美元信貸增長,對亞洲信貸市場具有正向溢出效應。許志偉等(2020)[6]的研究表明,美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會通過匯率傳導效應使中國的進口品價格下降,并引起中國國內生產成本下降、物價下跌和產出上升。
除了研究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以外,國內外也有許多學者對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進行研究。梁斯和郭紅玉(2015)[7]的研究發現,日本擴張的貨幣政策會對中國的利率及進出口貿易帶來顯著影響。張靖佳等(2017)[8]的研究表明,歐洲量化寬松政策的匯率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出口額和出口量具有正向溢出效應。Kucharcuková等(2016)[9]的研究則表明,歐洲央行的傳統貨幣政策沖擊對歐元區以外6 個歐盟國家的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是一致的,而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影響則差異較大。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中國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也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但相關研究無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未達到研究美國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成熟程度。Kozluk和Mehrotra(2009)[10]通過SVAR 模型研究了中國貨幣政策沖擊對東亞和東南亞主要貿易伙伴的影響,發現中國貨幣政策會對菲律賓和新加坡的產出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Johansson(2012)[11]分析了中國貨幣政策沖擊對東南亞五國股市的影響,結果表明,中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其中四個國家的股市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楚爾鳴和王真(2018)[12]采用面板回歸模型研究發現,中國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長存在溢出效應,并具有異質性。崔百勝和葛凌清(2019)[13]的研究發現,中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日本、美國和歐盟等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產生了溢出效應,并且在響應方向和程度上存在異質性。
迄今,貨幣政策溢出方面的國內外研究,總體而言:一方面,溢出主體的研究,以發達國家為主,而研究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文獻較少。另一方面,即使以中國作為溢出主體的研究,也存在溢出客體偏少、溢出機制單一等不足。本文擬從以下幾點補充現有文獻:第一,研究對象以中國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主體,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客體,對現有中國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研究做出有效補充。第二,針對大多數文獻樣本選擇的局限性,選取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28 個代表性國家進行研究,使研究更加全面。
三、模型構建、變量與數據選擇
(一)模型設定
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來實證分析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溢出效應。PVAR 模型由Holtz-Eakin 等(1988)[14]最先提出,它能夠在傳統VAR 模型的基礎上對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因此兼具了時間序列分析與面板數據分析的優點,極大地擴展了VAR 模型的功能。參照Love 和Zicchino(2006)[15]的研究成果,設置PVAR模型如下:

式 中,Yit=(CNIRt,CNM2t,IPIit,CPIit,IRit,ERit),其中i代表樣本國家,t代表月度數據,j代表滯后階數,p代表最優滯后階數。Γ0表示截距向量,Γj表示滯后向量的參數矩陣,αi表示個體效應,β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CNIR 和CNM2 為模型的自變量,表示中國的利率和貨幣供應量,IPI、CPI、IR 和ER 為模型的因變量,分別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貨幣市場利率和匯率。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選擇
雖然“一帶一路”覆蓋歐亞非三個大陸,涉及65個國家和地區,但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僅分析28 個沿線國家,樣本包括:俄羅斯、蒙古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印度、埃及、格魯吉亞、土耳其、以色列、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黑山、捷克、克羅地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烏克蘭、匈牙利、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
(三)變量與數據的選取
本文將中國的利率(CNIR)和貨幣供應量(CNM2)作為貨幣政策的代理變量,其中,利率選擇中國銀行間7 天內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貨幣供應量選擇廣義貨幣供應量M2 的同比①盡管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推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這一利率具有權威性、指導性,正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引導金融市場利率的參考,但是由于該利率尚欠時間序列,故本文不予采用。。模型的因變量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IPI)、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貨幣市場利率(IR)和匯率(ER),其中,匯率為直接標價法下各國貨幣兌美元的價格。
本文選擇的樣本區間為2013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IPI)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各國貨幣市場利率(IR)和匯率(ER)的數據來源于IMF 統計數據庫;中國銀行間7 天內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CNIR)和廣義貨幣供應量M2 同比增速(CNM2)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官網。
四、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在建立PVAR模型之前,首先對各變量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變量CNIRt和CNM2t為時間序列數據,因此采用ADF檢驗;而變量IPIit、CPIit、IRit和ERit為面板數據,則采用LLC檢驗和IPS檢驗。由表1 的結果可知,原序列均為平穩序列,可以進行后續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所有檢驗過程均由Stata 14.0 完成。

表1 變量平穩性檢驗
(二)滯后期選擇與格蘭杰因果檢驗
根據AIC、BIC和HQIC信息準則,確定P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 階,在滯后2 期下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
根據表2 中的結果,基本上可以確定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IR、ER的格蘭杰原因。其中,中國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IR和ER的格蘭杰原因,中國的貨幣供應量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和ER的格蘭杰原因,各國CPI在短期內并未受到中國貨幣政策的直接影響。但是,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論只能檢驗統計上的時間先后順序,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不能作為肯定或否定因果關系的根據。因此,仍需進一步論證。

表2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貨幣供應量是我國重要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當中國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發行大量貨幣時,本國貨幣貶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相對升值,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匯率和物價水平產生影響;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升值,會對其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出水平。利率是我國重要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中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變化會使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金流動,進而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利率和匯率發生變動;利率和匯率的變動又會對其產出和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貿易差額的變化亦會引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匯儲備的變化,進而影響到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率,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產生影響。基于此,本文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IPI、CPI、IR、ER存在實質性的影響,構成了因果關系。
(三)變量間的關系
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估計模型參數,對計量模型(1)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由于最優滯后階數為2,因此表中給出了滯后2期的影響系數。考察滯后2 期的CNIR(t-2)和CNM2(t-2)的影響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利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IPI、CPI、IR和ER的影響系數的絕對值大于貨幣供應量,表明價格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要強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利率是金融市場中的關鍵變量,由于金融市場的變化極其迅速,政策的滯后期時間較短,因此利率的溢出效應更為明顯。第二,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和ER的影響方向一致①利率下降和貨幣供應量上升表示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兩者影響系數相反表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方向相同。。CNIR(t-2)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 的影響系數小于0 為-0.438 5,對ER的影響系數大于0 為0.323 7,CNM2(t-2)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IPI 的影響系數大于0為0.396 7,對ER的影響系數小于0 為-0.085 2。這表明了中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會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體經濟產出上升和貨幣升值。第三,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CPI和IR兩個變量的影響方向相反,說明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物價水平與利率水平的影響存在差異,這可能是因為中國貨幣政策只是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物價與利率水平的一種因素,而世界其他國家宏觀政策的變動也會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這些宏觀經濟指標產生影響。

表3 PVAR 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四)脈沖響應分析
本文根據已建立的PVAR模型,分別給中國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同比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向沖擊,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對利率和貨幣供應量沖擊的響應。設定蒙特卡洛200 次模擬,沖擊時間長度為20 期,脈沖響應結果如圖1 至圖4 所示。

圖1 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的脈沖效應

圖2 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物價指數的脈沖效應

圖3 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的脈沖效應

圖4 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的脈沖效應
1.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的影響
圖1 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IPI)的沖擊效果。從圖中可以看出,面對中國1 個標準差的正向利率沖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的即期表現為正向變化,并在1 期~2 期后逐步轉變為負向反應,但負向反應的持續時間較短,在第3 期以后,利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的影響又逐漸回到正向變化,且在第10 期后正面影響呈穩定狀態。表明中國緊縮性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上升)在長期內會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出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面對中國1 個標準差的正向貨幣供應量沖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的響應始終為正,并且在第5 期達到最大值,此后影響效應逐漸遞減。表明中國擴張性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會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出水平上升。
2.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物價指數的影響
圖2 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物價指數(CPI)的沖擊效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利率的正向沖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物價指數的影響在第1 期短暫為正,在第2 期后逐步轉變為負向反應,且負向反應逐漸增大,負向沖擊效應在第15期后呈穩定狀態。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物價指數的影響始終為負,在前期中,負向影響一直呈遞增狀態,直到第15 期時負向影響達到最大,此后影響效應逐漸趨于穩定。這說明中國擴張性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在長期內會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物價上漲。
3.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的影響
圖3 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IR)的沖擊效果。兩幅子圖均顯示,中國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的影響始終為負。具體來看,中國利率的正向沖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的負向影響從第1期到第5 期逐步增強,并在第5 期達到最大值,此后影響效應逐漸遞減;面對中國1 個標準差的正向貨幣供應量沖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率的負向反應在即期達到最大,此后影響效應快速下降,在第1 期達到最小,在第2 期又有所回升,第2 期后影響效應呈波動下降趨勢。表明中國擴張性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數量型貨幣政策會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市場利率上升。
4.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的影響
圖4 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ER)的沖擊效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利率的正向沖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的影響始終為正,正向影響在前期處于遞增狀態,并且在第12 期達到最大值,此后影響趨于平緩并出現遞減趨勢。面對中國1 個標準差的正向貨幣供應量沖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的即期表現為負向變化,但負向影響逐步減弱,并在第6 期后影響效應轉變為正向,正向沖擊效應在第14 期后呈穩定狀態。表明中國緊縮性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在長期內會促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貶值。
(五)方差分解
進一步運用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變量的貢獻程度與解釋能力的變化。表4 分別給出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經濟變量在第10、20 和30 個預測期內方差分解的結果。
從表4 中可以看出:第一,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出(IPI)、物價指數(CPI)、貨幣市場利率(IR)和匯率(ER)均存在溢出效應,其中,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匯率(ER)的貢獻程度最大,利率的貢獻率最大達到了37.58%,貨幣供應量的貢獻率最大達到了3.19%。第二,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溢出影響的持續時間較長,均在30 期以上,且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對各經濟變量的貢獻率均處于遞增狀態。第三,利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宏觀經濟變量IPI、CPI、IR、ER的貢獻程度均大于貨幣供應量的貢獻程度。

表4 方差分解結果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28 個國家2013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的月度宏觀數據,采用PVAR 模型實證檢驗了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生產指數(IPI)、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貨幣市場利率(IR)和匯率(ER)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IPI、CPI、IR、ER均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且短期內中國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促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體經濟產出上升和貨幣升值。(2)價格型與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存在溢出效應,但其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一般來說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要大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3)中國貨幣政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溢出影響持續時間較長。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針對我國中央銀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別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對于我國中央銀行而言:(1)根據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異質性,合理地選擇貨幣政策工具,在實現國內貨幣政策目標的同時,也能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產生正向影響,促進各國共同發展。(2)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區域貨幣政策協調與合作,加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戰略合作。(3)將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作為長期國策,避免中國擴張性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使他國經濟產生劇烈波動。這個也就是中央銀行反復強調的政策思路,不搞“大水灌溉”。
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1)中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在短期內會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升值,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不利影響,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調整貿易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自身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尤其是他們與中國之間應加強國際經濟金融合作,協調好其國內經濟金融政策,在更高的層次,深挖他們與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金融合作潛力,最終實現各自國家持續穩定的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