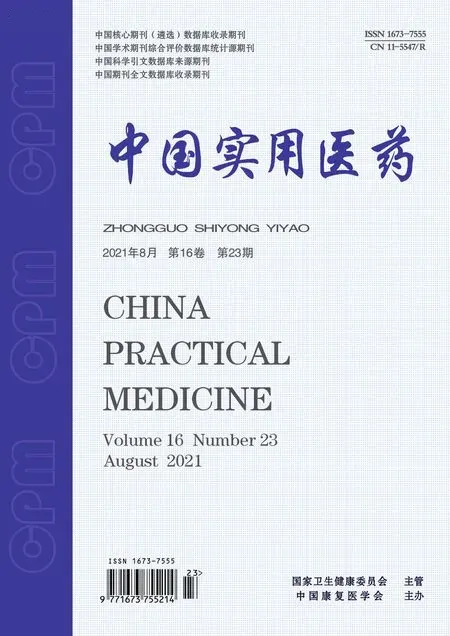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1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炎癥指標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劉寶英 梁干雄 葉凱云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慢性內分泌疾病,臨床根據其癥狀表現差異可將其分為1 型和2 型兩種,均具有明顯的遺傳特性。目前臨床對其發病機制的研究尚未有統一的定論,但普遍認為與胰島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損密切相關。當人體的胰腺B 細胞功能遭到破壞后,會直接導致機體胰島素分泌不足,機體無法進行有效的代償,從而造成血糖升高,此類患者通常需要終生接受藥物治療,如胰島素等。但有研究表明,T1DM患者發病年齡通常較低、自控能力較差,血糖控制難度較大,繼而各種并發癥的發生率較高,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安全[1]。腸道菌群作為調節人體內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影響著宿主的營養、代謝及免疫,有研究表明,腸道菌群紊亂可能通過改變腸壁通透性及免疫功能參與了T1DM 的進程,故而推測通過給予患者特定的飲食、或是添加益生菌以及使用抗生素等方式可以有效調整患者腸道內的菌群分布情況及腸道菌群的結構分布,從理論上來說有助于延緩T1DM 病情進展[2]。然而隨著生物信息學和宏基因組學的快速發展,腸道微生物作為一個環境因素在T1DM 中的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迄今基于人群的研究尚少,國內關于T1DM 患者腸道菌群的研究更是鮮有報道[3]。對此廣東省中山市政府于2014 年開始啟動T1DM 干預項目。本研究以中山地區T1DM 干預項目組入組的T1DM 患者為研究人群,收集研究對象新鮮糞便標本,提取糞便基因組DNA,通過生物信息學分析其腸道菌群結構特征,了解T1DM 患者腸道菌群特點,同時根據研究對象的HbA1c 水平分組,了解不同血糖控制水平患者腸道菌群差異,發現與血糖控制相關的腸道細菌類型,從而為基于腸道菌群的T1DM 的新的治療方法或基于腸道菌群的T1DM 預防藥物的開放奠定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 年1 月~2019 年10 月中山市人民醫院內分泌科診斷為新發T1DM 患者25 例作為T1DM 組,納入標準:①疾病確診時間≤6 個月;②并發酮癥酸中毒癥狀;③患者開始接受胰島素治療;④谷氨酸脫羧酶抗體(GADA)和/或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體(IA-2A)陽性;⑤血清空腹C 肽<130 pmol/L 或餐后2 hC肽<330 pmol/L。排除標準:①患者患有胃腸道疾病,如便秘、慢性腹脹、消化不良等;②患者患有過敏性或感染性疾病;③患者在參與研究前1 個月接受過影響腸道菌群的藥物治療。另選取同期25 例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排除標準與T1DM 組一致。T1DM 組男5 例,女20 例;年齡11~68 歲,平均年齡(40.84±10.81)歲;并且同時根據T1DM 組患者HbA1c 水平分為A 組(HbA1c≤7%,5 例)、B 組(HbA1c 7%~9%,15 例)、C組(HbA1c>9%,5 例)。對照組男6 例,女19 例;年齡12~67 歲,平均年齡(40.87±9.92)歲。T1DM 組和對照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項研究現已經過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和受檢者的知情同意,已簽署知情文書。
1.2 方法
1.2.1 樣本收集和檢測 首先采集患者的血液標本和糞便標本,其中血液標本采集后放置在-80℃的環境中保存待檢;而糞便標本則需要在排便后2 h 內儲存在封閉的儲存盒中,同樣置于相同溫度的環境中保存,前者進行生化檢驗,后者進行細菌DNA 的提取及定量,糞便DNA 提取方法根據試劑盒的說明完成;糞便DNA 的16SrDNAV3-4 的擴增及測序列由生物公司協助完成。
1.2.2 生物信息學分析 將測序得到的序列數首先應用Flash 軟件進行拼接,同時使用QIIME 軟件包過濾序列數的拼接效果及質量,同時校正序列方向,然后采用barcode 標簽序列對樣品進行識別和區分,進而采集有效數據;對所有序列進行歸類操作,相似度>97%序列聚類為一個操作分類單元(OTU),并根據最新版本過濾OUT。
1.3 觀察指標 比較T1DM 組和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差異,多樣性指數包括Shannon 指數、Simpson’s 指數和Chaol 豐富度指數[4]。比較A 組、B 組、C 組、對照組炎癥指標(hs-CRP、IL-6)和多樣性指數差異;分析腸道菌群與T1DM 患者血糖、炎癥指標水平的相關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表示,采用t、F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Pearson 相關分析。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T1DM 組和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差異比較 T1DM 組Shannon 指數、Simpson’s 指數及Chaol 豐富度指數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T1DM 組和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差異比較()

表1 T1DM 組和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差異比較()
注:與對照組比較,aP<0.05
2.2 A 組、B 組、C 組、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和炎性指標比較 A 組、B 組、C 組Shannon 指數、Simpson’s 指數、Chaol 豐富度指數及hs-CRP、IL-6 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A 組、B 組、C 組、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和炎性指標比較()

表2 A 組、B 組、C 組、對照組多樣性指數和炎性指標比較()
注:四組比較,P<0.05
2.3 腸道菌群與T1DM 患者血糖、炎癥指標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腸道菌群菌種的豐富度和多樣性指數與血糖水平及炎性因子hs-CRP、IL-6 水平呈正相關(r=0.622、0.601、0.596,P<0.05)。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臨床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發現糖尿病患者存在腸道菌群失調的現象,尤其是T1DM 患者更加顯著;而出生環境、日常飲食以及抗生素和益生菌等藥物則是影響腸道菌群的主要因素,故而推測腸道菌群會影響T1DM 的發病。一項動物實驗研究發現,在對其輸注特定腸道菌群后,T1DM 癥狀得到有效的預防和減輕,由此可見兩者之間關系密切[5]。目前,臨床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尚不明顯,但普遍認為可能是腸道屏障功能的改變或者是腸道免疫系統參與T1DM 的發病過程。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T1DM 組Shannon 指 數、Simpson’s 指數及Chaol 豐富度指數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見,T1DM 患者腸道菌群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明顯高于正常人群,推測其原因可能與腸道菌群失調有關。腸道不僅是機體最大的免疫器官,更是機體與外界環境發生相互作用的最大區域[6]。與其他組織微環境相比,腸道微環境的最大特點是存在定植數量眾多且群復雜的腸道微生物,而人類的腸道菌群由超過3500 種細菌組成。這類菌群的存在一方面用于消化人體的食物殘渣;另一方面它還參與宿主的能量代謝;并且在為人體提供維生素、氨基酸、抗菌素和多肽的同時,還可以分解宿主體內的有毒、有害物質,并且參與腸上皮的生長、分化、炎癥反應,促進腸道免疫系統的發育和成熟,但在部分外界因素的作用下極易導致其組成分支發生變化[7]。經臨床既往實驗研究發現[8],非肥胖型糖尿病(NOD)小鼠從無菌環境轉至無特異菌群定植的有菌環境后,胰腺炎程度減輕,糖尿病發生率降低,但若給予NOD 小鼠長期檸檬酸桿菌或抗生素干預,其腸道菌群穩態失衡、腸道屏障破壞從而誘發自身免疫反應,胰腺炎癥加重,糖尿病的發生率增高,并且糖尿病大鼠的腸道菌群與正常對照不同,其中擬桿菌屬菌群數量較多,更進一步證實T1DM 進程中存在腸道菌群失調的現象。除此以外,本研究結果還顯示,A 組、B 組和C 組Shannon 指數、Simpson’s 指數、Chaol 豐富度指數及hs-CRP、IL-6 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提示,伴隨著人體血糖和炎癥指標水平的升高,腸道菌群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會有明顯升高,推測其原因可能與T1DM 患者自身免疫功能失調有關,但具體的作用機制仍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T1DM 患者腸道菌群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明顯高于正常人,其血糖和炎癥指標水平越高的患者其糞便中的腸道菌種類越豐富,充分表明T1DM 腸道菌群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與血糖和炎癥指標水平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