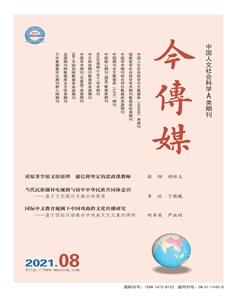危機傳播視閾下媒體融合的“危”與“機”
摘 要:自2008年起,各類社交軟件和平臺大量興起,使得媒體融合進入傳媒界和國家的視線,到2014年國家提出“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使得媒體融合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成為擺在國家和傳媒界面前的一項緊迫課題。本文從危機傳播視閾出發(fā),通過運用“危機傳播四階段理論”“風險傳播理論”“危機應對3T原則”等理論,對媒體融合的階段性加以分析和判斷,探尋媒體融合與危機傳播周期性和規(guī)律性之間的聯系,解析當前媒體融合中存在的“危”與“機”,以期在媒體融合向縱深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對媒體融合發(fā)展的實踐及融合應對提供一些有益參考。
關鍵詞:危機傳播;風險傳播;媒體融合;融合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1)08-0040-04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互聯網的興起和發(fā)展,使得網絡作為“第四媒體”進入國家意識形態(tài)宣傳領域,在拓展媒體傳播形態(tài)、功能、渠道及內容的同時,也對傳統媒體的傳播狀態(tài)和秩序構成潛在的威脅。21世紀,隨著網絡的興盛,全球進入信息時代,即時便捷的信息傳遞改變了中國的信息傳播格局,大量不確定性因素引發(fā)社會大眾的焦慮和恐慌,對社會系統的穩(wěn)定性構成潛在威脅。在社會異化的今天,網絡、手機移動端等新媒體的大量涌現,給傳統媒體造成了很大的沖擊,使得傳統媒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迫使其不斷通過各種實踐探索出路。
自2008年各類社交軟件和平臺的興起,到2014年國家提出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為傳統媒體所面對的危機尋找出路,即實現媒體的融合發(fā)展。
一、危機傳播概述
(一)基本概念
在中文中,“危機”由兩個字構成,一個是危險,一個是機會。從危機的定義來看,國內外學者把危機大致分為兩種,即狀態(tài)說和事件說。其中狀態(tài)說認為,“危機是一種形勢”,這種形勢對于決策者的根本目標亦或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等構成威脅,并且這種形勢在實踐中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需要盡快對其作出反應。而在危機前后及其發(fā)展過程中,政府部門、組織、媒體、公眾之內和彼此之間進行的信息交流過程就是危機傳播[1]。
危機傳播大致有三方面的特點,即危機傳播是混亂符號和不確定意義的共享過程;是信息傳播主體與客體非秩序化復雜互動的過程;是一個失衡的信息系統,是各種信息碎片的雜合體。從最根本上講,危機是不可能提前做好準備的。因此,積極正視和認識危機成為避免和應對危機的重要前提。
媒體融合正是傳統媒體應對新媒體的一種形勢和狀態(tài),信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引發(fā)各種不確定性,使得傳統媒體如何通過融合擺脫生存危機已成為媒體、大眾乃至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從危機傳播的特點來看,媒體融合也正是這些特點的表征。
(二)危機傳播相關理論
目前,危機傳播理論的研究有多個方面,而從媒體融合這種特殊的社會危機來看,“危機傳播階段理論”(即“四階段理論”)和“風險傳播理論”等對其更具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
“危機傳播階段理論”是斯蒂文·芬克(Steven Fink)在1986年提出的,他把危機傳播的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危機潛在(萌芽)期、危機爆發(fā)期、危機蔓延期、危機解決(恢復)期。該理論的優(yōu)點是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循環(huán)往復的危機全過程。
“風險傳播理論”是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在其著作《風險社會》中提出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包括風險評估、風險預防、緊急應對和災后重建等內容;狹義上是指危機發(fā)生前的預警階段,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消減風險。風險傳播是危機傳播領域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兩者又相互區(qū)別:危機傳播是基于現實危險的傳播, 風險傳播則是基于可能性的傳播[2]。
二、媒體融合概述
“媒體融合”一詞,最早由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在其著作《自由的技術》中提出,他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媒體融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是指不同媒介形態(tài)的融合而形成一種新的媒介形態(tài);廣義上則是指一切媒介及其有關要素的結合、匯聚甚至融合,不僅包括媒介形態(tài)的融合,還包括媒介功能、傳播手段、所有權、組織結構等要素的融合。媒體融合是信息時代背景下一種媒介發(fā)展的理念,是在互聯網迅猛發(fā)展的基礎上實現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有機整合[3]。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互聯網的興起和發(fā)展對整個傳媒業(yè)構成了潛在威脅,使得國家思想宣傳工作陣地得以轉移。在互聯網的快速發(fā)展和新興技術的開發(fā),特別是隨著微博、微信、微視頻、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使得傳統受眾的斷崖式下跌撼動著傳統主流媒體的主導地位,逐漸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戰(zhàn)場”,影響著媒體、大眾、國家和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成為一場現實意義上的社會危機。
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即當下正波及媒體、大眾、社會和國家等多領域的一個集過程、風險于一體的危機傳播,更是一場傳統媒體的生存危機。
在媒體融合向縱深發(fā)展的當下,國家、傳媒界、學界、技術行業(yè)等都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什么是媒體融合、為什么要進行媒體融合、怎么來實現媒體融合等問題。如何應對這場特殊的社會危機,就需要清晰準確地認識這一危機,積極正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融合發(fā)展,才能在這場媒體和社會變革的危機中贏得主動、找準先機、獲得長足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
三、從危機傳播看媒體融合
這場跨越20世紀和21世紀的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進行融合的過程充滿了危機和風險,在國家、學界和業(yè)界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應對后不斷消除或緩解。按照“四階段理論”,危機有一定的周期性,而在媒體融合不斷蔓延加劇的當下,如何通過把握這種內在規(guī)律對緩解和消除危機顯得至關重要。
(一)從“四階段理論”看媒體融合的進程
20世紀90年代,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和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網絡作為“第四媒體”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形勢,在發(fā)揮自身角色和功能的同時,也逐漸融入傳統媒體傳播的領域中,并對傳統媒體的傳播狀態(tài)、秩序構成潛在威脅。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傳媒業(yè)競爭的激烈程度與日俱增,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國外媒體集團正攜帶著強大的資本威逼著中國逐步開放傳媒市場,以各種方式悄然進入中國,這一切都使國內傳媒業(y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zhàn)。要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運,變革與發(fā)展勢在必行[4]。
1.危機的萌芽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
這段時期正是這場傳統媒體應對互聯網危機的萌芽期,整體表現為傳統媒體上網的媒體融合初期實踐和探索。
在我國,1995年1月《神州學人》首個進入互聯網,成為我國第一份中文電子雜志;同年10月《中國貿易報》的正式上網,標志著中國國內第一家日報上網發(fā)行,揭開了國內媒體大批上網的序幕,成為媒體融合的雛形。1997年《人民日報》創(chuàng)辦網絡版,初步探索與新媒體的融合;1999年《廣州日報》成立網絡版,成為中國大陸最早通過互聯網為大眾提供新聞資訊的媒體之一;到1999年成為我國媒體上網的一個高潮。隨后,由互聯網衍生出許多傳統媒介的新形勢和新媒體渠道,如播客、博客、網絡電視等。
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成熟以及人們對網絡傳播特點認識的不斷深入,媒體上網也從Web1.0時期網絡單向傳播,到通過集中物力、人力和財力進行橫向聯合,實現信息資源的整合,再到逐漸向Web2.0時期的初級互動平臺過渡,使得傳統媒體切實感受到了網絡傳播的威力和威脅。
2.危機的爆發(fā)期(2008年至2013年)
2008年起,新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不斷加速傳統媒體的更新換代,使得這場危機全面爆發(fā),各大媒體積極應對和探索,主要表現有:2008年煙臺日報傳媒集團研發(fā)使用的“全媒體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在全國范圍內首創(chuàng)全媒體新聞中心;2009年中國網絡電視臺(CNTV)正式開播;2010年四大門戶同時推出微博服務,成為引導輿論的新陣地;2011年浙江廣電集團率先開辦網絡廣播電視臺;同年7月人民日報社“全媒體新聞資訊管理系統”正式投入試運行;2012年人民網上市交易;同年7月《人民日報》開通法人微博;11月,各大權威網絡媒體以及門戶網站紛紛推出手機新聞客戶端;2013年《人民日報》宣布利用二維碼、圖像識別等技術,把部分稿件轉化為多媒體形態(tài)進行推廣和傳播;同年10月,上海報業(yè)集團正是成立等。
從微博平臺的亮相到后來微信、微視頻、客戶端、網絡社群等新興輿論渠道的不斷推出和發(fā)展壯大,給傳統媒體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使得傳統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急劇下滑,波及到整個媒體、大眾、社會及國家的方方面面。而如何加強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fā)展,便成了媒體和國家所要解決的題中之意。
3.危機的蔓延期(2014年至今)
從2014年開始,就媒體融合發(fā)展,國家不斷出臺相關講話和政策,來指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進一步融合發(fā)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fā)展的指導意見》,拉開了從國家層面出發(fā)指導媒體深度融合的大幕,把推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fā)展提上了國家日程。在隨后的幾年,國家不斷出臺關于媒體融合的政策和講話,例如,2016年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2019年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fā)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2020年的《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fā)展的指導意見》等。
在新形勢下,國家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探索出媒體融合發(fā)展的方向,對此提出明確要求,通過具體部署從國家層面出發(fā)來應對和解決這場危機。在專家權威對這一系列政策進行及時地解讀和分析下,準確把握媒體融合的內涵和要求。同時,業(yè)界積極響應,多措并舉,“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實現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深度融合,部分媒體在實踐中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發(fā)展。包括湖南廣電的“芒果模式”、《人民日報》的“中央廚房”、央視的首個國家級5G新媒體平臺“央視頻”、縣級媒體融合發(fā)展的“長興探索”等。這一系列實踐案例掀起了全國范圍內媒體融合發(fā)展的大潮,把媒體融合推向了深水區(qū),使媒體融合能夠在國家的指導下向縱深處發(fā)展,促使這場危機影響的消除。
隨著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進行融合的危機不斷逼近,加劇著媒體與大眾、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不斷解構著傳統媒體的主流地位,也影響著國家的發(fā)展和社會的穩(wěn)定,使媒體融合逐漸上升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在深刻認識到這場危機的迫切性下,國家不斷出臺的一系列關于媒體融合的講話和政策,對媒體融合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指導,來預警和消減新媒體快速發(fā)展所帶來的風險。
4.危機的恢復期(未來發(fā)展)
目前,這場危機的恢復期并未到來,從媒體融合到全媒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按照“四階段理論”,危機是有生命周期的,每一階段都不會被跨越。
只有深刻認識這場危機,厘清危機的各個階段,把握其生命周期和內在規(guī)律,遵循并加以利用,才能在實踐中有的放矢,加速媒體融合的步伐,使媒體融合的發(fā)展符合傳播規(guī)律,符合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全媒體發(fā)展,盡而為危機的恢復做準備。
(二)媒體融合中的“危”與“機”
媒體融合的過程,其本身也成為應對這場危機的法則。在這場危機的萌芽期和爆發(fā)期,媒體融合只是停留在表象上,認識也并不深入,直到媒體融合的不斷蔓延才加速了國家、業(yè)界、學界對這一危機的高度重視,并積極從理論、學術和實踐視角出發(fā)解讀和探究其深層次的內涵和癥結,盡而最大程度地消除危機、化解風險。
1.媒體融合中的“危”
在媒體融合向縱深發(fā)展的當下,盡管這一危機更多的表現為傳統媒體所面臨的危機,但從宏觀角度出發(fā),這種“危”波及多個層面,具體表現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從國家層面出發(fā),對內是國家輿論引導力面臨的挑戰(zhàn)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對外則是國際話語權的缺失、網絡主權的挑戰(zhàn)以及國家網絡安全等。
對業(yè)界而言,傳統媒體傳播力和影響力的下滑,一方面,是由于其體制機制的制約、傳統的經營方式、傳統載體的失靈、傳媒人才的流失及全媒體人才的缺位、權威優(yōu)勢內容的匱乏、受眾向用戶的轉移等;另一方面,則是新媒體把關機制的缺失,后真相、虛假信息和謠言的大量滋生,網絡亞文化及投入產出效果不顯著等,其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2.媒體融合中的“機”
盡管媒體融合過程中危機四伏,但對國家、傳媒界、大眾來說也充滿了機遇。技術的快速發(fā)展不斷滲透到傳媒業(yè),倒逼著傳媒業(yè)進行改革,在國家一系列政策的指導、業(yè)界不斷的實踐探索以及學術界的研究分析下,找到了這一危機的內在矛盾根源,即通過頂層設計來打破體制機制的制約,為媒體深度融合奠定堅實的基礎。
決定融媒體發(fā)展最根本的動力還是來自體制機制的變革。只有真正觸動深層改革,才能從人才、資金、內容生產等多個方面實現真正的聯動和融合,進而達到平臺層面的融合發(fā)展[5]。“媒體融合的關鍵還是頂層設計”,在媒體融合向縱深發(fā)展的當下,如何把握好機遇來擺脫這種危機,需要國家、傳媒界和技術界等各方共同努力。
對國家而言,需集聚各方力量從國家層面出發(fā)做好媒體融合的頂層設計,并繼續(xù)加大對媒體融合的政策、資金、技術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的支持,使政策真正落實,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形成國家為中心的國內傳媒中樞,重拾國家的輿論引導力和公信力;同時需同世界各國一道,加快“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確保各國網絡主權和網絡安全。
對業(yè)界而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統籌處理好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主流媒體和商業(yè)平臺、大眾化媒體和專業(yè)性媒體之間的關系,形成自上而下、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fā)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6]。同時,通過優(yōu)化內容生產和傳播流程打造新型傳播平臺。各級政府和媒體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改革機制、創(chuàng)新管理,同時加大媒體融合資金投入,全面引進全媒型人才,融活內容素材釋放內容產品強大生命力,使技術為融合賦能,真正建成各級新型主流媒體。
四、結 語
當下媒體融合正處于危機的蔓延期,其“危”主要體現在國家輿論引導力充滿變數、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媒體傳播力和影響力不足;其“機”在于國家對媒體融合的頂層設計,再配以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媒體的深度融合,實現全媒體發(fā)展。
傳媒界只有及時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國家關于媒體融合的各項政策,根據自身發(fā)展實踐,勇于破除舊窠臼,打破思維局限,積極擁抱新技術,使技術賦能媒體,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才能在未來發(fā)展中贏得主動和先機。
如何將這些“危”得以化解,將“機”得以把握,就要找準先機、把脈定向、破立并存、積極應對,才能徹底化解這場媒體融合背景下的危機。
參考文獻:
[1]史安斌.危機傳播與新聞發(fā)布[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6
[2]華冰.危機狀態(tài)下政府與媒體協作化解之策略分析[J].視聽縱橫,2010(12):38-40.
[3]徐敬宏,侯彤童.從現代傳媒體系到全媒體傳播體系——“十三五”時期的媒體深度融合之[J].編輯之友,2021(1):28-34.
[4]唐艷平.傳媒融合發(fā)展的趨勢[J].新聞愛好者,2010(19):15-16.
[5]周逵.生態(tài)與心態(tài):中國廣電新媒體平臺建設與發(fā)展之困[J].新聞記者,2017(3):43-51.
[6]胡正榮,張英培.我國媒體融合發(fā)展的反思與展望[J].中國編輯,2019(6):8-14.
[責任編輯:楊楚珺]
收稿日期:2021-04-19
作者簡介:蘇禮晶,女,蘭州財經大學商務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甘肅省廣播電視總臺文化影視頻道編輯,主要從事新聞與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