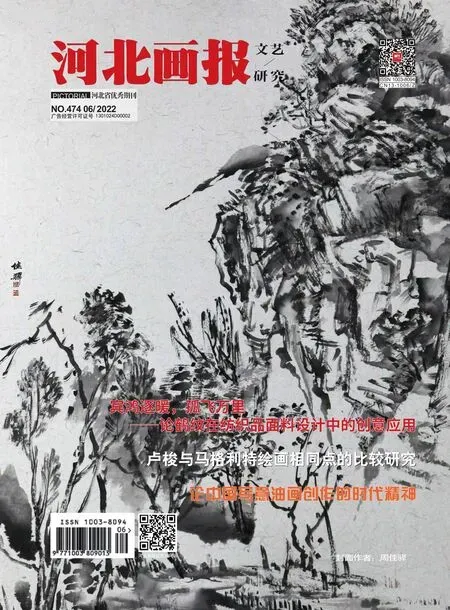美術館、博物館展示中“原境”問題研究
劉夢希 陳一凡
1.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2.廣西科技大學藝術與文化傳播學院
“原境”是巫鴻先生在《美術史十議》中提出的關于美術作品、藝術品研究的重要方法,對美術作品、藝術品研究與策展起到了重要指導意義。
巫鴻先生將“原境”一詞在《美術史十議》進行闡釋,從我們“日用而不知”的數個場合與概念入手,重新解釋和闡述美術史在現實中的位置、發展與研究對象。
巫鴻先生指出兩點:其一是“原境”的意義是廣博的,既可以是藝術品所處的時代、政治、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等整體氛圍,也可以是其曾經的陳設或使用的具體場景。其二是“原境”是無處不在的,當一件作品脫離母體來到博物館、藝術館等現代場所時它并非孤立的,而是被賦予了一個新的表現語境。首先,上文是對作品原有母體的重現,下文是參觀者的個人解讀,沒有上文的“提醒”下文也無法恰當進行。其次,也可以理解為現在美術館、博物館中館珍藏的歷史文物,它們并非在一個單調的陳列空間之中,而是與當下的建筑融為一體,藝術品是一定存在于某一個空間之中,而不是一個“孤品”。這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原境對藝術品研究、展示的重要性。
筆者對“原境”的理解有以下兩點:第一,作品不同原境不同。在“原境”的重現時要充分尊重每個藝術品的特點,對其進行客觀還原。第二,展館和藝術史的研究有著密切的相互作用關系。博物館中所收藏的藝術品都是藝術史考察的一手資料,反之,藝術史的研究正是對其形式美與人文,歷史特點的探索,能很好的還原作品在歷史或出土地的“原境”景象,會對博物館的展覽方式帶來影響。
一、為什么有“原境”的需要
隨著對美學教育的逐步重視、深入;美術作品、藝術作品數量的持續上升;展館數量、規模、作用的不斷擴大,作品、展館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如何去展示藝術品從而讓人更深入、客觀地去理解藝術品既加強對陳列作品有關美術歷史的“原境”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一)博物館性能升級
首先,我國博物館、美術館等展館性能的升級使對“原境”的研究與應用提上日程。近代中國博物館建立伊始,大多以收藏為主,博物館的展品只像是存放在其中,陳列方式、時期劃分、門類編制都散漫的像是擺件,沒有系統管理。隨著博物館的不斷發展,性質漸漸從收藏轉變為展示,其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也從“如何將博物館從‘收藏’的性質轉變為‘展示’的性質”這樣的問題上,凸顯出“藏品—觀眾—空間”這樣的一個傳播形式,而“原境”理論就剛好屬于現階段博物館、美術館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中的重要一環。
(二)作品的展示需要“原境”
現代展館的展覽方式使我們逐漸形成了一種孤立的觀看習慣,即把藝術品看作藏品收藏在博物館、美術館之中。但它們并非客體,展館也并不僅僅只有“儲存”這一種功能,展館與作品是密切相關的,這就需要“原境”的回歸,在“原境”的重構下,藝術品不再是孤立存在的“客體”,而是與建筑、陳設、燈光等共同組建的新語境。眾所周知,寺廟和石窟中的壁畫與雕塑在今天往往被分開展覽,但在母體環境中壁畫是其中一部分。例如:大同云崗石窟,窟中壁畫內容豐富,塑像像是在壁畫中放大化、立體化的某個人物形象,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由此看來可得知壁畫為前方塑像提供了故事背景和形象來源,也就是再現了前方塑像的“原境”,這樣的布局氛圍感更加濃厚,作品之間相互聯系,使參觀者更容易、更完整、更直觀的理解佛的塑像和石窟中壁畫。
(三)參觀者需要“原境”輔助理解
近現代展館所面對的是公眾群體,不是像是古代由文人雅士所組成的群體來觀賞,也不像是由那些了解美術史的學者,更多的是大眾。當大眾走進博物館、美術館這樣的藝術空間當中,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是陌生的。展館中所陳列的藝術品大多數時候只是為人們提供視覺上的欣賞,這不利于參觀者對展品的理解,對美育的作用也會大打折扣。美術館在公共教育中不應該以自身為中心,美術館是服務于群眾的。
二、美術館、博物館展示的現狀
(一)“原境”的缺失
目前許多藝術品的陳列展示中,“原境”仍然缺失。現存美術館所擁有的美術展品大多數都是脫離藝術品“原境”而存現在的,并且現存美術館的展示陳列方式作品缺少對藝術品背后的深層思考,只是一味地陳列,這導致展品的呈現缺少完整性和客觀性兩個問題。
1.完整性
由于“原境”的缺失,展品只能局部地展示自身的美感,但是其背后的人文歷史等則沒有進行展示,這些內容并不是簡短的介紹就可以呈現的。
例如,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展出的兩座交腳菩薩便是云岡石窟流失的珍寶,對于這件藏品的展覽方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仍延續了國外雕塑的展出形式,放在一個獨立的空間中,這種展示陳列方式已經脫離其原本所在的宗教環境,雖然參觀者可以看到交腳菩薩的形式美,但其背后更大的價值在于看不到的人文美。
這兩座交腳菩薩背后有著更多無法單獨陳列的意義,從云岡石窟整體來看,這兩尊菩薩像應該是屬于壁龕型,即在此壁上的某個區域所雕刻出來的特定形象,更重要的是云崗石窟的文化價值在于它是一個石窟群,53個洞窟的出現并非一蹴而就,這就意味著其形式美背后還承載著社會階層的更迭,文化習俗的演變等過程性的內涵,這是一尊佛像無法呈現的。
2.客觀性
由于博物館、美術館有著藝術傳播媒介的作用,是面向大眾的,參觀者看到脫離當時建筑空間以及傳統文化背景的藝術孤品,難免會產生主觀臆想。
除美國大都會交腳菩薩外,還有像這件大阪市立美術館佛頭,這尊佛像雕刻精美,表面處理光滑。在云岡石窟中,佛像并不只是傳遞著當時的雕塑技巧,還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服飾文化等眾多信息。從視覺方面的角度去考慮,云岡石窟的佛教造像里面的佛造像、菩薩造像的構圖很多都是三角形等幾何的樣式。修建、繪制云岡石窟的工匠們的這些三角形的構圖形式并非隨意設定,工匠們迎合當時的審美形式,將佛教中的佛陀的地位和修建的造像相結合,建構了嚴肅而且莊重的建筑體結構。從收藏意義來講,如果藏品單獨在展廳展出,那么這種藏品展覽是無法傳遞給參觀者整個收藏意義的。也就是說,大多數觀眾只能依靠銘牌上的微觀信息,不可避免會出現膚淺或錯誤的想象局面。
(二)展示方式單一
現存的博物館、美術館里面許多藝術品的陳列方式都是一樣的,大多為放在一個普通的展示柜中,或用3D模型來進行展示。這樣的展示方式很難調動起觀看者的興趣,從而對藝術品進行更深入地了解,并且無法傳達展品的真實感受。比如在云崗石窟的第20窟的大型佛造像,高就14m,其高大的形象就給人一種莊嚴的感覺,由于其體型較大,在美術館中展出時只能以3D模型的形式呈現,并沒有辦法以一種實物的方式呈現在參觀者的面前,缺少壯闊、高大的視覺沖擊,很難給觀賞者以較為確切的感受。
(三)忽略自身特點
強調藝術品的“原境”就是要還原這件藝術品的原來的空間環境,藝術品不同其原境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要關注這件藝術品的本身。提到西方繪畫,西方采用焦點透視進行繪畫,突出畫面所需的立體真實空間感,營造一種三維一體的空間,例如最典型的馬薩喬的《圣三位一體》濕壁畫,畫面上的所有點都最終集中到一個點上。對于西方的繪畫來講,一幅幅的繪畫作品放在博物館的墻壁平面上則是最佳的展出方式。然而中國的許多繪畫作品大多為寫意畫,遵循的透視原則與西方相反,用是散點透視的規則。云崗石窟壁畫就像是一幅在石壁上的佛教故事畫,可以使人多角度多視覺觀看。并且云崗石窟還使用穩固的三角形佛造像結構,佛造像只有在這種結構中才能凸顯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他們的法力無邊,其信仰佛教的信徒只有在這樣的空間結構中才能感受到其信賴感、崇拜感,這是其所有的獨特性。總而言之這表明了,不同的繪畫特點需要不同的展覽方式,不同的“原境”才能凸顯其自身的美感。
三、關于“原境”恢復的設想
“原境”的還原與重現需要我們不斷的思考和持續的嘗試,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
(一)政府扶持
博物館、藝術館利用“原境”全面、客觀的展示作品能起到很好的美育作用。但是由于像這種面向大眾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機構性質,其展館自身門票較低,所盈利的資金并不多,對于較為全面地“原境”重現來說有一定難度,這需要政府在政策、資金等方面予以支持,進一步提高博物館展品及展品環境質量,定期對各類展館運行情況進行評估,并確定級別,對于運行管理較好的予以獎勵,對于自身起點較低的展館予以補貼,促進地區展館整體水平提升。
(二)行業創新
現在藝術與科技都不斷發展,并且相伴而行,如果我們需要還原這些展品的原境,則需要更多的方式進行呈現,其中比較好并且方便現代的方式則是科技的注入,策展行業要不斷與高科技、新技術行業進行產業融合,例如AR、多媒體、數字技術等進行展覽,應用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打造數字化展廳實現對“原境”的還原,還可以增加與參與者的互動,展開這樣一種沉浸式展覽,切實達到構建“原境”對人們的感染意義。除此之外還要尋求多元化的展示“原境”3D打印技術、沙盤展覽等技術的創新都能實現文化藝術的傳播有突破時空限制的可能。
(三)策展人實地考察
如何更貼切地還原“原境”是對策展人知識與應用水平的極大考驗,這就要求策展人不僅要了解策展知識還要了解展品歷史,對于重要展品策展人可以通過參與實地的考察了解展品原有母體環境,雖然可能由于自然的(比如天然的風化、自然災害)或者人為的原因(國外的掠奪、人為的破壞)等,有許多的物品或者細節沒有辦法還原,但是仍然可以通過一些史書的記載、當地的習俗等推測,這樣也可以不斷提高策展人的策展能力,提高展館展示作品的能力與水平,進而促進“原境”的推廣。
四、結語
還原藝術品的“原境”不僅僅是對環境的再現,更是對其所承載的文化的還原,本文以云崗石窟為例,在美術館、博物館這樣的空間之中還原“原境”,更是對其所在的北魏文化、當時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重現。作為博物館、美術館這樣的傳播主體,在今后許多的展覽當中,我們需要更多的對藝術品的展覽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還原藝術品“原境”,并搭建好美術史與博物館、美術館之間的聯系,展覽時的“原境”能更客觀的、完整地再現其工藝技巧、文化的演變以及意識形態等提供借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