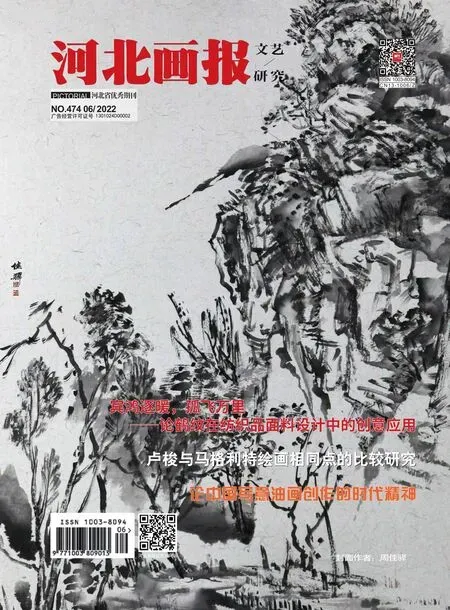卞之琳詩歌中的“距離”
曲宏一
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
在中國新詩史上,卞之琳是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其中《距離的組織》(1935)因晦澀、冷凝、注釋密集的特色,歷來為各家解讀。本來是對立的意象被聯系在一首詩中,彌合了時空上的距離。縱觀卞之琳的創作,一直存在對“距離”的書寫。鑒于1938年后卞之琳的寫作與30年代前中期有很大的風格差異,本文主要選擇卞之琳1930-1937年的作品進行研究。
一、卞之琳詩歌中普遍存在的“距離”
卞之琳詩歌中的“距離”可以劃分為具體和抽象的距離。在30年代前期,他首先書寫的是空間中的具體距離,如《航海》(1935)中,輪船一夜二百里的長途與多年前的“蝸牛銀跡”形成對照,這一長一短的空間距離暗含著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輪船行進的速度甚至讓人產生“時間落后了”的錯覺,似乎人類已經擺脫了自然規律的束縛。但是“多思者”又對距離差距感到疑惑,面對現代文明帶來的變化,他仍需要轉換思維。
此外,詩人還采用回憶追溯的方式,彌合了時間的距離。如《還鄉》(1933),在孩子興奮的講述中,成年人的感嘆反復插入,“綠帶子抽過去”暗示成年人不能重拾對未來的興奮感。詩歌雖聯系了兩段時間,卻不能使其中的距離感消失,反而凸顯了成年人對人生旅途的失望。
在進行不同時空的轉換跳躍時,卞之琳顯示出他精神上的迷茫。詩人將自己的心情概括為“小處敏感,大處茫然”[1]。自己與激昂的時代風氣格格不入,而個人命運的難題在永恒奔走的時間面前猶如滄海一粟,于是他只能像“倦行人”一樣在各個時空中徘徊。
1935年是卞之琳向“主知詩”轉變的年份。江弱水曾說:“從1月的《距離的組織》開始,就像是一道分水嶺,將卞氏的戰前詩劃為前后大異其趣的兩個部分。……是因為卞詩從情景的寫實一下子轉入觀念的象征。”[2]卞之琳對“距離”的書寫上升到了抽象的高度,分界在于“距離”傳達出的意境不同。
在書寫具體的時空距離時,詩人傳達的意境可以被讀者捕捉,而在抽象時空距離的書寫中,卞之琳以自己腳下的位置為圓點,將思維拋射到四面八方,讓思維探索夢境、深入微觀世界、延伸到歷史長河中,形成一個半徑無限的球體。他想表達的不再是某種具體的情感,而是通過距離的構建展示意識的流動與思維的美感,表現內心艱澀的探索過程。寫詩對于他是一種生命體驗,一種沉思與獨白,他并不要蘇息與逃避,而是要直面生存的痛苦,從而結晶與升華。[3]
此時卞之琳還書寫了另一種抽象的距離——人際距離。張棗在解讀卞詩時說:“這個世界上沒有陌生人,人與人之間玄妙的關系對于一些人來說就是詩意點,仿佛一條珠鏈上的珠子相互映照。”[4]如《淚》(1937):
巷中人與墻內樹
彼此豈滿不相干?
豈止沾衣肩掉一滴宿雨?
人并非無淚,
而明白露水姻緣,
你來畫一筆切線,
我為你珍惜這空虛的一點。[5]
即使人際之間存在物理上的距離,也會因“肩上的宿雨”產生聯系的機會。“淚”象征著人們心靈相通的結晶,哪怕相通的可能性如“圓上的虛線”一樣無望,詩人仍想珍惜人際聯系的一瞬。
可以看出,卞之琳從具體的時空距離轉向了抽象的象征,表現的詩境也有了極大地拓展。這既是符合他性格的自然選擇,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現代人的獨特體驗。
二、“距離”與存在:卞詩中的性格與現代體驗
在北大讀書時,卞之琳受法國象征主義詩派的影響,寫下了散文《流想》。(1930年發表于《駱駝草》,署名大雪)文章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細微感受,并進行思維的聯想與發散,與波德萊爾的《應和》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敏銳感受力的基礎上,他卻選擇了抒情的節制:“我寫詩,而且一直寫的抒情詩,也總在不能自已的時候,卻總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動物’。”[6]受這種抒情方式的影響,有人認為他的詩歌“不夠宏大”。對此,卞之琳很有“自知之明”:“如果說我還有點自知,如果說寫詩是“雕蟲小技”,那么用在我的場合,應該是更為恰當。”[7]這顯然只是詩人的謙辭。如果他的胸懷不夠寬廣,又怎么能寫出《距離的組織》這樣包含廣闊宇宙距離的詩歌呢?相反,卞之琳是一個具有“候鳥性格”的人。請看他的《候鳥問題》(1937):
你們去分吧。我要走。
讓白鴿在鈴在頭頂上繞三圈——
可是駱駝鈴遠了,你聽。
……
我的思緒像小蜘蛛騎的游絲
系我適足以飄我。我要走。
“那種生來就有候鳥習性的人,關在四壁中永遠也不會快樂。”[8]雖然身在北平,詩人的思緒早已飄到了遠方。最終他堅定了信念:“我要走。”他明白,要像候鳥一樣飛走,才能超越現實生活與個人喜怒,獲得真正開闊的精神世界。
“距離”也反映了卞之琳的現代性體驗。1932年,卞之琳翻譯了T·S·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艾略特提出“將傳統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即藝術家將眼光、審美趣味、創造的潛力局限于當下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必須要培養“歷史的意識”,理解傳統的過去性與現存性,在矛盾中認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存在方式。
卞之琳發現,“相對”的哲學觀可以將不同時空中的事物用聯想與想象聯系起來。《音塵》(1935)就是最好的體現:當我想象自己坐在泰山頂“一覽眾山小”時,朋友眼里龐大的火車站只是“金黃的一點”。在大自然中,一個人的存在就像“虛線旁那個小黑點”。人類實際上無法占有自己存在的空間,也不能永存于時間長河中,那么不如無為而治,將自己融入大環境中,達到個體與自然界的合一。這首詩的傳統題材被賦予了“歷史的意識”,將傳統與現實合二為一,“咸陽快馬的蹄聲”與“綠衣人的門鈴”將上千年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在相對性的宇宙中,幾乎所有對立的概念都互相抵消,被共同引向一片和諧的靜謐。[9]
但是卞之琳逐漸對這種去主體化的存在方式產生了疑惑。在散文《成長》中他說:“把一件東西,從這一面看看,又從那一面看看,相對相對,使得人聰明,進一步也使得人糊涂……”[10]“絕對的相對”使他能穿梭于時空中,但又找不到個體存在于世上的必要性。詩人轉向儒家哲學尋求解釋:“何妨平均一下,取一個中庸之道?何妨來一個立場,定一個標準?何妨來一個相對的絕對?……我們不妨就人立標準,我們腳踏實地,就用腳來量吧,一腳一foot,兩腳兩feet。”[11]于是他寫下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詩句——“黃色還諸小雞雛,青色還諸小碧梧,玫瑰色還諸玫瑰,可你回顧道旁,柔嫩的薔薇刺上,還掛著你的宿淚。”[12]此時卞之琳已經堅定了自己的信念:雖然“相對”能使他的思維自由地穿梭于時空之中,但他仍選擇腳踏實地,在世界上留下一點存在過的結晶。這是他1938年后詩歌創作的理論先聲。
除了對存在方式的思考,卞之琳還注意到現代社會中的人際距離。
傳統儒家思想認為“禮”是人際交往中必須遵守的準則。在一個人說話做事之前,重點是“做什么、怎樣做才符合倫理規范”,目的是將人際交往納入統治范疇,以維持封建政治的秩序。這樣的結果是只建立了個人與社會的聯系,而忽視了真正重要的“我和你”的聯系。[13]
在現代社會中,傳統的人倫關系被經濟關系接手,這種關系的問題是:人與人的聯結主要靠物質上的契約,情感聯系則越來越稀薄。人們在面對彼此時感到陌生、在相遇時有意疏遠,降低了理解與溝通的可能性。但這并不意味著現代人排斥親密的人際關系,只是現代人通常會將自我意識放在首位,害怕過近的人際距離會侵犯自己的精神獨立性,因此只能僵持在可望不可即的矛盾位置。卞之琳的《無題》五首就反映了這種復雜的現代人際關系:
在第一首中,詩人將自己喻為“一道小水”,戀人的到來使他的心猶如春潮。然而他是猶豫的,不敢貿然拉近二人的距離,又期盼她能發現自己熾熱的情感——“南村外一夜里開齊了杏花”。在第二首詩中,詩人陷入了熱戀:“門上一聲響,你來得正對!” 他將自己的癡念分擔在室內的物品上,當戀人來到這個房間,自己的心才活了過來。“點金指”、“門上一聲響”都代表的是二人精神距離消失的一瞬。但二人的精神聯系并不是緊密的,第三首詩人寫到“月臺上的綠旗”,代表二人在精神上無法消失的距離。但他心中仍不能釋懷,在第四首中表示“我想要研究交通史”——跨越遙遠的距離,將遠方的信物帶給心上人,使二人的心靈得以溝通。詩人的心情是矛盾的,如果二人更進一步,朦朧的美感就不復存在;如果拉開距離,這段聯系注定消散。詩人在其中不斷徘徊,咀嚼著人際交往帶來的矛盾感受。
本文通過分析卞詩中的“距離”,探究了卞之琳的個人氣質、現代意識與哲學觀念。限于學力不足,文中的分析仍很淺薄。筆者希望,隨著自己學識的不斷積累,在今后能繼續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