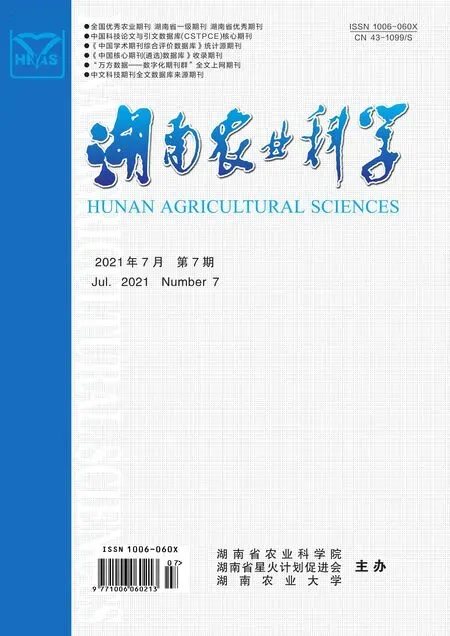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分析
王 蕾
(長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0)
隨著改革發展步伐的不斷推進,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此時,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1]。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因此,應盡快采取措施,提升西部區域經濟增速,促進東西部共同發展。資本流動能夠帶動生產要素的流動,進而影響地區經濟發展[2]。研究資本流動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現階段,眾多專家學者就資本流動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有學者通過構建貝葉斯模型就外資資本和國家中央資本2種融資途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差異進行了研究,發現外資資本會推動市場資本由東向西流動,而中央政府投資會促使資本由西部區域向中東部區域流動[3-4]。因此,筆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要素,通過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資本流動影響地區經濟發展進行實證分析,為進一步促進我國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1 指標體系與模型構建
1.1 指標體系的構建
1.1.1 被解釋變量的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能夠反映出特定時間段內國家或地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的總和[5-6]。因此,選取GDP作為被解釋變量(表1)。
1.1.2 解釋變量的選取解釋變量主要包括金融、財政和外資。(1)金融層面的解釋變量包括銀行資本與證券資本。銀行資本是指本幣、外幣存款余額-本幣、外幣貸款余額+資金凈流入,記為COB;證券資本是指國內股票年籌集資本額+國內債券年籌集資本額,記為CAP(表1)。(2)財政層面的解釋變量包括中央投資、中央轉移支付以及地方財政收入。中央投資是指中央財政基礎設施年投資,記為FAS;中央轉移支付是指中央向地方撥付的資金,記為TFT;地方財政收入是指地方財政年收入,記為LFR(表1)。(3)外資的解釋變量主要包括外資資本。外資資本是指能夠直接產生作用的外資投資額,記為FDI(表1)。
1.1.3 控制變量的選取(1)產業結構情況。產業結構是指區域內三產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產業結構高度化是指區域內經濟發展重心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過渡的過程,產業結構高度化指數越高,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7]。將二產、三產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作為衡量地區產業結構情況的控制變量,記為ISR(表1)。(2)城鎮化水平。區域經濟發展的另一項指標是區域的城鎮化水平。區域中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和聚集程度。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作為城鎮化水平的控制變量,將其定義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記為URB(表1)。

表1 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作用指標體系
1.2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部分省份數據缺失,將選擇29個省份2009—2018年數據作為數據樣本,按照地域將29組數據分為3部分,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為東部;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為中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內蒙古、廣西、寧夏、新疆為西部。為方便研究,先假設資本沒有滯后情況,所有資本當年全部進行投資。所用數據均來自《中國金融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權威調查報告。
1.3 構建模型
該文主要研究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哪些影響。由于各指標數據在量上存在較大的差異,為了使數據變化更加平穩,首先對各指標進行取對數處理,建立多元回歸模型,見公式(1),式中 表示誤差項。

1.4 描述性統計分析
借助STATA15軟件,各指標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29個省份整體GDP是4.215萬億元。從區域劃分看,東部區域的GDP較高,是4.393萬億元;中部區域第二,是4.163萬億元;西部區域最低,是3.967萬億元。解釋變量中,銀行資本(COB)、證券資本(CAP)、地方財政收入(LFR)、外資資本(FDI)4項指標東部區域最高,西部區域最低;中央財政基礎設施年投資(FAS)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TFT)中部區域最高,西部區域第二,東部區域最低。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情況(ISR)中部區域最高,東部區域第二,西部區域最低;城鎮化進程(URB)東部區域最高,中部區域次之,西部區域最低。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2 實證分析
2.1 Hausman檢驗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必須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回歸模型,如表3所示,全國及東中西部各區域在1%水平顯著,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表3 Hausman檢驗結果
2.2 回歸分析
討論資本流動對地域經濟發展產生的作用時,將區域GDP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資本流動要素作為解釋變量,為了使研究過程更加直觀,采用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城鎮化水平作為控制變量[8]。同時,為了解決因變量波動巨大影響運算結果的問題,首先將樣本變量取對數,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樣本變量對數回歸結果
2.3 實證結果
2.3.1 資本流動對東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東部區域固定效應模型R2=0.976 3,說明預測結果與實際發生情況的吻合程度較高。(1)政府轉移支付的財政資金和地方財政收入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2種資本在東部區域產生的作用與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的作用相當。東部區域與海洋接壤,地理位置與內陸相比更為優越[9]。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大力扶持東部沿海地區,向東部區域輸送大量的資金,打造沿海經濟帶,吸引了大量的高新產業落地生根。這使得東部區域能夠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2)外資資本中能夠直接產生作用的投資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且在東部區域產生的作用與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的作用相當。東部區域具有基礎設施良好,政策寬松,臨近海岸線方便往來貿易等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企業[10]。外資企業的入駐為東部區域帶來就業崗位和稅收的同時,也激活了東部區域各行各業良性發展的市場經濟體系,也促使東部區域國內企業學習外資企業的經營模式,形成鯰魚效應。這對東部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3)人力資源存量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由于東部區域發展較早,其就業機會、薪資待遇、社會資源等方面較中部區域、西部區域具有一定優勢,每年吸納大量高學歷人才,這些人才在地區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生產力提高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促進了東部區域的經濟發展。
2.3.2 資本流動對中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中部區域固定效應模型R2=0.981 5,說明預測結果與實際發生情況的吻合程度較高。(1)財政資本在中部區域對經濟的正向拉動作用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財政轉移支付和地方財政收入作用更加明顯,說明中部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這2項指標。近年來國家調整經濟布局,政策向中部傾斜,促進了中部區域的經濟發展[11]。(2)金融資本在中部區域對經濟的正向拉動作用較全國平均水平較弱。隨著國家調整地區經濟的戰略部署,國有銀行在信貸工作中向中部傾斜,東部區域多余的金融資本也涌入中部區域,促進了地區的經濟發展。
2.3.3 資本流動對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西部區域固定效應模型R2=0.980 7,說明預測結果與實際發生情況的吻合程度較高。(1)金融資本中證券資本在西部區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弱于全國平均水平。證券資本的投入向西部區域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但東部區域證券資本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高于中部、西部區域,導致了金融資本在西部區域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弱于全國平均水平。(2)產業結構情況在西部區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2]。這表明西部區域二產、三產所占比重大于全國平均水平,受自身環境影響和國家政策扶持,近年來西部區域大力發展制造業和旅游業,成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2大助力[13]。
3 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政府轉移支付的財政資金和地方財政收入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2種資本在東部區域產生的作用與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的作用相當;外資資本中能夠直接產生作用的投資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且在東部區域產生的作用與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的作用相當;人力資源存量有效拉動了東部區域經濟增長;(2)財政資本在中部區域對經濟的正向拉動作用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金融資本在中部區域對經濟的正向拉動作用較全國平均水平較弱;(3)金融資本中證券資本在西部區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弱于全國平均水平;產業結構情況在西部區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因此,我國政府還需著力引導資本向中西部區域流動,多層級、多類別地撥付中央轉移支付資金。注重扶持中西部區域市場主體。一是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管理,控制市場風險,確保市場順利運行。二是提高資本使用率,降低信貸門檻。三是建立中西部經濟特區,通過經濟特區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同時,我國政府應當加大對中西部區域的政策傾斜,通過寬松的營商環境吸引民間資本和外資進駐[14],并鼓勵國有企業創新管理模式。因中西部區域在地理位置上較東部區域處于弱勢,要克服這一問題,一是要制定優于東部區域的優惠政策,降低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門檻;二是要健全法律體系,為外資和民間資本提供公平、安全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