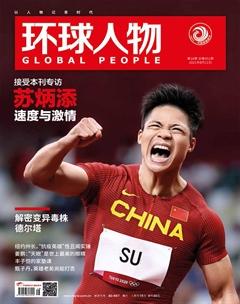衛,東晉士人的鄉愁
劉勃
永嘉六年(312年),洛陽陷落。在晉懷帝成為匈奴人俘虜之后的一年,江夏郡某處長江渡口,一個無比俊美的青年,看著眼前的滔滔江水出神。
這個青年的名字,叫衛玠。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言語》)
當時衛玠的職務是太子洗馬,所以稱他為“衛洗馬”——“洗”就是“先”,太子洗馬就是太子出行時,在馬前引路的人。
這一年衛玠27歲,面容憔悴,神情凄慘。他對身邊人說:“看見這茫茫大江,不禁百感交集。只要還不能擺脫感情,誰又能排遣得了種種憂傷!”
衛氏是河東高門,衛玠是曹魏尚書衛覬的曾孫、西晉太保衛瓘的孫子。衛瓘非常喜歡這個孫子,曾說:“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世說新語》把這條語錄收入“識鑒”一門,它既準確預言了未來衛玠的成就,也成為衛瓘自己致命的讖語。
公元291年,衛玠5歲,八王之亂最初的幾場屠殺就發生在這一年。衛瓘當初主張廢太子,但太子司馬衷終究還是成了晉惠帝,皇后賈南風自然會視衛瓘為眼中釘。
賈南風設局,借刀殺了衛瓘滿門。那個恐怖的夜晚,衛玠和哥哥衛璪剛巧都因病住在醫生家里,因而逃過一劫。
說到衛瓘的死,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衛瓘是遭了報應,因為當年滅蜀戰爭的時候,他陷害、殺死了功勛卓著、忠心耿耿的鄧艾。但更多名士和高官站在另一派,他們認為衛瓘是一個優秀的士族子弟,而鄧艾出身寒微,士族弄死寒人,能算什么劣跡呢?況且這一次,衛瓘確實是無辜遇難,他們的同情心自然在衛瓘一邊。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朝廷很快為衛瓘平反,殺害衛瓘的兇手也被處死。至于賈皇后,她一直隱藏在幕后,并不會為這次事件負責。
衛玠于是成了一個沒有家族負擔的孩子——昔日的罪孽在那個滅門之夜都已了結,滅門的兇手又已經伏誅,賈皇后之后也不可避免地死在了某次政變中,他不必再背負過去的血海深仇。
衛玠慢慢長大,越長越好看。10歲左右的時候,他坐著羊車路過市場,看見他的人都以為這是個美玉雕琢成的人,整個洛陽城為之傾倒。
這個轟動效應看起來和潘岳很像,但其實本質不同。潘岳“好神情”,“挾彈出洛陽道”,他知道自己的形象有多迷人,是以一種T臺走秀的狀態出現在大眾面前。但“觀之者傾都”對衛玠來說卻是意外,在發現自己的魅力之后,衛玠就不再這樣做了。
衛玠在意的不是這些。他總是沉浸在一些玄妙的問題里,比如說人為什么會做夢呢?他成天思索也得不出答案,終于想得生了病。
他的體質一直不好,后來成為中興名臣的王導,年輕時見過衛玠,評價道:“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容止》)雖然整天調理疏導,但最輕便的絲綢衣服穿在他身上,還是像不堪重負。
但就像西子捧心,病懨懨的衛玠顯得更好看了。
衛玠的母親不許衛玠再清談了,因為清談是最勞心傷神的事。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親友們才會請衛玠說兩句。衛玠一開口,聽眾無不以為達到精微的境界,歡喜贊嘆。

衛玠對身邊人說:“ 看見這茫茫大江,不禁百感交集。只要還不能擺脫感情,誰又能排遣得了種種憂傷!”(李云中 / 繪)
衛玠給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和人相處時的淡然。他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是人就有缺陷,因此體諒別人的過失是最根本的人情;別人冒犯了你,但這冒犯和你追求的東西無關,想通了這個道理,各種流言蜚語也就統統可以丟開了。
衛玠秀美的臉上從來看不見“喜慍之容”,正因如此,特別能讓那些飛揚跋扈的名士們感覺自己活得太刻意、太低俗。
衛玠的舅舅是驃騎將軍王濟。他是一個驕傲、自戀,但確實“俊爽有風姿”的美男子,可一看見衛玠就嘆息:“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澄王平子,名士領袖王衍的弟弟,也是一個自視極高的人,聽到衛玠的清談,卻佩服得五體投地。
永嘉四年(312年),衛玠突然對母親說,我們應該搬到南方去。母親并不想走,她舍不得在皇帝身邊做散騎侍郎的二兒子衛璪。可是衛玠說,為了保全衛家的門戶,必須要走。他對哥哥衛璪說:“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
所謂“在三之義”,指的是人生在世,要盡三種責任:對父母的孝,對師長的敬,對君主的忠。衛玠的意思,自己帶著母親南下盡孝,哥哥留在皇帝身邊盡忠。衛玠知道,在眼下危難的時局中,哥哥一定會死。他平平淡淡地說“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就是表示兄弟要從此訣別。
衛玠選擇自己活下來,當時的人并不會認為這是貪生怕死。在那個時代,江南卑濕的土地被認為是對男人壽命的致命打擊。中原流傳著各種傳說,南方遍布蠱毒、瘴氣和各種奇怪生物,比起引刀成一快的盡忠,南下冒險的使命更艱巨。只不過兄弟倆莫逆于心,“兄任其輕,玠任其重”之類的話,就不必說了。
衛玠之外,西晉任何一個聲譽卓著的名士,身上都難免纏繞著復雜的權力斗爭,也都有洗不干凈的人生污點。他是名士們關于“中朝”那段永遠也回不去的好時光的一個夢。
就這樣,衛玠帶著母親來到江夏郡。兩年后,北方局勢徹底不可收拾的消息傳來,衛玠繼續南下,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此刻,皇帝蒙塵,兄長遇難,自己不得不繼續南下,而過江之后,就真的要與北方的一切訣別了。所以一直無“喜慍之容”的衛玠,情緒一瞬間爆發出來。然而,他終究也只說了這樣一句話。
衛玠來到了豫章郡。在這里,他本該遇見當年為他絕倒的王澄,但王澄已被自己的同族兄弟王敦殺掉。所以他見到的是王敦,還有王敦的長史謝鯤。對衛玠來說,這也許沒什么不同。畢竟,見到身上散發著玉璧般溫潤光澤的衛玠,誰不會為之絕倒呢?
關于這次見面,《世說新語》留下了兩則記錄。謝鯤也很善于清談,他和衛玠聊得投機,不知不覺就從白天談到天黑,天黑又談到天亮。王敦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話,但聽得很入迷。
王敦說,想不到我們生在永嘉亂世,卻聽到正始年間那種最高水平的清談。他還有點惡作劇似的想起了被自己殺掉的族兄王澄,于是說了一句:阿平要是還在的話,應該再絕倒一回吧。
但這次清談對衛玠來說是致命的。他身體羸弱,又不適應江南的環境,本來胸中積郁難抒,現在突然興奮,于是得病去世了。
十多年后,晉成帝咸和年間(326年—334年),丞相王導想起了這個病弱的少年,下令說,把衛玠遷葬到都城建康來吧,他這樣的風流名士,受天下人仰慕,大家應該整治薄祭,以示我們對舊友的懷念。
于是衛玠改葬江寧新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菊花臺一帶。直到現在,這里仍是南京殯儀館所在。
顯然,建康城里的人們都希望衛玠這樣可愛的人物,離王敦那個亂臣賊子遠一點,希望他死于南京。所以另一個說法很快被發明并流行開來: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容止》)
劉孝標注釋《世說新語》的時候,引用了一條早期記載說,衛玠到豫章郡是永嘉六年五月六日,到六月二十日就去世了。這么短的時間,他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建康來。當時劉孝標還能看到許多其他記載,都說衛玠是死在豫章的。更何況,如果衛玠就死在建康,何必再有后來王導遷葬的事呢?
所以,這個“看殺衛玠”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實在太迷人,所以《晉書》的作者明明讀過劉孝標這段無可反駁的論證,卻還是選擇把這個故事寫進正史,直到今天,這個故事也仍然眾口傳播。
衛玠短暫的一生,被人們銘記的,就是無與倫比的美貌與超凡絕塵的清言。他沒有什么事跡可以稱述,但也許正因如此,他的人生顯得格外純潔無瑕。衛玠之外,西晉任何一個聲譽卓著的名士,身上都難免纏繞著各個政治派系復雜的權力斗爭,也都有怎么洗都洗不干凈的人生污點。
逃亡到江南的名士們,也就是所謂“衣冠南渡”者,心中往往都充溢著鄉愁。可是當名士聚會,思念一位故人的時候,你的摯友可能剛巧是我的仇人,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牽扯出無窮的昔日恩怨。一起重溫舊時光的甜蜜而憂傷的氛圍,就會被破壞得蕩然無存。
要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美麗而哀愁的象征,有誰比衛玠更適合呢?
衛玠被東晉士人譽為渡江名士第一人,實在是理所當然的吧。他是名士們關于“中朝”那段永遠也回不去的好時光的一個夢。